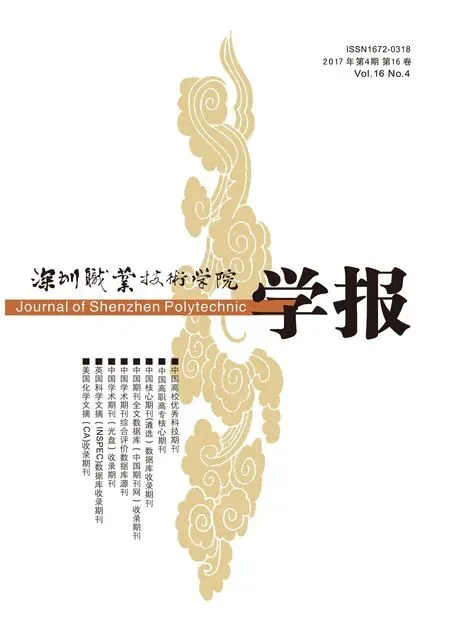底层的珍珠*
——“新工人诗歌”现象探析
陈新瑶,杨 兰
(1. 湖北理工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底层的珍珠*
——“新工人诗歌”现象探析
陈新瑶1,杨 兰2
(1. 湖北理工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新工人诗歌”的出现为广大读者带来了新的艺术体验。无论是诗歌创作者,还是诗歌传播者,他们用真挚、美好而博大的情怀传递着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对苦难的担当。在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显现了中国广大民众对自由、独立生命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社会意义深远。
新工人诗歌;情感诉求;现象探析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步伐的不断加速,中国新兴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特别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批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制造业发达的城市,成为新的产业工人。在他们当中,极大多数人是来自乡村的农民,少数人是来自城镇的下岗工人或无业人员。评论界将这些新产业工人写作的诗歌称为“新工人诗歌”,也有人将之称为“打工诗歌。”[1]23据不完全统计,在今天的中国,有近万名工人朋友在业余时间从事着诗歌写作。虽说,“新工人诗歌”在中国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一直以来,它并未获得中国文艺界的重视。近两三年来,“新工人诗歌”逐步进入大众的关注视野。来自文艺界的评论之声逐步多了起来。李云雷先生说:“新工人诗歌的‘崛起’,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经验、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元素”,“其意义不仅仅是将底层经验带入到当代诗歌,而且也在创造着一种新的中国诗歌。”[2]
仔细考察近些年来“新工人诗歌”的发展状况,读者不难发现,无论是“新工人诗歌”的写作者还是传播者,他们身上都有着真挚、美好而博大的情怀,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歌唱劳动,歌唱生活,歌唱美好的人生梦想。在他们身上,一种新的美学元素、一种新的文学力量正在形成与发展。尽管这些诗歌的创作者身份低微,诗歌的阅读者与传播者也多为同道中人,但他们犹如一颗颗宝贵的珍珠,映照着中国广大劳动者的生活与梦想,其价值不容忽视。
1 诗作者卑微而美好的情感诉求
那些被时代带入到现代工业生产活动的新产业工人,他们的命运与中国几亿农民工、无数城镇下岗工人的命运、与中国当代历史变革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他们写作的诗句中,读者不仅仅目睹了无数背负着苦难而真挚无畏的灵魂,更是看到了一个个卑微却又美好的心灵空间。
在工厂内外,这些工人们的身份低微,生存环境较为恶劣,很多时候,他们得依靠透支体力的方式来获取足够的工资,以此来养家糊口、来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在生产流水线旁,他们是“兵马俑”,每天需站着工作8到12个小时,甚至更多;没有人会去关注他们的劳作感受与所遭遇到的身体疼痛,更没有人会去关心他们的籍贯、家庭背景、兴趣与梦想,甚至绝大多数时候工友们只知道他的工号,而不知他的名字。在一个被异化的空间,一些工人学会用诗句来记录心灵的律动。在生活的困境中,诗歌成为他们表达生命情感、释放生存压力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在现代工业生产流水线旁如“铁”、如“兵马俑”般劳作的郑小琼、唐以洪、许立志、乌鸟鸟,还是在深深的地底下劳作的工人老井、陈年喜,他们自觉、勇敢而又略带着无奈、哀伤将一个个真实的劳作场景与令人震撼的生命感受带入了诗歌,这份文学创作上的自觉与对生命的珍视,足以让读者瞩目与敬佩。
虽说在艺术水平上,大多数工人写作的诗歌有待提升,但那些真实的情感、生动的细节、简单的句法以及纯净而大众化的语言却成就了他们诗歌的“俗格之美”[3]25。“我在一家钟表厂打工/钟表厂没有休息日/因为时间在走,生活没有停止/工作就没有停止/我有一颗纯净而充满梦想的心,像产品一样五彩纷呈……”[4]308在这首题为《钟表厂》的诗歌中,诗人池沫树用简洁、质朴而又具有韵味的文字展现了打工者复杂的生活情感。走动的钟表、流动的时间,无休止的工作,对未来生活的殷殷期盼,这些都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它使这首诗歌具有了较强的艺术性与典型性。钟表厂的打工者的生活是这样,其他厂打工者的生活也是如此。可以说,与所有的平民写作一样,广大工人朋友的诗歌创作拉近了文学与现实生活、与大众的联系,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生长形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进步。
秦晓宇说:“工人诗歌就是没有灰色收入的一群人纯然的精神需要,一种不受制于权力与利益的表达。它遥遥呼应着文学的起源——用文艺的方式象征性地‘应对’艰难苦痛的生存,同时又切入当代现实,为广大的命运同路人立言。”[3]21“新工人诗歌”不仅是工人诗人们写给生活、写给自己、写给命运同路人的诗篇,同时,它也是献给这个时代广大劳动者的诗篇。在这些诗歌中,读者不仅读到了写作者在艰难生活、人生苦痛面前的挣扎与哀伤,也读到他们在苦难生活前的那份执着、那份担当和充满希望的坚守。
在老井的诗歌《地心的蛙鸣》,在陈年喜的诗歌《儿子》,在郑小琼的《他们》、邬霞的《吊带裙》《谁能阻止我爱》、白庆国的《锅炉工》等诗歌中,读者能强烈地感受到几位诗人对生活苦难的担当、对生命尊严的坚守、对未来生活的希望。生活再艰难,但还是要继续走下去。在苦难的日子里,寻找到生的希望与快乐,这何尝不是一种让人称道的生活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人、灵魂与肉体、名利与尊严等冲突不断升级,身处其中的我们均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自己。在这个阶级分化极速加剧的年代,新产业工人群体虽只是一个小众群体,但它却真实地代表着所有的劳动者。他们与我们,其实本为一体。当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之中周旋之时,我们是该放弃,还是该为自己、为家人或是为所爱的人、为理想而坚守?“我说着,在广阔的人群中,我们都是一致的/ 有着爱,恨,有着呼吸,有着高贵的心灵/ 有着坚硬的孤独与怜悯!”[4]270在郑小琼的这首题为《他们》的诗中,“我们”与“他们”成为了命运的共同体。无论是会写诗歌的郑小琼,还是那些不会写诗歌的打工者,亦或是被大多数工人所羡慕的公务员、银行职员、教师、自由职业者等,大家都是一致的,“我们”都应都有着高贵的心灵、有着面对苦难和孤独时的坚韧,有着对生活的悲悯。无论生活境况如何,“我们”都应该振作精神,勇敢面对,就像美丽、善良、充满朝气的邬霞,“即使这座城市的户口簿上没有我的名字”,“我”也要去爱她,要去爱生活,甚至要让这种爱渗入到 “毛孔里、皮肤里、细胞里、血液里、骨头里 ”[4]329。
在众位新产业工人的诗句中,读者不仅仅目睹了一个个令人心悸的工业生产现场,更是触摸到了一个个在生活的重负下执着于向上生长的灵魂。诗作者在生活面前的那份真诚、那份执着以及敢于担当、乐观向上的情怀,在无形之中激发了阅读者面对生活的勇气,其人文价值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2 诗歌传播者真挚与博大的情怀
老实说,当今社会关于“新工人诗歌”的关注力度还不够,这些诗歌绝大部分在社会上的传播力度不足,这当然与部分诗歌创作者的投稿方式过于局限、与大多数诗歌艺术创新性不够等因素有关;但多年来,来自广大读者、文学评论界以及官方媒体对于平民写作的忽视,这也是“新工人诗歌”传播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好在还有一些人,他们在用自己的努力为这些可爱的劳动者、为那些感人的诗句努力做着宣传与推广。如柳冬妩、马忠、谢有顺、江冰、秦晓宇、叶光荣,这些人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
“新工人诗歌”在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在广东先后涌现出了多位优秀的打工诗人,如郑小琼、罗德远、谢湘南等。在广东地区,登载“打工诗歌”的刊物有很多,如《佛山文艺》、《特区文学》、《打工诗歌》、《打工诗人》等。虽说,早在21世纪初,郑小琼的成名让评论界对新产业工人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有了惊喜的发现,但一直以来,外界关于“打工诗歌”或“新工人诗歌”的传播与推广并不多。打开中国知网以及万方资源数据库,我们能查到的关于“工人诗歌”或者“打工诗歌”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对“新工人诗歌”进行持续关注的研究人员,大多数是一些曾有过打工经历、有过相关创作经历的人员,如广东东莞的柳冬妩、广东清远的马忠;除此之外,只有极少数研究“打工文学”的学院派研究者参与其中,如中山大学的谢有顺教授、广东财经大学与传播学院的江冰教授,这二位学者在关注、传播、声援、引导新产业工人的文学创作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从打工者群体中脱颖而出的柳冬妩和马忠,这两位在这方面做出的持续努力更是值得赞扬。柳冬妩在其著作《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一书中,他对中国新产业工人的诗歌创作进行了集中的研究与评论,该书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另外,柳冬妩的著作《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与马忠的评论作品集《站在低处说话》对包括“打工诗歌”在内的“打工文学”分别进行了正面与积极的评价,为“打工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努力。
2015年,是中国“新工人诗歌”广为传播的一年,也是中国“新工人诗歌”走近广大民众的重要一年。2015年6月,由吴晓波策划、吴飞跃与秦晓宇导演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荣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年度最佳纪录片奖。该影片记录了老井、陈年喜、乌鸟鸟、邬霞、许立志、吉克阿优这六位普通工人诗人的人生故事,向观众展示了六位诗人的优秀诗作。2015年8月,秦晓宇主编的诗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正式出版发行。该诗集收录了建国以来50多位诗人写作的工业题材诗歌作品。在这些诗人中,有因诗歌成名而走上其他工作岗位的诗人如梁小斌、舒婷、于坚、郑小琼、谢湘南等,也有至今仍在工业生产空间一边劳作,一边执着于诗歌创作的诗人,如陈年喜、邬霞、吉克阿优等。郭金牛、老井、绳子、陈年喜、阿鲁、唐以洪、乌鸟鸟、池沫树、邬霞、吉克阿优、许立志等这些“无名”的工人诗人。因为这部诗典,他们的名字被人们所知晓,他们的诗歌被记入中国当代诗歌史册。2015年9月,影片《我的诗篇》在上海首次以众筹的形式与广大观众见面。其独特的选材、真实而生动的影片语言、令人动容的情感力量,深深打动每一位观众的心。据报道,截止到2016年8月初,这部电影在全国以众筹的方式播放了500场次,观众超过5万人,观众的收看效果非常好。除了纪录片《我的诗篇》、出版诗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之外,秦晓宇等人还在“爱奇艺”等大众媒体推出不同工人诗人的微电影,还采用举办“工人诗歌朗诵会”的形式来推广“新工人诗歌”。这些直面而独特的推广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接触与认识到“新工人诗歌”的艺术力量,进而对其存在的文学价值、社会价值进行确认。
“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底层的发声,首先是因为这些声音真的是事关社会正义与历史真相,能够真正评价现实的兴衰得失的,恰恰是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基于真实的所思所感,说出来一些老实话、大白话,这个在社会学意义上有绝大的价值。”①正如秦晓宇所言,关注“新工人诗歌”,不仅仅是在关注一种新生的文学形式,而是在关注着一群独特的社会群体。为了编撰这本《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秦晓宇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浏览了众多打工诗人发表在各种网络媒体上的诗歌,然后再一个个将一些好的诗歌收入那本诗集。这样的一个资料收集过程耗费了他个人的大量心血。如果没有那份博大的胸怀,秦晓宇将无法完成这种伟大的事业。
同样,执着于诗歌创作,并且执着于传播工人诗歌的英雄还有广东的叶光荣。2016年4月,全国首个由新产业工人个人设立的诗歌奖“叶光荣诗歌奖”在广东佛山启动,该奖项的设立者叶光荣只是一位普通的打工者,尽管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500多元,但他愿意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每年拿出5000元用作该奖项的奖金,用以表达他对诗歌、对工人诗人的敬意,其行动确实是让人肃然起敬。该奖每年开奖一次,直接面向中国3亿多的打工群体,奖励优秀的工人诗人或诗歌。2016年5月第一届“叶光荣诗歌奖”开奖,已经离世的青年打工诗人许立志获得该奖,来自广东南海的女孩潘妍宇获得提名奖。“叶光荣诗歌奖”的出现,弥补了国内在奖励新产业工人诗歌创作方面的不足。
同样值得庆幸的是,在广东这个拥有一亿多新产业工人的省份,广东省各级政府与单位对打工者的文学创作活动极为关注。由广东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赛”,自2012年开赛以来,共有10多名产业工人的诗歌作品获得该赛事的诗歌奖。该协会在推动产业工人的文学创作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3 结 语
在今天的中国,在无数个分散的地点,还有无数的工人朋友在继续着诗歌写作,在那些或长或短的句子间抒发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抒发着他们的人生梦想。他们的诗歌虽然不甚完美,但不容忽视;他们的声音虽然低微,但需要被大家听到。面对众多渴求诗意栖居的生命,几个相关的诗歌奖项、几部电影或是几本诗集以及由之而衍生出的“工人诗歌朗诵会”,这些远远不够。也因为如此,我们的媒体、文学评论家、广大民众以及相关的各级领导,需要多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正在劳作间隙写作的工人诗人,投向那些身处困境却依然坚守美好人生梦想的人们。今天的陈年喜,依然是一个背负着沉重家庭负担的爆破工,邬霞还在工厂里缝制、熨烫手中的吊带裙……同“农民诗人”余秀华一样,这些诗人也需要得到众人的关心和鼓励,他们坚强、勇敢地对待生活的态度也需要得到大家的正视、赞赏和学习。当然,他们诗歌的艺术精华也需要得到公正的评价。
从郑小琼到许立志,从《我的诗篇》到“叶光荣诗歌奖”,那些热爱诗歌、热爱生活的人们用他们的诗句与勇气,向这个时代展示了他们存在的价值。可以说,“新工人诗歌”的出现,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同样,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中国当代产业工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自我提升,显现出了中国广大民众对自由、美好、独立的生命追求。
注释:
① 见新京报记者李昶伟与秦晓宇的对话,《我的诗篇》的编者秦晓宇:他们在中国深处采撷诗歌,“我的诗篇”官方微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6d06dd60102 vzfc.html。
[1] 侯灵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痛苦见证[J].飞天,2009(6).
[2] 李云雷.新工人诗歌的‘崛起’[N].文学报,2015-3-26(21).
[3] 韩少功,蒋子丹,秦晓宇.献给无名者的记忆[J].天涯,2016(2).
[4] 秦晓宇.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M].作家出版社,2015.
Pearls Emerging from the Grassroots—An Analysis on the “New Workers’ Poetry”
CHEN Xinyao1, YANG Lan2
(1.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3; 2.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The emergence of “New Workers’ Poetry” brings readers a new artistic experience. The poets and the poem lovers sincerely express their love and passion for life and their courage to endure hardship. This literature phenomenon shows the Chinese people’s pursuit for freedom, independence and their longing for a better life. It has a deep and far-reaching social influence.
“New Workers’ Poetry”; emotional appeal; analysis
I207.22
A
1672-0318(2017)04-0024-04
10.13899/j.cnki.szptxb.2017.04.005
2016-12-15
*项目来源: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梦’视域下的产业工人文学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5D131)
陈新瑶(1971-),女,湖北大冶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矿冶文学、工人文学。
杨 兰(1964-),女,江西樟树人,副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文化、校园文化。
——湖北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五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