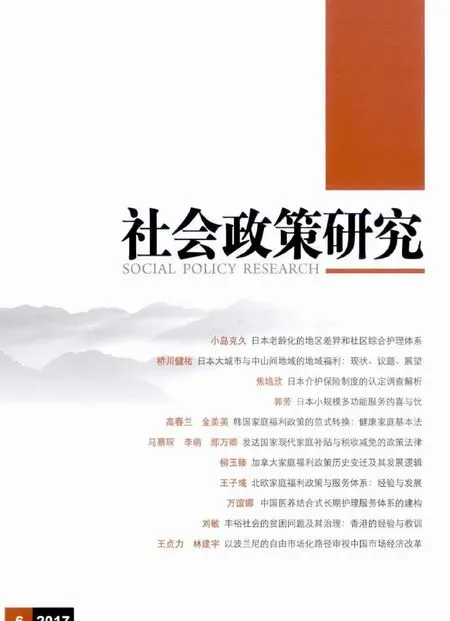北欧家庭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经验与发展
王子彧
北欧地区的合作可追溯至瑞典、挪威和丹麦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甚至语言的相近性。特别是路德教中关于工作价值观以及平等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后期北欧各国的福利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欧地区形成了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五个独立国家的新局面。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北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观:基于公民的普遍社会权利以及薪资–工作的制度化(Kettunen, 2006∶ 60)。在此价值观的影响之下,战后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北欧各国开启了多形式合作与福利扩张的“黄金”阶段。这一社会福利的变化也被学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自20世纪90年起形成了福利领域关于北欧社会福利的热门研究,而其中的最大理论建树莫过于各类福利模式的提出。
一、北欧家庭福利模式
“北欧模式”价值发掘的最大贡献者当属丹麦学者Gosta Esping–Andersen,特别是其《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一书中关于世界福利体制的“三分法”。Esping–Andersen的学术关注点在整个福利体制,其分类维度主要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针对其分类维度上家庭因素的欠缺,家庭福利和女性研究学者相继提出了多种家庭福利模式分类方法。
早 在 Esping–Andersen之 前, Kamerman和Kahn (1978)就已针对各国家庭福利政策作了类型划分。鉴于当时家庭政策并未在全球范围推行,Kamerman 和Kahn采用了家庭政策的清晰程度、覆盖范围以及各家庭政策间的合作程度来划分家庭政策的形态。当时瑞典和挪威已被划归为实行明晰且全面的家庭政策。20世纪末期,受Esping–Andersen著作的影响,大批针对家庭福利的研究涌现。首先对Esping–Andersen福利理论批判缺少性别研究因素的是Lewis (1992),其详细阐述了根据劳动力市场形态、社会保险、税收以及儿童照料的提供四种主要变量划分的福利模式。瑞典和丹麦凭借其税收、假期以及儿童照料等支持女性就业的措施远离传统的“男性养家福利模式”(Male Breadwinner Model),而呈现出双职工养家的家庭形态 (Lewis, 1997)。同时,在Gauthier(1998)划分的四种家庭福利模式中,北欧也凭借其男女平等的显著特征被归纳为平等主义倾向模式(Pro–egalitarian Model)。家庭政策历史证实,瑞典和丹麦政府为平衡女性就业与家庭责任全力创造条件和机会,同时敦促父亲在儿童照料上发挥更大的作用(Gauthier, 1998∶204)。 在此基础之上,瑞典学者Korpi (2000)从现金转移、收入税收结构以及公共服务三个角度,构建了三种双职工照料支持和传统家庭支持不同倾向的家庭政策模式:传统家庭模式(General Family Support)、市场倾向的家庭模式(Market–oriented Policies)以及双职工家庭支持模式(Dual Earner Support)。在对18个OECD国家1985–1990年情况的具体比较之中,北欧四国(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位居双职工照料家庭模式的榜首。其中,Kropi将双职家庭支持模式的评估操作化为四个指标:为幼儿提供的公立日间照料服务、有偿母亲假期、有偿父亲假期以及为老人发放的养老金和支持居家养老的服务。
由上可见,北欧家庭模式经历了从清晰地区别于传统照料模式,到注重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再到将国家、家庭和市场三者结合考虑而形成的双职家庭支持模式的理论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北欧家庭政策的特征为性别平等以及平衡家庭和工作:政府通过公立儿童日间照料服务促进女性尽早回归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通过有偿假期、幼儿生活费用的补贴以及强调父亲照料幼儿的责任为减轻女性生育及抚养幼儿负担提供全面支持。
二、北欧家庭福利政策及家庭问题的历史变迁
家庭政策变迁是随着社会整体发展及不同群体不断博弈的结果。在北欧的家庭福利政策变迁中,一方面可以看到经济状况以及家庭形态、问题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不同政党、不同阶层以及女性组织在争取权力过程中对家庭政策的塑造。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了家庭政策的发展阶段,下文将详细论述人口与家庭变迁研究的佼佼者Gauthier (1998)和 Hiilamo (2002)的观点,从四个阶段简述北欧家庭政策如何随社会变迁演变。因为社会政策主要发展于工业化之后,不同于Gauthier与Hiilamo, 本文将20世纪初开始的工业化作为分析的起始点。此外,第三阶段并未接续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主要是强调20世纪70年代是北欧乃至整个工业化国家家庭政策发展的重要转折 (Gauthier,2002),并不表示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间的家庭福利是断裂的。
自工业化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批家庭完成了由农业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过渡。同时,北欧各国政府也开始救助孤儿和贫困儿童,并关注生育率以及儿童的生活质量 (Gauthier,1998∶ 36)。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北欧国家主要是农耕文化。这种社会形态下,家庭以多子为财富,而且多数女性在照料孩子的同时也要参与到家庭农业生产之中。大规模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样给北欧各国带来了工人阶层的贫困,政府对贫困儿童的救助也由最初的志愿宗教活动转到后期的由国家颁布法案救助,例如瑞典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实施的《济贫法案》。由于生活的贫困,生育率持续走低,加上有孩子的母亲因生活所迫很难照顾孩子,造成贫困儿童营养不良等社会问题。因此,不同政党相继开始推行促进生育以及帮助家庭照顾孩子的政策 (Hiilamo, 2002∶ 68)。该阶段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女性开始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下工作。在农业社会,为了维系家计,女性可能需要从事家庭的农业劳动。由于低廉的工资,工业化初期女性也需要外出工作以补贴家用。女性参与劳动开启了女性组织的壮大以及争取性别平等权利的道路。不仅在北欧,绝大多数工业国家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带薪母亲假(Gauthier, 1998∶ 50)。
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针对有孩子家庭的普遍性补贴措施正式出台,而且女性力量在家庭政策的制定中越来越受到关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传统农业社会的多子家庭逐渐变化为少子的核心家庭,不过这一家庭形态随着战后的婴儿潮有短暂的变化。婴儿潮的出现使得战前促进生育率的政策目标逐渐失去吸引力,政策关注点转到战争给家庭带来的贫困方面(Hiilamo, 2002∶ 73)。在此背景下,北欧各国相继出台了普遍性的儿童津贴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带来了各国家庭政策的大范围停滞,但也使得女性大规模进入生产领域以取代上前线的男性劳动力。战后大量女性迅速丧失了工作的机会,同时家庭也期待女性的回归。到60年代中期,北欧国家的女性开始积极活跃于政党与工会之中,家庭政策逐渐开始强调性别平等并关注女性的需求 (Hiilamo, 2002∶ 78)。
20世纪70–80年代的家庭政策在制度构建和绝对的公共支出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稳健增长(Hiilamo, 2002∶ 1),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促进女性就业和提高生育率的法律政策相继实施。随着女性进一步参与劳动力市场,家庭政策的双职工特征逐渐显露出来。此外,随着结婚率的降低、离婚率的增加,单亲、未婚等家庭逐渐增多,传统核心家庭不再是唯一的家庭形态。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是最低值 (World Bank, 2016)。针对多项社会变化,北欧各国在继续发展之前政策的基础上,新增为幼儿提供公立的日间照料服务(瑞典)以及为女性提供在家照顾儿童的津贴(芬兰)。多项政策带来了良好的收效,女性就业率不断提升,生育率也较为稳定。
随后,由于90年代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持续扩张的福利水平自此出现了明显的断裂。随着就业率严重下滑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几乎所有的福利水平均被削减,多项政策遭到搁置,同样波及到了家庭福利领域。即便面临着经济危机的挑战,北欧各国仍旧坚守北欧福利模式的身份(Kvist,1999)。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危机的缓解,福利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北欧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各种家庭形态下成员权益的保障再度站到了世界前沿。
三、北欧家庭福利政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
家庭福利政策不仅反映了国家、市场和家庭在福利提供上的差异,同时也反映出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文化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异质性(Hiilamo,2002∶ 17)。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讲,家庭政策追求家庭和家庭成员福利的最大化。北欧家庭福利模式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主要表现出以下原则和目标(Esping-Andersen, 1990; Hiilamo, 2002; Korpi, 2000):
第一,普遍性原则。普遍性原则意味着只要是该国公民就可享受到福利,无须其他任何附加条件。在北欧国家早年的家庭政策中,公民必须通过资产审查(Means Tested)以证明自己的资格才可申请到相关福利。而在目前的家庭政策中,这一做法已经基本上被普遍性原则取代。普遍性的另一个关键点是收入转移和服务的享受直接针对个人而非家庭,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观念大大减轻对配偶及家庭的依赖,使个人直接、独立地享受国家福利。
第二,政府成为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在为公民提供福利方面政府的作用远远大于市场,而且政府提供的公立服务也以高质量著称。北欧模式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国家、个人和市场的关系中,国家力量更为强大。通过法律和政策介入家庭决策,国家承担的责任也最为广泛。例如瑞典对已生育女性回归劳动力市场持有非常积极的政治态度。当然,并不是说北欧国家没有市场为家庭提供服务,只是相较于公立服务数量较少。
第三,强调性别平等原则,特别表现为男女分担照料儿童的责任以及支持女性就业。性别平等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早已提出多年,只是北欧国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独特的双职家庭支持模式。此模式通过国家提供公立服务以及男性分担家庭责任等具体措施促进了性别平等的进程。此处性别平等并非一味地强调女性权利,而是通过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方法削弱男女在工作和家庭中的不平等分工。
第四,儿童福利至上的原则。贫困儿童悲惨的生活状况是推动家庭政策建立的最初动机,北欧国家对儿童福利的维护体现在其详细的法规和政策上。儿童从出生开始,北欧家庭政策就开始了“无缝”支持:从刚出生到16岁的现金补贴,从出生到一岁为其主要照料者提供的带薪假,从一岁到六岁的公立照料服务,从六岁开始即可享受的免费学校教育。在这条福利主线之下,还有针对父母、住房、教育、医疗等各项政策的支持。对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国家也为其提供额外的补贴以及专门的照料。
在这四项原则之中,父母在照料儿童上的共同责任以及支持女性就业是北欧家庭政策中最突出的政策取向,而这些政策取向背后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也是政策发展的结果 。
四、北欧家庭福利政策与服务的内容
对家庭政策的不同理解会影响政策研究范围。从广义的角度讲,凡是政府对家庭进行的干预均可称为家庭政策,例如税收、学校、生育政策。不过在实际研究与分析中,对家庭政策的范围界定以收入转移、福利服务为主(Hiilamo, 2002∶ 21)。这一趋势体现了福利视野下对家庭政策的理解 ——以家庭为研究对象,以收入转移与服务为主要干预手段。本文亦采用该研究范围,详细探索实施时间最为持久的婚姻政策、现金转移政策中的儿童补贴、工作福利中的双亲假以及照料儿童的公立服务政策。由于北欧各国政策存在一些差别,本文以北欧模式最明显的瑞典颁布的家庭福利政策为主。
(一)与婚姻相关的政策
与婚姻相关的政策是各国家庭政策中很重要的内容,本文着重介绍北欧近年婚姻政策的重大改变以及与儿童相关的政策。一方面,家庭法律中大部分关于婚姻的规定是从法律角度来规范公民行为的,而本文更侧重从社会福利角度探讨,更关注福利观念转变下的政策演变;另一方面,家庭政策的目标从更加普遍意义上讲是为了给有下一代的家庭提供福利与帮助,因而更加关注与儿童相关的政策发展。在该前提下,可以发现瑞典在秉持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精神下,很早就意识到家庭在保证儿童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其家庭法律中许多法条均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同时,瑞典的家庭法律也根据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不断修订家庭法律以保障儿童权益。
在20世纪初期,北欧各国的婚姻法经历了一次大变革。调整之后的婚姻法不仅将离婚去污化而且突出了夫妻双方在经济等方面的平等地位 (Melby、 Pylkkanen、 Rosenbeck &Wetterberg,2006)。此后,北欧国家率先经历了低结婚率、高离婚率的婚姻状况变化。这一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尤为突出,90年代以后结婚率和离婚率一直比较稳定(OECD, 2015b)。到21世纪初,随着同居家庭的普遍化(OECD, 2015a),北欧各国相继颁布《同居家庭法案》(例如瑞典的《Swedish Cohabitation Act》)以保证同居家庭享有和注册结婚家庭基本相同的权利,特别是在针对孩子的福利方面 (Ministry of Justice, 2003)。此外,经过多年的努力,2011年前后,北欧各国也开始或即将认可同性婚姻的法律效力 (Wells& Bergnehr, 2014)。这些法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儿童的生活质量,尽量做到儿童福利不与婚姻形态相挂钩 :未婚母亲可以在法庭、社会福利委员会(Social Welfare Committee)甚至DNA鉴定的帮助下确认履行照料责任的男性(包括亲生父亲、继父、养父等)或与其达成照料协议,以此敦促父亲履行抚养儿童的义务;离婚家庭经常会以联合行使抚养权(joint custody)的形式共同照顾儿童;而独自抚养儿童的母亲(或父亲)也会在各类家庭津贴中获得额外补助 (Stevenson & Wolfers, 2007)。
(二)儿童补贴政策
1. 儿童补贴政策
以社会平等著称的北欧国家,通过发挥国家的财富再分配功能,为有孩子的家庭直接提供各类资金支持。为降低生养孩子带来的家庭经济风险,北欧各国为全体具有公民身份的儿童(一般是18岁以下)提供“儿童补贴”(Child Allowance)。这一补贴对儿童所在家庭的结构、儿童自身的情况、父母收入均没有要求,不受国家经济通胀影响,免税,也无需申请,只要儿童具有该国公民身份,从出生起即可享受国家或者各地方政府提供的额定补贴。在瑞典,目前的儿童补贴金额约合830元人民币,补贴持续到16岁。这一补贴方式不仅体现出北欧政策降低家庭生养孩子经济风险的目标,也折射出政策的普遍性。
2. 针对在家照料儿童的补贴政策
芬兰政府在1985年宣布各地方政府在保证所有三岁以下儿童在公立照料幼儿机构有入学位置的同时,右派执政党提出了HCA(Home Care Allowance)政策。作为幼儿进入公立机构照料的另一选择,父母可以通过领取HCA自己在家照顾孩子或者将孩子送入私立机构照料 (Sipila & Korpinen, 1998)。在针对HCA的态度上,各国不尽相同。自20世纪90年代芬兰开始实施HCA的二十年以来,尽管中间受津贴额度减少影响申请人数骤减,但领取这项津贴的家庭比例一直超过50% (Repo, 2010∶50)。瑞典则从2008年才开始实施HCA,而且由于其政治体制原因,截至2011年,只有37%的地方政府启动了这项津贴。在已实施的地方中,也仅有4.7%的家庭申请了这项福利(Ellingsater, 2012∶ 6)。可在补贴额度上,最早实施的芬兰在北欧四国中却是最低:芬兰每月为申请家庭提供约为2289元的津贴,瑞典约为2380元,挪威约为5250元,丹麦则高达6510 元 (Ellingeater, 2014)。
HCA的发展首先体现了人们对性别平等理解的变化。最初瑞典和芬兰均从“母亲的工资”角度赞同发展HCA。这一观点认可母亲在照顾儿童、保护儿童安全、家务事以及家庭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价值,反映了传统的男性养家福利模式下对男女平等的理解。至20世纪70年代,北欧国家的福利模式开始向双职家庭支持模式转变,人们对性别平等的理解也向劳动机会平等发生转变。此后两国在HCA对性别平等的意义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芬兰认为这一补贴将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家庭,女性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在家照顾孩子还是将孩子送去照料中心。瑞典却认为这一自由选择实质是“妇女的陷阱”(Hiilamo & Kangas, 2009),它将严重损害妇女工作的机会,是一种让女性承担双重压力的政策。研究也表明,HCA的主要使用群体是低学历者 (Ronsen, 2000) 以及移民母亲(Ellingeater, 2014)。因为就业难度较大,这部分女性在生育之后更倾向于选择申领HCA自己在家照顾孩子。不过最终造成两国在HCA政策上的巨大反差还是两国的政治情况。
HCA在北欧国家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各党派力量的差别。一般来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反对HCA,中立和右派政党支持HCA。左派政党力量在瑞典作为执政党的历史悠久,而在芬兰却和其他党派的力量相当。这一政党力量差异反映出了上述芬兰和瑞典对HCA 的不同态度,不过这一政治立场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在20世纪60年代,HCA首先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出,而保守党当时是持反对意见的。不过十年之后,双方的政见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Hiilamo& Kangas, 2009)。持社会民主主义政见的瑞典女性们开始转向认为HCA对女性带来了双重压力,母亲会失去工作机会,父亲会减少照料儿童的责任,儿童也会失去尽早融入社会的权力。也正是这些强烈的男女平等的观念,使得瑞典一直被认为是北欧模式,即双职家庭支持模式的代表。随着近年瑞典政局的变化,其他中间和右派政党力量的壮大,瑞典政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自1994年短暂提出并同年废止的HCA,在2008年以性别平等奖励(Gender Equality Bonus)的名义重新实施 (Nyberg,2010∶ 67–68)。这一政策废止与实施的最直接原因即为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失利。
(三)工作福利中的双亲假政策
双亲假(Parental Leave)是一种在职父母为照料刚出生(或刚领养)的婴儿而享有的一种有偿假期。在北欧,这一假期涵盖了母亲享有的母亲假(Maternity Leave)和父亲享有的父亲假(Paternity Leave)。下面按婴儿的成长阶段,简要列明各个假期之间的关系。当婴儿刚出生时,母亲可以开始休母亲假(一般为14周),父亲开始休父亲假(一般为两周),这两周的父亲假也被称为爸爸假期(Daddy Days)。之后父母可以自由协商休完剩下的双亲假 (一般为一年)。为提倡父亲参与到照料儿童之中,父母协商享有的双亲假中有一段约为两个月的父亲限额假期(Father Quota)必须由父亲享有,不可以转让给母亲 (Gupta、 Smith & Verner,2008)。 瑞典的双亲假一共有480天,其中的390天,休假期的父亲或母亲可以获得之前收入近80%的补贴(补贴最高限约合每天750元)(Bjornberg & Dahlgren, 2008∶ 51),剩下的 90天以每天约140元单一税方式(Flat Rate)补贴 (Sweden Sverige, 2016)。相较于其他国家,北欧的双亲假在时长和补贴额度上都非常慷慨。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制度在保障女性就业和照顾家庭中呈现出的灵活性。如果父母愿意,他们可以通过半天休息半天工作的方式延长他们整体双亲假的天数。而且只要孩子在8岁或者小学一年级之前,父母都可以休双亲假。这种灵活性有助于女性自由选择一个较长假期的同时兼顾工作,或者选择一个相对集中的假期后全面投入工作,亦或积攒假期以便孩子稍微长大时使用。
双亲假并非起源于北欧,不过国家强制且有偿的特点却由北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和其他国家一样,北欧国家的双亲假起源于母亲假,而母亲假的发展又可以分为无偿和有偿两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开始,瑞典引入母亲补贴(mother allowance)用以支持贫困家庭的孩子。1955年,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创政府性母亲假的国家;到1963年瑞典完成了从非常规补贴到与收入关联的转变,补贴额度以及假期时长都在不断增加;1974年,瑞典实施了由母亲假向双亲假的过渡 (Hiilamo, 2002∶112–113)。至此,瑞典双亲假政策基础基本完成,此后的政策更多是围绕补贴额度和时长的微调。其他北欧国家也基本上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
双亲假的发展历程突出体现了北欧国家支持女性就业的男女平等政策理念。在女性理论中主要有三种关于工作和家庭的观念:第一种从社会功能角度视母亲工作为一种职业;第二种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有权工作;第三种则属中间道路,认为女性有权自由选择在家相夫教子或出外工作。这三种工作家庭关系是划分家庭福利模式时的重要依据 (Gauthier, 1998∶48)。总体来说,北欧模式强调男女平等,特别是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权利。国家帮助减少女性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也通过各种措施保证女性在哺育期之后仍可以回归劳动力市场。不过,北欧各国对男女平等的解读以及国家政策也各有侧重。瑞典政府的政策明显采纳第二种观念,为母亲们提供优厚假期的同时,大力倡导将儿童送入照料中心,以此减少母亲们全职照料孩子的时长,使其及早回归劳动力市场。而芬兰则坚持让女性自由选择,不断完善HCA,由家庭自己决定采用何种方式平衡。此处平衡女性家庭与工作的政策倾向与之前所述各国政党力量分布大体保持一致。
父亲假的引入使这种男女平等的理念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也阐述了父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首先,为了敦促父亲使用父亲假,北欧各国规定了部分不可转让给母亲的父亲限额假。因为传统女性持家的观点以及男性收入相对较高等因素,双亲假主要由女性享用。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人员发现,享有休双亲假权力之后,有些雇主开始雇佣新的雇员或者不愿雇佣女性。于是政府开始建议,如果男性和女性都强制休一定时期的双亲假,那么雇主则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Earles, 2011)。因此,在20纪末北欧国家逐步开始倡导父亲参与到照料儿童中来,并由最初的家庭自由选择享有双亲假到近年强制规定其中的父亲限额假期不可转让。这一政策的实施确使北欧国家父亲假的使用率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EU,2016)。同时为了加强男女平等政策目标的实现,随着右派政府执政的开始,瑞典2008年在重启了HCA的同时也实施了性别平等税收减免(Gender–equality Tax Bonus),所有双职工家庭在享用双亲假时均可以获得这一补贴。在父亲假和母亲假所休时间达到最大的平衡时,减税力度将高达净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不过由于政策的复杂性,夫妻可能要耗时一年才能获得此税收减免 (Ferrarini & Duvander, 2010)。其次,父亲假引入的另一目标是保障儿童福利,特别是帮助建立父子或父女之间的感情。近年来瑞典男性或者父亲的认同度在逐渐发生变化,现在以孩子为中心的“男子主义”逐渐盛行,这一观点认为照料孩子也是男性的责任之一(Bjornberg & Dahlgren, 2008∶ 52)。积极照料孩子、陪同孩子玩耍不再被视为是没有男子气概的行为。研究证实,父亲与子女间的沟通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Haas & Hwang, 2008)。
(四)公立照料儿童服务
双亲假一般仅覆盖儿童自出生到1岁或1岁半的时间段,此后北欧各国为儿童提供日间照料服务 (Day Care Service)。日间照料服务主要包括为学龄前儿童(一般为2岁至6岁)提供的公立日间照料以及为小学生(一般为一至四年级)提供的课后照料服务(After–school Child Care Service)。北欧国家享受日间照料服务的孩子和家庭高达60%以上,瑞典、丹麦与冰岛甚至超过90% (Gupta et al., 2008)。针对幼儿的公立照料在北欧福利体制的创建时期经历了激烈的讨论 (Hiilamo, 2002∶ 117),最终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选择支持儿童照料服务的原因不尽相同,在芬兰,最初选择日间照料中心是工人阶级为维持生活不得已的做法。在1968年的瑞典,应女性劳动者的要求,政府成立了儿童照料委员会,指导如何发展儿童照料体系以满足社会、教育和监督的需求 (Boucher,1982)。
公立照料儿童服务首先基本由地方政府负责为所在地的适龄儿童提供服务,不过中央财政给予大量补贴,而且孩子父母也会缴纳一定的费用,不过各国基本上都根据家庭经济情况给予适当的减免。近年瑞典更是根据家庭收入以及孩子数量规定了费用的上限 (Bjornberg &Dahlgren, 2008∶ 47)。其次,各国对服务目标侧重有所不同,不过高质量的服务却是共同点。日间照料服务除了照料的目标之外,芬兰强调尽其教育目标,瑞典也同样随着规范照料中心的法律由社会服务法案转为教育法案增添了终身学习的目标,但丹麦却更强调其帮助儿童社会化以及自我认同上的功能 (Abrahamson &Wehner, 2008∶ 67)。目标的不同倾向却并不影响北欧各国在提供高质量服务上的共识:不仅师生比很低(瑞典仅为1∶5.2),而且对中心工作人员的教育资格要求也很严格 (Skolverket, 2006∶27)。 儿童照料观念的转变以及法律的支持引起对儿童照料中心的需求激增,经过多年的努力,至20世纪90年代,北欧各国地方政府均能保证每个适龄儿童接受高质量的公立日间照料服务。
五、北欧家庭福利政策的基本发展规律与经验
通过以上对于北欧家庭福利政策的探讨,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律和经验:
第一,国家是福利的主要提供方,这是北欧福利模式与其他模式的根本区别。从多样的家庭支持措施可见,北欧国家承担更多的政府责任。国家承担更多责任来源于其悠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传统。相较于自由主义占主流的英国,北欧政府几乎为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支持,而这种支持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高额的公共支出费用,例如,2014年芬兰和瑞典在OECD公共支出费用国别比较中处于第二和第五位 (OECD, 2014)。如此庞大的公共支出费用对国家经济状况影响非常明显,从对福利政策历史的梳理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90年代的银行危机期间国家不得不缩减福利开支以减轻经济压力。但随着国家福利体制的不断完善,可以看出,到90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福利水平虽然受到了影响,不过国家整体的福利体制并未受到大的冲击。经此重大变化,北欧在经济危机之后并未选择其他道路,而是坚持完善这一福利体制。对这种“费钱”福利模式的坚持源于其带来的明显且持久的社会效益。
第二,政策通过为多样化家庭形态提供灵活的支持方式,促进北欧地区生育率的稳定。据前文所述,北欧国家不断调整家庭政策以支持单亲家庭、同居家庭、离婚家庭等多样家庭形态的不同需求。此外,家庭政策还针对孩子数量、孩子们出生的时间间隔、家庭收入、孩子身心状况、家长工作性质等情况制定了详细可变的政策。例如在夫妻双方如何分配共有双亲假的时候,父母可以同时休假,也可以错开休假;可以选择休全天假而缩短假期的天数,也可以选择休半天假而兼顾工作;如有需要也可在修完有偿假期后再延长一段假期陪伴孩子。这些灵活全面的家庭支持政策带来的最显著效果就是北欧地区生育率的稳定。与之相对应的是近年来整个欧洲地区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欧盟国家2005–2016年间人口年增长量约为150万,而20世纪70年代平均约为330万(EUROSTAT, 2016b)。不仅欧盟地区,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出现严重的低生育率现象(OECD, 2016)。人口生育率短时间内的骤然变化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因此各国均出台政策予以干预。与此相比,北欧各国的生育率自20世纪70年代家庭福利框架基本完成起至2014年一直维持在1.7–1.9之间, 基本接近2.1 的人口更替值,高出许多欧洲国家(EUROSTAT, 2016a)。北欧国家几十年平稳的较高生育率证实了其家庭政策的长远效果。
第三,强调父母双方在照顾儿童上的共同责任,在家庭生活中最大化保障儿童权益。将儿童的抚养视为一种国家责任,最大限度地保障儿童权益是北欧各国家庭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首先,基本认同儿童尽早进入机构照料有益于儿童成长。北欧国家支持婴儿一岁至一岁半在父母的全职照料下成长,同时也在儿童一岁后开始提供公立照料服务。在入学之前的这段时间,幼儿可以尽早社会化并接受教育。其次,为需要特殊照顾的儿童增添额外的服务。例如,在所有北欧国家,父母根据法律或合约决定其中一人在家照顾儿童。瑞典每个生病的孩子每年最长可由父母在家照顾120天。如果是短期生病,各国基本也会为父母提供全额带薪照看孩子的假期。同时,所有国家对长期生病或者重病的孩子也提供延长双亲假并申请额外补贴的福利 (NOSOSCO, 2015∶ 54)。再次,倡导父亲共同照顾儿童,建立父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结。北欧各国近年一直在推进父亲参与家庭生活中,一方面可以减轻母亲照顾家庭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增进父亲与孩子之间的感情。特别是自爸爸假期和父亲限额假期实施后,休父亲假的人数一直在不断攀升 (Haataja, 2009)。针对瑞典父亲假实施之后的调查显示,父亲假的时长对父亲与孩子相处的满意度以及父亲照料儿童的参与度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 (Haas &Hwang, 2008∶ 8)。这些保障家庭成员平等权利以及各自需求的灵活措施,不仅体现出北欧国家落实保障儿童权益的原则,同时也体现出其在性别平等上做出的努力。
第四,衔接其他社会政策目标,推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发展。社会政策很少单独发挥效果,需要各项社会政策相互支持以达成为社会提供福祉的总体目标。家庭政策设计中,并非盲目地仅为家庭提供各项福利,而是也与其他政策构建网状的社会福利体系,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北欧家庭政策与减少家庭与工作的冲突、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关联程度非常高。家庭和工作是成年人生活最重要的两部分,各国福利均设法减少公民在履行家庭责任和工作职责上的矛盾。北欧国家选择了双职家庭支持的福利模式,在这种夫妻双方均要工作的情况下,女性将面临照料家庭抚养下一代与工作的双重负担。因此,北欧一方面大力支持父亲加入到家庭生活之中,为年轻父母提供带薪假期以使其安心照料幼儿;另一方面在休完双亲假后,母亲可因家庭情况选择在家照看,或将幼儿送至机构照料而尽早回归工作。可见,北欧国家在保障儿童权益的同时,通过国家提供服务以及父亲分担照料的方式,极大地减轻了女性就业的压力。OECD国别比较显示,北欧国家生育率不是世界最高的,但其在保持如此稳定的较高生育率的同时,女性就业率在所有OECD国家中也一直保持首位 (Gupta et al., 2008;OECD, 2015c、 2015d)。鉴于此,北欧家庭福利模式并不是通过单一政策,而是通过整个社会福利体系发挥作用。
六、北欧家庭福利政策的争议与未来发展方向
在建立了相似的家庭福利体系基础之上,近年北欧各国开始更加关注各自国家的特殊情况。在家庭福利体系的研究中,北欧各国之间的差异逐渐被学者们发掘,最为明显的是瑞典和芬兰在公立照料服务和HCA政策导向上的区分。瑞典对公立日间照料服务的青睐以及抑制HCA政策的做法与芬兰自由选择的取向截然不同。因此,北欧家庭政策作为一种福利模式的一致性受到质疑 (Ellingeater, 2014)。此外,随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瑞典悠久的执政历史于2007年首次断裂,该国右翼联合执政党上台后实施了性别平等税收减免以及HCA政策,并对日间照料中心进行改革。这些措施均呈现出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特征 (Ferrarini &Duvander, 2010)。而这一现象在Ferrarini (2006)比较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各国家庭政策时,被归纳为双轨模式(“two–edged” model)。这种模式是在检验Korpi的家庭福利模式理论时,根据国别数据新增的福利模式。这种双轨模式指一种福利模式取向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家庭福利开始呈现出多价值取向的趋势,而且这种双轨模式已经在北欧国家有所显露 (Kvist & Greve, 2011)。不过,就目前来看,经过几十年完善的北欧家庭福利模式并未有大的变革,而且这一模式的价值观已深入人心 (Christiansen & Markkola, 2006)。这种双职家庭支持模式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会是北欧家庭福利的主要模式,至少其尊重性别平等、保障儿童权益以及平衡工作家庭的综合政策效果在世界范围内仍首屈一指。
参考文献
[1]Abrahamson, P., & Wehner, C., Current Issues of Family Policy in Denmark. In I. Ostner &C. Schmitt (Eds.), Family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Change (pp. 57–74). Wiesbaden∶ VS Verlag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8.
[2]Bjornberg, U., & Dahlgren, L., Family Policy∶ the Case of Sweden. In I. Ostner & C.Schmitt (Eds.), Family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Change∶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37–56). Wiesbaden∶ VS Verlag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8.
[3]Boucher, L.,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Swedish educ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2.
[4]Christiansen, N. F., & Markkola, P.,Introduction. In N. F. Christiansen, K. Petersen, N.Edling, & P. Haave (Eds.), The Nordic Model of Welfare∶ a Historical Reappraisal (pp. 9–30).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2006.
[5]Earles, K., "Swedish Family Polic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Nordic Welfare State Model",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1, 45(2), 180–193.
[6]Ellingeater, A. L., "Nordic Earner–Carer Models – Why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4, 43(3), 555–574.
[7]Ellingsater, A. L. Cash for Childcare∶Experiences from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Retrieved from Berlin∶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09079.pdf, 2012.
[8]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9]EU (Producer). Sweden∶ Successful Reconciliation of Work and Family Life. Official Website of ht Eupean Union. Retrieved from http∶//europa.eu/epic/countries/sweden/index_en.htm,2016.
[10]EUROSTAT (Producer). Fertility Statistics. Statistics Explained. Retrieved from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Fertility_statistics, 2016a.
[11]EUROSTAT (Producer).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Change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Population_and_population_change_statistics, 2016b.
[12]Ferrarini, T., Families, states and labour markets ∶ institution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family policy in post–war welfare states,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6.
[13]Ferrarini , T., & Duvander, A.–Z.,"Earner–carer Model at the Crossroads∶ Reforms and Outcomes of Sweden's Family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ocial Policy and Quality of Life, 2010, 40(3), 373–398.
[14]Gauthier, A. H. l. n.,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amily polic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Gauthier, A. H. l. n., "Family polic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s there convergence?",Population, 2002, 57(3), 457–484.
[16]Gupta, N. D., Smith, N., & Verner, M.,"The impact of Nordic countries’ family friendly policies on employment, wages, and children",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08, 6(1),65–89.
[17]Haas, L., & Hwang, P. C., "The Impact of Taking Parental Leave on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Chilcare and Relationships with Children∶ Lessons from Sweden", Community, Work and Family, 2008,11(1), 85–104.
[18]Haataja, A. Digital Reposi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athers's Use of P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Retrieved from https∶//helda.helsinki.fi/bitstream/handle/10250/8370/FathersLeaves_Nordic.pdf,2009.
[19]Hiilamo, H.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dic family policy?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during the 1990's in Sweden and Finland. University of Turku, Helsinki. 2002.
[20]Hiilamo, H., & Kangas, O., "Trap for Women or Freedom to Choose? The Struggle over Cash for Child Care Schemes in Finland and Swede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09, 38(3),457–475.
[21]Kamerman, S. B., & Kahn., A. J., Family Policy∶ Government and Families in Fourteen Count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
[22]Kettunen, P., Th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a Perspective on the Making and Challenging of the Nordic Welfare State. In N. F.Christiansen, K. Petersen, N. Edling, & P. Haave(Eds.), The Nordic Model of Welfare∶ a Historical Reappraisal (pp. 31–66).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2006.
[23]Korpi, W., "Faces of Inequality∶ Gender,Class and Patterns of Inequalit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Welfare States",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000, 7(2),127–191.
[24]Kvist, J., "Welfare reform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the 1990s∶ Using fuzzy–set theory to assess conformity to ideal typ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999, 9(3), 231–252.
[25]Kvist, J., & Greve, B., "Has the Nordic Welfare Model Been Transformed?", Social Policy &Administration, 2011, 45(2), 146–160.
[26]Lewis, J., "Gend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 Regim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992, 2(3), 159–173.
[27]Lewis, J., "Gender and Welfare Regimes∶Further Thoughts", Social Politics, 1997, 4(2),160–177.
[28]Melby, K., Pylkkanen, A., Rosenbeck,B., & Wetterberg, C. C., "The Nordic Model of Marriage", Women's History Review, 2006, 15(4),651–661.
[29]Ministry of Justice, Family Law.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www.government.se/information–material/2013/08/family–law/, 2003.
[30]NOSOSCO. Social Protection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2013/2014∶ Scope, Expenditure and Financing. Norden Open Access. Retrieved from http∶//norden.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882555/FULLTEXT01.pdf, 2015.
[31]Nyberg, A., Cash–for–childcare Schemes in Sweden∶ History,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J. Sipila, K. Repo, &T. Rissanen (Eds.), Cash–for–childcare∶ the Consequences for Caring Mothers (pp. 65–88).Cheltenham∶ Elgar, 2010.
[32]OECD, Social Expenditure update(SOCX).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els/soc/OECD2014–SocialExpenditure_Update19Nov_Rev.pdf, 2014.
[33]OECD, OECD Family Database∶Cohabitation Rate and Prevalence of Ohter Forms of Partnership.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els/family/SF_3–3–Cohabitation–forms–partnership.pdf, 2015a.
[34]OECD, OECD Family database∶ Marriage and Divorce Rates.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els/family/SF_3_1_Marriage_and_divorce_rates.pdf, 2015b.
[35]OECD, OECD Family Database∶ Maternal Employment by Partnership Statu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els/soc/LMF_1_3_Maternal_employment_by_partnership_status.pdf, 2015c.
[36]OECD, OECD Family Database∶ Maternal Employment Rate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els/family/LMF_1_2_Maternal_Employment.pdf, 2015d.
[37]OECD, OECD Family Database:Fertility Rate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els/family/SF_2_1_Fertility_rates.pdf, 2016.
[38]Repo, K., Finnish Child Home Care Allowance– Users' Perspectives and Perceptions.In J. Sipila, K. Repo, & T. Rissanen (Eds.),Cash–For–Childcare∶ the Consequences for Caring Mothers (pp. 46–64). Cheltenham Elgar,2010.
[39]Ronsen, M. Impacts on Women's Work and Child Care Choices of Cash–for–Care Programs. Statistics Norwa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sb.no/a/histstat/doc/doc_200013.pdf, 2000.
[40]Sipila, J., & Korpinen, J., "Cash Versus Child Care Services in Finland", Social Policy Administration, 1998, 32(3), 263–277.
[41]Skolverket. Descriptive data on pre–school activities, school–age childcare, schools and adult education in Sweden 2006. Retrieved from Stockholm∶ https∶//www.skolverket.se/om–skolverket/publikationer/visa–enskild–publikation?_xurl_=http%3A%2F%2Fwww5.skolverket.se%2Fwtpub%2Fws%2Fskolbok%2Fw pubext%2Ftrycksak%2FRecord%3Fk%3D1705,2006.
[42]Stevenson, B., & Wolfers, J., "Marriage and Divorce∶ Changes and Their Driving Forc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 21(2),27–52.
[43]Sweden Sverige (Producer). Gender Equality in Sweden Sweden Sverige. Retrieved from https∶//sweden.se/society/gender–equality–in–sweden/, 2016.
[44]Wells , M. B., & Bergnehr, D., Families and Family Policies in Sweden. In M. Robila (Ed.),Handbook of Family Policies across the Globe (pp.91–107). New York∶ Spring, 2014.
[45]World Bank (Producer). Fertility Rate,Total (Births Per Woman). The World Bank.Retrieved from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end=1980&start=1960, 2016.
——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