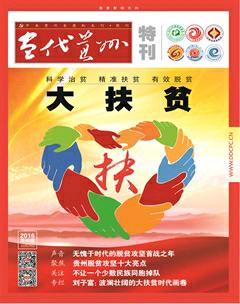消除贫困的思考:谁来解决她的“最后一公里”
资深报人,曾任中国青年报贵州记者站站长、香港经济导报执行总编辑、深圳商报前沿观察总监。辟有杨柏工作室,从事深度报道、公益文化出版等。
贵州在加速改变落后贫穷的面貌,仍然存在贫困和消除贫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需要实施效率更高的消除贫困计划。
前不久,随同贵州薪火基金会的两位督导专家志愿者,去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考察几所收留有不少留守儿童的童趣园。看到一些乡村儿童在原小学校舍改建的幼儿园中,在幼教老师带领下游戏,快乐成长,感受到了如今城乡差别在缩小,增添了宽慰。可也同时听说,一个留守的孩子,不仅失去父母的照顾,唯一带她留在乡村的外婆几周前不幸遭遇车祸,“我要外婆”成了这孩子这一段时间梦中持续的哭喊。她实际面临着失养即贫困威胁的问题。尽管这仅仅是一个个案,但却让人从中体察到了现实生活演进结构的脆弱,贫困的阴影犹存。我们能从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看到她的贫困“最后一公里”消失么?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当记者不久,就遇到贵州团省委和贵州财经学院一起举办了一个反贫困的青年论坛。大家集中讨论了贵州的贫困问题和解决贫困的对策。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举国思想解放空前活跃。农村正在展开波澜壮阔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城市改革的命题也已呼之欲出。记得贵州财经学院的学报编辑部还汇编了论坛成果,出了一本小册子《贫困的思考》。贵州青年才俊们,面对现实,那些穷则思变的鲜活思想,改革的愿望和强烈的反贫困诉求,简直是一个时代的号角,划破时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然而,当年思考贫困的那些人,如今都到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年龄。此刻,贵州怎么样了?一个宏观的标志是我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也已十六七年,在这个大格局中,贵州的发展同样石破天惊。记得那时一说贵州穷,就有三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那时贵州的产业结构在计划经济下,“墙内现代化、墙外刀耕火种”,生产力二元结构强烈不兼容,也成为经济贫穷的一个显著特征。网上有人计算,1978年贵州省人均GDP排在全国除港澳台外31个省的第31位,人均104美元。贵州人均GDP排名倒数第一,一直持续到2009年,此后开始逐步加速。2015年,贵州人均GDP达4804美元,是1978年的46.19倍。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描述的那种逻辑开始逆转,贵州单是一个生态气候资源的比较优势,已让全国和全世界“重新发现”这方宝地。贵州在加速改变落后贫穷的面貌,仍然存在贫困和消除贫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需要实施效率更高的消除贫困计划。那个小女孩,其实也就是这处于微观“最后一公里”贫困地带的脆弱人群中的一个。
消除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有经济学家注意到,即使是在大规模的发展中,也相应会存在贫困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同向增加的现象。这是因为,绝对贫困是一个顽症,他的存在机理,有非常深刻复杂的原因,消除它不是一道命令朝夕之功就可以完胜的,所以对贫困现象既需要短期干预,也需要找准根源,从源头上消除贫困的土壤条件,并长期坚持,务求干预有效;其次贫困是一种相对现象,相对贫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会伴随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而相对存在和产生新的贫困。更何况,有时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其实也只是一种相对均衡,其发展战略是否正确,发展的动力是否充沛,是否可持續,改革和改革措施是否到位,各项工作哪怕纯粹是从技术角度而言是否落实,是否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都是决定贫困现象产生的原因。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都是为了消除贫困,具有清晰的反贫困取向,尽管两者使用着不同的斗争手段和政策工具。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反贫困的路径、任务与方法是不同的,舍此就无法抽丝剥茧步步深入。
贫困不仅仅是物质短缺,还是发展与自谋能力的后天丧失。可行能力的建构不足,比如受教育的权利不足,或被某种力量剥夺,是贫困人群陷入贫困命运的原因。如果没有有效干预,那场车祸,就足以使丧失外婆抚育的小女孩,陷入失养,即建构可行能力不足的状态。一不小心,她就可能摆脱不了被贫困尾追的命运。谁来解决她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呢?或许这问题本身已超出了个案范围。(责任编辑/张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