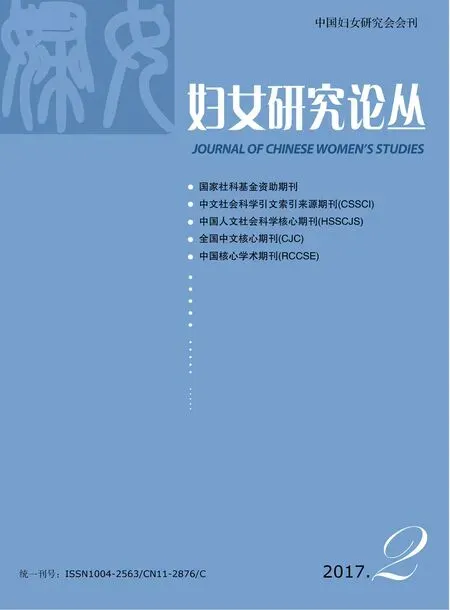托尼·莫里森文学视野中的黑人母性书写∗
王 蕾
(1.复旦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200433;2.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201306)
托尼·莫里森文学视野中的黑人母性书写∗
王 蕾1,2
(1.复旦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200433;2.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201306)
黑人母性;奴隶制度;创伤;重忆;莫里森
莫里森的作品记录了奴隶制度带给整个黑人群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暴力创伤。本文从心理创伤理论和莫里森的“重忆”概念的角度,探讨黑人母性在创伤代际传递中的作用以及通过激发黑人群体“重忆”,保护与指引他们通过触摸文化根脉修正创伤性的过去,重新达到心灵的完整与平衡。
黑人母性源于约鲁巴语中的“黑人母女精神关系”(Àjé)[1](P171),原指非洲族裔文化中女性间的代际精神纽带,特里萨·N.华盛顿(Teresa N.Washington)用这个词强调黑人女性特有的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主要通过子宫展示出黑人女性的强大繁育生存力与掌控一切的杀伐决断力[1](P171)。在美国独特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它逐渐演化为深受种族与男权主义围剿的美国黑人女性保护非裔文化完整性的独特策略。众所周知,奴隶制通过强行拆除黑奴家庭以获得无代价的劳动力,大量黑人母亲在黑人父亲缺席的环境中通过传承这种黑人母性精神独立支撑着家庭。因此,黑人母性人物不仅是种族延续的肉体纽带,而且成为黑人社会的精神支撑。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是当今重要的非裔美国作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她已发表长篇小说11部以及一些其他文学作品,代表了黑人文学的最高成就。1993年,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蕴涵着对黑人特别是对女性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探讨的性别问题常常与黑人母性对文化创伤的代际传递、对种族发展的支撑以及对非裔文化的传承作用相联系。
莫里森作品中的黑人母亲形象已在国际学界引起重视。安德莉亚·奥莱利(Andrea O'Reilly)考察了莫里森的小说、文论、演讲和访谈,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诠释了黑人母性的多元性存在,以及为母之道如何成为黑人女性在历史、文化、性别的多重压迫下自我赋权、延续种族的独特方式[2](PP1-180)。 华盛顿从非洲族裔文化中的“黑人母女精神联系”的维度解析了莫里森代表作《宠儿》(Beloved,1987)中错综复杂、深具悖逆性的母女关系,却未从创伤的维度解读奴隶制度带给黑人母性的创痛记忆[1](PP171-188)。伊夫林·贾菲·施莱伯尔(Evelyn Jaffe Schreiber)提出了莫里森小说中的“代际创伤”(generational trau⁃ma),却未深入剖析黑人母性的介质作用与救赎功能[3](P65)。
中国学界对莫里森的母性书写也有一些研究。曾艳钰从母亲在黑人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出发,从创伤记忆的角度切入,分析了《考瑞基多拉》与《乐园》中的母亲如何传承历史记忆中的“不能承受之重”[4](PP106-112)。 孟庆梅和姚玉杰从文化的维度探讨了莫里森如何通过母性诉说之悲剧主题来揭示美国非裔种族、非裔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5](PP192-194)。 李芳以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母性空间理论为切入点,对莫里森的母性书写进行了探讨[6](PP73-80)。中国的莫里森研究者多是从种族、历史和文化维度切入,主要集中在黑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文化身份认同等方面,却普遍缺少从心理分析维度考察奴隶制创伤带给黑人母性的戕害。
鉴于黑人母性在莫里森母性书写中的重要性以及无处不在的奴隶制创伤,本文将创伤理论与“重忆”理论结合起来,阐释莫里森笔下奴隶制度带给黑人母性的文化创伤、黑人母性对此创伤的代际传递以及黑人母性人物如何通过激发黑人群体“重忆”来抵制奴隶制的阴影与白人文化霸权。
一、黑人母性与奴隶制创伤的代际传递
美国黑人的母性观带有鲜明的非洲文化印记。在西非文化传统中,女性的生育与哺育功能成为一个宗族延续的基本保证,女性通常在没有丈夫的参与下独自抚养孩子,男孩在青春期或之前离开母亲,加入以血缘为基础的父系宗族社区,女孩则留在母亲身边直到婚配。所以,母亲与孩子特别是与女儿之间形成了更加持久的精神纽带[7](PP42-43),华盛顿将其描述为“黑人母女精神关系”[1](P171),它穿越了从非洲到美洲的贩奴旅程,给美国黑人社会施加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美国蓄奴制下,黑人被剥夺了基本人权与文化身份,他们组建的家庭因为缺乏法律制约,呈现出很大的随意性:男性黑奴可以被当作商品随意卖掉,女性除了进行和男性相等程度的田间劳作,还必须独自抚养家庭,与非洲传统家庭模式有很大的相似性。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黑人女性很难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她们的身体在繁重的劳作与男性欲望之下“解体”。芭芭拉·奥莫拉德(Barbara Omo⁃lade)指出,女奴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被白人主人利用过[8](P7)。一方面,她们被迫不断地生育,为奴隶主储备劳动力;另一方面,她们还被剥夺了母亲身份,因此,多数黑人母亲对孩子产生了强烈的控制欲,在心理上将孩子视为自我的延伸,以此来改写深受创痛的自我。
废奴之后,美国进入重建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黑人传统上的人口、就业和家庭结构,对黑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E.富兰克林·费雷泽(E.Franklin Frazier)指出,在蓄奴制下组成的黑人家庭在内战、重建、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冲击下极易解体,往往形成以女性为中心的单亲家庭[9](P88)。多数黑人女性因为被迫进入美国劳工阶层而逃脱了父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规范和约束,然而她们却要在奴隶制阴影之下独自艰难支撑着家庭,成为处于美国主流社会边缘的文化他者。
在莫里森作品中,奴隶制度具体化为带给黑人女性的性别创痛。“创伤”(trauma)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意指肉体上的创伤,现在亦为精神分析理论的专业术语,用来指创伤事件带给心灵的疮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将“创伤”描述为短时期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致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干扰的经验[10](PP223-224)。 在《身上记忆之痕》(The Body Keeps the Score,2014)中,贝塞尔·凡·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指出,人类大脑分为左脑和右脑,右脑是在胎中最早发育的部分,与直觉、触觉、视觉以及情绪有关;左脑与逻辑、语言有关。在创伤发生的那一刻,受害者关闭了一部分左脑知觉意识系统,最大限度降低创伤性事件带给心理的摧毁性打击,这个过程同时激活了右脑中与身体相连的神经系统,帮助受害者逃脱创伤性的环境。然而,如果受害者行动受到限制,他就会留下创伤记忆[11](P54)。
创伤的神秘之处在于其强制复现性或轮回性。在《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1967)中,弗洛伊德用“潜伏期”(latency)一词定义“原初创伤”(precipitating trauma)与“创伤复现”(traumatic reenactment)之间的沉潜期[12](PP120-121)。 换言之,原初创伤只是暂时沉潜下来,等待将来被激活,幻化为失控的“躯体化症状”(somatic symptom),即创伤复现。卡伊·埃里克松(Kai Erikson)指出创伤的成因非常多样化,既有长期折磨虐待的慢性创伤,亦有突发的危险或恐怖事件造成的毁灭性打击[13](P457)。莫里森描写的黑人母亲大多因为遭受剥夺、凌辱、家庭离散而备受创痛,缺少对孩子的心理关照,将奴隶制引发的“原初创伤”传递给了黑人后代。
在小说《宠儿》中,莫里森借饱受弑婴创伤折磨的女奴塞斯(Sethe)与人鬼难辨的女儿宠儿(Beloved)之间的爱恨纠葛,展示了奴隶制创伤挥之不去的阴影。塞斯儿时,因为未脱奴籍,母亲永远在田间劳作,将她丢给独臂保姆楠(Nan)照顾。后来,母亲独自出逃失败被奴隶主处死,塞斯的右脑通过母亲脸上被牲口嚼子压出的畸形笑容记录下了对母亲最后的创伤记忆。
塞斯因为创伤的存在未能形成完整独立的人格,以至于自己为人母后,将孩子视为自我的延伸。在创伤环境中,她通过极端行为来维护自己对孩子的控制欲。在“甜蜜之家”(Sweet Home)奴隶庄园,塞斯无意中听到白人奴隶主“学校老师”(School⁃teacher)试图平衡自己的“人的属性”与“动物的属性”[14](P193),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奴隶主眼中只不过是一头可以被随意处置、任意消遣的牲口,于是义无反顾地逃出了“甜蜜之家”。成功逃出28天之后,奴隶主疯狂追来,塞斯在绝望中亲手割开了宠儿的喉咙,以期摆脱世代为奴的家族命运。惨剧发生之后,塞斯的两个儿子不堪家中鬼魂骚扰,一起出逃,婆母萨格斯(Suggs)忍受不了当地黑人社区的背叛与遗弃,很快撒手人寰,只留下塞斯与小女儿丹芙(Den⁃ver)相依为命。
海伦·莫格林(Helene Moglen)将这种既孕育又毁灭的母亲称为“原始母亲”(primal mother)[15](P204)。18年之后,小鬼宠儿幻化人形,向塞斯索要失落的母爱,塞斯这样向宠儿解释自己的杀戮行为,她原计划带领全家到“那边”与自己的母亲团聚,因为计划受阻,只有宠儿顺利到达彼岸[14](P203)。 因此,塞斯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疯狂的“原始母性”实为连接原初创伤(母亲缺位)与创伤复现(弑婴行为)之间的桥梁,表现为奴隶制度带给黑人母女代际精神纽带的戕害。
塞斯用暴力诠释母爱之后进入了创伤的沉潜期,仿佛被“活埋”:她的眼白消失了,眼睛如同她的皮肤一般黑,直勾勾盯着前方[14](PP150-151)。 这些躯体化症状表明塞斯处于一种人格分裂状态。凡·德·科尔克指出,“通常情况下,人的左右脑同时工作,任何一边关闭,即使是暂时性的,或者切除一边,都具有致残性”[11](P45)。 这一摧毁性事件虽然被塞斯大脑的认知系统排斥在外,却在其身体上留下了记忆,预示着它将以“轮回”的形式强行复现。
惨剧发生之后,塞斯的精神裂成碎片,无力顾及丹芙的心理健康。塞斯的精神状态令丹芙倍感孤独压抑,只有在学校才能得到暂时的缓解。然而,当她从小伙伴尼尔森(Nelson)口中得知母亲多年前一手制造的家庭悲剧之后,患上了失语症,被迫辍学,被“活埋”在时常闹鬼、怨气冲天的家中。丹芙的失语实为一种躯体化症状,因为她无法接受母亲对家人的屠戮行为,又无力反抗逃脱,只能与“杀人犯”母亲同居一室,将其对母亲的理解以感官信号的形式储存于身体潜意识之中。
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母性场域中,丹芙被记忆与忘却的悖论撕扯,常常分不清是睡着还是醒着,她晚上尚可感受到已故祖母萨格斯的保护性存在,白天却“分不清是自己在呼吸还是身边的人”[14](P207),只能通过自我分裂来暂时维持心理的平衡,因此沦为一个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凝视目光。丹芙被一个同样的噩梦反复折磨:塞斯割下她的头,拎到楼下,慢条斯理地给她梳辫子[14](P206)。 丹芙通过这个杂糅着母爱与暴力创伤的噩梦强制复现了塞斯多年前亲手制造的弑婴惨剧,同时言说了自己对母爱的渴望。最终,塞斯用暴力诠释的母爱跨越时空与主体,成为一种阴魂不散的家庭记忆。
正如美国创伤理论家凯茜·卡鲁斯(Cathy Ca⁃ruth)所指出:创伤性的历史事件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在“另一时间和另一地点才能真正进入意识层面”[16](P17)。18年后,人鬼难辨的宠儿突然闯入塞斯的生活,向她索要欠缺的母爱,强迫她直面不堪回首的过去。由此分析,宠儿实质上是塞斯的躯体化症状幻化出来的角色,她具有象征意义的“回家”印证了卡鲁斯强调的创伤的跨时空结构,是家族甚至整个社区黑人失控的精神分裂症状的隐喻化呈现。
创伤复现时,身体蒙受创伤的感觉无法分辨过去与现在,往往对原初创伤机械模仿。宠儿回归后,母女三人形成了一个女性乌托邦,完全忘却了外部的世界。塞斯仿佛回到少女时代,每天沉溺于满足宠儿稀奇古怪的欲望,母女二人经常换衣服,换床铺,手挽着手走路[14](P240)。 宠儿“处处模仿塞斯,像她那样说话,像她那样笑,就连走路、手的动作、鼻子里的叹息、仰头的神态,也全是她的样子”[14](P241)。塞斯喜欢摆弄宠儿的头发,编辫子,打结,打发蜡,她的爱抚动作散发出令丹芙不安的气息[14](P240)。 这一动作实际上暗射了塞斯当年的弑婴行为,因为宠儿的回归虽然满足了塞斯对女儿的疯狂欲念,却也带回令她无法言说的过去,在这种生死张力结构中,塞斯失去了时间意识与自我界限,与宠儿逐渐融为一体,直到宠儿用双手扼住塞斯的气管。这诡异的一幕是对塞斯多年前杀戮行为的机械模仿,向读者呈现了塞斯把奴隶制度造成的黑人母性创伤跨代传递的过程。
在莫里森看来,黑人母亲是种族身份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守护者,是黑人女性力量之所在。然而,莫里森的小说聚焦于奴隶制引发的创伤如何通过黑人母性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文化创伤与集体记忆,莫里森也由此暗示只有当黑人母亲勇敢地带领黑人社区直面过去,才有可能带领社区走出创伤的阴影。那么,她们是以什么策略引领黑人社区直面创伤、超越创伤,并在超越中创造丰富而又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将创伤之痛转化为创造之力呢?
二、黑人母性与社区中的“重忆”
在《宠儿》中,莫里森创造了“重忆”(rememory)一词来探讨奴隶制文化创伤带给黑人群体挥之不去的阴影。如前文讨论,创伤发生之时,受害者会启动一种防卫机制,大脑向身体发射信号,帮助受害者逃脱。如果身体活动受限,大脑在创伤过后会继续向身体发射虚假“报警”信号,“重忆”就表现为由此引起的失控的强制性回忆。在莫里森的作品中,“重忆”揭示了黑人在奴隶制度与种族歧视的围剿之下,面对创伤性事件的毁灭性冲击,往往无力反抗逃脱,身体上录写的记忆导致他们不断强制重复创伤。玛丽琳·桑德斯·莫布利(Marilyn Sanders Mobley)将莫里森的“重忆”解读为“黑奴往往沉溺于对过往的回忆”[17](P361)。莫里森塑造的黑人惯于通过暴力言说沉潜在身体上的创伤,实质上是对奴隶制引发创伤的“重忆”,同时反映了他们试图改写创伤的努力。
在一次和丹芙的谈话中,塞斯将“重忆”解释为无法逃脱的强制性回忆:“一栋房子可能被大火吞噬,但其所占据的位置,在我们脑海中形成的图画却留下来,不仅在我的“重忆”中,而且在那儿,遥不可及。”[14](P36)塞斯的“重忆”表现为一种外化的强制性记忆,因为被压抑的死亡记忆在创伤过后还向她的身体发信号,使她的精神世界分裂出来,幻化为一个失控的图画,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宠儿幻形入世之后,不但消耗着塞斯的精神内力,而且蔓延至外部空间,表现为一种富有攻击性的力量,体现了塞斯甚至整个黑人社区的“重忆”。当地黑人只有把自己的过去投射到宠儿之上,在与宠儿的爱恨纠葛中,才能“重忆”创伤性的过去,才能寻回内心的平衡与完整。所以,“重忆”实为一种超越个体的黑人群体对奴隶制创伤的集体记忆。
作为美国黑人作家,莫里森对生死轮回、个体与社区、过去与现在、黑人母性等问题的探讨都体现了非洲哲学和宗教的影响,她定义阐释的“重忆”也表现为两个相互焦灼的过去,既有对奴隶制创伤的死亡记忆,又是美国黑人通过触摸非洲文化根脉达到疗愈创伤、提升种族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林登·皮切(Linden Peach)强调,对于一个深受蹂躏践踏的民族来说,“重忆”是最好的救赎方式,“因为奴隶制度不但摧毁了黑人社区,拆散了黑奴家庭,而且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音乐”[18](P118)。 所以,“重忆”强迫黑人族群直面历史重创,同时通过黑人母性人物的引导,帮助黑人通过非裔传统文化与艺术形式来改写创痛的过去。
莫里森通过“重忆”揭示了黑人母性带给这个族群的创伤记忆,也展示了黑人母性人物如何通过讲故事与歌唱等非洲口述传统帮助后代继承传统和传续历史。在《宠儿》中,保姆楠告诉塞斯,自己与塞斯的母亲从海上来,途中多次惨遭船上水手蹂躏,塞斯母亲将生下的混血儿全部扔掉,只留下了与黑人生下的塞斯。楠的口述帮助塞斯认同潜藏在黑色体肤之下的种族基因,修复了断裂的母女精神纽带。非裔黑人被强行掠夺到美国之后,面临着文化与身份缺失的双重困境,而口述传统成为这个族群传承民族文化精髓、构筑心灵家园的一个重要途径。小鬼宠儿幻化人形之后,经常哼唱塞斯曾经哼唱的歌谣,督促塞斯讲述过去的故事,唤醒了塞斯对母亲的创伤记忆,最终,宠儿通过口述传统激发了塞斯的“重忆”,为其后来重新融入当地黑人社区铺平了道路。
奥莱利指出,莫里森探讨的黑人母亲通过黑人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放克”(funk)精神来实现自我赋权,完成族裔文化与种族的延续[2](P19)。 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中,莫里森将“放克”精神描述为一种从身体内喷薄欲出的“冲动、激情和丰富的情感”[19](P83)。 “放克”展示了黑人族群对触觉、听觉与味觉等带来的愉悦感官体验的孜孜不倦的渴求,与追逐名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创伤复现之时,知觉意识系统失去作用,创伤记忆以右脑中储存的不能被吸收的、失控的感官体验入侵现实。然而,凡·德·科尔克指出,右脑保留着母亲与婴儿之间的非语言交流体验[11](P44),所以,“放克”实质上暗示了右脑所储存的直觉感官信息对于人类创伤的母性抚慰与解放作用。因此,黑人母性人物承载着黑人文化与历史记忆,她们能在激发黑人族群“重忆”历史创痛的同时,用“放克”精神指导他们从生活的色彩与律动之中体会愉悦,释放无意识欲求,缓释在美国文化他者空间中备受压抑的生存体验。
在《爵士乐》(Jazz,1992)中,莫里森创造性地将非裔文化传统中的爵士乐与讲故事技巧结合起来,探讨疗愈奴隶制创伤的有效途径。《爵士乐》的灵感来源于莫里森为《哈莱姆死者之书》做序时偶然发现的一幅18岁黑人女孩的遗像。《爵士乐》以重建之后的纽约哈莱姆区为背景,讲述了南方黑人夫妇乔(Joe)与维奥丽特(Violet)来到北方城市艰难谋生,后来年过半百的乔与18岁的多卡丝(Dorcas)深陷一段忘年恋,最后,乔在爱恨纠结中开枪打死了移情别恋的女友。维奥丽特为此大闹葬礼,后来通过访谈,维奥丽特逐步了解了多卡丝,与现实中的乔也达成了和解,开启了新生活。
爵士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于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糅合了黑人音乐丰富的节奏感与非洲的和声音乐形式,演奏中讲究即兴(improvisation)与“启应”(call and response)技巧①“启应”常见于黑人劳动歌谣、布鲁斯、灵歌等口述传统中,这种演奏技巧存在于爵士演奏的两个层面,一是爵士乐手在旋律上相互呼应,二是演奏者与观众之间的召唤与回应。在爵士乐演奏中,观众处于和演奏者同样重要的地位,他们现场的回应赋予演奏者不同的灵感,直接影响着后者的即兴表演。,整个乐曲是由多位乐手对旋律主题的和声重复和单独变奏构成。所以,即兴实为一种变奏,然而并未脱离旋律主题的走向,以便于乐手独奏之后转入既定的轨道与其他乐手汇合,从而达到情感的宣泄与共鸣。这部小说以爵士乐演奏技巧架构故事情节,旋律主题是黑人母性对奴隶制的代际传递。故事中主要人物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家庭离散创伤:多卡丝的父母均死于种族骚乱,乔生下来就不知道父亲是谁,又被神志失常的母亲抛弃,维奥丽特的母亲在家园被摧毁后投井自杀,导致她结婚后拒绝生育,因为不想延续母亲带给她的摧毁性打击。
爵士乐表演充分体现了黑人音乐中的“放克”精神修复创伤的能力。表演可以创造一种安全的氛围,在一种可以与心脏跳动产生共振的节奏中,表演者与听众进入一种“迷狂”的“重忆”状态,在理性状态中包围创伤的“硬壳”被潜意识长期聚集的压力打破,听众在叫喊、哭泣、摇摆中爆发,即兴释放被压抑的创痛体验与喷薄而出的“放克”式欲动,获得精神的平衡。每一个黑人个体的创伤是不一样的,但创伤本身却成为凝聚黑人族群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被爵士乐的旋律激活,表演中的“启应”如同神的手在挨个唤起听众的记忆,这个过程就是“重忆”的重要形式之一。因此,爵士乐作为激活机体创伤记忆的手段,是“重忆”最具体而灵动的引领者。
乔与多卡丝的爱恨纠葛揭示了他对母亲的“重忆”。乔自出生就不知道父母是谁,从14岁开始,他多次去林间洞穴寻找母亲的踪迹。跟多卡丝在一起的时候,乔眼前总是会浮现母亲的身影,因为多卡丝身上散发着一种俗世肉欲,激发了他大脑中对母亲的直觉记忆与疯狂欲念。多卡丝移情别恋之后,乔四处寻找,在去纽约枪杀多卡丝的路上,又回想起当年去寻找母亲的情景,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Carole Boyce Davis)将“重忆”描述为“在痛苦的回忆中与失散的家人重聚”[20](P17)。 乔对多卡丝的复杂情感揭示了他如何在对母亲的“重忆”中逐渐丧失了自我边界,最后导致他试图通过“吞噬”多卡丝来达到永远占有女孩/母亲的目的。
在这部小说中,多卡丝的故事以旋律主题形式在不同人物之间重复讲述,虽然内容稍有差异,却指向了黑人母性创伤的集体记忆。故事开始时,维奥丽特已经年届半百,却从未忘记母亲“跳下去的地方”[21](PP100-101),因此始终无法活在当下。 1888年,父亲常年外出缺位,母亲罗斯·蒂尔(Rose Dear)带着她们姐妹5人住在窝棚中,全靠几个好心邻居接济。外祖母特鲁·贝尔(True Belle)丢下在巴尔的摩的清闲工作,来帮助女儿一家度过难关,身心俱疲的蒂尔却跳井自杀,将为母之责永远丢给了自己的母亲。为了忘却母亲带给她的黑色记忆,维奥丽特遇到乔之后,来到哈莱姆谋生。相似的悲惨经历使两人达成共识,不要孩子拖累。然而,多年以后,当维奥丽特40岁时,母性的饥渴像一把锤子将她击倒,当她醒来时,丈夫已经开枪打死了一个姑娘。丈夫的背叛又激活了她对母性创伤的“重忆”,她大闹多卡丝葬礼,还试图划破尸体的脸。
为了摆脱过去的梦魇,维奥丽特开始登门拜访多卡丝的姨妈艾丽丝(Alice),两人的交谈展示了爵士乐的即兴演奏与“启应”技巧。卡罗琳·M.·琼斯(Carolyn M.Jones)指出,爵士乐演奏中的即兴性形成了一个“仅存于演奏者之间的空间”[22](P487)。在两位女性的交谈中,这一空间首先表现为在美国种族主义与男性主义围剿之下的女性他者空间。面对艾丽丝的悲伤与敌意,维奥丽特声称自己“不是那个让你害怕的人”[21](P80),她的柔弱与无助勾起了艾丽丝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她感觉“心中有什么东西敞开了”[21](P83),“启应”式地想起了30年前丈夫无情离开时,她也渴望见到“另一个女人的血”[21](P86)。两人通过讲故事相互激发,在“重忆”的过程中,走进了彼此的精神空间。
爵士乐演奏讲究演奏者相互激发灵感,在“启应”中不断即兴重复与修改自己的演奏。艾伦·J.赖斯(Alan J.Rice)认为,“黑人艺术的要旨正如爵士乐演奏所表现的,看似粗糙、随意、不着痕迹……而爵士乐手可谓老道,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与音乐水乳交融,甚至可以在台上即兴奏出”[23](P424)。 维奥丽特与艾丽丝的即兴联奏在于两人都有着类似的一触即发的创伤记忆。凡·德·哈特指出,右脑主要通过直觉或情绪记忆,很容易被记忆中类似的声音、面部表情、动作和地方触发[11](PP44-45)。 很显然,这些直觉信息表现为一个强制记忆痕,能激发个体跨时空、跨主体“重忆”,两位女性正是通过这个记忆痕激发并开启彼此的“重忆”。从维奥丽特第二次登门,艾丽丝就开始用密密的针脚帮她修补衣裙。艾丽丝做针线的手创造了一种非常安全的氛围,使维奥丽特想起借着火光缝缝补补的外祖母贝尔,这种母爱语言成为激发她“重忆”的直觉信号。
维奥丽特的“重忆”同时展示了爵士乐演奏所蕴含的创伤元素与黑人母性修复创伤的能力。当维奥丽特问道:“长大成人的人在哪儿?是我们吗?”“噢,妈妈”[21](P110),艾丽丝脱口而出,她的“启应”为两个人的即兴演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通过与别人“启应”式的“重忆”,维奥丽特发觉她与多卡丝有着极为相似的童年悲惨经历,她不断修改自己的即兴言说,杀死了那个要杀多卡丝的我”[21](P209),将自己的身体与精神整合起来,与乔重归于好。最终,支离破碎的语言片段汇成了创世的洪水,维奥丽特的即兴言说在艾丽丝“启应”式的共情认同之下得到了宣泄,爵士乐演奏将所有被母性缺位创伤的黑人凝聚起来,见证了从个人创伤走向集体复原、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
黑人群体对黑人母性的“重忆”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莫里森强调其作品中贯穿着一种类似合唱的背景声音,例如《最蓝的眼睛》中的“我”的画外叙述,《秀拉》(Sula,1973)中被赋予了活人性情的小镇,《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中相互关照的社区邻里,《柏油娃》(Tar Baby,1981)中被拟人化的大自然[24](P60)。 《爱》(Love,2003)中的母性人物L去世后更是与大海融为一体,幻化为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这些背景声音实为被历史记载忽略的黑人女性在美国主流社会独特的他者文化经验,它唤醒了小说中非裔族群对黑人母性过去的零散记忆,并将所有黑人连接起来,隐喻了非洲精神文化遗产的厚重。这个族群只有集体“重忆”母亲,才能言说不可言喻的过去,认同自己的族裔身份,实现民族救赎。
三、结论
多数黑人母性人物在种族主义与男性主义的围剿下独自艰难支撑着家庭,有意无意间将奴隶制引发的创伤传递下来,这种传递实为一种跨时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现象。然而,她们通过非裔口述文化传统中具有“重忆”功能的爵士乐和讲故事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放克”精神激发黑人的族裔文化意识,指引他们从生活中体会与继承非裔文化精髓,在社区中直面和超越历史创痛,最终完成对黑人个体与种族的救赎与再造。通过“重忆”奴隶制带来的族裔文化创伤,莫里森不但探索了黑人在白人主流社会的边缘化存在,而且揭示了身处男性霸权社会的黑人女性如何颠覆种族和性别宿命。黑人族群只有接纳黑人母性承载的种族奴役史与非裔文化遗产,才能抵御奴隶制对黑人性的压抑歧视,以及对黑人社区的分裂摧毁,才能认同自己的族裔文化身份,携手从历史重创中走出来。
[1]Teresa N.Washington.The Mother⁃Daughter Àjé Relationship in Toni Morrison'sBeloved[J].African American Review,2005,39(1-2).
[2]Andrea O'Reilly.Toni Morrison and Motherhood[M].Albany,New York:State Press of New York Press,2004.
[3]Evelyn Jaffe Schreiber.Race,Trauma,and Hom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M].Baton Rouge: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
[4]曾艳钰.记忆不能承受之重——《考瑞基多拉》及《乐园》中的母亲、记忆与历史[J].当代外国文学,2008,(4).
[5]孟庆梅,姚玉杰.历史语境下的莫里森母性诉说之文化解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6]李芳.母性空间的呼唤——托妮·莫里森的母性书写[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5,(6).
[7]Deborah Gray White.Ar'n't I a Woman?:Female Slaves in the Plantation South[M].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85.
[8]Barbara Omolade.The Rising Song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M].New York:Rougledge,1994.
[9]E.Franklin Frazier.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
[10][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车文博主编.《精神分析导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11]Bessel van der Kolk.The Body Keeps the Score:Brain,Mind,and Body in the Healing of Trauma[M].New York:Penguin,2014.
[12]Sigmund Freud.Moses and Monotheism[M].Trans.Katherine Jon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
[13]Kai Erikson.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J].American Imago,1991,48(4).
[14]Toni Morrison.Beloved[M].London:Vintage,1997.
[15]Helene Moglen.Redeeming History:Toni Morrison'sBeloved[A].in Elizabeth Abel,Barbara Christian&Helene Moglen eds..Fe⁃male Subjects in Black and White:Race,Psychoanalysis,Feminism[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16]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17]Marilyn Sanders Mobley.A Different Remembering:Memory,History,and Meaning inBeloved[A].in Henry Louis Gates,Jr.and K.A.Appiah,eds..Toni Morrison: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C].New York:Amistad,1993.
[18]Linden Peach.Toni Morrison(2nd Edition)[M].New York:St.Martin's,2000.
[19]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M].New York:Vintage Books,2007.
[20]Carole Boyce Davis.Black Women,Writing and Identity:Migrations of the Subject[M].New York:Routledge,1994.
[21]Toni Morrison.Jazz[M].New York:Vintage,2004.
[22]Carolyn M.Jones.Traces and Cracks:Identity and Narrative in Toni Morrison'sJazz[J].African American Review,1997,31(3).
[23]Alan J.Rice.Jazzing It up a Storm:The Execution and Meaning of Toni Morrison's Jazzy Prose Style[J].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1994,28(3).
[24]Toni Morrison.Rootedness: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A].in Carolyn C.Denard ed..What Moves at the Margin:Selected Nonfic⁃tion[C].Jackson: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2008.
责任编辑:含章
Black Maternity in Toni Morrison's Literary World
WANG Lei
(1.College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2.Foreign Languages School,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black maternity;slavery;trauma;rememory;Morrison
Toni Morrison's work highlights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imposed by the institution of slavery upon black people in general and black females in particular.This paper adopts trauma theories and Morrison's concept of“rememory”to explore the role of black maternity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mpact of slavery.Through forcing black people to“rememory”,black mothers have helped revisit the past that is at the base of recurring structure of trauma and the critical role of African cultural heritage for reconstructing racial iden⁃tity for African American people.
I106.4
A
1004-2563(2017)02-0104-08
王蕾(1977-),女,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美国文学和文论研究。
本文为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拉康‘小他者’视域下托妮·莫里森作品中的女鬼”(项目编号:D-8005-15-0021)、上海市教育科学课题“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文学与人生’的设置与开展”(项目编号:B14027)、上海海洋大学“对分课堂(PAD)模式下的人文素质类课堂群教学团队建设”项目、上海海洋大学“美国文学”重点课程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