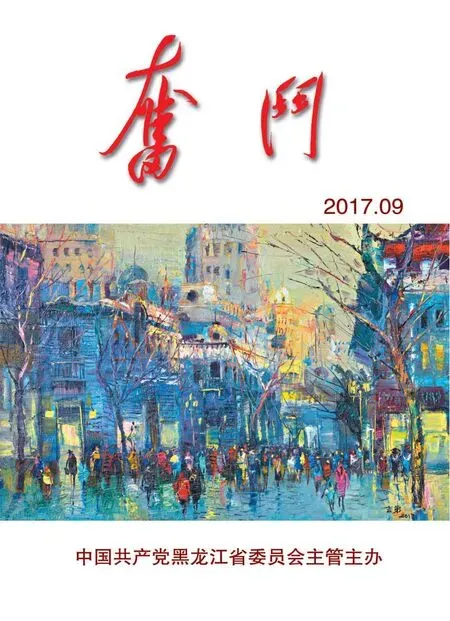毛泽东的“做”文之道
■ 安虎贲
毛泽东的“做”文之道
■ 安虎贲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文章大家。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他戎马一生,虽从没拿过枪,却从没放下过笔。他“意气风发,挥斥方遒”,通过手中的如椽巨笔,指挥千军万马,调度国计民生,书写历史长卷。他写诗、填词,作赋、撰联,写新闻稿和批语、做报告和演讲,可谓是“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
毛泽东的文章高屋建瓴,大气磅礴,说理透彻,文风泼辣,情感真切,言语生动,雅俗共赏,大家风范,独领风骚。揣摩毛泽东的“做”文之道,有这样几个特点。
道借文传 文须载道
“文者,贯道之器也。”文艺作品是思想的载体,作为思想家,毛泽东非常注重文艺的功能性。毛泽东早年受国文教师袁仲谦影响,苦读桐城派著作,尤喜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而姚鼐和曾国藩皆主张文以载道,皆以为考据、辞章应以义理为归。读这些文章,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还能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术。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经史百家杂钞》,“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干振则支披,将麾则卒舞”;“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两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古文辞类纂》已是文以载道之作,毛泽东仍嫌其偏重于文,以为《经史百家杂钞》突出“干”,算是道文具备,难能可贵。他还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二者不可偏废。道借文传,文须载道,可见他在文道关系中,对道的看重。
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逐步形成,“道”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怎么服务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地位的问题,提出了“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服务于政治”;“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是他对文道关系的最后定论,这篇讲话也成为文以载道的经典篇章。而更宝贵的是,毛泽东“做”文更注重“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能把生动的实践升华为高度的理论,又能把深邃的思想普及于普通大众。他曾评价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总之,“理论和实际没有结合起来”。用“革命家的话”发动和凝聚革命的力量,正是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一个重要使命。他要让广大普通的党员和群众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自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革命理论、传统文化和革命实践相统一,而毛泽东就有这种本事。大家耳熟能详的“老三篇”,就是这样的杰作。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中提倡了三种精神,一种是以八路军战士张思德为代表的“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一种是以加拿大援华大夫白求恩为代表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种是以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故事为象征的“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奋斗精神。这三种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初期,曾成为举国上下的行动指南,发挥过无比巨大的精神作用。而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也都是因应实际、推动实践而写,对推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抵得上多少千军万马,承载起多少人间大道啊!
文贵义法 力避气单
青年毛泽东在追随袁仲谦学文时,很看重行文技巧,在《讲堂录》提出:“文贵颠倒簸弄,故曰做。”颠倒簸弄就是技巧。即便是后来他成为革命的新文艺的指导者,强调“大众化”的时候,也告诫文艺工作者作文要讲技巧。1938年4月28日,他在“鲁艺”作《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时说:“清代桐城派作文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1955年10月11日,他把“做”文技巧具体归结为逻辑、文法和修辞:“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讲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相互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该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毛泽东“做”文更讲气势。他说:“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则病在气单。” “文章须蓄势”,他在《讲堂录》中非常形象地把文章的气势比喻成:“河出龙门,一泄至潼关。东屈,又一泄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泄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我们在毛泽东的文章中时刻都能感受到那磅礴凌厉的气势。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当中国革命遇到选择时,他写《民众的大联合》,“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在革命胜利在即,他豪迈一挥大手,写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不是说我们面前已没有困难。……凡此种种,全党同志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并准备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前途的势力。”毛泽东文章中的这种大气势、大气魄、大胸怀、大格局,源于一代伟人对时代大势的清醒把握,源于扎根中国大地的深沉情感,源于革命必胜的英雄气概,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劳其心、屡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而为文”(梁衡语)。
阳刚为主 不废简约
毛泽东一生饱读诗书陶铸的风雅气质,决定了他刚柔并济而以阳刚为主的审美趣味和“做”文风格。1957年8月1日他在读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后写下批语:“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毛泽东还爱读“三李”的诗。他说李白有道士气,又说李白“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欣赏李白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各种世俗规矩的人生价值观。他赞赏李贺诗奇峭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和奔放豪迈的激情、瑰丽多彩的语言。对李商隐的咏史诗和“无题”诗,也是一读再读,圈了又圈。在1958年1月16日南宁会议讲话中,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李贺《致酒行》最后四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以汉朝的主父偃、唐太宗时的马周先遭厄运、后被重用的历史人物自立自勉,不以遭际“零落栖迟”“幽寒”而气馁,表达了诗人希望有一天壮志得酬的愿望。“雄鸡一声天下白”一句,音韵高亢,意境开阔,毛泽东尤为欣赏,1950年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运用点化成“一唱雄鸡天下白”,形容新中国成立后,由黑暗走向光明,化旧句以新意。
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也是“偏于豪放,不废简约”。他一生创作的百余首诗词中,既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也有“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柔肠;既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浪漫,还有“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感叹。最拍案叫绝的还是那首《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撼动山河的气势,摇曳古今的志向,臧否风流的眼界,气象万端的风雅,酣畅淋漓的神气,抒展了一代伟人的真性情、大情怀,是代表其豪放风格的杰作。而作于1923年的《贺新郎》,则婉约细腻。“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1923年12月毛泽东离别杨开慧,离开长沙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离别之际,云滔霜重,半天残月,凄然相向,苦情重诉,断肠的汽笛和欲零的热泪,深切的表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缱绻缠绵的柔情爱意,透射出毛泽东并不经常流露的“重感慨”的内心底色。但“凭割断愁丝恨缕”为革命献出全副身心的豪情,“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的气概,又表现出毛泽东投身革命风暴的期待。这首词可算“中间派”吧。
文章神气 中国气派
毛泽东认为为人和做文应该有神气。这神气,应该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并列为延安整风的三大内容,号召全党抛弃党八股,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章写作和表达方式。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重要讲演,列举了“党八股”的种种危害,他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提倡我口讲我心,我手写我口。他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年轻时他办报刊,包括他在战争年代亲自撰写新闻报道,文风活泼辛辣,酣畅流利;与老一辈党外民主人士谈话唱和,文辞典雅,陈义高古;对青年后辈的教导,亲切自然,平白朴素;大会讲话,高韬宏略,态度鲜明;党内讨论,由此及彼,入情入理;批示批注,不掩性情,直率本色;政论理论,有论有据,醇厚自然;诗词文章,神气昂然,磅礴恢弘。这些不同风格的背后,表达的真诚与尊重,风范与魅力,正是毛泽东的“中国作风”。
毛泽东“做”文语言独特,引人入胜。他倡导古为今用,号召人们要充分地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还主张向群众学习,“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他在《反对党八股》中,引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1964年1月8日同吴冷西谈《人民日报》宣传问题时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他在学生时期苦读韩愈,严格训练古文,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在典籍中汲取养分。所以,毛泽东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说理与幽默相长,娓娓道来,入情入理。
与人民在一起,为人民书写,是毛泽东一生的情怀,也是他“做”文最具生命力所在。而要让人民接受你,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彻底解决“不熟”“不懂”和“大众化”。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谈到自己的心历过程,是“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他介绍了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伟人亦然;领袖风范是逐渐形成的,毛泽东亦然。这就是毛泽东的“中国气派”。
学习毛泽东“做”文之道,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转变作风,改进文风,大有裨益。
(作者系中共七台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责任编辑//郭存发guocunfa@fendouzazhhii..cc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