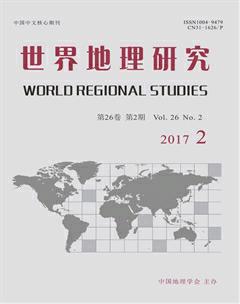威胁:地缘政治理论构建的前提与原始动力
熊琛然 武友德 彭邦文
摘 要:地缘政治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其命运就与国家的兴衰更替紧密相联。纵观西方部分地缘政治理论之构建过程,其构建的前提和原始动力都是理论构建者源于“他者”对于“自我”“威胁”的认知并经由理论构建者通过对“威胁”的历史和地理的分析而形成的政治结果。论文以“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和“大棋局论”4个地缘政治理论为研究样本,首先分析了威胁及其内涵和地缘政治中隐含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威胁与4个地缘政治理论构建关系,即:对美国海外扩张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英国海上霸权,使马汉意识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进而构建了“海权论”;英国霸权的最大威胁来自俄国在亚洲的扩张,使麦金德意识到陆上强国对心脏地带控制对英国霸权的威胁而构建了“陆权论”;斯皮克曼认为控制边缘地带的国家会对美国实力地位构成巨大威胁,进而形成了“边缘地带论”;布热津斯基为冷战后巅峰上的美国在未来可能的霸权衰落而面临来自欧亚大陆某一超级大国的威胁,为维护美国霸权而作以理论上的未雨绸缪构建了“大棋局论”。最后尝试探讨了当前中国崛起面临的外界威胁以及對构建基于外界威胁的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启示。
关键词:威胁;地缘政治理论构建;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大棋局论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作为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科学,地理学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就一直是影响国家重大发展策略的基础学科之一,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欧洲和北美国家兴起并参与到帝国主义霸权争夺、全球性殖民行为实践中的地缘政治理论[1]。西方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主张介入国家对外战略的现实事务而与国家的兴衰更替紧密相联。
纵观世界历史,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一不受地缘政治法则的支配[2]。在19世纪末和几乎整个20世纪里,部分西方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因其在部分大国、强国崛起以及对外地缘战略筹划实践当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对现代国际政治的演进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影响[3]。这些地缘政治理论包括:1)马汉(Alfred T. Mahan)提出的“海权论”,将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置于重要地位,特别是对全球海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的通道、海峡的控制对一国历史的重要性[4]。2)麦金德(Halford Machinder)“心脏地带论”,强调控制“心脏地带”是控制“世界岛”、进而控制整个世界的基础和前提[5]。3)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的“边缘地带论”,认为控制“边缘地带”是控制整个世界和保持美国实力地位的关键[6]。4)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提出“大棋局论”,其思想核心是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够控制全球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7]。
这些地缘政治理论虽然在表现形式和研究内容上存在差异,但都是指导当时国家崛起或维护国家霸权的全球地缘大战略[8]。直到今天,这些理论对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地缘政治实践”(practical geopolitics)指导作用仍然明显。美、俄、欧三方围绕乌克兰危机上演的地缘政治“演义”[9],俄罗斯主导欧亚经济联盟整合后苏联空间[10],克里“5+1机制”启动美国中亚战略第五阶段[11],安倍遍访中亚,欲“有所作为”[12],中国“西进”战略与中美俄中亚博弈[13],印度布局海洋强国战略[14],美日印澳积极构建海陆型“印太”地缘战略弧形带[15]和“印太安全体系”,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战略,美国强推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构建欧亚安全体系[16],各主要地缘政治行为体抢滩登陆,占领制高点,现实仍在延续“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大棋局论”的历史地理规律。
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经邦济世之学[17],对国家发展、民族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中国虽然具有源远流长地缘政治思想,但并没有构建起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地缘政治理论。21世纪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却被一些西方大国视为对其世界领导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巨大威胁而遭到极力阻遏。在中国和平崛起、国家发展、民族发展亟需地缘政治理论支撑之时,中国地理学者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积极研究和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的地理政治理论[2,8,17-22]。
社会需求是科学进步的不竭动力,任何一门学科的生长、发育与发展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支撑,而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17,23]。纵观西方地缘政治发展史,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认为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源于“他者”对于“自我”的“威胁”这一“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换句话说,地缘政治理论构建的前提和原始动力是源于“他者”对于“自我”的“威胁”在一定历史、地理、政治及社会环境下经由地缘政治理论构建者所构建的政治结果。基于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本文拟主要对“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和“大棋局论”四个地缘政治理论之构建进行解读。
1 威胁与地缘政治
1.1 威胁及其内涵
威胁,即对危险的知觉,是国际危机的核心概念之一,其作为一种现实存在自古有之,而且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威胁也演变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实际上,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威胁是人为建构的,正如坎贝尔(Campbell)曾说:“危险不是一种客观条件,对那些可能变成一种威胁的人来说,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危险是一种解释出来的效果”[24]。今天,全球化带来的扁平世界虽然深化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但并没有使冲突变得难以想象、使合作成为必然。而越来越清晰的是大国在维护和寻求地缘利益时彼此碰撞、相互威胁、建构威胁,围堵与反围堵已成为守成国与崛起国地缘博弈常态。人类自己正在编织一张可怕的威胁网,并使自己成为这张可怕威胁网下的囚徒。
威胁这一概念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一个行为体通过语言或行动向另一个行为体发出威胁,对其施加制裁;第二层含义是指一种消极的被动感受,源于以往的经历、内在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利益需求所感受到的威胁,是对本国即将遭受的损害的预料[25]。本文中涉及的威胁是指第二层含义,即国家地缘体对于来自“他者”的威胁的感知和认知。而对威胁的感知既可以是“实际的”,即或多或少地从确定的信号中推断而来;也可以是“潜在的”,即通过一国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或对手的能力来判断[25]。当威胁不被感知时,即使面对明显的客观证据,国家地缘体也几乎不会动用其防御性的资源;反之,当威胁被感知时,即使被假设的对手并无恶意,国家地缘体也会采取相应的反威胁措施予以应对[26]。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最早对威胁进行较为系统探讨的是戴维·辛格(David Singer)。他认为,威胁源于某种军事敌对情势,敌对双方都会视对方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这种对威胁的认知是由被估计的能力和意图决定的,即“威胁=被估计的能力X被估计的意图”[27]。换言之,威脅是由客观上存在的被估计的力量和主观上存在的被估计的意图共同构成的。这种被估计的力量和意图移植到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想象上就主观臆造为多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
1.2 地缘政治中隐含的威胁
地缘政治在其创造者—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创造时就隐含了来自于“他者”对于“自我”的威胁感知。19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显著恶化使契伦深为忧虑,并表露出对自己的小国在一个大国主宰的世界中未来命运的担忧。他认为欧洲强国正在走向一场无法避免的残酷的战争,瑞典作为小国,不可能阻止灾难的发生或防止这一后果的出现。他从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思想中受到启发,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威胁的实质。契伦这种新的关于国家及其行为的思想和理论方法,强调地理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就是地缘政治,并将其定义为“国家作为空间范围的科学或国家作为空间的一个地理有机体或现象的理论”[28]。契伦从他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家是维持秩序和防止混乱的唯一真正保障,是领土组织的基本单位,其安全是第一位的,国家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人”,而正是国家观念的冲突成了“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的根源。自地缘政治被创造出来后,与契伦同时期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在研究地缘政治时都隐含着来自于“他者”的威胁要素。
在此之前,金字塔式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念已经根植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中。金字塔顶端是欧洲人和刚升上来的美国人,最低端是其他大陆的“未开化的”土著,欧洲被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他大陆被视为黑暗的和“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西方社会被视为“文明的”、“自由的”、“优越的”和“安全的”,处于地缘政治的卓越地位;而广大非西方社会则被视为“落后的”、“野蛮的”、“专制的”和“可怕的”,是西方文明的“敌人”和“威胁”,地缘政治地位被刻意贬低和极端敌视[29]。然而,一旦非西方国家的兴起或崛起,则被视为是毁灭西方文明的潜在力量,甚至是“威胁世界自由和挑战西方地缘政治卓越地位的黄祸(Yellow peril)”[30]。
2 威胁与地缘政治理论构建
地缘政治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家所处的国际局势的背景进行研究,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是地缘政治的最终目标和辩白[31]。地缘政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到形成,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构建起了多种学说和理论。“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和“大棋局论”等已经成为公认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在指导国家崛起或维护国家霸权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每一个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都是当时国家和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要理解地缘政治理论构建就必须审视理论诞生时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地缘威胁。
2.1 威胁与海权论的构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海权霸主英国。美国的崛起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到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1%;而它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则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在对外投资方面更是远远落后于英、法、德三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声称:“至少有1/3的机械和农产品超过我们的需求,我们必须输出这些产品,或者驱逐生产这些产品的人[32]。”因此,改变这种经济实力与其国际地位极不相称的状况,就成为19世纪末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马汉详细考察英国在17、18世纪同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争夺霸权的多次重大海战后指出,英国的繁荣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那时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建立了地球上一流的和最强大的海军[32](表1)。当时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控制着大西洋东北部和英吉利海峡,沉重地打击了荷兰海外航运业和世界贸易;控制着连接大西洋与地中海的咽喉——直布罗陀海峡,使法国海军力量难以集中。马汉认为,美国要实现全球大国目标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尤其是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逐渐意识到急需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甚至成为英国接替者的可能。但此时的美国海军仅是一支由142艘过时的木质结构船只组成的舰队,没有一艘铁甲舰,其中较大的适于远航的只有12艘,且都已服役多年。而英国的帆船、轮船和运载力合计占世界船舶航运能力比重几乎都接近1/3(表2),美国海军实力远远落后于英国,暗指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英国。
为了保护美国的海外利益、运输安全和在国际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海军以对抗来自海权霸主英国的海上威胁。由此,马汉于1890年在其代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结合史实阐述了影响和制约国家建立和发展一支强大海军力量的条件并提出了海权概念[4]。在海权论思想指导下,美国国会通过《海军法案》大规模复兴海军,到1900年美国海军实力飙升到仅次于英、法两国的世界第3位。从19世纪末起,通过对英“战争威慑”,与英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共治”和战略上互信,美国逐步化解了来自英国的威胁,“二战”结束后完成了美英霸权转移并一跃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冷战后,美国宣布控制全球16个海上重要战略通道,海外军事基地遍布全球[33]。
2.2 威胁与陆权论的构建
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问世时,大英帝国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自拿破仑战争的失败导致英、俄势力上升,并获得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后,大英帝国的“恐俄症”就日益增强。随着跨欧亚大陆铁路时代的到来,麦金德视欧亚大陆国家的崛起为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到19世纪晚期,强大的大英帝国和俄帝国成为两极,英国依仗海洋、俄国凭借陆地逐渐将它们的触角伸向全球,它们成为争夺世界“不动产”的主要对手[28]。英国认为,只有那些通过陆路攻击英国殖民地的强国才会对帝国绝对的海上霸主地位构成真正的威胁。然而,这种假设到19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事实。1873年,俄国人控制了中亚最后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可汗政权卡瓦;到1884年,俄国人牢牢地控制了阿富汗的边境地区;1891年,俄国人开始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声称满洲(中国东北)是他们的特殊势力范围[34]。英国人担心,这些铁路网能为强大的俄军提供补给,使它容易在较近的距离对印度发动进攻和威胁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麦金德对历史的地理阐述充满着后哥伦布纪元海上强国已处于守势的基调,以及对于陆上强国俄国在亚洲扩张严重威胁到大英帝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担忧与恐惧。麦金德“陆权论”的构建所关注的就是海上霸权好像不再能保证世界霸主地位的时候,如何去捍卫英帝国政治、商业及工业优势地位。
2.3 威胁与边缘地带论的构建
边缘地带论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于1944年在其发表的《和平地理学》一书中提出的。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都因远离美国本土而使得美国成为世界大战的最大赢家。“二战”结束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开启了称霸世界的序幕。斯皮克曼指出,“对地缘政治的认知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现代国家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要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他们的实力地位。因此,凡是健全的地缘政治分析,都是以反映有关的一国或几国在地球上位置的世界地图为基础的”[6]。斯皮克曼通过对美国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国际格局的预测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分析,指出真正威脅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是欲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从而构建了边缘地带论。
斯皮克曼认为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带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带的强国[6]。这也印证了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俄国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所领导的边缘地带的侵略国家。而美国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目的就是不使边缘地带落入单一的强国之手,以保证美国的实力地位不受威胁。
斯皮克曼构建边缘地带论的另一个前提和动力是预测二战即将结束、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即将取代英帝国和俄帝国的位置,苏联将成为美国在西方世界核心区新的威胁。他站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角度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提醒美国注意苏联这个枢纽地带强国向边缘地带的扩张。苏联在边缘地带的扩张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与当年英国受到来自俄国领土扩张的历史威胁情况相同,美国极有必要与苏联争夺边缘地带甚至需要控制边缘地带以封锁苏联进入大洋的通道。此外,在远东要注意中国“霸权势力”的出现。斯皮克曼修正了麦金德的观点并指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是世界上最具权力潜质的中心,构建了与“陆权论”齐名的“边缘地带论”。其地缘政治公式是:“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6]。“二战”后,这一地缘政治思想成为美国围堵、遏制苏联、中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工具。
2.4 威胁与大棋局论的构建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大棋局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大棋局》一书中预计到21世纪上半叶美国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在此之前,美国需要未雨绸缪,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此,美国必须防止另一个威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的出现,和任何一种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7]。
纵观国际政治历史,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的中心。维护美国的首要地位,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应有目的地管理在地缘战略方面有活力的国家,并审慎地对待能够引起地缘政治变化的国家,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即在近期保持美国独特的全球力量,将来逐步把这种力量转化为机制化的全球合作,使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而对美国地位构成威胁的是欧亚大陆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即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的国家,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有多变的潜力和/或倾向。能与美国在欧亚大陆棋盘上对弈的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包括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美国尤其视俄罗斯和中国为其首要地位潜在的挑战者和威胁国。布热津斯基是在冷战后为巅峰上的美国在未来可能面临来自欧亚大陆某一大国崛起的威胁构建了大棋局论,其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世界领导地位[35]。
2.5 对地缘政治理论构建总结
在鲁道夫·契伦创造“地缘政治”时就预含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和“大棋局论”四个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都是构建者源于对“他者”对于“自我”威胁的历史和地理的认识和预测而形成的政治结果,目的是服务国家崛起或维护霸权地位和既得利益(表3)。从19世纪后期起,美国海外扩张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英国强大的海上霸权,使马汉注意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进而将海权强国提到极为显赫的历史位置而构建了“海权论”。俄国在亚洲扩张严重威胁到英国霸权地位,使麦金德意识到心脏地带的重要,将陆权强国和心脏地带提到极为显赫的地位,进而形成“陆权论”。对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地理记忆分析与前瞻,使斯皮克曼意识到控制边缘地带的国家是威胁美国实力地位的“祸源”,进而将边缘地带提到显赫位置产生了“边缘地带论”。同样,冷战后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和世界领导地位可能会因某一欧亚大陆国家的崛起而受到巨大的威胁,使布热津斯基意识到控制欧亚大陆是维护美国首要地位的主要基础,从而提出维护美国首要地位的“大棋局论”。
3 对构建基于外界威胁的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启示
威胁是地缘政治理论构建的前提和原始动力,西方部分大国在崛起或维护霸权过程中都面临了不同程度的威胁。这也使得某些地理学家或战略学家从国家利益出发基于威胁构建了地缘政治理论,又用地缘政治理论来指导地缘战略规划以求化解国家崛起或维护霸权过程中面临的威胁。中国和平崛起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而西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构建的历史地理规律对于构建基于外界威胁的中国地缘政治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1 中国崛起面临的外界威胁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会给全球地缘环境和地缘格局带来影响[36]。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大变革过程。历史地看,中国崛起属于第二代崛起国,因处于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崛起时的不同地缘环境,又与西方国家迥异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崛起过程不仅会引起守成大国的恐惧与敌视,而且面临着来自守成大国的重重围堵、遏制与封锁(图1)。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不断上升,特别是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国际权力结构“金字塔”中的“生态位序”,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西方强权势力直接把中国想象为挑战和改变现行国际体系的“威胁性的他者”,甚至还将中国崛起等同于“中国威胁”而主观臆造出多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导致中国崛起的地缘环境异常复杂多变。当前,中国崛起面临的首要外界羁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维护与拓展,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有效遏制境外企图分裂西藏和新疆势力的渗透、如何妥善解决台海问题、东海与南海的领土与领海争端问题等有形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如何化解因中国崛起而面临外来的“中国威胁论”这一无形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冲突、以及如何有效应对“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强权势力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37]。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则指出:在冷战时代,苏联这一“自由世界”的敌人的存在有助于强化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身份,而敌人的消失则会使这一身份的磁力随之消失;而中国崛起则在后冷战时期填补了苏联解体导致的“自由世界”敌人“缺失”的空白[38]。
3.2 對构建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启示
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互为对偶,大国崛起愈猛烈,面临的外部压力就会愈强烈[39]。当前中国的战略思维已经从韬光养晦的“周边防卫”逐步过渡到奋发有为的“要点突破”;从消极被动的“拒止战略”逐步过渡到积极主动的“前沿威慑”;从“安全搭车与消费者”逐步过渡到“安全驾车与供给者”,迈入“奋发有为”和“如何作为”的战略新纪元[40]。同时,中国面临的地缘安全环境也比以往更为复杂。在这种背景下,探索构建基于外界威胁的中国地缘政治理论,就必须要突破西方地缘政治学100年来发展所形成的理论“正统”、思维定式和思想垄断。因此,中国探索构建基于外界威胁的地缘政治理论不仅要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对抗性思维,而且要反映地缘政治当代精神,服务于中国和平崛起大局。评判中国构建基于外界威胁的地缘政治理论的根本依据是是否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崛起的根本战略目标的实现,具体体现在是否有利于规避和消弭“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以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否有利于构建基于战略互信而形成的区域合作安全?是否有利于降低中国崛起的体系结构性压力?是否有利于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对程度?
因此,当中国和平崛起亟需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支撑之际,中国学者应紧跟时代的步伐,高度关注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准确把握国家利益之所在,抓住机遇做出贡献[2]。对此,中国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与思考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苏浩提出“地缘重心论”,主张各个地缘重心国之间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合作, 建构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 维持人类的长久和平与繁荣[41];潘忠岐提出综合、多层次、由近及远的地缘学理论[42];倪世雄等提出和谐世界的“新地缘政治”[43];胡志丁通过对中国周边地缘环境解析提出“地缘周边论”[44];刘江永基于“一带一路”理念提出可持续安全的“海陆合和论”[45]。这说明中国学者已经在尝试打破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统治地位,突破地缘政治理论研究中唯“海权论”、“陆权论”和“陆缘论”等经典地缘政治理论马首是瞻的思维定式。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地缘政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新地缘政治应运而生”[46],这为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发展地缘政治理论提供了难得的“理论试验场”。面向未来,中国学者在构建基于外界威胁的中国地缘政治理论时,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1) 中国地缘政治理论需要建立在正确理解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思想文本基础之上。这里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主要是指“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和“大棋局论”,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探讨地理因素对一国外交政策的机遇和挑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中国的地理因素特征是海陆兼备,并正在快速步入海陆复合型地缘经济政治崛起大国,其机遇是中国的战略谋划方向既可以是“西进”和“东出”,又可以是“固北”和“拓南”,其挑战是西部陆疆“弥散式”跨国恐怖主义、“潜在式”藏独与疆独势力和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问题在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之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东部的东海、南海问题“波涛不断”。因此,如何有效化解这些威胁,找准战略突围的地理方向,是在构建中国地缘政治理论时亟需应对的重大问题之一。这也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把握了中国的地理因素特征,为中国地缘经济政治战略指明了方向,也为构建中国的地缘政治理论提供了“试验场”。
2) 中国地缘政治理论需要建立在正确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地缘政治实践”基础之上。“地缘政治实践”是指地缘政治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地缘政治决定、行动或战略政策。自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根据其地缘影响力提升和全球地缘环境变革的新形势提出了一些新主张,如亚洲新安全观、“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大国关系等,主动谋划中国和平崛起与发展的新地缘。“他者”的“地缘政治实践”主要表现在部分西方强权势力应对因中国崛起引起的国际秩序结构性变化而对中国施加的地缘压力。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因其在地理空间上穿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而拥抱“世界岛”,引起了以美国为首要的强权势力的疑虑和担忧。不论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日本极力构筑的“大小双菱形包围圈”,其地缘政治实践的目的都是“规则制华”、“战略遏华”。这种地缘政治实践的主体间性需要中国在探索构建地缘政治理论时既要明确“自我”的地缘政治实践,又要清晰地判断“他者”的地缘政治实践目的。
3) 中国地缘政治理论需要建立在正确理解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历史社会性基础之上。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巨变,一些地缘政治学者从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以“国家中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特征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结合现实发展提出的地缘政治学的一个新分支[47],主张要改变过去偏重客观因素,强调主观因素中的文化差异、政治认同、民族性、价值取向、伦理判断等在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作用[48]。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过于偏重控制某一地理区位对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与后果以及地缘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忽视了社会结构中的人地关系而暴露出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上的不可行性的“理论悖论”[49],也反映在美国“遏制”战略对苏联和中国所产生的不同的主体间作用。地缘政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结构中的人地关系,也可以说是批判地缘政治学强调的主观因素。因此,加强对批判地缘政治学研究对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总之,加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研究,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民族发展的需要,还要明确未来主要研究方向[2,17]。面向未来,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首先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其次要回答‘我们在哪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第三则要回答‘我们和谁在一起,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最后则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提出‘21世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规划,回答‘我们要干什么的问题”[50],为实现中国梦、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Gearóid ó Tuathail,Simon Dalby,Paul Routledge. The Geopolitics Reade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p8,p18.
[2] 陆大道,杜德斌. 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J]. 地理学报,2013,68(6):723-727.
[3] 葛汉文. “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战略的新精神[J]. 热带地理,2015,35(5):609-613.
[4]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M].安常容,成忠勤,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78.
[5]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著. 历史的地理枢纽[M].林尔蔚,陈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60-61.
[6] [美]斯皮克曼,著.和平地理学[M].刘愈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0-21,76,78.
[7]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译序,52-53.
[8] 胡志丁,骆华松,葛岳静.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研究视角及其对发展中国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启示[J]. 热带地理,2014,
34(2):184-190.
[9] 康晓. 乌克兰危机与大国地缘战略新态势[J]. 国际展望,2015(2):50-67+147-148.
[10] 杨辉,毕洪业. 普京对后苏联空间的整合及前景——以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为例[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4):33-43.
[11] 李雪. 克里“5+1机制”启动美国中亚战略第五阶段[EB/OL]. http://gb.cri.cn/42071/2015/11/10/8211s5161094.htm.
[12] 常思纯. 安倍遍访中亚,欲“有所作为”[J]. 世界知识,2015(22):24-25.
[13] 高飞. 中国的“西进”战略与中美俄中亚博弈[J]. 外交评论,2013(5):39-50.
[14] 李家胜. 印度海洋战略成效评估[J]. 太平洋学报,2016(4):62-72.
[15] 赵青海. “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J]. 现代国际关系,2013(7):14-22.
[16] 李海东. 美国与欧亚安全制度的构建——北约东扩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比[J]. 美国研究,2013(2):9-28.
[17] 杜德斌,段德忠,刘承良,等. 1990年以来中国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J]. 地理研究,2015,34(2):199-212.
[18] 于国政. 关于建立地缘学新学科的构想[J]. 世界地理研究,2005,14(2): 106-112.
[19] 于国政,樊华. 地缘地理学学科构建探析[J]. 世界地理研究,2009,18(3): 146-153.
[20] 毛汉英.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和对策[J]. 地理科学进展,2014,33(3):289-302.
[21] 李同昇,龙冬平. 中亚国家地缘位置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J]. 地理科学进展,2014,33(3):303-314.
[22] 胡志丁,陆大道. 基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经典地缘政治理论[J]. 地理学报,2015,70(6):851-863.
[23] 马克思,恩格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2.
[24] [英/美]威廉·A. 卡拉汉. 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中国威胁论”:建构认同的一种手段[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1):35-41.
[25] 夏厦. 从威胁认知視角解析伊朗核危机[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2):52-60.
[26] 朱翠萍. 感知威脅—建构威胁与美印海洋战略延伸[J]. 南亚研究,2013(2):1-15.
[27] David Singer. Threat-perception and the armament-tension dilemma[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2(1):90-105.
[28] [英]杰弗里·帕克,著.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M]. 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4,127.
[29] 葛汉文. 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J]. 国际观察,2010(4):42-48.
[30] Robert D. Kaplan. 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 How far will China reach Land and at Sea?. Foreign Affairs,2010,89(3):22-41.
[31] [英]杰弗里·帕克,著.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 李亦鸣,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2.
[32] 丁则民,等,著. 美国通史—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34,339.
[33] 杜德斌,马亚华,范斐,等. 中国海上通道安全及保障思路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2015,24(2):1-10.
[34] [英]P.J.马歇尔,著. 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M]. 樊新志,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46-47.
[35] [美]亨利·基辛格,著. 美国的全球战略[M]. 胡利平,凌建平,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1.
[36] 巩茗霏. 中国崛起的周边地缘环境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7):29-33.
[37] 陆大道. 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念与全球战略[J]. 地理科学,2016,36(4):483-490.
[38] 孔祥永. “他者”想象与美国的焦虑[J]. 美国研究,2015(4):69-88.
[39] 杜德斌,马亚华. 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2012,21(1):1-16.
[40] 姜鹏.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J]. 东北亚论坛,2016(2):23-36.
[41] 苏浩. 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J]. 现代国际关系,2004(4):54-61.
[42] 潘忠岐. 地缘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一种分析框架[J]. 国际政治研究,2008(2):21-39.
[43] 倪世雄,潜旭明. 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世界[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5):123-130.
[44] 胡志丁.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解析[D].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
[45] 刘江永. 海陆和合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J]. 国际安全研究,2015(5):3-21.
[46] 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37.
[47] 许勤华. 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15-21.
[48] Gearoid O Tuathail, Simon Dalby. Rethinking Geopolitics[M].London; Routledge,1998:P5-6.
[49] 张文木. “麦金德悖论”与英美霸权的衰落——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5):1-15.
[50] 王志军,张耀文. 西方地缘战略理论批判与中国地缘战略理论构建[J]. 学术探索,2015(2):27-34.
Threat: Hypothetic prerequisite and driving force on geopolitical theories construction
XIONG Chen-ran1, WU You-de2,3, PENG Bang-wen4
(1.College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2. Yunna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3.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Frontier Developmen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in Southwestern China, Kunming 650500, China; 4.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irthday of geopolitical theory, its destiny has been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big powers. From a general survey on some western geopolitical theories, thei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 and driving force are derived from threat, which resulted from theory builders perception and based on the historic and geographic analysis of threat. This paper takes the Sea Power theory, the Land Power theory, the Rimland theory and the Grand Chessboard theory as samples. Firstl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concept of threat and threat in geopolitics. And then,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at and geopolitical theories construction. Faced the greatest threat of the UK marine supremacy, which made Alfred Mahan to recognize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and further to construct the Sea Power theory. The greatest threat on the UK marine supremacy comes from Russian expansion in Asia, making Halford Machinder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Heartland for maintaining the UK marine supremacy. It is Russian threat that made it certain for Halford Machinder to construct the Land power theory to the UK. Nicholas John Spykman thought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USA to control the Rimland, the greatest threat on USA supremacy is the big powers controlling Rimland, making Nicholas John Spykman to invent Rimland theory.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the sole and last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But, Brzezinski predicted that USA may be declined as a world superpower or the other superpower will emerge to threat USA supremacy in the Eurasia some day. To maintain American supremacy, Brzezinski constructed the Grand Chessboard theory. Lastly, the paper analysed outside threats to China rise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geopolitical theory.
Key words: threat; geopolitical theory; sea power theory; land power theory; Rimland theory; grand chessboard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