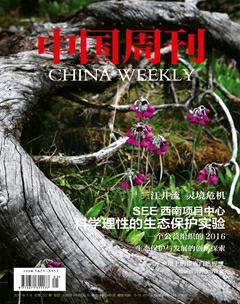大地上的行吟歌者读苗秀侠《农民的眼睛》《皖北大地》
张晓东
在阅读苗秀侠的两部长篇小说《农民的眼睛》《皖北大地》过程中,我的脑袋里闪现过沈从文、张爱玲、萧红、余华、阿莱、哈耶克、毕飞宇、米兰·昆德拉的影子,还不期然地记起过《论语》及一些西方大哲们的哲学论断,我的这些无意识的连缀或许向我昭示了苗秀侠作品的某些品质。她不是在模仿,而是在回应一些伟大传统的召唤。可以说,苗秀侠是位有情怀的作家,在艺术表现力上也已有相当积累,她毫无疑问地已在中国优秀作家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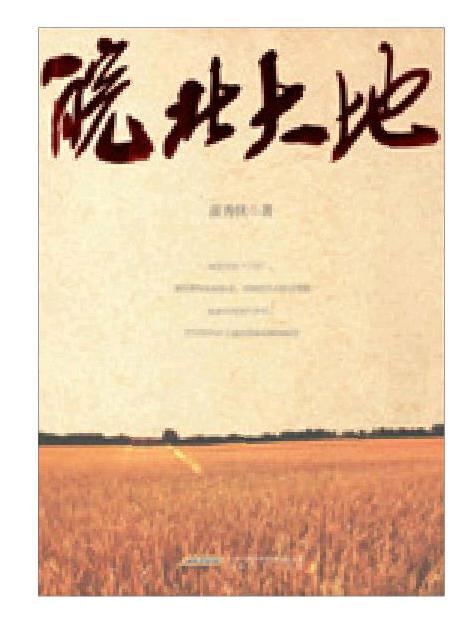
苗秀侠从来不在写作中着意炫技,她的写法一直“很老套”。她的这两部近作则从标题开始就让我眼睛一亮。《农民的眼睛》就像苍鹰的“复眼”,很有巴赫金所言的“复调”意味,却又声色不露:农民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又是小说的讲述者;农民的眼睛是乡村医生“农民”的眼睛,又是天下蒼生“农民的眼睛”,还是躲在后面的苗秀侠那一双深情忧伤的眼睛。《皖北大地》也很好,莽莽苍苍,悲壮苍凉。扉页上的题词:“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却永远长存。”直接衔接《论语》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言虽尽于此,意却在言外。苗秀侠懂得让小说自己说话、让人性说话、让生活的必然性说话。两部作品的命名,已足可看出作家的匠心独运。
苗秀侠近年小说还成熟于对叙事艺术的理解。两部作品的结构一个单纯,一个稍繁复。《农民的眼睛》,叙事人农民讲述了一串故事,一线到底的“糖葫芦结构”;《皖北大地》多线结构,以大农庄、安大营、小龙河湾的农瓦房、安玉枫、老尾巴为主线,用人物的离去、归来结构全篇,在每一个主要人物的背后牵扯出一个个广阔的世界,纵深立体,展现了比《农民的眼睛》更广阔的社会图景。而在真正支撑小说的人物塑造方面,两部作品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农民的眼睛》刻画的是当代农民的群像,《皖北大地》里的人物要立体得多,农瓦房、安玉枫、老尾巴、杨二香、安云礼乃至一些着墨不多的如李文化都给人留下挥之不去的记忆。苗秀侠笔下的人物多面、变化、成长,再现了艺术的“过程性”力量。总之,我在苗秀侠近期的小说中看见了她的巨大进步,她已脱蛹化蝶。
读苗秀侠,我不期然会想起沈从文,想起,无他,乃因“乡下人”这个说辞。苗秀侠早已身居城市多年,是所谓文明世界里的白领精英,她的红尘人生也早已与城市融为一体,像一尾自游自在的鱼;然而,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生命或性灵深处,她实在还是个“乡下人”。而真正的写作,从来都是灵魂的呓语,苗秀侠眷恋乡土和所谓关怀三农的使命意识不过是自然而然的叠合罢了。表面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深里看是“生命的自然选择。”
2012年莫言在诺奖颁奖会上的发言《讲故事的人》同样适合苗秀侠。苗秀侠也是个沉迷讲故事的人,她陈述句式的小说标题就最鲜明不过地表达了这一点;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她已慢慢懂得了释放叙事自身的力量,她也懂得自己所要站立的边界和拿捏的分寸,“作者死了”的自觉意识让她从自己的文字世界中抽离,她把“现场”交给了“叙述人”或者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她懂得“整体性”对于作家来说是其终生追求的目标,对人的“完满性”的认知使她深深沉溺于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对真善美的渴望并没让她忽略对假恶丑的深度凝视。
《皖北大地》中最感染我的则是有关“人精”杨二香的篇章,特别是她和自己老公的前情往事,苗秀侠写得真情动人。还有农瓦房对土地的痴迷也感人至深。“他喜欢顺着树身看到树根,再目不转睛地盯着树根边的地,那些被树根牢牢扎实的地,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韵味。”“当老尾巴的几片青幽幽的麦子地,突兀地铺到农瓦房面前时,他的膝盖骨不由地一软,呼了一声‘我哩个娘呀,扑通把自己摁跪下了。”“那些麦棵支棱着返春前柔嫩的小芽,像从土里伸出的一只只小手,拽着农瓦房的衣襟子、裤脚子、袖筒子。”“农瓦房跪趴着身子,把鼻尖杵到麦根子上,闭起眼睛,陶醉地闻着,嘴里啧啧有声:‘你咋会有这么好的地,这么香的地,你咋弄的?农瓦房泣不成声,‘你这个老头子,你凭啥有这样好的地块,凭啥……”。
苗秀侠是在大地上行走的行吟歌者,她把中国乡村的斑斓和伤痛,融注文字里面,让文学的清音,缭绕于天地之间,撑开了逼仄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