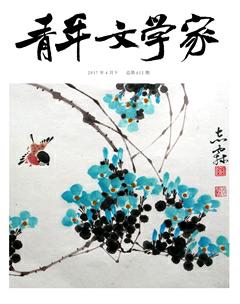曹文轩少年成长小说赏析
摘 要:从儿童文学的体裁来看,少年小说与成长小说的界定一直以来比较模糊,较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即成长小说表现的是少年的成长,二者不可断然分开。以少年成长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文学的世界中占据很大的比重。曹文轩的少年成长小说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面旗帜,成功摘取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桂冠无疑是其创作实力得到广泛认可的最有力的证明。本文通过对曹文轩少年成长小说的分析来发掘其作品的独到之处,寻找其中独特的魅力与价值所在。
關键词:曹文轩;成长小说
作者简介:迂卓(1992-),男,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文学硕士,渤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2-0-03
一、从自我封闭的空间走向开放的格局
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界力求摆脱“文革”以来长期形成的儿童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单一,说教色彩明显等消极因素,多次开展有关重建中国儿童文学的讨论会。“写什么”和“怎么写”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随后,一时间如潮涌般的儿童文学作品被儿童文学作家呈献于儿童读者的面前,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值得人们关注的现象是表现少年成长的成长小说在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曹文轩的代表作《草房子》出版于1997年,成为此时期少年成长小说的经典之作。令人担忧的是,当少年成长小说层出不穷涌现的同时,“一味追求童心童趣,忽视儿童内心深层次的心理渴求,总抱以俯视儿童而非仰视儿童的姿态进行儿童文学创作,儿童的学校生活几乎成为其生活的代名词”(班马语)。少年成长小说题材日益枯竭的问题日益显现,使得儿童文学作家很难突破原有的窠臼走向新的生发点,狭窄视野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不易于儿童读者的接受,反而给儿童带来的是枯燥乏味、千篇一律之感。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班马将此现象称之为“自我封闭系统”,并认为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已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中。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王泉根在《儿童文学教程》中提到,儿童文学最大的问题是儿童文学作家与儿童读者之间的关系,儿童文学作家的儿童观决定了儿童文学作品将以何种面貌呈现于儿童面前,也决定了儿童对作品的接受与否。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曾说:“儿童作家要蹲下身来,与小孩子们处在同一个平行视角上写作”。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读者接受层次这一常识性问题的忽略导致了中国的少年成长小说陷入到“封闭的自我空间”中去。
在儿童文学界有一条著名的黄金定律:什么年龄的孩子看什么书。由于对儿童的界定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儿童文学界将儿童划分成幼年、童年、少年这三大阶段,所谓“儿童文学的三大层次”由此得来。不可否认的是,杨红樱的上述观点是儿童文学界所提倡的,“低下身子和孩子说话”几乎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共识,但凡事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少年成长小说的阅读对象既然是少年读者,而儿童文学作家简单地将少年和幼年、童年笼统地归置到一起,忽视少年读者自身存在的特殊性,过分地追求童心童趣,这对于少年读者来说不免显得有些幼稚可笑。班马所指出的“忽视儿童内心深层次的心理渴求”可说是造成少年成长小说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曹文轩的少年成长小说取得的成功有很大一点在于其关注少年的特殊心理,使得其作品别开生面、意味深长。首先,儿童需要的是能够理解和认同自己的人群,站在成人立场上的父母与老师难以承担这个重任。正如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所说的那样,孩子的成长需要三种食品:营养食品、大脑的食品(知识)、爱和情感,其中爱和情感对少年而言是理解与同情。曹文轩的少年成长小说将故事的背景选择在广阔的乡村,学校的应试教育在这里被有意或无意的淡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展示少年成长的场所,同龄人之间的理解与同情给作品带来暖色调。例如:桑桑曾以恶作剧的方式当众捉弄过秃顶的陆鹤,并把其作为取笑的对象。在夜晚的池塘边看到因别人的嘲笑而哭泣的陆鹤以后,桑桑意识到自己以往犯下的过错,与陆鹤建立了平等的关系(《草房子》);梅玟告诉细米要尊重任何人,喊别人绰号是不礼貌的行为之后,细米口中以前经常提到的“三鼻涕”变成了彬彬有礼的朱金根(《细米》);为给病重的父亲筹集医药费而不得不捡垃圾的黑罐在明子的眼里“像一只拖着沉重木锨的老鼠”《山羊不吃天堂草》)。通过同龄人之间的善意行为向少年读者隐约的传递出诸如尊重、友爱、自尊等教育的启示,这恰好突破少年成长小说以往囿于“儿童的学校生活几乎成为其生活的代名词”的狭窄空间。其次,儿童的目光足够多的停留于同龄人的身上之后,潜藏于内心深处对异性不可名状的情感也在悄然萌芽。日本心理学家依田新指出:“当意识到异性美之时,人就得到了新生。”当桑桑得知温柔、安静的纸月的不幸身世后,不惜冒着同别人打架的危险,奋不顾身地保护纸月免遭别人的伤害,桑桑对纸月受到别人的欺侮进行有力地还击(《草房子》)。明子在看到双腿瘫痪的紫烟时,情不自禁地想为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给紫薇讲乡下有趣的故事,推着轮椅带紫烟去公园采芦花。不仅作品中的主人公明子对紫烟充满了同情,那支在风中“银光闪闪的芦花”也多少寄托着曹文轩对作品里主人公的怜悯之情(《山羊不吃天堂草》)。少年对异性的朦胧情感丝毫不掺杂性欲的成分,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颇符合少年对异性的复杂心理。除夕夜与梅玟在一张床上就寝的细米其行为不禁令人哑然失笑,担心梅玟看到他那瘦骨嶙峋的肋巴条,像老鼠似的飞快钻进被窝。梅玟回城后,那道被梅玟漆过的白栅栏比往日更干净、鲜亮,“泪水涌出时,他的眼中是一片纯洁的白色……”(《细米》)。曹文轩运用细致的笔法将少年面对异性时产生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恰如其分,丝毫无做作之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忍不住想看她几眼”,(《细米》)就已说明曹文轩在捕捉少年男女正常交往时心理变化所具有的深厚功力。最后,王泉根先生提出,儿童在人生的旅途中经历过两次断乳,一次是生理上的,另一次是心理上的。心理性断乳给少年带来的是“主我”(“作为知觉者的我”)与“客我”(“被知觉者的我”)的分化。按照王泉根先生在《儿童文学教程》中的说法,一方面,心理性断乳使“主我”与外界的联系上,产生“主我”与“他人”的分化,并由此产生自我认识。众所周知的儿童在13、14岁出现的叛逆心理就是由此产生。《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的明子在看到师傅三和尚怂恿黑罐盗窃工地上的木材时,他义无反顾地进行指责与揭露。《根鸟》中的根鸟为追寻自己的梦想,不顾父亲的再三劝阻,毅然决然地踏上寻梦的征程。另一方面,在“主我”和自身的关系上,经历了由“主我”向“客我”的转变,儿童前所未有的集中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关注自身的变化,客观的审视自我。人们常见的少年儿童开始注重衣着打扮、外貌整洁就是明显的例证。少年由“主我”向“客我”的变化在曹文轩笔下也有清晰地展示。桑桑在未遇到纸月以前是一个不注重自己外表的孩子,当仪表整洁、衣着干净的纸月出现在他的面前时,桑桑为自己的邋遢外表感到前所未有的惭愧,去河边洗澡的桑桑在不经意间透过清澈的水面第一次认真而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面庞时,他不自觉地惊呆了,怎么也不相信映在水面上的人影就是他自己,桑桑从这一刻起,当他以后出现在油麻地人们的面前时,已经俨然成为一个注重外表与形象的“小大人”(《草房子》)。
诚如上所述,曹文轩对少年心理的揭示使得其少年成长小说具有可贵的深度与广度,其作品中蕴含着一般儿童文学作家不可比拟的思想深度。
二、苦难是沟通少年成长的桥梁
曹文轩说过:“文学不是写粪便、小便与厕所,不是写令人恶心的东西,文学决不能成为單纯描写丑的存在。”苦难描写是曹文轩作品的一大特色,有研究者就儿童对于苦难是否具有接受能力而对曹文轩的苦难描写提出质疑。从儿童文学真实性的角度来看,颇具“成人化倾向”的少年不同于其他年龄段的儿童,他们怀着一颗好奇心渴求进入成人世界,迫切地希望了解现实的成人世界,对一切现实问题的回避乃落入儿童文学的“诈作”(鲁迅语)中去。但少年仍属于儿童,对呈现于少年眼前的真实要有所取舍,儿童文学的“真”要建立在坚持远离成人的恶俗游戏;暴力冲突;政治权力斗争;两性关系的价值尺度之上向儿童有所展示。曹文轩笔下的苦难多是疾病(桑桑患鼠疮)、残疾(青铜是哑巴;陆鹤是秃顶)、贫穷(明子和黑罐的家庭一贫如洗)、天灾(油麻地遭受蝗灾)等不幸事件,以儿童文学真实性的标准衡量是完全可被少年儿童接受的。桑桑、细米、根鸟、明子等少年主人公在面对现实苦难时展现出来的那份优游不迫、处变不惊的态度正是曹文轩传递给少年的一笔可贵财富,少年不仅仅需要身体上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健全与成熟。曹文轩让少年主人公在苦难得洗礼与净化中得到生命的升华,独自探寻生命存在的特殊意义。俄国美学家别林斯基曾指出少年“分裂时期”的概念:“幼年之后是青年时期,也就是向成年过渡的时期,这种过渡往往总是分裂、不调和,因而也是犯罪的时期。他必须经过千百次的迷误,必须对自己作斗争,所以也有蹉跌的时候。这一点无论对于个人,或是对于人类,都是一个确定不移的法则”。[1]在曹文轩的成长小说中,通过苦难领悟到人生及生命意义的少年主人公大致经历了由自我迷失向自我醒悟的转变,少年主人公的未来人生走向在读者面前初露端倪。具有正直、憨厚与乐观等品质的乡村少年明子在面对都市的灯红酒绿时,因自身的贫穷而多次产生莫名的耻辱感与自卑感,在他就要犯罪的一念之间,内心的激烈斗争使他想起那群因“不是自己的草就不肯吃”而饿死的高贵的山羊,他顿悟到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最后明子迎着“那时已是初夏的太阳”昂首向前走去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立而自尊的少年形象(《山羊不吃天堂草》);原本生活得无拘无束、自由快活的少年桑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让他产生对生命的彻悟,“虽然没死,但他觉得已死过一回”(《草房子》);在寻梦的旅途中路过青塔、鬼坡、莺店时的遭遇,让少年根鸟亲身体会到实现人生梦想的艰辛与不易(《根鸟》)。
曹文轩认为今天的人们似乎一头钻进享乐主义的圈子中去,完全忘记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种种痛苦与不幸。曹文轩赋予苦难以揭示人生意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别林斯基所说的“必须经过千百次的迷误,必须对自己作斗争,所以也有蹉跌的时候。”无论是桑桑、明子还是根鸟和细米,在疾病、贫穷等苦难面前也曾有过沮丧与灰心,甚至对自己坚守的信念产生过动摇,在经过自我斗争之后,对苦难,尤其是人生有了更透彻的了解。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曹文轩笔下少年主人公未来的人生走向,饱受苦难洗礼后的少年对今后的人生道路有着更坚定的方向。正是在对少年主人公未来人生走向的大致把握上,才使得曹文轩的少年成长小说由“自我封闭的空间”走向“线性开放的空间”(班马语)。
三、独特的语言构成人物形象
诗意的语言在曹文轩的作品中任意流淌,工笔式的遣词造句颇具匠心,色彩斑斓的词汇构成对自然景物的细致描摹,书面语的大量运用在保证作品文学性的同时,也为少年读者文学素养的提高起到很大的帮助。桑桑从木桥向河中跳跃的一瞬间,曹文轩就使用了“俯冲”、“遨游”、“滑翔”、“鸟瞰”等诸多文学性色彩的词语加以描绘,原本一场嬉戏玩闹仿佛成为一件庄严的大事。曹文轩将色彩斑斓的语言赋予到一株草、一朵花、一棵树的身上,植物成为具有鲜活生命力与情感的化身。曹文轩运用独到的语言塑造出诸多的人物形象也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干净柔美、温柔善良、落落大方的少女:“体面、白净而细嫩的皮肤”的紫薇、“浑身上下干干净净,略显苍白的面颊”的梅玟、“文弱、恬静、清纯而柔和”的纸月、“银铃般清脆的好嗓子,梳着一根又黑又长的辫子”的白雀。温文尔雅、朴素整洁、多才多艺是曹文轩所塑造的少女形象的特征。在作品里,这些少女的善良大方、善解人意在悄无声息之间深深影响到了少年主人公。
儒雅、谦恭并不失刚强的男人:谦恭有礼的桑乔、“头发被他很耐心地照料着,一年四季油亮亮的:分头,但无一丝油腔滑调感,无一丝‘小开的味道”的蒋一轮、身材修长,目光中有些忧郁,吹口琴的郁容晚。这些“透出一股挡不住的文气”的男人给人带来的是一副知识分子的儒雅形象。当洪水来临,桑乔面对乱哄哄的人群大吼一声“都给我安静的站好”时,我们眼前除了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男性形象外还看到的是一个有勇气承担责任与义务的伟岸而又刚强的男性形象。
高贵、安详且具有神性光环的老人:“拄着拐棍,一头银发”的秦大奶奶、“浑身上下穿得干干净净”的奶奶、“一双深深隐藏在长眉下的眼睛,目光透露出一股幽远与固执,还含了少许的冷漠”的板金。曹文轩笔下的老人在慈祥、倔强中透露出一种威严,威严中夹杂着高贵的气息,她们的周围笼罩着颇具神性的光环,受人尊敬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四、结语
曹文轩在基于对少年心理深度挖掘的基础上,将少年成长小说带到了广阔的天地里。苦难在曹文轩笔下成为展示生命美好的一面镜子,流动性的诗意语言塑造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令人难以忘怀,期待曹文轩未来在少年文学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注释:
[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参考文献:
[1]曹文轩.青铜葵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曹文轩.根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曹文轩.山羊不吃天堂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曹文轩.细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曹文轩.草房子[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6]王泉根.儿童文学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新视野[M].武汉: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