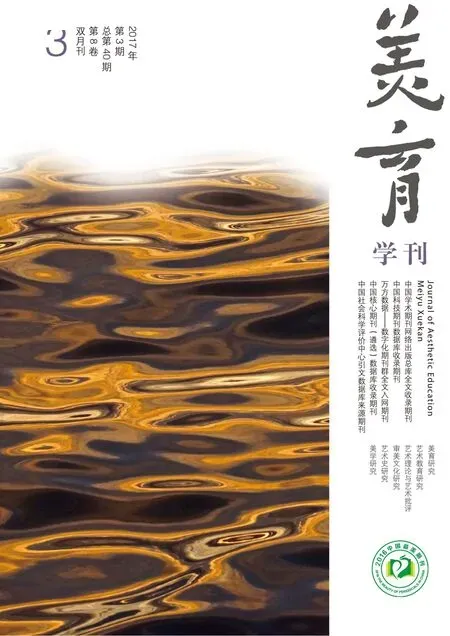清代英国人在华的植物采集与广州外销植物画
关晓辉
(华南农业大学 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清代英国人在华的植物采集与广州外销植物画
关晓辉
(华南农业大学 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清代外销植物画是在华的欧洲博物学家和中国画师合作的产物,它们显示了中国和欧洲、科学和艺术的两种不同视觉文化的互动关系。需要重点考察博物学家、植物收集、画师、外销植物画等几个方面的交集,揭示其中东西文化接触的细节,包括东西方植物交换,行商、外国名流和博物学家的交往,中西写实观念的差异等,并借此讨论视觉表现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
英国;植物采集;广州;外销植物画
广州外销植物画*广州是中国最早的(有80年时间是唯一的)通商口岸,也是清代时期西方人活动最多的地区。从18世纪中期开始,十三行一带就有众多的外销画坊,因此广州是外销画最集中的地区。而外销植物画几乎全部被运往国外,英国收藏的数量最多,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简称V&A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和林德里图书馆(Lindley Library)收藏了成千上万幅广州外销植物画。是18、19世纪在华的欧洲博物学家在收集植物的过程中,雇用当地画师描绘实物或标本的画作。由于博物学家收集到的植物经不起从中国到欧洲的远航,干燥的标本无法体现植物的颜色和形状,对博物学研究没有价值,因此雇佣当地画师写生或绘制标本是常见的事情。外销植物画是欧洲博物学家和中国画师共同合作的成果,在此意义上,范发迪(Fa-ti Fan)认为它显示了中国和欧洲、科学和艺术两种不同视觉文化的互动关系。[1]55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博物学家、植物收集、画师、外销植物画的交集之上,会发现很多中西文化接触的细节,其中包括东西方植物交换,行商、外国名流和博物学家的交往,中西写实观念的差异等。而把这些细节联系起来,将拼贴出一幅生动丰富的中西文化互动图像。
一、英国人采集中国植物的热潮和外销植物画的绘制
18世纪末法国耶稣会教士已经在中国收集大量的植物和种子,并运回国尝试进行移植。相比之下,英国人尽管在对华贸易方面占有优势,但在对华博物学研究方面却尴尬地落后于法国人之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人无法像耶稣会教士那样深入中国内地。为了打开外交和商贸新局面,英国政府先后在1792年和1816年派遣马戛尔尼(Macartney)和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领使团访华。两次出访成为英国人深入中国内地采集博物学标本的难得机会。[1]16
负责安排植物采集工作的是出身富豪阶层的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34—1820)。他是皇家学会会长、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的园长。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最积极提倡中国博物学研究的人士,竭力将中国植物引进英国。班克斯把植物采集员安插进访华使团,对他们作出两项指示:一旦遇到“有用、新奇或美观”的植物,就要抓住机会弄得;尽量获取“神秘的”中国园艺知识,将它们引介到英国。[1]19可惜的是,两次出使无论在外交还是博物学上都不成功,由于无法深入中国内地,博物学家和植物采集员只能在广州这个据点工作。
曾经有数位英国博物学家和植物采集员在广州工作,而在他们之中贡献最大的是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1774—1856)。他在中国的科学活动赢得英国博物学界极大的尊重,由此被推荐为动物学会和园艺学会的会员,还在1817年被选进皇家学会。里夫斯是一名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的茶叶监察员,在1812年来到广州洋行工作,此后二十几年一直在南部沿海城市活动。事实上,里夫斯对博物学有高度的热情,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把科学当作一种绅士活动,一种体面的爱好,而不是真正的职业。可以说,他是“业余博物学家”。
里夫斯在1816—1817年间回国,暂时留在伦敦。此时英国园艺协会邀请他将带回国的中国植物画建立一个藏品系列,并支付一定的费用。里夫斯开始着手整理从中国带回的水彩和素描植物画,共有138幅,现在藏于林德里图书馆。这批画作分为两类:一类是里夫斯指导画师绘制的,画在厚实的英国水彩纸上,纸张由沃特曼(Whatman)公司生产,尺寸为48*36厘米。比如说,一幅《七叶一枝花》(图1)的水彩画,上面有中国墨水写的中文植物名称,有明显的模仿西方水彩画的痕迹;另一类是购买的小画,画在半透明的宣纸上,如一幅描绘紫珠的画,没有中文名称,只有数字编号。

图1 七叶一枝花 佚名 林德里图书馆
与普通的风景和风俗外销画不同,植物画对画师的要求特别高。在一般情况下,外销画的画师是以流水作业方式作画的:有的专门画树,有的专门画海,有的专门画房屋,有的专门画人物……。因此很多画作显得呆板、生硬,匠气十足,被视为“行货”。而植物画非一般流水线画师能够胜任,它要求画师有精确的造型能力和较强的色彩表现能力,因此必须由一位画师单独完成。此外,植物画需要画师有西方博物图画的概念,但普通的中国画师没有接受过西方科学的训练,要他们遵守“科学式的精确”并不容易。由于职业习惯的影响,他们喜欢在作画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加入自己的想象。所以,里夫斯必须约束画师的想象力,使其符合博物学绘画的既定原则。有资料显示,里夫斯开始时让画师到自己的家里,以严苛的标准指导他们绘制植物画和动物画,等他们掌握了博物学的原则后才可以在自己的画坊里作画。[2]70
与其他外销画相同,植物画没有画师的署名。根据里夫斯1829年的一本笔记本记录,他经常雇用四位画师,名叫“阿库”(Akew)、“阿康”(Akam)、“阿昆”(Akut)、“阿升”(Asung),其报酬是按每幅和每天计算的。[2]72“A”或“Ah”的前缀是粤语发音,是对地位低下的人的称呼,由此推断,要找到关于他们的记载应该是不可能的。
二、花棣和行商花园中的奇花异草
在清代广州,洋人的活动范围很有限,博物学家和园艺师一般只能在洋行附近的花市和园林搜寻植物品种。在当时的广州花卉市场中,花棣是最多外国人光顾的。花棣是指现在的“花地”,位于广州市芳村的花地乡。而清代的花棣则不限于花地乡,还包括附近的茶滘、东滘、涌口等地。花棣在清末已经是大规模的花木培育基地和贸易市场。《番禺县志》有记载:“花棣在珠江南岸,距广州十里许,居人以栽花为业,士大夫名园亦在焉。”《岭南名胜记》也描述过,当时花棣已“有花园楼台数十,栽花木为业”。花棣有很多苗圃,栽培的花卉品种繁多,从晚清广东诗人梁修的《花棣百花诗》中可以找到佐证,“岭南名花有木棉、金步摇、蜀葵、紫荆、红豆等;岭外名花有梅、杏、牡丹、莲、茉莉、秋海棠、玉茗等;国外的名花也有近十种。”[3]如此丰富的花卉品种想必会让西方人流连忘返。纽约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在1825年来广州并居住过几年,他在《旧中国杂记》(1855)一书中回忆了在花棣度过的愉快一天:一位名叫“阿庆”的卖花商热情地向他介绍名花的品种和园艺知识,他在鞭炮声中结束一天的行程。[4]282
随着外国顾客的增多,花棣苗圃作出调整,培育迎合他们需求的品种,甚至设计出适合长途航运的花盆。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几幅外销植物画中描绘了带把手的花盆和吊篮,很明显为了方便长途运输。《流苏的蕨类植物》(图2)是其中一幅。画中植物被放在一个造型奇特的木盒中,目的是为了方便顾客随时提起并放在任何地方。尽管盆栽是中国园林的传统摆设,但古代花匠绝不会将植物放在木盒之中。当时的文人很反感商人为经济利益而破坏传统。比如李调元(1734—1803)在他的《南越笔记》就批评了广州花商把植物放在劣质的盛器中的做法。[5]

图2 流苏的蕨类植物 佚名 自然历史博物馆
除了花卉市场以外,行商园林是另一处欧洲人搜寻奇花异木的地方。由于行商在清末对外贸易中取得巨大财富,他们建造的豪华宅院均达到本地区的顶峰水平。行商家宅的园林更是精致华丽,园中种满新奇的观赏植物,令中西访客钦羡有加。例如,潘长耀花园结合了中式庭院和西式室内设计(图3),庭院建筑布置错落有致,别出心裁,园内有风满楼、醉月楼、门精舍、水明楼等。张维屏的《游惹枝湾》描述的正是它的景色:“游人指点潘园里,万绿丛中一阁尊。别有楼台堪远眺,叶家新筑小田园。”亨特曾经受潘长耀的邀请参观其豪宅,他在书中回忆自己见到的景观和植物:“露台上,小径旁、亭阁边陈列着成千成百的花卉树木,包括许多中国人最欣赏的花木,如菊花、山茶和盆栽矮树。还有外国人在商业苗圃中很少见到的奇花异木,比如特别优良的牡丹。牡丹是英国人最渴望的花木之一,广州很少有优质牡丹。莲塘中耸立着假山或嶙峋的岩石,水里养着鱼儿、睡莲和乌龟,小桥流水罗布其间。”[4]320

图3 托马斯·阿罗姆 潘长耀花园 版画 19世纪
行商很喜欢与西方人打交道,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友谊,他们经常在家宅的园林中设宴招待西方官员、商人和各个行业的人。英国博物学家和园艺师会借此机会在园中寻觅心仪的品种。像科尔在广州时,曾得到行商首领潘振承的邀请到潘家大院的花园参观,并挑选了一些百合和其他球根花卉。[6]1812年,里夫斯到广州上任,在短短几个月就参加过两三次潘有为为外国人举行的宴会,并在主人家的两三千盆优质菊花中寻宝。1821年约翰·波茨在到广州的第二天就被里夫斯带到潘有为花园,在接下来几天他们又造访了其他行商的花园。[2]56-58英国的第一棵紫藤是里夫斯从潘长耀花园中的一棵树上剪下来的。如今被林德里图书馆收藏的一幅外销画描绘的就是这株植物。画的名称为《丽泉行的紫藤》(Conseequa′s Wisteria)(图4),丽泉行正是潘长耀商行的名称。此画非常细致地描绘出单枝紫藤的形态特征:紫红色的像小甜豆大小的花朵茂密地蔓延下垂,花朵从上到下由大变小,构成很强的垂坠感;叶子分成红色和绿色两种,红色的叶子要小很多。此画所用的也是传统的西方水彩画技法。

图4 丽泉行的紫藤 佚名 林德里图书馆
三、宋代院体画与西方博物图画的融合
我们不妨以里夫斯的藏品为例,探讨外销植物画的艺术特征。笔者根据描绘对象的不同,将它们大致分为观赏植物和实用植物两类。描绘观赏植物的有《茉莉花》《玉兰》《金银花》《龙船花》《紫玉兰》《蔷薇》《条叶百合》《麝香百合》《渥丹》等。它们的统一特点是画尺幅小巧、取景单纯,绘画技法以双钩敷色为主,我们会发现这些特点与宋代的院体花鸟画十分接近。院体花鸟画有深远的渊源,它是在“对景写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赵昌画花“每朝晨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到了兴盛之时,画师们更将“摄集花形鸟态”的严谨态度发展到很高的境地。与院体花鸟画相比,外销植物画对“写生”的要求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连植物凋谢或树叶被侵蚀也毫不掩饰地描绘出来。如《茉莉花》(图5),画中花朵的线条纤细、秀逸,体现出花瓣娇嫩、轻盈的形态;勾勒枝叶的线条较为沉实,遒劲有力,准确表现出枝叶的造型和生长的方向。敷色方面,花朵的色彩清淡,使白色的花瓣被衬托出来,而枝叶的颜色厚重,其质感与花朵有明显区别。院体画中也有《茉莉花》(图6),画者是赵昌。与外销画相比,院体画有很明显的美化痕迹:花瓣的造型十分讲究,像飘荡的裙摆;枝叶的弧线变化夸张,大小、疏密变化也经过刻意的处理。相比之下,外销画的艺术处理就更少,更接近实物。我们再来看《玉簪》(图7),画师用淡淡的灰蓝色渲染出花瓣的轮廓,使白色的花瓣在白色的背景下突出,这是国画中常用的方法,适合衬托轻盈透明的对象。植物叶子的色彩厚重,层次清晰,所用的是水粉颜料,因为西方材料在表现立体感方面更有优势。此画采用了中西兼并的技法,画面呈现的却是宋代院体画的意蕴。

图5 茉莉花 佚名 V&A博物馆

图6 茉莉花 赵昌 12世纪
另一类是实用植物画,它们缺少文人气息,而更接近西方博物画。这类画包括《苹婆》《苏木》《蒲桃》《红花蕉》《甘蔗》《牛心番荔枝》《慈姑》《黄蓉花》《响盒子》等。实用植物的形态粗壮、旺盛,在传统的中国画家眼中显得俗气和张扬,缺乏“雅致”,一般情况下不会成为其作画的对象。《槟榔图》(图8)是典型的例子。画中左边是一棵槟榔树,它的细干、单干、顶枝生叶都显示出“典型”的槟榔树外形。画的下半部分是重点,有两组图像。左边是一串果实的放大图,果实呈椭圆形,长在一只刚刚折下的枝条上,枝条的顶端稍稍向下倾斜着。整个枝条显示出花朵和果实的分布,以及它们的成熟程度。右下角还有小图,描绘带核果实的剖面、花朵的部位。此画并列式的构图很明显是模仿了西方的博物画。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画师是在里夫斯的指导下完成的此画。从表面看它很像博物画,但画中细节却透露出其外销画的特征:用色大胆而鲜艳,线条坚实,甚至有点僵硬;笔触细腻,明暗过渡并不自然,画面显得过平。不妨想象,《槟榔图》的画者对博物画的规则和西洋画技巧并不精通,但他还是尽力完成客户的要求。事实上,外销画师是很优秀的视觉艺术工作者,他们努力地在不同文化、不同领域的交界区内穿行,并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就连班克斯这样的科学权威也赞扬他们:“中国人画的植物,包括画在家具上的,都是如此精确,毫不掩饰,植物学家完全能够看得出来画的是什么。”[1]63

图7 玉簪 佚名 林德里图书馆

图8 槟榔图 佚名 林德里图书馆
四、余 论
范发迪认为外销博物画是“文化遭遇的场所”,英国博物学家和中国画师“都是制造、传播混合文化产品的媒介。在外销博物画中,艺术、商贸和博物学汇集在一起。而且我们应该把这些画看作更广泛的文化接触的一个缩影,这些文化接触包括商品及货币的交换、爱好及思想的通融、人际关系的延伸以及帝国间的遭遇。”[1]71他提出的“文化遭遇”,是指当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中国传统的草木鸟兽虫鱼之学相遇时,显示出二者的不同并试图相互协调。外销画师的植物画成为中西文化遭遇的视觉见证,实际是他们被动接受西方科学和艺术的规范,无意为之的结果。而与他们不同的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蔡守和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则是自觉地、主动地学习西方科学和艺术,以启发国人的心智和改良中国传统艺术的技法。*蔡守(1879—1941)曾任《国粹画报》编辑,并在1907到1911年专辟“博物图画”专栏,前后共刊博物图画128幅,题材包括植物、动物、民俗和地理;高剑父(1879—1951)在1906年留学东瀛,曾到过东京的“名和靖昆虫研究所”,在那里临摹动植物的标本与图谱,又到过日本的帝国博物馆、帝室博物馆和帝国图书馆临摹动物、植物的标本和图谱。有关记述见程美宝《晚清国学大潮中的博物学知识——论〈国粹学报〉中的博物图画》,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蔡、高二人的实践或许可以被视为另一种“文化遭遇”的体现。同样是接受西学,外销画师在中国正统的绘画史中没有留下半点痕迹,而类似于蔡、高二人的画者则被冠以“改革者”的称号,这本身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1] FAN F T.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 MAGEE J. Chinese Art and the Reeves Collection [M]. London:Natural History Museum,2013.
[3] 闵定庆.节日狂欢氛围与花埭百花诗坛的共时性呈现——试论《花埭百花诗》的“狂欢化”写作[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4):71.
[4] 亨特.旧中国杂记[M].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5] 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6.
[6] 基尔帕特里克.异域盛放[M].俞蘅,译.广州: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193-195.
(责任编辑:刘 琴)
Collection of Plants by the British in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Selling of Paintings of Plants from Guangzhou
GUAN Xiao-hui
(College of Fine Arts,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Guangzhou 410642, China)
Paintings of plants sold in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are a product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European naturalists and Chinese painters which show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n cultural perspectiv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and between science and ar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naturalists, plant collection, painters and the selling of paintings of plants to reveal details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cluding the exchang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lants, communication between businessmen, foreign dignitaries and naturalists and differences in realism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discuss the role visual expression plays in Chinese-West exchange.
United Kingdom; plant collection; Guangzhou;the selling of paintings of plants
2017-03-12
关晓辉(1977—),男,广东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美术学博士,主要从事美术史学与理论研究。
J209
A
2095-0012(2017)03-006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