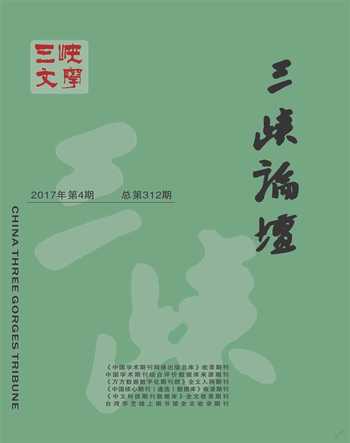《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著录校正
刘本才��
摘要: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首次对我国的石刻拓片进行大规模汇集整理,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历史文献。但作为鸿篇巨帙,百密一疏,难免会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文章以隋唐五代著录部分为校正对象,主要从著录碑刻标题问题、镌刻系年讹误、志盖错讹、撰书刻石者讹漏、误收伪刻、书体误判等方面做考察校正,以便此项文献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石刻文献;校正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7)04-0069-08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所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各类石刻兼收,以时代先后为序,上迄东周,下至民国,蒐集了近两万种拓片图录,分装101册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对石刻拓片进行的大规模汇集整理,亦是目前最大的一部通代拓本汇编,给学界提供了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宝贵素材,自出版以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全书除收录拓片图录外,编者还为每幅拓片撰写扼要说明,介绍其长宽高广、拓本真伪、流传存佚、刻石年代、出土地点、书体及撰文书丹刻石者等情况,这都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遗憾的是,因所收拓片众多,卷帙浩繁,整理过程中难免出现疏漏之处。
本文以《汇编》著录部分为校正对象,比勘石刻图版,同时又参考《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中研院史语所1984-1993年版)、《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版)、《隋代墓志铭汇考》(线装书局2007年版)等文献,借助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研制的《隋唐五代石刻语料库》,对隋唐五代所涉及的第9至36册著录部分进行校勘,订正其讹误之处。其著录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类:碑刻标题问题、镌刻系年讹误、志盖错讹、撰书刻石者讹漏、误收伪刻、书体误判。每条均列其页码或编号,以《汇编》卷次及页码排序,以便查检。笔者不揣淺陋,现就审读所及,试举例如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碑刻标题问题
金石学界一般以碑志首题作标题,更常见的是自拟标题,如墓志、造像记只书姓名,作“某某墓志”、“某某造像记”,妇人则称“某某妻某某墓志(造像记)”。不论何种拟定方式,都应以标题文字的正确为前提。《汇编》著录碑刻标题存在以下问题:误读首题或志文,造成碑刻标题讹误;未审志文及稽考文献材料,造成志主姓名缺字;照录碑刻原形字,没有进行对应转换等,兹罗列于下。
(一)误读首题或志文,造成碑刻标题讹误
1.第10册第87页《常德将墓志》,志文無首題,未提及志主姓氏,其志盖作“廗君之铭”,廗字作,即席字。《隋代墓志铭汇考》第4册第365页、《西安碑林全集》第1530页皆作“席德将”,无误。
2.第18册第93页《□士尉神柩记》,首题云“大周故中大夫使持节上柱国会州诸军事守会州刺史公士尉之神柩”,《千唐志斋藏志》431页、《唐代墓志汇编》万岁通天010与《全唐文补遗》2-231皆照录首题作为标题。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二〇考公士尉为万岁通天年间任会州刺史。又公士为爵位之一,如《居延汉简》509.7有“田卒淮阳郡长平东乐里公士尉充年卅,袭一领”。此处当姓公名士尉,应作《公士尉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7-85作《公士尉神柩记》,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作《会州刺史公士尉墓志》,极是。
3.第24册第45页《竹敬敬墓志》:“府君讳敬敬,字思敬,安喜郡河南人也。”“敬敬”当是“敬猷”之误。后一敬字,原刻作“”,分明是“猷”字,释“敬”为形近而讹,古书“猷”多训作“谋”,与其字中之“思”相对,古代“敬猷”常用作人名,而作“敬敬”者罕见,《魏书》卷六十二有《高敬猷传》;唐代有徐敬猷,又叫李敬猷,为李绩之孙。《千唐志斋藏志》767、《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10-142、《唐代墓志匯编》开元460、《全唐文补遗》2-516均收录该志,皆误作竹敬敬,当据此订正。
4.第26册第5页《刘娩妻高氏墓志》,据首题“大唐吏部□彭城刘君故妻高氏墓志铭并序”与志文“君讳娩,字温,渤海蓨人也。”可知著录者误将妻名当夫名,当定名为《刘君妻高娩墓志》。
5.第26册第30页《李混(荣王)第八女墓志》,志文云“夫星有七,北方曰婺女;岳有五,东方曰天孙。……婺女者,今上幼孙,荣王之第八女也。”婺女为星宿名,即女宿,又名须女、务女,言星宿以高其义、扬其名,或以为“婺女”为第八女之名。荣王名李滉,两《唐书》有传,原名李嗣玄,唐玄宗第六子。开元十二年,改名李滉,封为荣王。二十五年,改名李琬。《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第130页作《唐荣王(李婺)故第八女墓志铭》,著录者误“婺女”为李婺之女,据此当定名为《唐荣王(李滉)故第八女墓志铭》。
6.第26册第130页《郑偓佺妻陈氏墓志》,据首题“□□故河南侯莫陈夫人墓志铭”与志文“夫人侯莫陈氏,河南人也。”可知陈氏前脱“侯莫”二字,“侯莫陈”乃三字复姓,其先出自鲜卑别部,此志题名应作《郑偓佺妻侯莫陈氏墓志》。《周书》卷一九有《侯莫陈顺传》,第21册第23页有《侯莫陈大师寿塔铭》,可资比勘。
7.第36册第35页《任元页墓志》又见于《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壹》第437页《任墓志》,并误。据志文“府君讳元贞,字表则,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邢部尚书知郑州搉税回图茶盐都院事守别驾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涛之长子也。”字形作,知前者释“页”误,当释为“贞”字;后者又误“元贞”作一字(字形作),据此当定名为《任元贞墓志》。
8.第36册第102页《顾亭林法云寺感梦伽蓝记》,首题云“顾亭林法云寺感梦伽蓝神记”,“神”字脱文,“伽蓝神”为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训作佛教寺院守护神,碑文载后晋开运年间僧人造立佛寺,感梦梁侍郎顾野王之事,題名当为《顾亭林法云寺感梦伽蓝神记》。
(二)未审志文及稽考文献材料,造成志主姓名缺字
《汇编》著录在碑刻定名上较为混乱,以石刻大宗墓志为例,妇人墓志标注夫名,偶又省去不录;合葬墓志常不标,一般只标著夫名,时而又标。著录碑名上的混乱,是导致志主姓名缺字的另一原因,有些墓志题名可据志文及稽考文献材料补缺。如:
1.第10册第62页《志修塔记》,志文云“大隋大业八年岁次壬申六月丁丑朔十三日庚寅,上柱国岐州刺史正义公孙志修塔述。”按:正义公当是郑译,《隋书》卷三十八有传。郑译,字正义,荥阳开封人。隋任隆州、岐州刺史,位至上柱国,开皇十一年,以疾卒官。修塔者是其孙郑志,当定名为《郑志修塔记》。
2.第12册第170页《王君妻郭氏墓志》,据志文“幼笄纔冠,来适王宗。”知郭氏丈夫为王宗,可补为《王宗妻郭氏墓志》。
3.第18册第136页《许公妻王氏墓志》,首题云“大周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嶲州诸军事守嶲州刺史上柱国高阳县开国男许公夫人琅瑘郡君王氏墓志铭并序”,志文有“子左奉裕长史惟忠等”。第19册第6页《许枢墓志》首题云“大周故正议大夫使持节都督嶲州诸军事守嶲州刾史上柱国高阳县开国男许君墓志铭并序”,志文有“君讳枢,字思言,高阳新城人也。……嗣子前朝议郎行太子左奉裕长史上柱国惟忠等”两者吻合,《许公妻王氏墓志》可补作《许枢妻王氏墓志》。
4.第20册第37页《□文政墓志》,志文首行残泐,故志主姓氏不详,据志文“高取汉皇之印”用赵尧事,“后将军之车骑”用赵充国事,“京兆尹之风神”用赵广汉事,知志主应姓赵,可补作《赵客及妻何氏墓志》。
5.第28册第124页《李□□题名》,据志文“□□□主开府□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州诸军事、前□海青密曹濮曹齐等七州刺史、□□□使御史中丞、安固郡王李百威……贞元十三年岁次丁丑三月丁亥朔廿六日。”可補为《李百威题名》。
6.第32册第176页《韦君妻齐氏墓志》,据志文“夫人字孝明,……姑小子曰素,美秀而文,姑常抚夫人首曰:笄无他从,必为我季妇。”可补作《韦素妻齐孝明墓志》。
7.第33册第128页《张君妻刘冰墓志》,撰文者是志主侄子张绍仁,据志文“笄年归于我季父蔼然严君。”可知其季父为张蔼然,应补作《张蔼然妻刘冰墓志》。
8.第33册第138页《孙氏女墓志》,首题云“唐乐安孙氏女子墓志铭并序”,志文有“父澥,前任河南府叅军。子即参军之长女也。”可知志主父名孙澥,应补作《孙澥女墓志》。
9.第33册第177页《刘君妻王氏墓志》,据志文“其先大夫、先太夫人在洛京,遂辇致於所居,经岁乃得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彭城刘公思友”,可知刘君应名思友,应补作《刘思友妻王氏墓志》。
(三)照录碑刻原形字,没有进行对应转换
依《汇编》著录体例,标题及录文中的古、异、俗、别体字一律按标准繁体字书写;不能辨认者,直书其原形。但有些俗别字,仔细审读是可以辨认出的,著录者失考而照录原形。如:
1.第11册第139页《宋君妻斑氏墓志》,首题为“唐故班夫人墓志”,原刻作,当释为班。当定名为《宋君妻班氏墓志》。
2.第12册89页《邢仙姖墓志》,志文云“夫人讳仙姬,字玉女,其先周之苗裔。”原刻作,“姖”是“姬”的碑别字,应释为“姬”。碑刻中例证甚多,编者不察而误。又如第12册第132页《姖推墓志》作、第16册92页《姖恭仁殡志》作。以上三志,皆著录为“姖”,当替代为“姬”。
3.第14册第71页《漫墓志》,志文云“女□澷仾,琅耶临沂人也。”原刻作即仾字,是“低”的碑别字,当释为“低”。《广韵·齐韵》:“低,俗作仾。”著录者依样葫芦为“”字,当改作《漫低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4-133作《漫低墓志》,无误。
4.第16册第072页《靳墓志》,志文云“君讳勖,字大廉,汾州西河人也。”原刻作,是勖的碑别字,碑刻中例证甚多,应释为“勖”。又如《汇编》第4册第173页《元悦妃冯季华墓志》:“仁智外衍,幽闲内勖。”勖字作。《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6-13与《汇编》同,亦误。《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9-852作《靳勖志》,无误。
5.第17册第71页《高墓志》,志文云“君讳夔,字安本,渤海蓨人也。”原刻作,当释为“夔”字。唐碑刻中例证甚多,如第18册104页《赵睿墓志》作、第32册9页《曹庆妻樊氏合祔志》作、第16册104页《乐玉墓志》作,皆为夔字。
6.第21册第63页《温炜妻李上座墓志》,志文云“夫人号上座,字功德山,滑州卫南人也。”原刻作;应释作“寳”字,为“寳”的省形字。《说文·宀部》:“珍也。从宀、从王、从贝,缶声。,古文寶省贝。”第9册第129页《刘多墓志》作、第23册第145页《贞一庙碑》作,亦是“寳”的省形字。《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6-1574;《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9-3;《唐代墓志汇编》开元047;《全唐文补遗》2-428,皆收录此志,均释作寳。
二、镌刻系年讹误
《汇编》拓本年代的著录,一般根据刻石立石年代,墓志则根据葬年,无葬年者根据卒年。其所收石刻一般都有明确的时间标示,但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一些讹误,或因文字漫漶残泐造成误读,或错把卒年当成葬年;或混淆年号而致张冠李戴;或折合成公元纪年时出错。王丽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正误》(《文献》2003年第3期)曾订正其中4处讹误,今再补充数例。
(一)误读镌刻时间,造成系年误判
1.第11册第151页《张锺葵墓志》,著录为“贞观二十年十月十九日葬”,志文云“以贞观十八年五月廿六日遇疹奄终。……即以其年十月十九日合葬于洛北邙。”其字作,即“亓”字,借为“其”形,著录者或误作“廿”字,遂作“二十年”云云,葬期应为贞观十八年十月十九日。第10册第58页《刘德墓志》:“公知其密谋,潜守穴口。”“其”字用作形,可作比堪。
2.第13册第84页《张婉墓志》,著录为“显庆三年(658)九月二十二日葬”,大误,应为长庆三年(823)。撰者是张婉的父亲张士阶,志文云“安定张氏之女曰婉,赠秘书监府君讳翔之孙,湖州刺史士阶之息女也。……□庆三年六月十一日奄然终于吴兴郡舍,甲子才廿春矣。以其年九月廿二日,归窆于洛阳金谷之旧原。”另据第31册第59页《张婵墓志》,志主张婵是张婉之妹,卒於开成五年(840)二月十一日,志文乃兄张涂所撰,志文有云“长庆中,吾先君由真司封郎,出为湖州牧”,则张婉当卒于长庆年间,残泐之字当为“长”字,著录者误作“显”字。
3.第17册第128页《李叔墓志》,著录为“天授二年(691)正月二十四日丙申葬”,“二年”当作“元年”,志文云“粤以大周天授元年岁次辛卯正月癸酉朔廿四日景申,夙奉神柩迁祔于洛阳县北里之髙原。”“元”字字迹甚清晰,著录者误录。
4.第28册第117页《广济桥碑》著录为“唐贞元十一年(795)十二月刻。碑在山东长清。……周实撰,正书。”志文有“宋熙宁中,居民靳□同□严寺僧架成石桥。奈何虹小而狭,不任水力。本朝贞元岁,山水暴至,一荡毁圮。……始于丙戌之春仲,告成于丙申之冬季。”熙宁(1068-1077)为北宋神宗之年号,据碑文可知,广济桥兴建于宋熙宁年间,碑文所谓“本朝贞元岁”,实为金海陵王完颜亮之贞元(1153-1156),著录者误作唐德宗李适之贞元(785-805)。重修广济桥当是在金朝之事,又碑文有“邹人有孟子者,怪其未尽善也,乃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兴梁成,使民免病。”著录者误作“唐贞元十一年(795)十二月刻”。据其工期推断,此桥之兴建当在丙戌岁(1166年),告竣之期在丙申岁(1176年)。
5.第35册第97页《嵩山六十峰诗刻》著录为“唐某年五月五日刻。石在河南登封。……傅梅撰,王正民行书并篆,袁进德镌。”该拓片左上角残缺,作“□□年五月五日刻”,著錄者误作唐某年刻。碑文署“登封县令刑州傅梅元鼎譔”,傅梅(1565-1642),字符鼎,河北邢台人,《明史》卷二四一有传,非唐人。傅梅万历年间曾任登封知县,足迹遍布太室山、少室山,曾仿《史记》体例作《嵩书》十三篇,并撰有《嵩山六十峰诗》。第35册第97页《嵩山六十峰诗刻》当移至明代部分。
(二)误读镌刻时间,造成碑拓重出
《汇编》收录石刻拓片图录,以刻石时间先后为序,有碑刻重出者。或因拓片为前后分拓,收藏来源不同,由于编者在镌刻时间上及其他方面的讹误脱漏,造成一志重复收录;或一志而分在两处,当缀合。
1.第10册第86页《傅叔墓志》,又见第11册第152页,题名相同。两者著录葬期不同,前者为“隋大业九年十月十四日葬”,后者为“唐贞观二十年十月十四日葬”。
此志为傅叔与其妻梁氏合祔墓志,志文云“粤以大业九年奄从沦化,……夫人京兆梁氏,……以贞观廿年终于洛阳之里第,春秋七十五。即以其年十月十四日,合葬于北邙之平乐里。”前者误将傅叔卒年当成葬年,后志系年为是。
2.第12册第102页《三十馀人造桥记》又见于第12册第113页,题名为《建永桥碑》。前者著录为“唐永徽四年(653)八月建于安徽灵壁县”,后者著录为“唐永徽四年(653)十二月建于河北栾城,清同治年间邑人修洨河得之”,另形制介绍略有差异。
据志文“大唐永徽四年岁次星纪月维大吕,遂□于程村之南,洨水之上,立永桥一所。”大吕月指夏历十二月,又“赵州之地,……有洨水者,出自龙山之北,经于程氏之南。”知当以后者著录为是,第12册著录有误,重出当删。
3.第16册第119页《高珍墓志》,又见于第17册第117页,题名相同,碑拓重出。第16册所附拓片每行末字失拓,又有残缺,而第17册之字形则非常清晰,二者当为前后分拓。前者著录为“调露元年(679)十二月十□日葬”,当以后者“载初元年(690)腊月十三日葬”为是。
据志文“以载初元年正月廿二日卒于私宅。有一夫人王氏……以调露元年十二月十日奄晞朝露,以其年腊月十日迁窆于州西北二里平原,礼也。”前者把高珍妻王氏的丧期错当成葬期,当以后者为是。又,两者著录出土地点亦不同,前者作河南安阳,后者作河南洛阳,考志文“其先渤海人也。分珪食邑,橘徙兰移。簪居魏壤,遂留相土。今为安阳人焉。”当以安阳为是。
4.第18册第186页《元瑛墓志》,又见于第19册第076页,题名相同,形制介绍略有差异,又葬期前者著录为“唐圣历三年(700)八月二十四日葬。”后者拓片著录为“唐长安三年(703)八月二十四日葬于河南洛阳。”依两处拓片之内容、书体、残泐情况,应出自同一志石,《汇编》重出。
此志是元瑛与其妻朱氏合祔墓志,据志文知:元瑛薨于长安三年五月卅日,妻朱氏终于圣历二年腊月廿四日,以长安三年八月廿四日,祔葬于北邙山合宫县平乐郷之原。葬期当以长安三年八月廿四日为是,《汇编》第18册著录当据此订正,第19册著录的《元瑛墓志》当删。
5.第22册第39页《张漪墓志盖》与第23册第115页《张漪墓志》之志盖相同。前者著录为“唐开元十一年(723)十月葬”,志主名及葬期据《金石汇目分编》补。后者葬期著录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十月葬”,据志文“以开元廿年十一月廿五日寝疾,……越明年孟冬月才生魄,与君合窆于相城旧茔王坟之甲,从先也。”可知后者无误,前者重出,当删。
6.第23册第100页《房君妻崔顺墓志》,又见于第24册第61页,题名相同,形制介绍略有差异。又葬期前者著录为“开元二十一年(733)四月十三日葬”,后者为“开元二十六年(738)四月十三日葬”。据志文“以开元十五年寝疾,至廿一年后二月十五日终于……即以其年四月十三日,旋窆于北邙山平阴之原。”可知当以前者为是,第24册著录当删。
7.第27册第124页《谦卦碑》,又见于第35册第145页《谦卦爻辞》。第27册拓片按原碑分成四片,第35册则集成一篇,第35册重出,当删。《谦卦碑》,为唐篆书名家李阳冰所书,原刻于木,明嘉靖年间勒之于石,石在安徽芜湖,碑刻四石,此碑是明嘉靖五年张大用摹刻,尾有其隶书题跋。
8.第34册第129页《李氏墓志盖》与第31册第066页《孙君妻李氏墓志》之志盖为同一志盖,皆作“唐故赠陇西县太君李氏墓志”,重出当删。前者著录为“唐刻,拓片长宽均14厘米,正书。”后者相应部份作“拓片志及盖均31厘米。”前者只拓其文字部分。
9.第34册第107页《竹女墓志盖》与第14册第017页《竹妙墓志》之志盖为同一志盖,皆作“竹女之志”,前者重出当删。前者著录为“唐刻。拓片长宽均41厘米。阳文篆书。”后者相应部份作“盖长宽均41厘米。”
10.第36册第181页《张瑞鸠墓志》,又见于第45册第9页,题名为《张正嵩墓志》。前者著录为“南汉乾亨三年(919)十一月八日刻。”后者著录为“辽乾亨三年(919)十一月八日刻。葬于辽宁义县双山。”形制介绍略有差异,
此志文《全唐文补遗》《辽代石刻文编》《全辽文》皆已收录,中国历代之年号有两个乾亨:一为南汉刘龑之乾亨(917-925);一为辽景宗耶律贤之乾亨(979-983),且均有乾亨三年。此墓志解放前出土于辽宁义县双山,刻于辽乾亨三年(981),而《全唐文补遗》和《汇编》误当成了南汉乾亨三年(919)。志文云:“清河府君瑞鸠传裔,灵剑得学,宰晋相韩,兴蜀霸汉。……府君考讳谏,南瀛洲河间县人也。……次子正嵩,为朔州顺义军节院使,即府君也。”墓主应是张正嵩,而非张瑞鸠,前者著录时误以祖名为志主名。第36册第181页《张瑞鸠墓志》重出,当删。
(三)未稽考文献材料,造成葬期失考
1.第33册第139页《王容墓志》,著录为“咸通某年七月十八日葬”。志文云“王氏殇女其名容,名由仪范三德充。诵诗阅史慕古风,卑盈乐善正养蒙。是宜百祥期无穷,奈何美疹剿其躬,芳年奄谢午咸通。季夏二十三遘凶,翌月十八即幽宫。”咸通年间有两个午年,咸通三年(862)岁次壬午,十五年岁次甲午。当以咸通三年为确,葬期是咸通三年七月十八日。
2.第34册192页《孙君妻李氏墓志》,著录为“唐某年七月二十五日葬”,按志文云“遂以大唐乙亥岁六月十六日终于……即以其年七月廿五日归窆于……”,又“祖母夫人姓李氏,外祖博陵崔稜,皇朝户部侍郎、凤翔节度使”,崔稜,他书又作崔倰。考《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十五年正月壬午,以湖南观察使崔倰知户部侍郎、判度支。”《旧唐书·穆宗纪》:“长庆二年正月甲寅,以工部尚书、判度支崔倰检校礼部尚书,兼凤翔尹,充凤翔节度使。”据推测此“乙亥岁”当为大中九年(855)。
三、志盖错讹
墓志盖是墓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世墓志往往仅存志身,佚失志盖,这与以往收藏者重视志文有关。志盖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其上大都刻有志主姓名、祖籍、官爵等,有代替碑额的作用,可视为墓志的标题,当墓志首题文字残泐时,可据志盖铭刻补足。在测查隋唐五代志盖篆文时,我们发现《汇编》收录志盖存在以下问题:志盖张冠李戴、志盖重出、志盖失缀。例如:
(一)志盖张冠李戴
1.第21册第117页《韦希损墓志》与第26册第136页《韦琼墓志》所附志盖为同一志盖,皆作“大唐故韦府君墓志铭”。两志皆西安出土,属端方旧藏。《韦希损墓志》又见于《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7-1623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大卷1-118;《韦琼墓志》又见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卷1-201,其所附志盖亦同,两者必有一误。
2.第23册第100页《房君妻崔顺墓志》,又见于第24册第61页《房君妻崔顺墓志》,碑刻重出。又两志所附志盖不同,前者作“大唐故崔夫人墓志铭”,阴文篆书,盖长宽均24厘米;后者作“崔氏墓志”,阴文正书,盖长宽均35厘米。志长宽40厘米。该志又见于《唐代墓志汇编》开元371作“大唐故崔夫人墓志铭”,未审何者为是。
3.第25册第145页《崔水墓志》(当为《崔永墓志》)与第26册第40页《崔虞延墓志》所附志盖为同一志盖,皆作“唐故清河崔府君墓志”,其中必有一误。《崔永墓志》云“清河崔府君讳永,武城人也。”《崔虞延墓志》云“君讳虞延,字师,其先清河东武城人也。十二世祖浑,晋怀帝辅京将军,迁上党太守屯留侯。”《崔永墓志》又见于《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23作“唐故清河崔府君墓志”;《崔虞延墓志》又见于《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73志盖失,《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1-122,所附志盖亦同。
(二)志盖重出
1.第22册第39页《张漪墓志盖》与第23册第115页《张漪墓志》之志盖为相同。前者著录为“唐开元十一年(723)十月葬”,志主名及葬期据《金石汇目分编》补。后者葬期著录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十月葬”,据志文“以开元廿年十一月廿五日寝疾,……越明年孟冬月才生魄,与君合窆于相城旧茔王坟之甲,从先也。”可知后者无误,前者重出,当删。
2.第34册第129页《李氏墓志盖》与第31册第066页《孙君妻李氏墓志》之志盖为同一志盖,皆作“唐故赠陇西县太君李氏墓志”,重出当删。前者著录为“唐刻,拓片长宽均14厘米,正书。”后者相应部份作“拓片志及盖均31厘米。”前者只拓其文字部分。
3.第34册第107页《竹女墓志盖》与第14册第017页《竹妙墓志》之志盖为同一志盖,皆作“竹女之志”,前者重出当删。前者著录为“唐刻。拓片长宽均41厘米。阳文篆书。”后者相应部份作“盖长宽均41厘米。”
(三)志盖失缀
1.第22册第30页《崔泰之墓志》无志盖,首题作“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赠荆州大都督清河郡开国公上柱国崔公墓志铭”,第35册第041页《崔君墓志盖》云“大唐故工戶部尚书赠荆州都督清河郡开国公崔府君墓志铭”,两者大致吻合。《崔泰之墓志》又见于《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7-1697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9-104,其所附志盖皆与第35册同。《汇编》第22册失志盖,当与第35册缀合。
2.第30册第141页《崔藩墓志》无志盖,首题作“大唐故朝议郎河南府登封县令上柱国赐绯鱼袋崔公墓志铭并叙”,与第35册第042页《崔君墓志盖》云“唐登封县令崔府君墓”相类。《崔藩墓志》又见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大2-95,也无志盖。
四、撰书刻石者讹漏
正确著录碑刻题名外,著录撰者、书丹者和刻工也是同样重要和不可忽视的。不少撰者为文坛巨擎,所撰文章有文集未收者,据志文可补别集之阙;书丹者有颜真卿、柳公权、李阳冰等名家,其书迹弥足珍贵;技术精湛的刻工,对保存书丹者的神韵作用异常重要,著錄刻工姓名亦存在重要研究价值。《汇编》撰者、书丹者和刻工的著录,偶有讹漏。例如:
1.第20册第75页《束良墓志》,未著录撰刻者姓名,据志文“前左卫翊卫中山郎南金续铭序”,可补撰刻者为南金续。
2.第24册第61页《房君妻崔顺墓志》,据志文“哀子宽书”,可知书者为崔氏之子房宽,著录者误以妻姓作夫姓,误为崔宽。
3.第25册第89页《刘昇墓志》,著录为“李撰”。志文云“右补阙李翊撰”,原刻作,为翊字。清人劳格以为或珝,皆为翊字。其《读书杂志》卷七称:“参考诸书,李翊、李,疑即一人。”按唐人名李翊者数人,《唐文拾遗》卷三十《监察御史代监左藏库奏》之作者,武宗朝御史中丞;《登科记考》卷十五之进士,出贞元十八年权德舆榜下;皆与时代不合。《尚书省郎官题名》卷十二“户部员外郎”,时代相近,或为其人。
4.第28册第91页《李皋墓志》,未著录刻工姓名。据志文“镌字人屈贲、马瞻”,可补屈贲、马瞻镌字。
5.第29册第4页《卢沇妻李氏墓志》,著录为“李潔撰”。志文云“季弟前池州至德县令潔述”,此志是卢沇与妻李氏合祔墓志,当题作《卢沇及妻李氏墓志》,撰文者是卢潔,非李潔。第29册第135页《李孔明妻刘媛墓志》,著录为“从侄三复撰”,当为“李三复撰”。
6.第30册91页《卢初墓志》,著录为“李公撰”。志文云“其志文,府君外舅故相国李公撰述,故因而不改。”前文又谓“故臧公揆以其子妻之”,则李公即李揆,字端卿,志主卢初之岳翁,两《唐书》有传。又著录应补卢商记,卢知退书。
7.第31册第104页《杨宇妻杜絪墓志》,志盖失拓,据志文“陇西李义山篆”,可补李义山篆盖。
8.第33册第139页《王容墓志》,著录为“王长仁撰”。志文云“厥考长仁命不融,外族清河武城东。……仲父刻铭藏户中,以纾临穴嫂哀恫。”长仁是对其父的赞词,不是他的名字,考志文文意,撰文者是其仲父。
五、误收伪刻
墓志的辨伪工作,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为了保证研究资料的可靠性,辨别真伪就成了研究的首要工作。《汇编》伪刻不录,但因对石刻真伪鉴别不够,收入了部分伪品。如:
1.隋大业八年《李肃墓志》,拓片著录于《北图》第10册59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东江苏卷》第1册8页、释文见于《隋代墓志铭汇考》第4册206页,该志系窜改摹刻唐先天元年《契苾明墓碑》(《北图》第21册7页)而成。[1]96-100
2.第10册第102页《贾玄赞殡记》,署刊葬时间为隋大业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仅有拓本传世,实为伪刻。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已辨其伪,后人偶有失察而误收伪刻,《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陽卷》6-118、《全隋文补遗》312等皆作隋志不疑,周绍良《唐代墓志彙編》将其列入垂拱007,《隋代墓志铭汇考》6-225详辨其伪,具体可见其考证。
3.第35册第127页《剑阁诗刻》,内容为《题剑门》的一首其言律诗,作者题为李商隐。其诗曰:“峭壁横空限一隅,划开元气建洪枢。梯航百货通邦计,键闭诸蛮屏帝都。西蹙犬戎威北狄,南吞荆郢制东吴。千年管钥谁镕范,只自先天造化炉。”吕蒙《<剑阁诗刻>拓片辨伪》(《文献》2011年第4期)以为伪刻,详细可见其考证。
六、书体误判
《汇编》所收石刻拓片,篆、隶、正、行、草等诸种书体兼备,每件石刻编者都注明其书体,惜其间有误判。例如:
1.第9册第157页《郭休墓志》,书体著录作隶书,实际上该文隶篆夹杂,如志文中例句 “大节清高”、“汪汪济济”、“无别玉山之势”、“无明自息”、“弘誓未充”,等字以篆文书写,当著录为隶书间杂篆书。古人有爱杂用篆、古文的习尚,隋唐墓志中偶有篆隶、篆楷夹杂现象,又如第11册第32页《□祎墓誌》,篆、隶、正杂书,与之相类。
2.第23册第114页《许君妻李肃邕墓志》,著录为“阳伯成撰并正书”,此志一志二体,首题“大唐侍御史歙州司馬許公故夫人趙郡李氏墓誌銘并序”及末二行铭文部分隶书,其馀则楷书。当著录作“阳伯成撰并正书,首题及铭文隶书。”第25册第5页《贾令琬墓志》,首题二行隶书,其馀楷书,与之相似。该志著录为“王弼撰,正书,首题隶书。”可资比勘。
注 释:
[1] 刘本才:《李肃墓志辨伪》,《中国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责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蒋文艳
作者简介:
刘本才(1981-),男,山东平邑人,文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字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