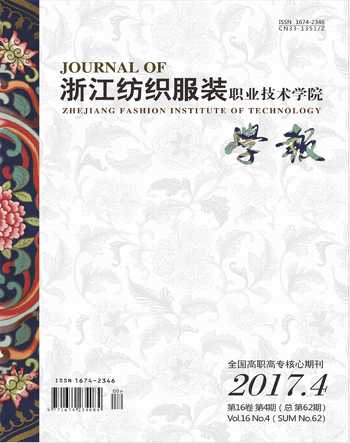新疆出土汉唐染缬图案与工艺研究
朱桐莹
摘 要:染缬是中国古代织物印染的总称,主要的工艺有绞缬、蜡缬、夹缬和灰缬。从新疆地区出土的汉唐染缬发现,图案主题可分为4类:植物纹、禽鸟纹、几何纹以及人物纹。其中植物纹发现最多,图案排列形式也最为丰富,是十分流行的题材;禽鸟纹多与花卉结合;几何纹因工艺限制多为绞缬;人物纹发现较少,时间集中在唐代,体现了纺织品图案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联。
关键词:新疆地区;出土文物;汉唐时期;染缬工艺;图案纹样
中图分类号:J5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46(2017)04-0077-06
中国古代有图案的织物根据加工技术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在织机上完成的多彩织锦和两色或单色花的绮、绫、罗等;另一类则是在成品上后加工形成的,如刺绣、彩绘、贴金和染缬等。“染”为染色,“缬”为织物的印花手段。《韵会》:“缬,系也,谓系缯染成文也”,从字的本意来看,“缬”单指绞缬,即将织物扎紧染成花纹,类似于现代的扎染。唐代有四缬之说,除绞缬外,还有蜡缬、夹缬和灰缬,就是今天的蜡染、夹染和蓝印花布。
染缬自汉代开始发展到唐代走向兴盛。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中记载:“缬,秦汉间始有,陈梁间贵贱通服之。隋文帝宫中者,多与流俗不同。次有文缬小花,以为衫子。炀帝诏内外官亲侍者许服之。”另有《中华古今注》:“隋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宫人及百僚母妻。”可见,染缬织物在隋唐时已极受欢迎,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愿穿着染花服饰。
汉唐时期的染缬实物主要发现和收藏于甘肃敦煌、日本正仓院和新疆地区。前两地的参考资料较为集中,以唐代为主;而新疆的发现品多分散于各个地区,时间分布也从汉至唐不等。主要有:吐鲁番阿斯塔纳、民丰尼雅、扎滚鲁克、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营盘、山普拉、吐峪沟以及楼兰。现选取其中部分实例探讨汉唐时期染缬织物图案的类型和发展规律。
1 植物纹
植物纹是表现植物形象的纹样的总称,是工艺美术和纺织品常用装饰纹样之一,其表现既有写实化的,也有图案化的。在新疆发现的染缬织物中,植物纹样可分为2类:一类是是葡萄纹,另一类是花卉纹。
1.1 葡萄纹
在佛教艺术中,菩萨手持的葡萄蕴含着五谷丰登的意义,所以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装饰题材。葡萄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引入中国的,至隋唐代时,吐鲁番和敦煌文书中已有葡萄名目的记载,同时,葡萄作为纹样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展,应用于纺织品、壁画和铜镜等物品上。196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了白地葡萄纹印花罗(图1),在白色地上以深棕色印制图案,纹样写实,属于新疆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夹缬。但织物破损严重,只能看到分散的葡萄纹、葡萄叶以及卷草纹,未发现排列规律。1973年又出土褐地葡萄叶纹印花绢(图2),织物面积较大,长100厘米,宽41厘米,幅边宽约2厘米。褐色地上紧密缠绕着黄色的葡萄藤蔓,其中分别填充葡萄、葡萄叶和花朵,二方连续,图案比白地葡萄纹印花罗更显抽象,独具异域风情。根据武敏的研究,此件织物为灰缬,在填充花卉处可以看到明显的接版重叠痕迹,花版经向长度为15.3厘米,纬向宽度为54厘米。
1.2 花卉纹
花卉纹是新疆出土染缬织物中所见最多的图案,花卉的种类和排列方式也各不相同,有分散的独立小花,有主次分明的组合,还有菱格骨架内填充朵花的。
1.2.1 散点式独立小花
阿斯塔那108号墓出土过1件绛纱地柿蒂花灰缬(图3),属于盛唐时期,长139厘米,宽16厘米,绛色地上均匀分布白色四瓣小花,花瓣空心,内填小圆点,花蕊也呈圆点状,每片花瓣周圍点缀小叶子,各行间错位排列。小花直径约2厘米,花纹清晰,颜色鲜艳。斯坦因也曾于阿斯塔那发现了图案完全相同的黄色四瓣朵花纹灰缬绢,长约33厘米,宽约7.6厘米,小花直径约为2厘米,可能为同一花版印制。同样以散点式排列的还有1972年于阿斯塔那出土的绞缬印花罗(图4),长63厘米,宽15厘米,墨绿地上显白色花纹,四瓣小花,花朵中间有浅棕色十字纹,是将图案缝绞后半浸染成果。
1.2.2 主次分明的结构
主次分明的结构不仅是绘画重要的构图手法,也是纺织品图案排列的常用手段,染缬织物也一样。这一特点在1968年阿斯塔那出土的土黄地黄白印花绢(图5)中就显而易见,土黄地上显黄色六瓣和白色四瓣小花,六瓣花布局稀疏,空隙处填简易的四瓣小花,两种花时有重叠,可推测为分量套花版先后上染。类似的还有暗绿色套印花绢(图6),显示2组图案,绿色的六瓣团花和十样花,以及一上二下为一组的白色小点,图案互相覆盖,也通过2套花版印染而成。这2件织物都是在同色系的大花朵和地上套染白色小型图案,既完成了花型上的主次区分,也表现了颜色上的不同效果。除此之外,还有单纯以六瓣花和四瓣花组成的图案的主次之分,黄纱地麻花灰缬、小花印花绢、绿地印花绢裙以及绛地印花绢裙都是这种结构。还有一件天青地花卉印花绢(图7),主体图案为六瓣深青色花瓣和五瓣橙色花芯,外部穿插着和花芯相似的五瓣小花以及互相缠绕的深青色枝叶。这件印花绢相比其他的主次构图结构更加饱满,也与敦煌发现的花卉纹夹缬更加接近。
1.2.3 菱格骨架
魏晋南北朝时期,菱格骨架作为一种新型骨架出现在纺织品上,其表现形式是在联珠或条形构成的菱形内填以主题纹样,吐鲁番所出的一件织锦就是此形式的骨架,内填小花,菱格四边也点缀花朵(图8)。染缬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图案排列:1968年阿斯塔那北区墓中出土的棕色印花绢(图9),主题纹样为六瓣朵花,菱形外框四边为等距的4个小圆点和4瓣小花;还有阿斯塔那85号墓发现的西凉时期蓝地蜡缬绢(图10),在蓝色地上以大小相同的白色圆点组成菱形骨架和花朵,同样的图案在新疆出土染缬中还有很多。另外,联珠菱格框架也可以产生变化,屋于来克古城遗址发现的一件蓝色印花毛织物,就将菱形外框的联珠全部替换成与主题纹样相似的小花(图11)。这类骨架与几何纹染缬中的菱形网格纹有异曲同工之处。
2 禽鸟纹
与植物纹相比,禽鸟纹染缬植物的发现少了许多,而且都与花卉相结合。如阿斯塔那108号墓出土的黄纱地花树对鸟纹灰缬(图12),纹样表现了2只对小花树而立的鸳鸯,鸳鸯的正下方有一折枝花,图案完全对称,成散点式排列,线条匀称,对鸟造型精准,极富装饰性。另有一件浅棕地团窠立鸟纹印花缣(图13),原为女裙残部,长109厘米,宽83.6厘米,在蕾形宝相花中置立鸟,团窠直径12厘米,每4个主花间填“十”字形折枝卷叶花作宾花,花型华丽,装饰意味极浓。花纹对称,四方连续。这种纹样正是自唐初风靡近百年,由四川窦师纶设计的“陵阳公样”,可见染缬织物图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流行纹样的影响。
此外,德国探险家勒柯克于1904~1905年间,在高昌K遗址“藏书室”旁边的窄回廊和吐峪沟右岸寺庙“遗书室”盗掘了2件夹缬丝织品(图14)。一件印两低垂的雁首,身体残缺,上方有联珠菱形装饰,颜色保存好,显橙色和蓝色,白色勾边。另一件颜色退化,白边勾勒出伸展的翅膀,可能和前一件为同一织物上的残片。
3 几何纹
在各种各样的织物图案中,不仅有丰富多彩的动植物具象纹样,更有结构精炼、风格独特的抽象几何纹样。几何纹是以点和线为基础,通过组合排列形成的有规律的装饰纹饰,注重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在新疆发现的几何纹染缬织物可分为以下几种:散点式小菱形、菱格网纹和晕繝条纹。
3.1 散点式小菱形
在织物上有规律的填充空心小菱形,且各菱形之间距离相等,是此类图案的表现形式。年代最早的出土实物是发现于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群的一件绞缬方格圆圈纹残毛布单(图15),属于墓葬的且末文化时期,即春秋至西汉年间。织物长110厘米,宽96厘米。平纹,分区显紫色、绛红色和红色的方格纹,格纹长2.5厘米,宽2.2厘米,格内扎染白色空心小菱格纹。根据细节图可发现,绛红色纱线少部分显红色,红色纱线中也有白色混入,因此这件织物可能是棕色和白色的方格纹毛布将白色部分扎绑后浸入红色染液的结果。与此图案类似的还有在屋于来克古城遗址发现的北朝红色绞缬绢(图16),以及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红地、绛地和蓝地绞缬绢等(图17)。这些织物都是先在素色平纹地上以均匀间距扎绑后再上染,属于绞缬的典型工艺,比较常见和流行,从春秋至唐代都有出土,但纹样变化小,一直保持着单纯的散点菱形状。
3.2 菱格网纹
菱格網纹最先出现于远古时代的陶器,后逐渐发展变化成纺织品上的装饰纹样。扎滚鲁克曾发现过一件绞缬菱格网纹毛布(图18),是衣服残片,长56厘米,宽53厘米,分布大小相近相互连接的菱形,菱形四边由2排细密的白色圆点组成,每排大约有12个。织物上未见针眼,可能用扎绑法制成,要在毛布上扎系出为数众多的点,其复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阿斯塔那304号墓和117号墓也分别发现了网格纹绞缬绢(图19),菱形四边以单排圆点组成,圆点面积较大,每排仅分布约4个,纹样较扎滚鲁克的发现品粗旷。这2件织物上都能看到明显的针眼和褶皱痕迹,因此采用了与前件不同的缝绞法。
3.3 晕繝条纹
晕繝是唐代织锦中常见的表现手法,由不同颜色过度组成色彩斑斓的条纹,给人以丰富华美之感。《续日本纪》中记载:“染作晕繝色,而其色各种相间;皆横终幅。”因此,晕繝本是染缬的一种。阿斯塔那227号唐墓中出土的一件条纹染缬绮,红、白、黄、绿4色相间,非常美观。其制作方法是先将织物分段按横向扎起,然后再浸水染色,是绞缬中的绑扎法。与之类似的还有在青海都兰吐蕃墓发现的染缬葡萄纹绮(图20),染成绿白相间的条纹状,印染方法和阿斯塔那的发现品相同。这2件实物都是织绮染色,使本来就复杂的织物更显华贵。
根据以上出土实物可以发现,绞缬多表现为几何纹,图形规整,常用缝绞法和绑扎法。除晕繝外,颜色也较单一,地染色,花白色。
4 人物纹
新疆出土的人物纹染缬中,最著名的要属民丰尼雅东汉墓的“蜡染蓝白印花棉布”(图21)。蓝色棉布上蜡绘出白色图案:一位袒胸露乳的女子手捧一只角形器,里面盛满好似葡萄籽的实类物品,她体态丰润,神态安详,颈饰璎珞,头像后的一圈背光近似佛光,女子的身份在学术界也颇有争议,但其形象源自西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可以推测此印花棉布是可能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印花布中心有一个大方框,内见残损的人脚、狮尾和狮爪。棉布下方的图案一般被认定为中国龙,只是没有爪,龙的上下皆是振翅欲飞的鸟,还有一只怪兽咬着龙尾。由于图像残缺,因此对其要传达的真正内容,至今众说纷纭。
同样引人注目的人物图案还有在阿斯塔那出土的2件唐代狩猎纹印花织物。一件是绿纱地狩猎纹灰缬(图22),墨绿色地上显以线勾勒的粉绿纹样,散点分布着骑马的猎手、飞翔的禽鸟、奔跑的兔子和鹿,以及花卉,形象生动活泼;另一件是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图23),为褥子的贴边,由4块拼成,图案比前一件精细,印出骑士回首射猎狮子的场景,为一个花纹单位,上下循环,左右对称,有的花纹上还有因碱剂印花而形成的孔洞。狩猎是唐代封建统治阶层喜爱的活动之一,狩猎纹在染缬上的应用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
综上可知:1)新疆地区出土的染缬织物时间跨度大,春秋至唐代都有。可以大致理清4种染缬的发展顺序:绞缬和蜡缬产生较早,在汉代均有发现;夹缬和灰缬则最早出现于唐代。2)染缬图案和工艺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绞缬多制抽象几何纹样,风格质朴;蜡缬、夹缬和灰缬则产生具象的动植物图案,表现细腻。发现最多的是花卉图案,图案的布局分为散点、主次和框架结构。3)虽然4种染缬都有出土,但是绞缬、蜡缬和灰缬数量多,夹缬少,因此想要全面了解汉唐时期的染缬图案,还需结合敦煌和正仓院的藏品。
参考文献
[1]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538.
[2]马缟.中华古今注[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2.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图版17,图版55,图版 49,图版18.
[4]柳洪亮.1986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J].考古,1992(2):143-156.
[5]李征.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J].文物,1973(10):7-27.
[6]新疆考古文物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十次发掘简报[J].新疆文物,2000(3-4):84-168.
[7]赵丰,尚刚,龙博.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上[M].北京:开明出版社, 2014:278,289.
[8]赵丰.织绣珍品[M].香港:艺纱堂服饰工作队,1999:102-103.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107,112.
[10]武敏.唐代的夹版印花――夹缬――吐鲁番出土印花丝织物的再研究[J].文物,1979(8):40-49.
[11]赵丰.王?与纺织考古[M].香港:艺纱堂服饰工作队,2001:82-97.
[12]新疆考古文物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第十一次发掘简报[J]. 新疆文物,2000(3-4):190-192,210.
[13]勒柯克.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M]. 赵崇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图版50,181.
[14]王博.扎滚鲁克纺织珍宝[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25,183.
[15]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0(6):11.
Study of Resist Dyeing Patterns and Craftworks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Unearthed in Xinjiang
ZHU Tong-ying
(Fashion and Design College,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200051,China)
Abstract:Xie is a general term of printing and dyeing fabrics in ancient China.The main process includes tie dye,clamp resist dye,wax resist dye and ash resist dye.From the findings in Xinjiang,the motifs of resist dyeing patter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plant,bird,geometric and character patterns.Among them,the plant patterns were the most abundantly found with the richest pattern arrangements,which are the most popular subjects.The bird patterns always combine with flowers.The geometric patterns always come with tie dyed silks due to technological limitations.The character patterns were the least found,mostly from the Tang dynasty,and they reflec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extile patterns and the social life then.
Key word:Xinjiang region;unearthed relics;Han and Tang dynasties;resist dye;patte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