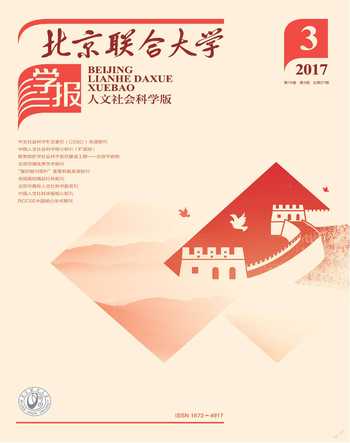台湾人口老化与少子化问题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王建民
[摘要]台湾人口老化与少子化问题日益突出,已进入“高龄化社会”,并将进入“超过高龄社会”,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来临。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比例持续上升,没有子女的单身家庭越来越多,总量已超过非单身家庭。人口红利会逐步消失,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社保基金财政吃紧;少子化对台湾高校招生与教育事业发展带来新挑战,普遍面临生源不足、高校老师失业与高校倒闭现象增加等一系列新问题;老年人口“长期照顾”成为新课题。
[关键词]台湾;人口老化;少子化;人口红利;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675.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7)03-0052-07
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时期的台湾,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寿命延长(2015年台湾男女平均寿命为80.2岁)、社会价值观念变化以及晚婚晚育与不育人数的显著增加,台湾人口老化与少子化趋势日益明显,对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動力短缺,社会保障压力增大,老人赡养照顾问题日益突出。
一、台湾人口老化与少子化双重发展态势
人口老化与少子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与发展趋势,尤其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尤为典型,非台湾地区所独有。依据联合国资料,到了2050年,全球将有超过半数以上地区进入“高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与“高龄社会”(aged society),甚至进入“超过高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其中,欧洲地区是人口老化最早开始的地区,届时最严重;其次是北美洲地区;由于亚洲人口众多,基数庞大,老年人口总量最多,2000年老年人口数已超过预计2050年时的欧洲老年人口数量,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亚洲高龄人口超过9亿人[1]。2013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数约达5.7亿人,预计2050年达到14.9亿人;65岁以上人口占全球人口比率从8%上升为15.6%。[2]
据日本总务省于2016年6月公布的资料,2015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达334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6.7%,为全球最老化的国家;同时15岁以下儿童人口所占比例为12.7%,是历年来最低[3]。
(一)台湾人口老化与少子化问题日益突出
2017年2月老年人口数首次超过幼年人口数。据统计,1993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进入“高龄化社会”;2015年达到10.7%,预计2018年达到14%,进入“高龄社会”;2025年将达到23%,进入“超过高龄社会”[4];台湾老化指数(65岁以上人口与0~14岁人口之比)由2005年的52.1,上升到2015年的92.2,2016年达到98.9,2017年首次超过100,达到100.18[5]。
从台湾各县市人口老化指数看,这一趋势更典型。2011年,只有3个县市人口老化指数破百,2015年破百指数县市达14个,已超过一半以上,2017年2月达到15个,显示台湾人口老化在急剧加快。不过,台湾各县市人口老化指数差别较大,其中2017年2月,人口“老化”前五县市为嘉义县(177.0)、云林县(141.87)、南投县(139.48)、屏东县(137.38)与澎湖县(136.71),基本上以农业或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县市为主;人口较“年轻”的县市则为新竹市(63.87)、新竹县(70.59)、连江县(82.28)、嘉义市(95.32)等,老化指数均不超过100[6]。在“六都”(直辖市)中,台北市人口“老化指数”最高, 2016年底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近42万人,2017年老化指数为113.07,台南市与高雄市老化指数分别达到111.02与110.25[6]。
在人口老化的同时,台湾少子化问题也日益突出。一方面,人口出生率下降,新增人口增长放慢,1996—2010年,台湾年出生人口数减少50%,预计到2061年,台湾人口将减少24.2%,其中幼年、青壮年人口减少50%。据统计,1961年出生人口为42.2万人,1991年为26万人;1998年是台湾人口显著减少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出生人口(受中国传统“虎年”因素影响)首次降至30万人以下,为27万人,此后除“千禧年”2000年再次达到30万人外,均每年不到30万人,2010年只有16.6万人(虎年),此后在人口生育政策鼓励下,出生人口有所回升,但依旧有限,2015年仍只有21.5万人。另一方面,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大幅下降,从1993年的25.15%降到2013年的14.32%,10年降了11个百分点,预计到2025年降为11.93%。①
据最新统计,2015年底,幼年人口较老年人口多出近25万人;到2016年底,幼年人口较老年人口多出3.2万人。到2017年2月底,0~14岁幼年人口为313.37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3.31%;65岁以上人口为313.94万人,占总人口的13.33%,台湾老年人口首次正式超过幼年人口[6]。可以说,台湾面临人口老化与少子女化的双重压力,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二)妇女生育率显著下降,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成为普遍社会现象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达经济体妇女生育率下降已成为全球现象,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台湾也不例外。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妇女生育率下降更为明显。台湾妇女生育率从1950年代的全球最高之一转变到目前全球最低之一,即从一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7个子女,1970年代平均为4.9,2004年降为1.2,2015年为1.1。[4]其中,2010年,台湾总生育率为0.895,为全球最低生育率之一。
进入后工业化或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价值观念的改变与生存压力的增加,台湾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比例持续上升,成为少子化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2013年,台湾男性初婚年龄为32岁,女性初婚年龄为29.7岁,男女初婚年龄平均超过30岁,按大学生23岁毕业进入社会,即近8年时间才能成家结婚。大都市晚婚现象更为严重,以2015年台北市为例,男女平均结婚年龄分别为34.8岁与33.3岁。
台湾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1975年平均为25岁,2015年达到31岁(2004年时为27.4岁)。据台湾“内政部”统计,2015年,台湾有11个县市妇女生育第一胎时平均年龄30岁,其中台北市平均生育年龄达32.44岁,生育第三胎的比率只有7.22%,在各县市最低。
在晚育的同时,少育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台湾生育3胎以上的妇女比例从1975年的38.17%降为2011年的9.76%,创历史最低,随后有所回升,2015年为10.67%。[7]就是说,40年前,10个育龄妇女中有近4个育龄妇女生育3胎,目前10个育龄妇女中只有1个生育3胎。
面对晚婚与少育现象,台湾当局的人口政策也不断调整,从限制转向鼓励生育政策。早期,台湾推动“家庭计划”即计划生育,1967年提倡婚后3年再生育,間隔3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3个孩子。到了1970年代初,台湾家庭计划生育政策有所调整,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的口号。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进入1990年代后,台湾开始鼓励生育政策,1990年正式提出“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的鼓励妇女生育的政策口号。此后,为鼓励适龄结婚与多生育,台湾当局采取了多项鼓励生育政策,包括健全生育保健体系、提高育儿家庭经济支持,特别是马英九执政时期推行包括育儿津贴、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养育幼儿特别扣除额等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但效果有限,不敌价值观念的改变。据调查,高达87%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因生育补助而生小孩,少育现象未能明显改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台湾不婚或不育现象显著增加。台湾单身人士越来越多,没有小孩的家庭越来越多。从台湾财政部门公布的2001—2013年综合所得税的申报资料观察,台湾单身、不婚、不生及老化情况日益严重,充分提示了台湾社会家庭结构的重大变迁。2013年,台湾综合所得税申报户数达600万户,较2001年的497万户增加了103万户。其中,单身申报户数达311万户,超过总数的一半,较12年前多了四成。目前台湾单身户占所有家庭总数的51.83%,有配偶家庭占48.17%。就是说,台湾单身家庭已超过有配偶的家庭。在311万户单身家庭中,完全没有抚养亲属的增加最多,比12年前增加了55万户[7]。据台湾学者估计,到了2035年,台湾40%的家庭可能无小孩,50%没有孙子,其社会经济影响十分深远。
另据调查,受访民众中有45%者没有小孩,其中根本没有生育计划的约占16%。同时,税收申报者的年龄越来越大,成为人口老化的另一观察指标。2001—2013年,51~60岁的综合税申报者从55万户增加到102万户,所占比例从11%上升到17%;20~30岁的年轻人申报人数从146万户降为130万户,所占比例则从29.3%降为21.7%[7]。
二、台湾人口老化与少子化的社会经济影响
人口老化与少子化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供给减少,高校生源减少,社会保障压力,青年人的抚养压力增大,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
(一)人口红利消失,经济竞争力下降
人口红利主要是指妇女生育率与人口出生率较高,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持续供给,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以人力相对充足与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创造经济发展机会。随着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放慢,人口红利会逐步消失,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经济发展。
台湾总人口变化经历了从迅速增加到缓慢增加再到未来负增长的变化过程。据统计,1911年,台湾总人口为343万人,1946年为609万人,1958年突破1000万人,1989年突破2000万人,2008年达到2300万人。其中,1949—1966年为“战后婴儿潮时期”,18年间出生人口达到600多万人。1980年代后,出生人数持续减少,由过去每年新增加40多万人降至近年只有20万人左右,2015年前后开始出现负增长,35年后总人口将降到2000万人以下,预计2060年降为1800万人。[4]
长期以来,台湾有较高的出生率,总体呈现“地小人稠”格局,一直享有人口红利,而且至今并未完全消失。学界对于人口红利的认知标准存在一定差异。一般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较有利的人口条件,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专家认为,人口红利是指15~64岁人口比重高于70%,若低于70%,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目前台湾这一人口比例为73.4%,仍在人口红利范围之内,但预计6年后这一比重将低于70%,人口红利消失[8]。有台湾专家估计,2025年是台湾人口老化的红色警戒线,届时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超过20%,台湾正式结束人口红利时代[9]。据最新预计,2020年台湾将走出人口红利期(工作人口占比为66.7%以上),进入“人口负债期”;到2060年台湾人口将剩下1800万人,且40%为老人[4]。
据台湾专家估计,从2016年开始,台湾劳动力人口开始递减,至2060年平均每年将减少18万工作人口,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开始出现。根据2016年台湾“国发会”发布的最新人口推估,台湾工作年龄人口高峰已过,即15~64岁的劳动人口于2015年达到1736万人,2016年略降为1729万人,证实了专家的预测基本正确,预计10年后再减少约150万人[8],预示着台湾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
2016年12月,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公布一项调查,台湾15~64岁的非劳动力(潜在劳动力)占全体非劳动力比率,从1992年的近80%逐步降为1996年的77.3%,2016年降为66.96%,20年下降了10.34个百分点。到2016年5月,整体非劳动力825万人,其中仍处于工作年龄者(15~64岁)降至552万人[10]。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预示着未来劳力人口的持续减少,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不再,不利于经济发展。
(二)未来青年人抚养压力增大
人口发展与人口结构情况直接涉及劳动人员的抚养压力问题。长期观察,抚幼比例(每百人抚养幼年人数比例)呈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51人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21人,预计到2060年降为17人。抚养老人(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则持续上升,而且未来也是急速上升,1980年代只有7人,2015年增加到15人,到2060年将大幅增加到80人。换算后就是,目前台湾5.6个人养1个老人,预计10年后就变为3.2个人养1个老人,20年后是2.2个人养1个老人,压力显著增大[8]。
总体抚幼与抚老比例呈现U型或V型趋势,即负担压力先升后降再升,其中2020年前后开始回升,总体负担比例加大。到2060年,约100个劳动人口抚养97人,接近一人养一人。另据估算,目前平均一位老年人由6.4个劳动人口抚养,到2060年将由1.3个劳动人口抚养,社会负担增加5倍。
(三)少子化对台湾高等教育发展带来冲击
在经济呈现较快发展时期,台湾教育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高校改革促成高校大发展。在人口增长率持续与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高校有一定的生源保障,不影响高校招生。但随着出生率的显著下降,少子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台湾教育尤其是高校招生与教育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台湾高校普遍面临生源不足、高校老师失业压力增大与高校倒闭现象增加等一系列新问题。
1990年代,台湾大学入学年龄人数达40万左右,目前已降到28万人左右,预计2025年前后降至20万人左右。[11]2011年,台湾高校报考人数有8万多人,2016年只有5.78万人,创下历史新低,大学新生减少约2万人,在理论上约有10多所台湾高校招不到学生。[12]高校为争取更多生源以维持生存,大学录取分数线一降再降,几乎只要参加联合招生考试,就不担心没有大学上。这样一来,高校生源质量大幅下降,客观上降低了高校教育水平,不利于教育竞争力的提高。
据台湾教育部门统计,2016年8月入学的大一新生,将比上年减少1.5万人,2017年再减少1.4万人,即未来两年大学新生减少近3万人[11]。2017年度,台湾高校招生名额减少19840人,其中,大专院校的大一新生为238048人,比上一年学生减少13954人[12]。同时预计六成高校减少招生,有143个所、系、科申请停招。大专招生名额从2013年的442148人降为2017年度的391113人,五年减少了约5万人,其中以技专院校下降最为显著,普通高校下降相对较为缓和。台湾教育部门预估,到2028年,大一新生仅剩15.8万人,较2006年的25万人减少10万人[13]。依目前这一趋势发展,预计未来台湾将会有1/3的大学倒闭。
生源不足,招生减少,学校倒闭,必然造成更多教师面临失业压力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依台湾教育部门推估,2013年,台湾大学教师为5.24万人,因学生减少,学校相继裁员,到2016年大学教师减为48601人,预计2023年进一步减为39579人,即从2013年到2023年10年间将减少近1.5万大学教师[14]。事实上,近年来,“流浪教师”成为台湾教育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现象。他们没有固定教职,只有无保障的不定期兼职,处于半失业状态,生活困难。台湾教育部门估计,未来10年,平均每年减少1000名大学专任教师,或总计10年内计有1万名大学教师将成为“流浪教师”。
面对少子化对教育发展的冲击,台湾当局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推动老师转型辅导方案,辅导教师转行转业,但困难重重,效果不佳。部分台湾高校教师不得不转赴大陆发展,但仍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改变不了许多大学老师失业与半失业状况,未来“流浪教师”问题将更突出。一些高校早在10年前就开始应对少子化的冲击,增加聘任短期专任教师及专案教师,待遇与一般教师一样,但一年一聘,投劳保而非公保,以降低成本。这类兼任教师面临许多困难,常放无薪假,七成私立高校兼任教师钟点费23年未涨,一年只能领9个月工资,月薪一般4万多元(新台币,下同)[15],与普通劳工没有区别。近年,台湾教育部门鼓励大学改革与合并,提出来五年内让50所大学合并转型。近年间已有多所高校推进合并,尽管部分合并方案因学校之间利益的分配引起一定的反对声音,但在现实生存压力下,未来高校的转型合作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另外,少子化与高校的过度扩张发展,录取分数的大大降低与大学生普及化,造成了大学生就业困难与严重的低薪现象。台湾劳动部门公布了2015年职业类别薪资调查结果,大学毕业生起薪为26655元/月,高中职业毕业生平均起薪为22980元/月,两者相差4675元,其中有近1/5的大学毕业生起薪低于高中职毕业生的起薪[16]。低薪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低薪现象成为当今台湾社会面临的另一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四)社会保障压力越来越大
人口老化与少子化,造成缴交社保基金的人相对越来越少,而领取社保基金者尤其是不工作的老年领取者越来越多,社会保障的财务压力越来越大,社保基金面临着破产与没钱可发的严峻挑战。
目前台湾各类社会保险基金存在不同程度的财务危机或潜在的财务危机。据报道,劳工保险的老年给付潜藏负债达8.7万亿元,军公教旧制与新制合计潜藏债务为8.5万亿元,加上军保、农保与“国民年金”(无职业者社会保险基金)未提足的负债合计达17.8万亿元(截止到2015年6月)[17]。目前社会保附带潜藏负债余额合计是每年台湾当局财政预算的9倍之多。
其中,多个专项社保基金面临破产的风险。以人群最大的劳工养老保险基本观察,参保人数接近上千万人,截止到2016年4月基金余额为6519亿元,如果不改革,采取适当的“多缴少领”办法,预计到2027年基金将用完,面临破产的挑战。
就社会保障角度看,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将会造成债留子孙的严重后遗症,即未来年轻一代的年金负担过重,生活压力过大。据推算,目前台湾有近18万亿元的社保基金潜藏负债,以目前20岁以下的530万人口计算,每个孩童背负了340万元的退休金负债。若再加上台湾当局6万亿元、地方政府1万亿元的政府债务,这些孩童就平均背负了470万元的公共债务,而且再过两年就会突破500万元[17]。这虽然是理论上的数字计算,但足以說明人口老化、社保基金需求增加与未来年轻一代的负担压力增大的严峻现实问题。
在人口老化与少子化不可逆的趋势下,唯有进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马英九执政时期就努力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即所谓的“年金改革”,但因涉及不同群体的个人切身利益,加上复杂的政治问题,未能完成这一改革使命。蔡英文上台后,也将“年金改革”作为五大社会改革的重中之重。尽管这一改革面临很大的争议与困难,但没有其他选择,必须改革,且总体改革的方向是“多缴少领”:延长退休年龄(目前教师是“75制”,公务员由“80制”改为“85制”,劳工于2018年延长到61岁,每两年延迟1年,最后普遍延迟到65岁,公教人员大约也同时延迟到65岁),提高保险费率(改革平均投保薪资年资计算办法,职业群体实现统一计算标准),降低领取退休年金的所得替代率(缩小不同职业与群体的所得替代率,主要是降低军公教人员的所得替代率),降低年金支付标准。
(五)老年人口的“长期照顾”成为新的课题
人口老化的另一后果是失能老年人口的显著增加,未来需要长期照顾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据台湾学者估计,2015年台湾失能人口约为75万人,预计到2031年达到118万人,其中93万人是老年人[9]。这些人需要专门的服务人员照顾。“长照人员”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行业,也是一个人力严重短缺的行业,学者估计2017年长照人力短缺达5万人。
台湾从2000年开始研究与推动“长照制度”,尤其是加强长照服务人员培训。2003—2014年,接受长照服务训练的人数达6万多人,但就业率只有六成,实际进入职场的只有约3万人。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统计,到目前已取得长照服务结业证书者达11万人,但2015年实际从事长照服务者仅2.3万人,与其月平均收入为2.2万元的低工资密切相关。多年来,台湾从事老人照顾的服务人员主要依靠外籍劳工,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主要是照顾老人为主)的外籍服务人员从2002年的12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22万人,其中70%是印尼人[18]。不仅长照服务人员严重不足,而且相关的护理师、物理治疗师等专业医事人员也严重不足。
2007年,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公布了“长期照顾10年计划”,以建立完全的“长照体系”。依服务对象界定与预估,需要长期照顾的人口即失能人口(包括65岁以上老人、55~64岁的山地原住民、50~64岁的身心障碍者及其他独居老人),2007为2.5万人,2010年为2.7万人,2015年为3.3万人,2020年近4万人[2]。另外,由于家庭人口规模缩小,户均人口从1990年的4人减少为2015年的2.77人,独居老人增多。台湾列册需要关怀照顾的独居老人(遗孤老人)比率自2000年到2015年增长了20%[18]。
2015年5月,台湾三读通过“长期照顾服务法”,并于2017年5月正式实施。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为应对人口老化与失能人口的增加,大力推动“长照制度”。事实上,蔡英文在选举时就提出“十年长照2.0计划”,成为蔡英文执政后积极推动的“五大社会安定计划”之一。该计划主要包括:以增税方式筹措每年400亿元经费,成立基金支付特约服务机构,成立“长照局”统一管理支付,扩大居家服务,强化社区医疗体系与长照体系,用4年时间完成社区长照基础建设。其中,长照服务对象范围扩大,从原65岁以上老人、55岁以上山地居民、50岁以上身心障碍者、65岁以上IADL独居者扩大到50岁以上失智症患者、55岁以上平地原住民、49岁以下身心障碍者、65岁以上衰弱者(其中50岁以上失智症患者与65岁以上衰弱者均需经过失能评估确认),扩大了服务对象,让更多民众受惠,即服务对象从51.1万人增加到73.8万人;同时服务项目也由8个扩大到17个[19]。这一“长照制度”的改革与推行,是一项很好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但面临很大的财务压力,长照服务与医事人力短缺更为严重。如何应对人口老化尤其是失能老年人口显著增加问题,是台湾面临的重大挑战。
[参考文献]
[1]高雅玲:《全球高龄化商机与挑战》,《经济前瞻》(台北)2014年第9期。
[2]吴淑妍:《因应人口高龄化的居家照护产业发展》,《经济前瞻》(台北)2014年第9期。
[3]雷光函:《最老国家日本26%破65岁》,台湾《联合报》2016年6月30日。
[4]李顺德:《蔡政府遇“少子化+高龄化”双重危机》,台湾《新新闻》第1562期。
[5]钟宁:《台湾老年人口首度超过小孩》,台湾《工商时报》2017年3月10日。
[6]丘采薇、潘姿羽:《台湾老人首度比小孩多》,台湾《联合报》2017年3月10日。
[7]沈婉玉:《不婚、不生、老化激增》,台湾《联合报》2016年6月27日。
[8]社论:《台湾人口推估报告里的五大隐忧发生之后》,台湾《工商时报》2016年9月18日。
[9]崔慈悌:《薛承泰:人口老化,10年內红色警戒线》,台湾《工商时报》2015年9月3日。
[10]于国钦:《高龄化,潜在劳动力史上新低》,台湾《工商时报》2016年12月26日。
[11]张锦弘、冯靖惠:《未来两年大一新生将少3万人》,台湾《联合报》2016年5月2日。
[12]洪欣慈:《六成大专明年减招万人》,台湾《联合报》2016年12月27日。
[13]洪欣慈:《学生少、注册率糟,不再是私大退场条件》,台湾《联合报》2017年2月8日。
[14]简立欣:《高教空洞化,台师生疯赴陆》,台湾《旺报》2016年5月1日。
[15]王彩鹂:《少子化!今年大一生大减1.5万人》,台湾《联合晚报》2016年7月5日。
[16]王剑洪:《如何构筑黄金屋,孩子多想想》,台湾《联合报》2016年7月1日。
[17]社论:《年金改革的最终目标:不要债留子孙》,台湾《工商时报》2016年6月7日。
[18]施柏荣:《台湾面临独老化,智慧照护得有温度》,台湾《工商时报》2017年1月1日。
[19]彭祯伶:《超高龄社会,长照2.0上路》,台湾《工商时报》2016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