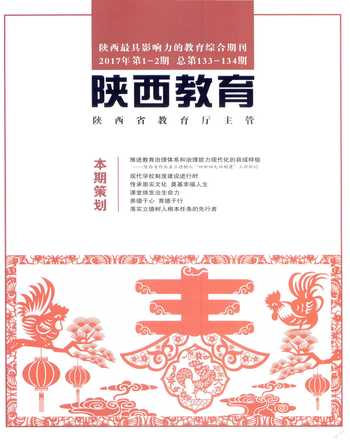叙事的力量
谢啸实
编者按:2016年,是中国电影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连续十年以百分之三十左右速度增长的中国电影票房,在2016年第一次滑落。广电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为457.12亿。而在2016年年初,业界对于这一年的票房估计是600亿。泡沫的跌破不是坏事,一个被高估的电影市场,早晚有一天会露出本来的样貌,从市场的长期良性发展而言,这一天来得越早越好。实际上,持续10年的疯狂增长,已经让中国电影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一下前行的方向。电影票房下滑,原因固然众多,但对于电影而言,内容为王天经地义。而内容的虚浮和缺失一直是中国电影最大的硬伤。2016年的华语电影延续了这种缺失,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17年的第一篇稿子,我们就以2016年一些极具代表性的华语电影为例,探讨内容对于电影的重要性。
最近看了一集关于毕加索的纪录片,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在西方主流评论体系中,非常坚决的没有之一这个后缀,毕加索以令世人震惊和彻底颠覆了传统绘画方式的抽象绘画闻名。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接受到的信息都是,毕加索是个天才的抽象派画家。然而,事实上,作为一名美术教师的儿子,毕加索自幼接受的是传统路数的美术教育,在16岁的时候,他的古典绘画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于是,在这里,一个讯息被非常强烈地传达出来,毕加索高超的极富表达力的抽象绘画能力是建立在严谨规范的传统绘画技法训练之上的。
为什么会在这里谈毕加索?答案很简单,这部纪录片,更加确定了我的一些关于电影创作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正如乍一看令人难解其意的现代抽象绘画来自于通俗易懂的古典绘画,所有能拍出好的以不单纯讲故事为目地的电影的电影人,他们电影生涯的起步阶段,都做过一件无一例外的事情——练好叙事的本领。
稍微关注华语电影的观众都会注意到现在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那就是:我不想拍一部只是讲故事的电影。这句话的意思不难理解,并不是说导演不想在电影中讲故事,实际上,任何一部电影,无论是不是剧情片,无论故事性多么薄弱,只要有时空,有人,只要能被语言叙述出来,它最终就是以故事的方式呈现。无论导演想表达多么复杂的东西,归根结底,导演的意图,还是要通过他叙述的内容传达出来,只不过,这些导演总想在故事之外,再说点什么。而有的时候,想要的东西有点多,到最后,难免忘记初心,失却了一部电影最核心的元素——讲故事。
到年底为止,2016年最受到关注的几部国内电影,无论是走商业销售路线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摆渡人》,还是实打实的独立电影《长江图》《路边野餐》,没有一部是把心思放在讲一个无需二度阐释的故事上面的。这几部影片涵盖了商业和艺术两种大的电影类型,但是却不约而同选择了不以常规方式叙事。而这种选择中明显充满了一种叫做志不在此的趣味。以上几部电影中,两部商业片都是改编自文学原著,自然也延续了原著的特质和精神。两部改编作品本身风格截然不同,总体而言,《罗曼蒂克消亡史》是正面评论较多,而《摆渡人》局面就有些尴尬,让苦心等待的很多影迷极为失望。不过,在关于它们的众多负面意见中,有一条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故事讲得不好,换个说法,没讲清楚。这非常有意思,两部风格和内容截然不同、整体质量也有差别的电影,却在同一个问题上受到批评。当然,有人说不好,就会有人说好。这里不为它们定论。数十年后,影史如何评价,现在我们无从知道,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已经在影史中具有的作用——那就是它所代表的电影思维,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发展方向产生多大影响。或者说,它说明了这样的一种思维在华语电影界已经占据了多大的分量。
和以往将重心放在叙事之外的华语电影相比,《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文本,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是很扎实的。有一定小说阅读量的观众,都很容易接受并且理解作者如此做的用心。对于小说而言,摆弄结构的目的和电影创作是一样的,创造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并借此表达小说主题,最终使得形式和内容完美结合。在此基础上写就的剧本,拍成的电影,在艺术追求上,并无二致。当然,最终的结果如何,这可能会受制于诸多因素,如观众的接受度,创作人自身的才华还有临场表现。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稍微有点艺术追求的电影人,都希望拍摄出与众不同的电影,尤其在题材其实是有限的情况下。对于《罗曼蒂克消亡史》而言,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传奇故事,是华语影视圈常常会涉及到的题材,常规叙事,很难出新意。这样的情况下,打乱时空,多线叙事,就成了推陈出新的好办法。而对于文本而言,某种程度上,结构就是内容。很多一流的现代作家,也都在这条路上做着探索,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伟大作品。因此,导演的叙事理念是创作的正途,算不得哗众取宠。但是,目前关于影片,存在不少的质疑之声。而其主要内容,就是它令人费解的叙事方式。而各种看不懂的呼声此起彼伏,又产生了很多阐释电影内容的文字。抛开所有借机宣传的商业目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部需要额外解读的电影。于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产生了,对于这个故事而言,这是有必要的么?然后,默默回想,总觉得,这些年来,似乎在华语电影范围内,这方面的声音越来越多。排除观影不认真的因素,每当我看到关于看不懂之类的言论,都忍不住会想一下,为什么一部普通的院线电影,要拍到常常让观众看不懂,需要有人发文替导演和编剧解读他们的创作思路和目的。这似乎有些荒谬。《罗曼蒂克消亡史》以及它無法与之比拟的《教父》和《美国往事》,三部影片在渴望达到的气度和格局上较为相似,然而,后面两部影片,除了因为太长,人物众多,背景繁复会要求观众必须集中注意力之外,它们不存在看不懂故事的可能性。这不由令人感到,很多时候,花样翻新的结构并不是让电影出众的良方,反而是遮掩叙事功力不够的技法。当然,不能以此断言程耳会如此写他的黑帮故事的原因,至少,哪怕是当年一部电视剧《上海滩》,都已经切断了所有想要以常规叙事取胜的同类影视剧的退路。导演的心思,由此可以理解。但还是那句话,对于当前这个故事,这样的影片结构合适么?更直白一点的说法是:这个剧情是否能掌控结构,结构又是否能带动剧情。
《摆渡人》没有结构上的复杂性,它的问题不是看不懂。而是文本在经过改编后,因为表现形式的不同,一定程度上背離了大家对一部电影的期待,比如台词占据影片大部分的篇幅。这固然是直接从文本而来的特点,但在一部电影中,这就是问题。这导致因为过度迷恋台词,使得原本该由人物行为支撑起来的故事,没有充足的空间。至于演员的表演、台词内容本身、整部影片的格调、导演手法的生疏等,这些是更专业更细节的问题,不属于故事缺乏的范畴,而是故事讲的不够好。这又是另外的话题了。
相比商业片对驾驭流畅叙事的无力,所谓的艺术电影天然被认为可以没有清晰的叙事,可以是残缺破碎的。事实上,这也许是中国艺术电影的独特现象。印象中,参与全球三大艺术电影节的参展影片,也基本都是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哪怕是圣丹斯这样的独立电影节,参与其中的大部分电影也是要说故事的,剧情甚至可能非常饱满。不重叙事在国内艺术电影中由来已久,不过《长江图》将这种意趣拔到了新高度。这部电影大概是2016年在院线出现过的国产电影中最难懂的一部。虽然是以长江的壮美风景为号召,但是毫无疑问,长江只是背景,观众需要的,是知道在角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一点都不明白也冤枉了《长江图》,可是我觉得,观众走出影院的时候,希望自己比较清楚地知道刚看过的电影讲了什么,并不是太高的要求。但我想,大部分的人会如我一样对影片内容深感迷茫。记得在为这部电影辩解的声音中,有类似于这部电影的观念比较超前之类的话语。在听过了太多类似言语,失望了太多次之后,我很想肯定地说,《长江图》就是叙事无力,超前只是欲盖弥彰的遮掩。《路边野餐》在投资和影片背景上无法和上面几部相比,但鉴于它是2016年小成本艺术电影中名气最大,口碑最好的,且在国外获了不少奖项,那么它对有志于成为导演的年轻人具有的影响力就不应该被低估。这部影片的不重叙事是很明显的,也符合此类影片爱好者一贯的观影口味,对于这样的电影,观众本能的需求都是叙事的弱化。看起来,情况恰是如此。它因为无故事而赢得了属于它的观众的喜爱。不否认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需要各种各样的艺术尝试,但是,当《路边野餐》中长时间的风景画面出现的时候,我想,考虑一下如何恰当抒情的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而这,正是叙事技巧的一部分。
《一千零一夜》中,那个叫做山鲁佐德的女孩子,用每天讲一个故事的方式拯救了自己的生命,这充分体现了叙事的力量;或者说,讲好故事的力量。对于有一百二十一年生命的电影而言,叙事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毕竟,所有电影天才的不拘一格,都起步于扎实的叙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