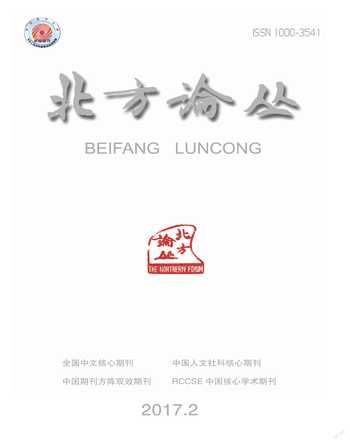二十世纪“龙学”的经典之作
戚良德
[摘要]詹锳先生是20世纪“龙学”史上的大家,他以《文心雕龍义证》一书集成了《文心雕龙》的校注成果,不仅成为大陆第一个《文心雕龙》的会注集成本,而且至今亦无出其右者。这部皇皇巨著广征博引,严谨细密,以集解汇注的形式探求《文心雕龙》的本义,以证得对《文心雕龙》原文的确解,从而完成了一部既有会注与集成之功,又具个人理论色彩的“龙学”巨著,成为中国大陆20世纪“龙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亦成为百年“龙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詹锳;龙学;《文心雕龙义证》
[中图分类号]I20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44-06
Abstract: Zhan Ying, a master in the history of 20th-century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epitomizedfruitful recensionsand commentariesin his book, Wenxin Diaolong Yizheng, which wa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corpus of Wenxin Diaolongs commentaries. This magnum opus quoted copiously from many sources and developed rigorous logic to explore the true nature and exact understanding of Wenxin Diaolong by gathering various commentaries, thusmaking a great book on Wenxin Diaolong with not only gathered commentaries but alsounique personal theory. It is a landmark in 20th-century study of Wenxin Diaolong and even a classic work in the one hundred yearshistory of Wenxin Diaolong study.
Key words:Zhan Ying;study of Wenxin Diaolong;Wenxin Diaolong Yizheng
《文心雕龙》是一部只有三万七千多字的书,但研究它的专著中,却不乏大部头的作品。在20世纪的“龙学”史上,有两部规模较大的著作,一是我国台湾地区李曰刚先生《文心雕龙斠诠》(1982年),180余万字;二是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34万余字。这两部著作分别成为海峡两岸二十世纪“龙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尤其是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一书,被收入影响极大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中,一直被作为“龙学”和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参考书目,可以说已成为具有集成性的“龙学”经典。这部皇皇巨著广征博引,严谨细密,做到了“把《文心雕龙》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处和典故,都详细研究,以探索其中句义的来源”[1](p.3)。正如詹福瑞先生所说:“这部书,既反映了詹先生几十年研究《文心雕龙》的创获,又可以看出自古及今历代研究《文心雕龙》的成果,是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之后,又一部全面而谨严的证义为主,兼有汇注、集解性质的本子。”[2](p.126)
一、版本与汇校
《文心雕龙义证》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其集成性,并首先表现在版本搜罗和汇校之功上。翻开《文心雕龙义证》,开篇的《序例》之后紧接着就是《〈文心雕龙〉版本叙录》。詹先生说:“《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可是由于古本失传,需要我们对现存的各种版本进行细致的校勘和研究,纠正其中的许多错简,才能使我们对《文心雕龙》中讲的问题,得到比较正确的理解。”[1](p.9)正是这种强烈的版本意识,促使詹先生多年来跑遍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济南等地,搜罗《文心雕龙》的各种版本,从而为《文心雕龙义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詹先生之前,于版本校勘方面用力颇深、成果显著的学者主要是王利器和杨明照两位先生,其代表作分别是《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和《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詹先生于“杨王二家所校各本”“大都进行复核,写成《文心雕龙版本叙录》”[1](p.4),显然具有集成、补正之功。詹先生所录从最早的刻本即元至正本到近代发现的敦煌残卷中的唐写本,共32种。他对这32种《文心雕龙》的不同版本都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还特别强调“眼见为实”,所录入的版本除了乾隆四年(1739年)刊李安民批点本《文心雕龙》和顾千里、黄丕烈合校本《文心雕龙》未见外,其它版本皆为自己亲眼所见。詹先生着重介绍的版本主要有:元至正本,明徐火勃校汪一元私淑轩刻本,明曹学佺批梅庆生第六次校订本,明谢恒抄、冯舒校本。在王利器和杨明照先生的著述中,这几个版本或信息不够详细,或付之阙如。
也正是有此强大的版本学基础,《文心雕龙义证》一书基本网罗了众家的校勘成果。比对各家所校异同,指出其中校勘错误,提出修订意见和说明,詹先生尽展自己的汇校之功。如《文心雕龙·宗经》篇有“义既挻乎性情”一句,其中“挻”字,各种版本不一,历来注家亦争论不断,詹先生引用了多家校勘成果予以对比说明:
《校证》:“‘挻原作‘极。唐写本及铜活字本《御览》作‘挺,宋本《御览》、明钞本《御览》作‘埏。按‘挺‘ 埏俱‘挻形近之误,《老子》十一章:‘挻埴以为器。‘挻与‘匠义正相比,今改。”桥川时雄:“极字不通。挺、极形似之误。挻字始然反。《老子》:‘埏埴以为器。《释文》引《声类》云:‘柔也。河上公注云:‘和也。”斯波六郎同意赵万里《校记》之说,谓应作“埏”,是“作陶器的模型”。又说:“此字又可作动词用,如《老子》第十一章‘埏埴以为器,《荀子·性恶》篇‘故陶人埏埴而为器,《齐策》三‘埏子以为人等。”潘重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埏盖‘挻之伪。《说文》:‘挻,长也。《字林》同。《声类》云:‘柔也。(据《释文》引)《老子》:‘挻埴以为器。字或误作‘埏。朱骏声曰:‘柔,今字作揉,犹煣也。凡柔和之物,引之使长,搏之使短,可析可合,可方可圆,谓之挻。陶人为坯,其一端也。”[1](p.61)
一字之校,詹先生慎重引用了王利器、桥川时雄、斯波六郎、赵万里、潘重规等五家校语,最后才按曰:“‘挻通‘埏,此处犹言陶冶。”[1](p.62)于此,不论我们是否同意詹先生的结论,对这个字的来龙去脉总是了然于心了。
詹先生不仅充分罗列并运用前人的校勘成果,而且进一步补证前人。如《才略》篇有“傅玄篇章,义多规镜;长庾笔奏,世执刚中;并桢干之实才”等句,其中“桢干”二字颇有异文。詹先生先引述《文心雕龙校证》:“‘桢,冯本、汪本、两京本、王惟俭本、《诗纪》《六朝诗乘》作‘杶。”再引《文心雕龙校注》:“‘桢,黄校云:‘汪作杶。按元本、弘治本、活字本、张本、两京本、胡本、训故本、四库本亦并作‘杶;《诗纪别集》引同。皆非也。《程器》篇赞:‘贞干谁则?‘贞为‘桢之借字,可证。”然后举出两条新的佐证:“《书·费誓》:‘峙乃桢榦。‘榦亦作‘干。‘桢干,支柱,骨干。亦作贞干。《论衡·语增》:‘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贞干也。”[1](p.1818)显然,詹先生补充的两条证据极有说服力,不仅佐证了杨先生所谓“并作‘杶……皆非也”的结论,而且进一步证明无论作“桢干”还是“贞干”,皆有所据,则连“借字”之说亦可不必了。
补证之不足,詹先生还会对先贤的校勘意见予以商兑或指正,例如,《神思》篇有“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之句,对于这个“应”字,其校曰:
“应”字,元刻本、弘治本、佘本、王惟俭本、两京遗编本均作“胜”,那样和末句“垂帷制胜”的“胜”字重复。张之象本、梅本并作“应”,今从之。这两句说:所求于事物的是它的外部形象,而内心通过理性思维形成感应。《校注》《校证》均谓“应”字当作“胜”,解说迂曲,今所不取。[1](p.1008)
可以说,詹先生的选择是较为合理的,多数《文心雕龙》研究者也早已认可《神思》篇的这两句名言。不过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文心雕龙义证》的读者多未细察,我们既然说到了,当为詹先生一辩。查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其明确表示各本“并作‘胜,与下‘垂帷制胜句复,非是”,而认为:“文津本剜改为‘媵,是也。尔雅释言:‘媵,送也。‘心以理媵,与上句‘物以貌求,文正相应。‘媵与‘胜形近,易误。章句篇‘追媵前句之旨,元本等亦误‘媵为‘胜,与此同。附会篇:‘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是舍人屡用‘媵字也。”[3](p.234)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龙校证》亦云:“案‘胜疑‘媵误,《章句》篇:‘追媵前句之旨。‘媵即原誤作‘胜。《附会》篇:‘媵句憔悴。”[4](p.190)
显然杨、王二位先生均以“胜”为“媵”字之误,则詹先生所谓:“《校注》《校证》均谓‘应字当作‘胜,解说迂曲”云云,似乎是误解了两位先生,但以詹先生之严谨,这样低级的错误自不应有,则其必事出有因。细思之下,笔者觉得上述詹先生所言,原本应是“《校注》《校证》均谓‘应字当作‘媵”,这才是杨、王二书的实际,詹先生不会不察;只是《文心雕龙义证》一书乃繁体字版,排版过程中把詹先生原稿的“媵”字误为繁体的“勝”字,后未能校出而已。詹先生所谓“解说迂曲,今所不取”者,所指正是杨、王二位先生论证“应”当为“媵”之语。若果真如此,这可真是一个小小的历史玩笑,杨、王二位先生均力证《文心雕龙》各版本误“媵”为“胜”,但詹先生不以为然,而其《文心雕龙义证》却正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自然,詹先生于此可能一直未有察觉作为“龙学”经典著作,《文心雕龙义证》一书多有重印,笔者所见1989年初版本和1994年初版二印本的《神思》校语,均误“媵”为“胜”,希望出版社再印时改正这一关键性的小错误。,更不意味着这就足以证明杨、王二位先生所谓“应”当为“媵”之说。但这不经意的一字之错,可能伤及三位“龙学”大家,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版本的校勘实在是《文心雕龙》乃至古代文化研究的根本和基础,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斯其谓乎?
二、会注与集解
《文心雕龙义证》一书的主体部分无疑是对《文心雕龙》文本的会注和集解。詹先生明确指出:
本书带有会注性质。《文心雕龙》最早的宋辛处信注已经失传。王应麟《玉海》《困学纪闻》中所引《文心雕龙》原文附有注解。虽然这些注解非常简略,本书也予以引录,以征见宋人旧注的面貌。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大多采录明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简称“梅注”)、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简称“训故”)。明人注本目前比较难得,王惟俭《训故》尤为罕见。兹为保存旧注,凡是梅本和《训故》征引无误的注解,大都照录明人旧注,只有黄本新加的注才称“黄注”。[1](p.5)
可见,詹先生的“会注”,首先是汇集宋明以来至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龙》旧注成果。这些成果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多,但却代表了数百年《文心雕龙》研究的成就。詹先生以此为基础,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他又说:“全书以论证原著本义为主,也具有集解的性质,意在兼采众家之长,而不是突出个人的一得之见,使读者手此一编,可以看出历代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看出近代和当代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有哪些创获。”[1](p.7)如此明确的思路和目标,使得詹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成为大陆第一个《文心雕龙》的会注集成本,至今亦无出其右者。
既为“会注”,当然是要汇聚各家的成果,但却并非简单地罗列在一起,而是仍然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而选择不仅要具备犀利独到的眼光,更要有尽可能广泛的范围,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闻见广博。因此,真正做好古籍的会注集成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对“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而言,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比兴》开篇有云:“《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1](p.1333)其中“风通而赋同”一语,向为理解的难点,其“会注”就显得格外必要了。正因如此,詹锳先生不惜笔墨,对这五个字进行彻底索解[1](pp.1335-1336)。刘勰的五个字,詹先生用了一千余字来注解,规模不可谓不大,但从其引录可见,涉及“龙学”八家成果而已,真要做到囊括无遗,篇幅肯定还要成倍扩大,但那显然是不可取的。这里便见出了詹先生的“会注”之功。他特地分段标注,正显其用心所在。第一段是王利器、黄侃、范文澜和杨明照四家之说,“龙学”大家的校注成果我们看到了;第二段是李曰刚之说,代表我国台湾地区“龙学”的基本观点;第三段和第四段都是郭绍虞先生的见解,却不是有关《文心雕龙》的注释,而是来自郭先生的两篇文章,这便充分显示出詹先生独特的眼光和取材;第五段和第六段是郭晋稀和牟世金先生的见解,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大陆最有影响的“龙学”观点。如此,我们不能不说,詹先生的“会注”决非不加选择的简单罗列,而是颇为用心的集其大成。
其实,上述这种“会注”固然见出功力,选择固然需要眼光和视野,但还不能完全代表“集解”之功。在笔者看来,上述“会注”还只是汇合别人的见解,尽管这种汇合有着充分的取舍,体现了选择者一定的学养,但其中所“会”,毕竟都与所“注”的内容密切相关,因而范围毕竟还是有限的。而真正的“集解”,固然首先要集中别人的见解,但更要在此基础上,提出集解者自己的意见,至少也要显示某种倾向性,则集中哪些见解,其选择性就主观得多了,其范围也就大得多了,从而对集解者的学术水平也就要求更高了。如《原道》开篇有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1](p.2)其中“文之为德也大矣”一句,历来为解释重点和难点,各家说法不一,但詹先生却没有采用“会注”的方式,没有引用任何一家对这句话的注释,而是引用了《论语》《中庸》《四书集注》《周易正义》等语来进行释义,其云: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朱注:“为德,犹言性情功效。”此处句法略同,而德字取义有别。《易·乾·文言》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德即宋儒“体用”之谓,“文之为德”,即文之体与用,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文之功能、意义。重在“文”而不重在“德”。由于“文”之体与用大可以配天地,所以连接下文“与天地并生”。[1](p.2)
显然,这些引文都不是对《原道》开篇这句话的直接注释,是否引证,引证哪些,完全取决于注释者的判断和选择,而这又都成为其对刘勰原文进行阐释的基础和根据。这里便更充分地体现出詹先生的学养和功力了。之所以要引用《论语》和《中庸》的话,是因为刘勰的句式与它们相同,但詹先生随后指出:“而德字取义有别”,至于何处“有别”,则再引《周易正义》之语,然后作出判断;这一判断虽以之为据,但重在解释刘勰,因而有很大的跳跃和跨度,不仅解释了什么是“文之为德”,而且还对下文“与天地并生”的逻辑予以点出。如此“集解”,既体现了“无征不信”的原则,又充分表现了詹先生对《文心雕龙》的理解,因而使得《文心雕龙义证》一书不只是简单的“会注”之作,而是成为“以论证原著本义为主”的理论著述。
在广泛征引各种元典和經典解释《文心雕龙》的同时,詹先生还充分利用刘勰自己的说法证明刘勰,所谓“参照本书各篇,展转互证”[1](p.3),也就是利用可靠的“内证”,对《文心雕龙》进行阐释。如《章表》篇“赞曰”有“肃恭节文”一语,詹先生就利用《文心雕龙》中的多篇来进行互证:
《乐府》篇:“辞繁难节。”《诔碑》篇:“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书记》:“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镕裁》篇:“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附会》篇:“夫能县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斟诠》:“节文,谓礼节文饰也。《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管子·心术上》:‘礼者因人之情,像义之理,而为节文者也。”[1](p.850)
这样的互证,有些可能一望而知,有些则出于研究者自己的判断,完全取决于对《文心雕龙》一书的整体把握和融会贯通程度。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普及的今天,我们或许觉得这不算难事,但在詹锳先生作《文心雕龙义证》的时候,能够如此信手拈来,没有遗漏,却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这段注释还不仅仅是“互证”,而是在集中了刘勰的相关说法之后,又引用了李曰刚先生的注释,予以进一步的说明。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詹先生除了引录,没有多余的话,那表示他同意李先生的概括,即“节文,谓礼节文饰也”,可见《文心雕龙义证》虽皇皇巨著,长逾130万言,但詹先生仍是惜墨如金的。二是李先生的注释主要是引经据典,詹先生予以全部引录,这既是以经典证刘勰,又不埋没李先生发掘之功。这样的集解方式,詹先生在该书中多有运用,其良苦用心,我们不得不察;其良好学风,值得我们学习。其《序例》有云:“当代著述,笔者认为可资发明《文心》含义者,多径录原文,注明出处。各家所引古书资料,本书注明转引。有时笔者原稿已有引文,而他人已先我发表,也说明已见某书,以免‘干没之嫌。”[1](p.6)这正是“虽杼轴于予怀,怵佗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5](p.145),其谦谦儒风,令人景仰。
作为一部会注和集解之作,取材广博是自不待言的。根据詹锳先生所列“主要引用书目”,《文心雕龙义证》一书参考到的经传子史和汉晋以来的文论约70种,具体到每一篇的校注集解,自然还有大量没有列入这个书目的书籍或篇目。至于为研究者们所习见的资料,该书更是详加搜罗,片善不遗。由“主要引用书目”可知,詹先生共参考了中外现当代“龙学”著述九十多部,相关著述二十多部,甚至还有一些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尤可称道者,詹先生不仅大量参考了近代的各种资料,而且有些资料极为难得,像听课笔记,詹先生亦注意搜罗,甚至还对某些信息缺失的笔记进行考订而加以利用。如《文心雕龙义证》之“引用书名简称”的最后一条是“朱逷先等笔记”,詹先生说:“朱逷先、沈兼士等听讲《文心雕龙》笔记原稿,只有前十八篇。朱、沈皆章太炎弟子,疑为章太炎所讲。”[1](p.38)詹先生多处引用了这个“疑似”的课堂笔记。此悬案后经周兴陆先生采用纸张鉴别的手段,证实了詹先生猜测的正确性[6]。作为首位大胆提出此朱、沈二人《文心雕龙》课堂笔记乃章太炎在日本“国会讲演会”之演讲记录的学者,詹先生对“龙学”史和章氏文学理论的研究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此外,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心雕龙》研究来说,我国大陆之外的“龙学”成果并不如今日这般容易检索和得到。《文心雕龙义证》的集大成还表现在它不仅汇集了常见的我国大陆学者的成果,而且搜罗了许多我国台湾地区、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海外学者的成果。我国台湾地区的潘重规、李曰刚、张立斋、王金凌、黄春贵等人的观点,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饶宗颐、石垒等人的主张,以及日本的户田浩晓、兴膳宏、目加田诚、斯波六郎等人的见解,我们都可见到,甚至在“主要引用书目”中还列举有“匈牙利英文书目”,这在当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三、释义与评说
《文心雕龙义证》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其集成性,但却决非一部资料性的工具书,而是具有重要的个人见解和理论色彩的专著。尽管詹先生说这部书“具有集解的性质,意在兼采众家之长,而不是突出个人的一得之见”,但它又是“以论证原著本义为主”[1](p.7)的一部著作,因而与一般的会注集解之作是颇为不同的。对此,詹福瑞先生曾经明确指出过。他说:“这部书虽有集解性质,然其主旨则是论证原著的本义。故书中对《文心雕龙》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处和典故,都详细研究,悉心探索其中句义的来源,以求得对本义的正确理解。”[7](p.310)笔者以为,福瑞先生的这一说法是深得詹锳先生之“用心”的。
从著述形式上说,《文心雕龙义证》当然是一部以校勘与注释为基础的著作,但《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理论之作。詹先生既以“义证”为目的,则最终能否得“证”其“义”,仅仅靠网罗众家之见,显然是难以完成的。实际上,我们上面已经看到,从“会注”到“集解”,詹先生在一步步完成“义证”的目标,这是明确而坚定的。《文心雕龙·论说》有云:“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1](p.701)刘勰认为,注释类的文字,可以看成是分散之论;其虽掺杂于文中而与论文有别,但汇总起来仍是完整之论。可以说,《文心雕龙义证》一书正是很好地实践了刘勰的主张。这当然得益于詹先生自身良好的理论素养及其对《文心雕龙》的精心研究。其以《刘勰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风格学》等理论专著作基础,《文心雕龙义证》对刘勰文论思想的阐释,虽然字数不多且分散为论,却往往具有点睛的性质,与前两部著作可谓異曲同工。
如所周知,詹先生建构了《文心雕龙》的风格学理论体系,他甚至将整部《文心雕龙》都看作是风格学的论著,《文心雕龙义证》一书也明显贯穿了这一观点。在《序例》中,詹先生就指出:“笔者希望能比较实事求是地按照《文心雕龙》原书的本来面目,发现其中有哪些理论是古今中外很少触及的东西;例如刘勰的风格学,就是具有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对于促进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克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会起一定的作用。这样来研究《文心雕龙》,可以帮助建立民族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以指导今日的写作和文学创作,并作为当代文学评论的借鉴。”[1](pp.7-8)正因如此,在很多篇目中,詹先生都会把自己的风格学思想熔入其中进行解说。除此之外,无论《文心雕龙》的创作论、批评论、修辞学以及文学史论等,詹先生都在引经据典的同时,不忘对其进行理论的阐发或评点,自然也常有远见卓识。如《神思》篇“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二句,詹先生一句注曰:“这句照唐宋散文的写法是‘思理之为妙也,意指‘形象构思的妙处是。”另一句注曰:“即物我交融,也就是人的精神和外物互相渗透。”[1](p.977)这种着眼文论的释义不但是明显可见的,而且顺便指出以骈体论文的《文心雕龙》与唐代散文之句法的不同,其点睛之妙,可谓无愧“雕龙”之称。又如该篇“窥意象而运斤”句,詹先生注曰:“‘意象,谓意想中之形象……在西方心理学中,意象指所知觉的事物在脑中所印的影子;例如看见一匹马,脑中就有一个马的形象,这就是马的意象。其所以译为‘意象,是因为和王弼的解释类似……这句是说:有独到见地的作者,能够根据心意中的形象来抒写。”[1](pp.983-984)这里的注释不仅同样从文论的角度入手,既着重阐释“意象”一词,又不忘整句话的意蕴,而且詹先生充分发挥熟悉心理学之长,把古今中外熔为一炉,把自然与人文予以贯通,亦可谓“深得文理”了。
当然,作为一部“会注”和“集解”之作,詹锳先生既然明确宣称“无征不信”,则其理论阐释亦自然不会架空立说,而是充分引证各种资料,从大量相关的论说中提炼自己的观点,陈说自己的看法。我们以《风骨》篇的“题解”为例,来看一下詹先生是如何把大量的资料与自己的陈说相结合的。仅晋代至中唐时期有关“风骨”的资料,詹先生便列举了《世说·赏誉》篇、《世说·容止》篇、《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宋书·武帝纪》《南史·宋武帝纪》《南史·蔡樽传》《北史·梁彦光传》《新唐书·赵彦昭传》、高适《答侯少府》、谢赫《古画品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后画录》、齐王僧虔《能书录》《法书要录》、梁武帝《书评》、梁袁昂《书评》、唐李嗣真《书品后》、唐张怀瓘《书议》及《书断》、唐窦泉《述书赋》《魏书·祖莹传》、杨炯《王勃集序》、卢照邻《南阳公集序》、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卢藏用《陈氏别传》《大唐新语》、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以及《河岳英灵集》刘昚虚小序、陶翰小序、高适小序、岑参小序、崔颢小序、薛据小序、王昌龄小序,乃至日本近藤元粹辑评本《王孟诗集》诗话部分等。而对于近人和当代学者的成果,詹先生先后引用了梅庆生引杨慎之注解、曹学佺之批语、马茂元《论风骨》、寇效信《论风骨》、刘禹昌《文心雕龙选译·风骨》、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关于“风骨”的论述以及钱钟书《管锥编》、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论著中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关于“风骨”的资料,尤其是刘勰时代前后的资料,近乎一网打尽了;在20个世纪80年代,能做到如此琳琅满目而洋洋大观,仅翻检之劳亦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料,詹先生又是如何评说的呢?在引证谢赫《古画品录》之“六法”后,詹先生说:“气韵生动是其它各种要素的复合。创作能达到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是笔致。骨法用笔就是笔致,就是所谓骨鲠有力。”[1](pp.1041-1042)短短的几句话,由“气韵生动”而到“骨鲠有力”,也就很自然地把画论引入了文论,把《古画品录》与《风骨》篇联系在了一起。在列举了中唐以前的相关资料后,詹先生总结说:“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风骨一词在人物品评,画论、书评以及诗文评论中都是经常出现,而且它的含义是一致的。”[1](p.1045)这一总结与对“气韵生动”的解说遥相呼应,进一步说明不仅绘画与文章的“风骨”是一致的,而且与人物品评、书法也是一致的,从而六朝乃至唐代的“风骨”论就是一脉相承的了。如此,刘勰的“风骨”论便有了广阔的文学艺术理论背景,而刘勰之后的“风骨”论也不再是无源之水,则《风骨》篇这一空前的美学范畴专论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意义,也就不言而自明了。与资料引证之繁富相比,詹先生的几句评说可谓简洁之至,但又不能不说,其视野开阔而要言不烦,对理解众说纷纭的“风骨”论具有重要的帮助。至于在引证曹学佺对《风骨》篇的批语后,詹先生说:“曹学佺的意思是说,气属于风的一个方面,而在‘风骨二者之中,风又居于主导的方面。黄叔琳在《风骨》篇论气的一段加顶批说:‘气即风骨之本。纪昀又反驳黄氏评语说:‘气即风骨,更无本末,此评未是。这样一来,反而把问题弄混了。”[1](p.1046)这是引证之后的评说,评说之中复有引证,看上去有些缠夹,但这里詹先生之所以不惜笔墨,盖以涉及有关《风骨》篇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风骨”和“气”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见,《文心雕龙》的“会注”和“集解”,若非对“龙学”的历史和现实了如指掌,是难以做到有的放矢的,而进一步的释义和评说,也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义证》是一部既有会注与集成之功,又具个人理论色彩的质地优良之作;在20世纪“龙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
[参考文献]
[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詹福瑞.詹锳先生的治学道路与学术风格[J].阴山学刊,1992(3)
[3]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6]周兴陆.章太炎讲演《文心雕龙》[N].中华读书报,2003-01-22.
[7]詹福瑞.学者简介·詹锳[C]//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责任编辑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