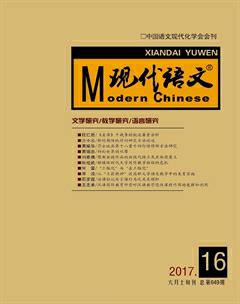叶朗与李泽厚审美愉悦观的比较
摘 要:叶朗质疑李泽厚的认识论美学观,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不同的审美愉悦论。叶朗重体验,强调主客观的统一,认为审美愉悦是情感体验的结果;李泽厚重认识,强调社会实践性,认为审美愉悦是建基于理性的“新感性”。他们又根据各自的美学理论将审美愉悦与生理快感进行比较,进而从不同方面把审美愉悦进行分层。
关键词:审美愉悦 生理快感 美的本质 理性与感性
一、引言
叶朗和李泽厚都是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大家,他们各从不同角度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审美愉悦观也是研究美学所必须触及和深入挖掘的一个重要范畴。叶朗对李泽厚审美愉悦观提出质疑。比较两者之异同,对于推进我国美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二、审美愉悦观的思想基石
叶朗的美学体系是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之上的,在中国美学理论上开辟一个新天地,进入一个新领域,把中国传统的“意象”理论融入其中,继承并发展了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的统一”[1]的美学观点,站在主客观统一的角度提出“美在意象”[2]的美学原理观点。基于此,叶朗展开对美感的讨论。在他的美学理论中,“美感”与“审美愉悦”没有明显的界线只是侧重点不同,各有其局限性。本文侧重研究“美感”的“审美愉悦”方面,作为叶朗的“美感”同义语来使用。叶朗反对李泽厚站在认识论角度脱离现实的审美活动所提出的“美感的矛盾二重性”,通过否定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的认识论,提出“美感不是认识是体验”[3]。叶朗认为认识活动是主体“通过思维,力图把握外物或实体的本质与规律”[4],它可以脱离主体孤立地研究对象世界。这样,认识活动必然是一种割裂主体与客体,将主客对立起来的活动,认为如果把审美活动变成认识活动,那就索然无味了,审美活动就不再引起审美愉悅了。因此叶朗认为人要获得美感应该“诗意”地生活,“跳出主客二分,用审美的眼光和审美的心胸看待世界,照亮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体验无限的意味和情趣,从而享受现在,回到人的精神家园”[5]。
而李泽厚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认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感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6]。而认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主客二分,将美看作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客观实体。在李泽厚看来,“美感体验说”是将直觉和理性对立和割裂开来,是对美感的直觉性质的夸张和歪曲,这类“把美感看作是与一切社会生活根本无关的错误学说,揭示了在所谓‘超功利的个人美感直觉中,实际含有着功利的客观社会性质”[7]。所以,李泽厚在谈论美感问题上提出要建立“新感性”,也就是人类心理本体。而且人类心理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人在审美活动中获得审美愉悦的途径也会随之扩大,比如艺术欣赏中的再创造程度不断提高,非美甚至是丑的审美对象也能进入审美活动进而引起审美愉悦。李泽厚在1956年提出了影响颇大的“美感的矛盾二重性”的理论,“一方面是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性的,另一方面是超感性的、理性的、功利性的”[8]。而由此得到审美愉悦也是具有二重性的。李泽厚的这些美学观点是基于人类本体论哲学也就是主体性实践哲学来研究的。他把美分为了三个层次,即审美对象、审美性质、美的本质,从而得出“美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它是自然的人化,因此是客观的,社会的”[9]。在此基础之上李泽厚又拟出了美感结构和过程图,他把美感分为了广义的美感即审美意识和狭义的美感即审美愉悦。在广义的美感上分为了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现阶段和成果阶段,狭义的美感即审美愉悦就等于第二个阶段即实现阶段。
三、审美愉悦与生理快感
叶朗从精神愉悦方面把审美愉悦与生理快感做了区分,虽然审美愉悦包含了生理快感,绝不停留在生理快感的满足,认为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愉悦性,这是一种精神享受。美感(审美愉悦)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愉悦,与生理快感是有区别的,认为这主要有两点区别:第一,美感(审美愉悦)是超实用的、超功利的,而生理快感则起于实用要求的满足,如口渴时喝水所获得的快感,肚子饿时吃饭所获得的快感;第二,美感(审美愉悦)的实质是情景交融、物我同一,美感(审美愉悦)必有一个审美意象,而生理快感受外来刺激所支配,它不可能出现情景交融、物我同一,不可能有审美意象。叶朗在谈论审美愉悦与生理快感的区别时,从直觉体验的美学思想出发,强调把理性排除在外,突出了审美愉悦的无功利性和直接的感性。但是,叶朗同时认为不能把生理快感与美感(审美愉悦)加以绝对化区分。首先,人的审美愉悦主要是依赖于视觉和听觉两种感觉,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视听两种感觉所引发的审美愉悦同时也引发一种生理快感,它们混杂在一起,如红色的鲜花使人感到热烈,蓝色的天空使人感到宁静,舒缓的音乐使人沉静,急速的旋律使人激情昂扬。其次,除了这两种感觉,其他感觉所获得的快感有时也会渗透审美愉悦当中,有时会加强或转化为审美愉悦,如中国园林艺术家常用“香”来营造美的氛围使人获得审美愉悦,“香”所引起的嗅觉快感就渗透到审美愉悦之中。
李泽厚和叶朗一样承认生理快感对审美愉悦的影响作用,但是认为审美愉悦与生理快感有质的区别。生理快感是五官生理引起的身体舒快,审美愉悦是社会存在引起的精神享受。不同于叶朗注重主观感性,李泽厚强调理性,强调“新感性”在审美愉悦中的作用,从不同的研究角度也把审美愉悦与生理快感进行区分:第一,审美愉悦是主动进行的心理活动,生理快感是被动的反应而已。就如人天生就有追求美的需要,但生理需求只是被动的满足;第二,审美愉悦是判断在先愉快在后,生理快感是愉快在先判断在后。与叶朗提出的审美体验的直接性,强调瞬间感觉的获取,排斥审美体验的认识、逻辑判断不同,李泽厚认为审美活动的过程包括感知、想象、理解、情感多种因素,审美愉悦的获得是这些心理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先有判断而后产生愉悦的。生理快感恰恰相反,是由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第三,审美愉悦是复杂多种心理活动的成果,生理快感是简单的感官感受直接产生。人们要获得审美愉悦必须调动多种心理功能,而生理快感不需要进行如此复杂的过程。
四、审美愉悦的层次
在叶朗的美学论述中从审美愉悦的深度和广度出发把审美活动所获得的美感(审美愉悦)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生活中最常见的,是对生活中一个具体事物所获得的审美愉悦。第二个层次是对整个人生的感受,我们通常称为“历史感、人生感”。第三个层次是对宇宙的无限整体和对绝对美的感受,我们称之“宇宙感”,这也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宇宙宗教情感和杨振宁所说的初窥宇宙奥秘的庄严感、神圣感、畏惧感。最高层次的审美愉悦与宗教所产生的宗教感是有共同点的,它们都是对宇宙生命的有限存在和有限意义的超越,是个体生命意义与永恒存在意义的统一。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不同的,审美体验是通过审美意象对主体自身存在的一种确证,是一种以个体为基点的超越性自由,而宗教感是排斥具体、个别、感性、物质并否定主体存在的,并没有获得超越性的自由。总体来说叶朗的审美愉悦根本上来源于超越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被局限在有限的天地之中,人与自身及其世界分离不能达到中国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在审美活动中,人可以通过审美意象超越主客二分,从而超越“自我”局限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审美愉悦就是在超越自我的基础上从心灵深处所引发的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而且叶朗所说的“审美愉悦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复合的情感体验”[10],可以和多种色调情感反应结合在一起。审美愉悦不仅仅是单一的、和谐的喜悦还可以是复杂的、不和谐的痛感,它包含了人类全部的情感体验,比如阅读小说时读者跟随情节或悲或喜或痛心或快活,这都能使读者在审美活动中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
与叶朗不同的是,李泽厚的审美愉悦层次分析是从愉悦享受方面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探讨的。李泽厚的美学理论注重情感本体“新感性”的建立,据此进行了审美形态的划分,分为了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个方面,这其实也是审美愉悦的三个层次。悦耳悦目是生理基础上又超出生理的感官愉悦,是生理性能与社会性的交织形成的。人们看到或听到美的事物不仅与人自身的生理诉求有关,而且受社会约束,“社会时代的积淀特征,这种积淀会渗透和呈现到耳目的感性之中”[11]。悦耳悦目主要是培育人的感知,是人类心理即情感本体成长的见证。悦心悦意远远不止于生理的愉悦,它通过耳目直达人的内心,能很好地培育人的情感心意,例如听音乐能丰富人的情感世界。悦心悦意可以解放被压抑的性欲、本能欲望,还是多种情感的满足和提高我们的心境的通道。悅志悦神是最高等级的审美形态,是道德基础上而又超越道德的至高境界。“所谓‘悦志,是对某种合目的性的道德理念的追求和满足,是对人的意志、毅力、志气的陶冶和培育;所谓‘悦神则是投向本体存在的某种融合,是超道德而与无限相同一的精神感受。”[12]它不仅是耳目感官、心意情感的愉悦,它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整个生命的奉献,从而达到“至乐”“极乐”的世界与神契合为一。从叶朗和李泽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研究角度不同,但是他们追求审美愉悦的最高境界是不谋而合的,强调心灵的无限感、天地大同、精神的洗涤。
五、结语
我们应该承认审美活动具有自身独特的审美特征,它给人类带来的愉悦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叶朗与李泽厚都注意到了审美愉悦的独特性,将审美愉悦与生理快感进行区分。他们对审美愉悦观的论说是对美学研究的一大贡献。但是,叶朗过分强调审美愉悦的感性,完全断绝了与理性的联系,没有注意到人本身所具有的思维逻辑与理性判断。而李泽厚先生强调人的参与、社会实践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审美愉悦,审美愉悦是先判断后体验而来的,这就忽视了审美活动的直觉性的特点。通过这两者的比较,我们能从多角度了解审美愉悦的特性,审美愉悦内在的包含着理性,但是它也是人直觉体验的结果,是主体从感性形式中体味出来的意味。
注释:
[1]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2]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3]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4]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5]叶朗:《精神境界与审美人生》,中国艺术报,2015年,第1期,第1页。
[6]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7]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8]李泽厚:《美学四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9]李泽厚:《美学四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77页。
[10]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11]李泽厚:《美学四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36页。
[12]李泽厚:《美学四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43页。
(李卉 湖南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