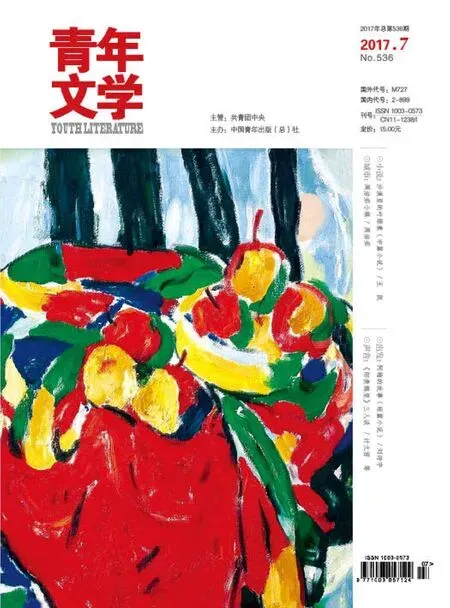骨科的表情
⊙ 文 / 谢枚琼
骨科的表情
⊙ 文 / 谢枚琼
谢枚琼:一九七〇年出生,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文艺报》《青年文学》《散文选刊》等刊。出版有作品集《向阳的山坡》《一路霜晨》等。
骨科设在住院大楼的十一楼。住院大楼共有十五层高,在这个只有十来万居民的县城的医院中,它属于第二高——最高的住院大楼在人民医院——而这个医院,叫作第二人民医院,也算是名副其实了。进入骨科,楼梯口雪白的墙壁上方贴着阿拉伯数字“11”,我看着看着就像看到两条站立的腿,心里想,骨科设十一楼,不管是刻意为之还是巧合,都是值得玩味的:住进来的病人,大多是伤筋断骨、横抬着进来的,却无一不是希望站立着像“11”一样走出去的。
二十多天前,年逾古稀的老父亲因为一个不小心扭伤了脚,被抬到这里住过一段时间。虽然是一瘸一拐地走出十一楼的,但毕竟还是能站起来了。
眼下却是我年近七旬的母亲又住进了十一楼。疼痛让她挪不开步子,也直不起腰,整夜整夜无法入睡,坐卧不安,其凄惨样让人不忍目睹而又束手无策。用轮椅推着她做了各式各样的检查,终于确定是腰椎第四、第五节严重压迫了神经,俗称“椎间盘突出”。医生说,具备了做手术治疗的指征,拖延下去会有瘫痪的危险。——倘若真是到了那种地步,再做手术亦于事无补。医生用平静的语气强调道。
在十一楼的病房里已进行了三天的保守治疗,无非是输液消炎止痛之类,但几无成效。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是手术还是不手术,我得拿定主意。
母亲有些担心,父亲也有些担心。担心这一做手术之后,还能不能真的站得起来。其实我更担心,这手术在我看来是有风险的,毕竟母亲年纪大了,万一伤及神经,那后果不堪想象。可骨科室廖主任信心满满。他说他亲自主刀,没任何风险。这让我悬着的心稍许地放平了些。我又向十三床打听,那是一个已经做了手术的老太太,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老人躺在床上,气色不错,和我一个劲地说做了好,做了好,她做了就没那么痛苦了,明天就出院了。我紧绷的表情在她的述说里又缓解了不少。于是下了决心同意做手术。父亲在一边嗫嚅了一句什么,我没仔细听,约是“可不可靠”的意思,我没有去细究他复杂的表情里有多少担忧,迎着母亲可怜巴巴地望着我的眼神,心里不禁涌上一股难以言说的滋味。我感觉到,不管年迈的父母在年轻时候多么有主见,等到老了,儿子就成了他们的主心骨。
手术终是做了。医生说做得不错。虽然暂且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还是在心底里长舒了一口气。
公休假正好还剩下一周。这一周,我请小姨来专司照顾母亲之职,我则是家里医院两头跑,有了空闲的时间,便在十一楼转悠。
我留意过,整座住院大楼里,不乏“请勿大声喧哗”之类内容的友情提示,但在十一楼要做到安安静静,却非易事。清静对骨科而言绝对是一种奢侈。因受不了伤痛的折磨,入住的病人要呻吟,要哭喊,那或许是他们减轻痛苦的一种方式。很多时候药物不是万能的,医师也并非是手到病除的“圣手”,他们也有太多的无奈。病房里有三个床位,母亲住四十四床,靠外边的位置。中间的四十五床是一个中年汉子,他是做灯具安装的,不慎摔了一跤,背脊骨破裂,仗着年轻力壮,坚持不做手术,选择静卧自然恢复,那当然会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此时他已经住了二十多天了,习惯了医院的节奏,他的神情最为轻松,时不时地还会从嘴巴里蹦出几句笑话或者调侃来。最里面的那位却惨了,她是一个七十多的乡下来的老婆婆,一跤摔碎了臀板骨,偏偏又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让医生都头痛了,风险摆在那里,不敢轻易给她手术。——糖尿病人做手术可不是好玩的。
四十五床的老婆婆,由她的并不年轻的女儿照顾着,老人整天整夜痛得叫喊,叫得女儿倚在床头暗自垂泪,眼睛通红。她的两个儿子在外打工还迟迟未归,她女儿六神无主,除了一通一通地打电话催促两个兄弟快点回来外,她只能泪眼婆娑地守候在老母亲身边。医生说,血糖降不下来就不能手术。几天后,赶回来的大儿子打听到有一个民间治疗跌打损伤的民间医生,拿了他母亲的片子去给人家看了,但没了下文。而老婆婆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呻吟着,说她不住院了,做手术要那么多钱,哪来的五六万?回去算了。谁都明白,如果她真的这样回去了,是挨不了多少时日的。约莫一周后,她的血糖指标总算降下来了,到底还是做了手术。我听到老人的女儿松了一口气,她的脸上有了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
一天上午我从医师办公室出来,见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倚着门框在哭泣,他不停地用他粗糙的手掌抹着眼泪,年轻的医生小王在一旁细声地向他解释着什么,老伯似乎听不进耳,一味地哽咽着哭诉。我见不得那样辛酸的场面,赶紧扭过头去。晚上给母亲送饭时听小姨说,斜对面的病房里一个老婆婆上卫生间时一不小心摔倒了,突然昏厥,还生生折断了一条胳膊,旧创未痊愈,又添新伤。老婆婆正是那位老伯的老伴。医方赶紧施以急救才把她从鬼门关给拽回来。老伯免不了抱着她又是一通哭诉。一个老汉的泪水,让我好一阵唏嘘。第二天,我便留心起那个流泪的老伯来,他迈着已不再轻盈的步子在十一楼进进出出,或找医生,或下楼买来饭菜,再坐在老伴的床边,一勺一勺地喂她。老伴已度过危险了,看得出他的表情也轻松了不少。小姨说起了她听来的关于那位老伯的故事:老伯这个岁数还在外面打着一份工,上半年本来赚了万把块钱,没想到老伴的一次骨折就将他半年的辛苦给弄得分文不剩;不过,他又说,钱没了可以挣,人没了,就真没地方找回来了。听了这话,我想老伯的眼泪绝不是为钱而流的。
陆陆续续地有人治好出院了,他们,和来接他们出院的家人们的脸上写着欣喜,一扫多日来沉郁的阴霾,总算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出院之时便不亚于人逢喜事般。他们挥手同病友们话别时,几乎都少不了说两层意思的话语:一是总算可以出院了,二是你莫急,住好了再走。
出院的表情那样轻松,而进院者的表情则是那样焦躁、惶惑、不安。
这天下午,十一楼突然闯进来一帮子人,他们抬着一位年轻男子。年轻人是从二楼上摔到地面的,下半身已无知觉。他的岳母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火急火燎地和医师说好话:咯怎么得了呢,刚刚三十岁,你看,你看,细伢子还只有半岁,要是瘫了,那日子怎么过啊?——伤者的妻子脸上木木的,好像还没从梦里醒过来似的。翌日,我在十一楼的走廊间听到娘俩堵住主治医师在做交涉,说要将伤者转院,要转到省城医院去。转院,在县级医院里是并不鲜见的事。现在伤者情况危急,家属们的要求自然无可厚非。想想吧,省城大医院集中了最好的、最齐崭崭的医疗资源,难免会让病人和家属们觉得要更放心些。年轻的医生在耐着性子和那娘俩分析转院的种种利弊,旁边的人早已听出来他其实是不大赞成转院这事的。他说这个时候转院风险大,伤者经不起路途上的颠簸,路上也难保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那可就麻烦大了。而且如果说省医院那边没联系好,转过去了还得等,人家大医院可不是你想去就去的。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在这里一样可以做手术啊,倘若硬是放心不下,还可以联系省医院的教授过来主刀的。如此种种理由,无非是在说明不转院的稳妥性。这一番话下来,原本态度坚决的母女俩似乎有些动摇了。旁边有人插话道,他们就是不想有人转院,转了就没钱赚了。年轻的医生显然听得清楚,他不再多言,也不反驳,转身进了办公室。我注意到他的脸上并未滑过一丝一毫的不快,也许是对诸如此类的议论听得多了吧,练就了一份淡定。
不知何时始,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已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我暗想,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如果不是年轻医生的适时离开,只怕也会酿成一番火药味十足的唇枪舌剑吧。我踱回母亲的病房里,听到里床的那个家属在感慨着,医院哩,一方面是个让人嫌的地方,一方面还真是不能没了它。
那个嚷嚷着要转院的年轻人终究还是没转院。第二天上午推进了三楼的手术室,只是当天并没见到他回到十一楼的那间病房里,时不时地有好事的人去瞧瞧,然后议论着,怎么还不见回来呢?看来是个大手术了。也有的说,年纪轻轻的,可别出什么意外。言语间,我听得出有惋惜,有担心。素昧平生的人们,在这样的时候,三言两语里透露出善良朴素的本真来。好在一天之后,那个年轻的伤者被医师和家人推回到了十一楼。家人用掩饰不住高兴的表情回答着好心人的询问,说手术做得还行,还行哩。
我母亲的病恢复得很慢,她本就急性子,静卧太久亦难免心烦气躁,时不时地抱怨脚发麻伤口痛,她一叫苦,我只好把医师喊过来,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弄得小王医师向我抱怨说,那些不适其实都是些术后的正常现象。主刀的廖主任一次巡房询问了母亲的伤情后,他干脆对我说,看来老人家是有些娇呢,说这话时,他脸上是略带调侃的微笑的表情。我听了只好忙不迭地替母亲辩解几声,呵,呵,肯定还是不舒服所致吧。廖主任笑笑,吩咐主治医师小王再耐心一些,多做安慰和疏导工作。
母亲伤口拆线已是半个月后的事了,小王医师说拆了线的第二天就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他还肯定地说,过些时日就基本能恢复如初,行走自如了。这在我们听来可是喜事一桩啊。特别是小姨,她甭提有多高兴了,这半个月她不分日夜黑白地陪护我母亲,完全打破了她平日里生活和作息的规律,而今随着母亲的出院她就可以慢慢恢复到原来正常的状态。可是,母亲提出来还想留在医院里再多观察两天。说到底她还是信心不足,对自己,也对医院。
母亲提出这个想法时的表情是那样小心翼翼的,一是又要辛苦小姨,二是在医院多住一天就要多一天的开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母亲这些天里一直在念叨着做手术花了的那好几万块钱,总在担心钱花了如果病没好又怎么得了呢,这应该说是纠缠着她的一个心结。母亲把目光转向我,我当然清楚其中的含义。我说,那就再住两天吧,多观察两天总会放心些。

⊙ 冷 冰· 穿过时光的印痕7
母亲出院时不是她自己走着离开十一楼的,她的身体状态决定了必须要平躺着抬回去。但是看得出她的表情放松,早先进院时的那种痛楚已不再困扰她那羸弱的躯体。我们在离开十一楼之际,我的目光似乎在有意与无意间落到了骨科的楼梯口那个阿拉伯数字“11”上,心里感叹着,真是像极了两条站立的腿,站得那么笔直,那么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