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谱事
孙修远
大约二十年前的事了,父亲离开这个世界也已经两年。
父亲一生基本上生活在老家山头。山头也称山子头,山子头没有山,现在是江苏省泗洪县界集镇的一个行政村。山头濒临成子湖,地理十分偏僻。村口原来有清代建立的祠堂可以作为地标,怎奈建国初期已经破坏,残砖旧瓦后来建了公厕。过去由孙圩、韩庄、王圩几个大的自然村落组成,村庄名称自是解放前聚族而居延续至今。随着村庄的散化,现在已经难觅旧迹。孙姓、韩姓、王姓祖上几乎同时流落到此,孙、韩始祖据说还是表兄弟,与王姓稍远。兵荒马乱年代,当局无暇顾及农村治安,村庄只有实行自保,几大姓之间常常抱团取暖,互相支援。当地家族氛围浓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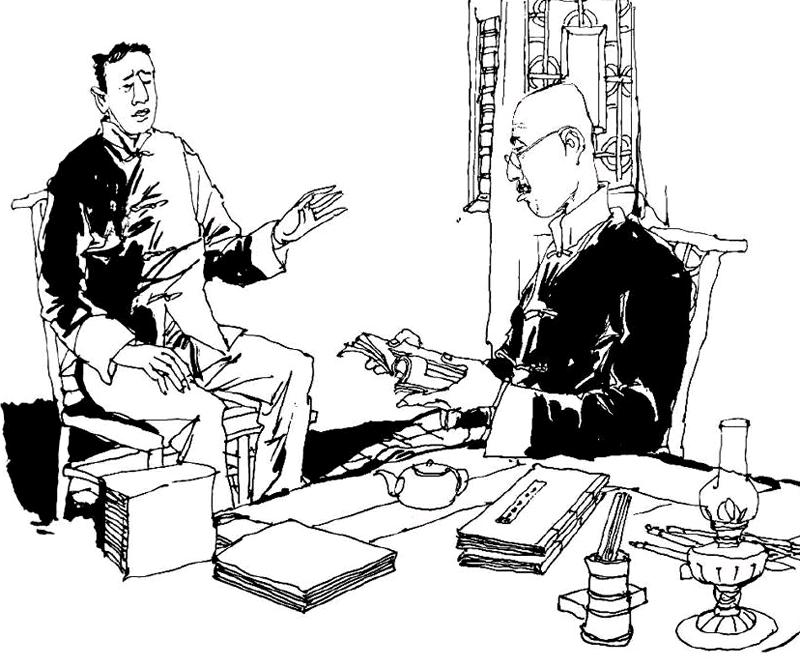
老辈人说,父亲曾经“四书包本”,意思是读过四书五经。村里人少见世面,可能过誉。我们家先祖秉承着勤俭刻苦农民的通行做法,一门心思置办土地,祖父辈时已有旱田百亩,也算地方上比较殷实的农户(土改时划为地主成分)。父亲又是三代单传的独子,因而有条件到私塾读书,他也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读过几天书的人。父亲十七岁参加工作,先后在地方和部队捉刀代笔。朝代蓬转,后来因故回乡务农。本地孙姓家庭婚丧嫁娶的笔墨事务非他莫属,操持礼仪悉遵旧制。父亲这一辈人受传统礼法制度浸染较深,家族、家庭的观念很强。他多次说过,不把家庭当回事的人心中不会有家族,心中没有家族的人不会爱国家。他还列举了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时,孙姓族人如何保护他少受冲击、少受折磨的例子。他的意思,我懂!
一九八几年吧,初春的一天,一个沭阳孙姓族人,几经辗转找到我家住址,提出续修孙姓家谱之事。可能是被对方真诚的态度打动,可能是受到当时各地纷纷修谱的做法诱导,也可能是本来就溶于血液的家族情结起了作用,在其反复游说下,父亲动了心思。续修家谱,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正努力迈上正轨,但是“文革”的阴霾真正散去尚有一个过程。政治气候既不可捉摸,民间能否组织起来也是个问题。人们对这类一贯视为“封建”的东西心有余悸。从我家来说,“地主”的帽子父亲戴了三十多年,当时父亲已经六十多岁,承包地不过人均一亩三分,我又先后在县城省城读书,家中依靠种田为生,父亲常常为我的书学费而颇费踌躇,经济时常捉襟见肘,甚至难以为继,加之此后母亲因为脑溢血后遗症瘫痪在床数年,家事全赖父亲一人,其中处境和困难可想而知。然而,父亲还是以坚强的毅力,参与到续修家谱的事务中。
兵连祸结常常推动人口迁徙。山头这一支孙姓始祖,系元末明初为避朱元璋追杀陈友谅余党之祸,弟兄四人从湖北监利县逃难来的。除山头枝枝蔓蔓近二百户外,其余后裔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泗洪、泗阳七个乡镇三十几个村组,过去都属于桃源县即今泗阳县管辖,来往相对频繁,解放后划为不同行政区域,几乎没有交往。父亲凭着模糊的历史记忆,挨村逐户寻找,走访稍有文化、热心修谱的孙姓族人。对于各地的零散住户,还要单独登门。酸甜苦辣在心头。比较多的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也曾经吃过闭门羹,遭到冷遇和嘲讽。那时交通主要靠步行,南辕北辙也是常事。有时还要多次走访,反复沟通,仔细核对。泥泞的乡间小路,偏僻村庄的房前屋后,不论陰晴寒暑,都留下父亲一行人的串串身影。父亲的坚定执着加上他的虔诚,唤起了孙姓族人沉睡已久的宗亲意识。参与修谱的人群不断扩大,人们的认识逐渐明晰,修谱的想法和做法逐步成熟。
树有根水有源。为了理清孙姓世系,必然要在正本清源上花大功夫。父亲曾经委托我借过《三国志》、《新唐书》等,考究孙姓来龙去脉。他尤其觉得庆幸的,是在“文革”破“四旧”时,冒着被揪斗的危险,从熊熊燃烧的火堆里偷偷抢出一部《孙氏家谱》,这使后来的家谱编修有了连续依据。他根据民国时《孙氏宗谱》“由湖北监利县来桃”的记载,赴监利县寻宗。由监利孙姓家谱对世系的介绍,追踪到山东惠民县认祖。父亲曾经在湖北崎岖的山路上攀登,在微山湖的渔船上流连,又曾经在惠民县与史志办的同志深入交流,在浙江富阳龙门古镇的各地孙姓聚会上据理力争。桃源孙姓家谱谱序上宋代先祖孙文若关于世系的一句话“孙氏本乐安郡即栎州厌次是也”(宋代的“厌次”在今山东省惠民县境内),成为惠民县是孙子故里的有力旁证,后谱序刻碑立在当地孙子故园内。孙姓族人祖居地的确认,地方政府的孙武故里之争,形成在历史考证方面的微妙契合和携手。他们根据考察,也写出了《孙氏姓源考查》、《孙氏故里考察》、《家谱修佚记》等。《孙氏源流考》一文后来还刊登在《泗洪县志》上。
撰修家谱讲究血缘伦理,规范辈分秩序,孙姓续修家谱均遵循旧例。在新修家谱序上,提出要“序昭穆,分世系,讲亲疏”。在老谱的基础上,父亲和一班孙姓修谱人反复斟酌,又新列了数十个字的辈分排序。有一次,我开玩笑地说,以后五百年的孙家辈分都排好了,父亲笑笑。父亲这一辈人对辈分是格外的较真。因为辈分上的争议,沭阳一个地方孙姓试图联合修谱的主张最终流产,本地一些孙姓旁支联宗的愿望也落空。父亲说,修家谱是要分清长幼尊卑,不是拉帮结派搞家族,应该对社会和谐有利,不能因修谱产生新的矛盾。他们清楚几十年来社会秩序的新变化,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早已分崩离析,对家族、家庭的身份地位不再作不合时宜的表述,对一些过时的规范作了改进。家谱中不仅仅孙姓男子可以入谱,入赘养子、女性同样可以列入家谱。这些民间修谱人也在尽力使规范辈分秩序行为,与国家法律政策相衔接,尽管家谱上这些规定的约束力是十分有限的。
家谱撰修纯属民间自发行为,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没有一批热心人的甘愿付出,很难完成。可以说是孙姓族人的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成就了孙氏家谱。说起当年孙姓家谱的艰难编修过程,父亲常常念叨:没有某某、某某,家谱是修不成的。他们有的七八十岁还不顾年老体弱四处奔波,有的放弃了红红火火的建筑装潢生意,有的家庭无怨无悔地无偿提供食宿等。家谱从登记、编纂、校对到印刷出版,倾注了修谱人的家族情感和无私付出。也听父亲说过,有的当初参与修谱的人想重温担任族长的旧梦,有的提出从筹集来的有限资金中拿点报酬,甚至有的别有用心试图从中额外捞点好处,这些显然是不现实的。父亲他们也不加争辩,只是让时间来淘汰,最后坚持下来的都是自觉自愿的。修谱无形中成为传统道德的复活过程,贯穿着家族观念的磨合和认知,这又何尝不是家族道德文化的重新累积呢?
父亲一班人的修谱活动,和全国许多地方孙姓建立了联系。如江苏的南京、苏州,山东的青岛、滨州,浙江的嘉兴、富阳,福建的厦门、漳州,江西的赣州、九江等。接触的人当中有大学教授、档案馆研究员、地方志学者、医务人员、中学教师等,修谱大舞台,生旦净末丑。他们或身居闹市或足立乡野,或从事学术研究或处于行政岗位,有耄耋老者也有青年才俊。通过接触,父亲他们也对各地家谱风格和修谱状况,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规范了修谱行为,提高了家谱质量。各地孙姓族人为了心中那若隐若现的小小家族梦想,千里迢迢赶来,有的还不止一次来泗洪。家谱这一特殊媒介,营造了和宗睦族的氛围,也推动了孙姓文化交流。山东滨州孙子研究院把泗洪孙姓修谱作为跟踪调研对象。苏州民间人士陆某,以泗洪孙姓收集的家谱资料为依据,编成了《孙姓世系源流》一书出版。惠民县邀请泗洪孙姓参与定期举行的孙子故里纪念活动。苏州吴中区推举泗洪孙姓族人主持祭奠孙武诞辰2500周年的礼仪活动。
尽管社会上有的对家谱不认可,一些孙姓人对修谱有不同看法,但父亲认为自己为孙姓家族完成了一件大事。修谱影响带动了本地一些孙姓人从事与家谱有关的活动。我的族叔曾经和父亲一起修家谱,收集了上万部各地家谱资料,成了圈子内闻名的孙姓谱牒专家,指导不少地方的孙姓续修了家谱。在近几年房地产开发中小有斩获的几名孙姓老板,拾起传统光宗耀祖的本分,受锦衣不夜行古训的影响,跃跃欲试在孙姓集中居住地建设村贤馆,有的甚至在筹划修复孙姓祠堂。最近还成立了孙氏谱牒研究的民间团体。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但是对家族文化包括家谱文化的热爱则是难得的。这些都或多或少与父亲的谱事有关,而父亲已经卧床数年。
今年初,我们回家收拾十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屋,看见父亲为修谱而积累的书籍堆满了半间房子,回想起修谱旧事,我忽然有种人事俱老的感觉。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段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