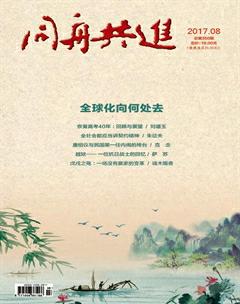“倘有英灵九天吼”
冯锡刚
【“纪事”之作让纪念会情景宛现眼前】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此后每逢忌日,多有纪念活动。在笔者的印象中,论影响,1946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因着国共和谈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在即而为世人瞩目;论规模,1956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因着举国主办,当为空前之盛,堪与其媲美的,是1961年的鲁迅八十诞辰与1981年的鲁迅百年诞辰纪念。然而,使笔者真正感兴趣的,却是1945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起因是读柳亚子题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忌辰,纪事有作》的一首七古,前有小序:
十月十九日下午三时许,举行纪念大会于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集者许季茀、叶圣陶、郭沫若、曹靖华、冯雪峰、舒舍予、茅盾、胡风、徐迟、赵丹、周恩来、冯焕章、邵力子等五百余人,余与瘦石赴之。
山颓木坏周年九,嵇生忍忆黄垆酒。
中华民国圣人殂,那比寻常折才秀。
忆昔相逢海上时,天魁谬让吴天柳。
论德论齿咸我先,怀惭我岂迅翁耦。
两楹梦奠事堪悲,百身莫赎歼良又。
此日招魂孰主盟,子将白发平生友。
叶适陈辞天水军,郭隗慕义燕台右。
及门弟子曹与冯,何事无言述周叟。
举世滔滔尽阿Q,绘声绘影舒郎茂。
茅盾沉潜席避人,胡风慷慨气冲斗。
现实理想要两兼,岂同驽马贪羁豆。
朗诵欢呼千掌雷,赵丹肥胖徐迟瘦。
醇醪公瑾寓深心,折冲樽俎由来久。
冯生诙谐邵生默,真怜病齿成牛后。
老夫敢哭复敢笑,誓共青年斗身手。
吴语何妨朗诵诗,土音忍割乡情厚。
却愁顽钝百无成,此意悠悠莫终负。
记取明年九二五,生辰还祝迅翁寿。
纪念今朝盛英京,万头攒孔遮墙牖。
归途却与尹生语,倘有英灵九天吼。
柳亚子不愧为南社(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团体,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成立,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编者注)巨擘,这篇“纪事”之作激情洋溢,生动流利,让纪念会的情景宛现眼前。参照当年重庆《新华日报》的报道和相关资料,不仅能了解此诗的具体内涵,尤可对当年国统区举行如此盛会,生发诸多历史的兴叹。
【诗句描摹纪念会上诸公的情状】
先看小序。
参加者名单的排列,既非《新华日报》以“发起和参加者”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为序,亦非以纪念会发言和朗诵者的先后依次,而是出于诗人谋篇布局的需要。[纪念会组织者的安排是:主持人许寿裳(季茀),发言与朗诵者依次为:冯玉祥(焕章)、柳亚子、郭沫若、赵丹、叶圣陶、徐迟、胡风、周恩来、老舍。]诗人的构思,不但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还受制于步韵的规范(当年9月作《自题〈辽东夜猎图〉》首用九字韵,《诗翁行,哭李少石,十月九日作》、10月11日所作《誓墓行》及本篇连续用此韵),足见其才气纵横,驱遣自如,在严格的限制中体现高度的自由。
此诗前十句为铺垫。
“忆昔相逢海上时,天魁谬让吴天柳。”《鲁迅日记》中有与柳亚子交往的记载。1933年1月,柳通过郁达夫转致怀念鲁迅的七绝:“逐臭趋炎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柳最引以为荣的是鲁迅以《自嘲》书为条幅相赠,“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久已脍炙人口。“两楹梦奠事堪悲,百身莫赎歼良又。”可能事涉先于鲁迅四个月前逝世的高尔基。鲁迅殁后,柳多有吊怀篇什,这篇《纪事有作》实为别开生面。
以下诗句以对比、借代、夸张等各种手法,描摹纪念会诸公的情状——
“此日招魂孰主盟,子将白发平生友。”“白发平生友”即许寿裳,为鲁迅30余年的至交,纪念会的主持人。据现场记者所写的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说话的音调,显得苍凉而沉郁”,开场白不过是寥寥数语:“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他的伟大非三言两语所能尽……”
“叶适陈辞天水军”,是指叶圣陶。叶适,南宋理学家,曾为韩侂胄北伐陈辞献策。诗人以姓氏的巧合而征引典故,乃是惯常的手法。叶圣陶说及与鲁迅的交往:“鲁迅曾送我一本他自己出版的《铁流》,并附有一封短信,我記得信中有这样的话:‘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相濡以沫一语,出于《庄子》。鲁迅先生对朋友,对青年,对不相识的人,都本着相濡以沫的精神,却并不勉强大家都走一样的路,造成‘只此一家,并无分出的局面。”查《鲁迅全集》,不见此信,可见已遗失。此一回忆提供了新的资料。所谓“陈辞天水军”,指的便是赠送《铁流》一事(此书描写苏俄早期一支游击队的生死存亡)。叶又以参加两次纪念会的不同感受,表达了对时代进步的庆幸:“我参加在重庆举行的鲁迅纪念会,这是第一次。去年我们在成都举行纪念晚会,到会的只有十几个人,而且主持人还得声明:到会的人都是个别接洽的,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说话……今年大不相同了,这是大可庆慰的。”这番话引发全场会意的笑声。
“郭隗慕义燕台右”,这一句说的是郭沫若。几年前柳与郭唱和,有“求真慕义吾何敢”,“郭隗肯慕燕台骏”之句,用的是燕昭王千金求骨,为郭隗筑黄金台的著名典故。诗人一再以“慕义”称道郭沫若,那么,这位与鲁迅未曾晤面却因文字之争而生龃龉的学者,在纪念会上说了些什么呢?郭沫若说:“主席刚才说我由苏联回来,我就想说说苏联对于作家的重视,怎样纪念他们的大作家,来作为我们怎样纪念鲁迅先生的参考和榜样。苏联的大作家,大抵都有以他命名的博物馆,例如托尔斯泰博物馆,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等。所以,我建议:应该设立鲁迅博物馆。陈列他一切的著作、原稿以及生活历史等等。地点上海、北平、广州。馆长应由许景宋(广平)先生担任。我在苏联,看过不少的普希金像,托尔斯泰像,艺术家以能铸造这些文豪的遗像为光荣。我建议:应该多多塑造鲁像。北平、上海、广州、杭州、厦门,以及其它的任何地方都应建立鲁迅像。自然以铜像为最好。莫斯科有高尔基路,普希金广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所以,我又建议:把西湖改名为‘鲁迅湖,把北平的西山改名为‘鲁迅山。为了使鲁迅的精神,由知识分子推广到大众中去,我提出以上的建议,具体地、切实地来纪念鲁迅先生。”这并非浪漫主义诗人的一时感兴,此后
还写成专文来陈述这些主张。“及门弟子曹与冯,何事无言述周叟。”这两句说的是曹靖华和冯雪峰。论到与鲁迅的关系,冯雪峰岂仅“及门弟子”,更是代表中共与之互通声气的最重要的人物,甚至为重病中的鲁迅起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重要文章。因此,要论对鲁迅晚年精神境界的了解,他无疑最有资格在这个纪念会上发言。柳亚子的发问有着遗憾,也带着困惑。冯雪峰既未受到邀请,也未主动要求,这其中的缘由,或许是身为中共要员的纪律所限吧。这令笔者联想到此前为郭沫若五十华诞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所举行的庆祝活动,乃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文化界实施的一次极为成功的统战活动。这次举行鲁迅逝世九周年的纪念会,在长长的发起者名单中,除了周恩来这位天才的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共产党人仅冯雪峰一人,其与鲁迅之关系又世人尽知。组织者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安排,是柳亚子不易理解的。
“举世滔滔尽阿Q,绘声绘影舒郎茂。”这两句写的自然是老舍(舒舍予),所朗诵的是《阿Q正传》第七章。“绘声绘影”是对这位剧作家朗诵风采的称道,但还当关注的是,他在朗诵前有一番寓沉痛于幽默的道白:“阿Q参加了革命,他说革命也好,到大户人家去拿点东西。今天,抗战胜利了,有人说胜利也好,到上海、南京发点胜利财,拿几只板鸭来吃。阿Q式的胜利是惨胜,比惨败还难堪的。拿阿Q的精神来建国,国必如阿Q一样是会死的。阿Q在陈旧势力压在他身上时,莫名其妙地画了一个圆圈就死了,如今虽说收复了东北、台湾,假如像阿Q一样,也会只画了一个圆圈就会死的!”听众中响起了会心的哄笑和热烈的掌声。
“茅盾沉潜席避人”,作为纪念会的发起者,茅盾虽然与会,不但未发言,居然未与其他发起者同坐一席,而是“沉潜”于会场五百余众的人丛之中。同样做派的还有巴金(柳诗未道及),在《新华日报》的报道里则名列其中。
“胡风慷慨气冲斗”,适与上句构成绝好的对仗,形成鲜明的比照(虽同为左翼文化阵营中的健将,茅盾与胡风龃龉颇深)。柳亚子以“现实理想要两兼,岂同驽马贪羁豆”概括和赞扬这位鲁迅大弟子的发言。胡风的发言并非毛遂自荐,而是出于纪念会组织者的要求(这正与冯雪峰的“无言”成为对照)。其实胡风并不长于演说,而是偏于理论的阐发,又喜用欧化的冗长句式,这于大众集会的实际效果,显然难以产生现场呼应。胡风的发言较长(似乎与周恩来的发言构成了纪念会的主题),让诗人感奋的“现实理想要两兼”的一段话是: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相结合的国家,压在我们身上的是沉重的负担,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使命,就有必须本着鲁迅先生的光明的目标和远景,向现实作流血流汗的斗争的必要。鲁迅先生不仅是极坚韧、极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也是有极宽阔的胸怀与眼光的极坚强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现实主义者,必须有理想!
“朗诵欢呼千掌雷,赵丹肥胖徐迟瘦。”说赵丹“肥胖”大概是诗人的错觉,或者是为了与“徐迟瘦”形成戏剧性的对比——世人实在未曾看到过赵丹“肥胖”的剧照和生活照。这位主演过《马路天使》和《十字街头》的电影表演艺术家颇具人望(主持人甫一点名,台下即响起热烈的呼叫),他的带有舞台腔的朗诵,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篇时政性杂文的讽刺魅力,使会场的气氛为之活跃和轻松。徐迟朗诵的《淡淡的血痕中》,是散文诗集《野草》中的名篇,意味隽永,但不易理解,朗诵者虽不乏诗人的激情,却因“音调太低沉,在这群众的场面中,没有发生巨大的反应”。
有趣的是,徐迟在其长篇回忆录《我的文学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中忆及柳亚子的这篇七古,并述及纪念会:“在这个会上,我朗诵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全文。这还是胡风选定之后,要我朗诵的。那时年轻,记忆力可真强呢。这篇小说的全文,我手里还不拿书本,居然都背了下来。当年我的朗诵是独具一格,反正是胆大妄为,但至少热情可嘉。这一次的朗诵反应也还很过得去。臧云远和高兰都说过,好像我并不是在朗诵文章,而是真正的发了疯似的。并不是在朗诵鲁迅先生的作品,而是很像有这么一个疯子在说着满口的疯话的味道。那也许就是我渗透到了原作之中去了,朗诵得颇为逼真的意思了。”笔者读到此处是颇为惊异的,一位并非演员出身的诗人,却能背诵几千来字的小说,须得具有过目不忘的禀赋。当年《新华日报》的报道自然真实可靠,也难怪,这是徐迟40年之后的回忆,只是由几百字的散文诗而错记为几千字的心理小说,出入委实大了点。而关于“徐迟瘦”,回忆录倒是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细节:“我那时确实很瘦很瘦,以至夏衍同志曾说我,‘瘦得活像一只螳螂!大家听了也都笑着说,‘真像,真像!于是我多次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用‘唐螂作过笔名。”
“醇醪公瑾寓深心,折冲樽俎由来久。”周瑜字公瑾,古语有“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之美誉。此句说的是周恩来的压轴讲话,然而以“折冲樽俎”来赞誉却是落了俗套。周恩来的讲话,其实就是纪念会的主题报告——
我也读过鲁迅先生许多著作,受过他精神的感召。刚才胡风先生说鲁迅先生是理想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战士,是不错的。他的许多话,至今还活着,做我们的指针。现在抗战结束,怎样和平建设一个新中国,是全中国、全世界共同注意关心的事,所以国共谈判,不只是国共的问题,而是全中国人民的问题。
鲁迅先生说过,“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现在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文化界、艺术家在这样的时代,一定会认识到政治与文化是脉息相关的。鲁迅先生的话告诉我们文化工作者不能离开政治。在将要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们主张要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参加会议,提出文化界的代表意见和主张,包括在施政纲领中去,进宪法中去。因为和平建设,除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建设之外,更包括着文化的建设。
胡風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革命的任务还未完成,鲁迅先生的路尚未平坦地建筑起来。但我们必须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要披荆斩棘,一方面就要开辟道路。过去我们的新文化是批判的居多,建设的较少。敌后解放区,虽说有了新的方向,成就也不大,这项工作要大家动手来建设。
我又记得十几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力。这句话,说明了、指示了我们三点:第一,和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的文化的斗争,必须是坚决的,他的目标非常清楚。第二,认识清楚了,如果没有持久的精神战斗下去,新文化建设的胜利也还不易获得。第三,我们的战线应该扩大,文化斗争不是小圈子、宗派的,应该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来开辟道路,广泛地吸收文化战士来参加,对青年总要抱着欢迎、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关门的,这点甚为重要。
鲁迅先生,一生与革命息息相关,他不是孤独的。我热烈地期待着文化界共同起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努力。
……
周恩来的讲话,在会场中激起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冯生诙谐邵生默,真怜病齿成牛后。”说的是冯玉祥和邵力子。以发起者的身份看,冯与邵均系国府要员,又都是同情乃至支持中共的开明人士。显然是出于统战的考虑,组织者安排冯为纪念会第一发言人。冯的发言不乏诙谐:“我平生爱讲故事,我要讲一个鲁迅先生在文章里写着的故事给大家听。故事是这样的:一家人生了一个孩子,来客纷纷道贺。第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发财的,主人听了大为高兴,迎入上座,端茶端蛋招待。第二个客人说,这孩子头平额阔,天庭饱满,将来一定会做大官的,主人听了更加欢喜,端出双份的茶和蛋来招待。可是第三个客人一进来,看一看孩子,却说:唉!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死的,主人不但不大高兴,而且把这客人赶出去了。鲁迅先生在文章结尾说:本来发财做官都是靠不住的,但人偏爱听,人会死倒是最真的,却有人偏不爱听。现在的世界也还是一样,靠得住的话,偏有人不爱听……”在掌声和笑声中,冯玉祥结束了讲话。
据报道,主持人在冯玉祥之后邀邵力子发言,邵因牙痛而辞谢。“真怜病齿成牛后”真是一语双关的巧妙写照(化用折齿孺子的典故,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亦源于此)。邵力子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入国民党,1920年入陈独秀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中共成立后的第一批党员,故称得上是国共两党的元老级人物。1926年他脱离中共,是国民党中出名的“亲共分子”。一直以来,邵力子对左翼文化人士持友好和善意,重庆谈判时,国共签订《双十协定》,在稍后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郭沫若表示了对邵力子的好感:“重庆的电影戏剧检查尚未废除,假如邵力子、陈布雷来审查,将受益无穷。”冯玉祥与邵力子被邀为纪念会的发起者,确实是中共统战策略的体现。
“老夫敢哭复敢笑,誓共青年斗身手。吴语何妨朗诵诗,土音忍割乡情厚。”邵力子以牙痛辞谢发言邀请之际,柳亚子即当仁不让地以诗人的激情发言:“鲁迅先生的精神,是教育青年人敢哭、敢笑、敢骂、敢打!更重要的是叫‘现代中国人,不要违背中国人为人的道德。在今天,努力和平、民主、团结,建立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新中国,就是这道德最高的表现。过去举行鲁迅先生纪念会,总遇着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今年好了,在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先生来重庆和蒋主席握手言欢,使孙先生所主张的三大政策,很有复活的希望。这就是现在中国人应做的事情。我想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一定很高兴。”“吴语何妨朗诵诗”成了纪念会事实上的压轴。纪念会行将结束之际,柳亚子又自告奋勇地朗诵了一周前应《大公晚报》之约而写的两首七律,兹录其一:
迅翁遗教堂皇在,不作空头文学家。
抗战八年成胜利,和平初步乍萌芽。
光明已见前途好,曲折宁辞远道赊。
论定延京尊后圣,毛郎一语奠群哗。
“归途却与尹生语,倘有英灵九天吼。”尹生即尹瘦石,画家,尊柳亚子为“今屈原”。毛泽东亲笔题写会标的“柳诗尹画联展”恰在重庆展出,显示的正是“倘有英灵九天吼”的浩然之气。
【“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副其实的”】
茅盾说:“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詩人”,其诗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副其实的”。证之于这首《纪事有作》,洵非溢美之词,它为后人留下了颇堪回味而又令人神往的一幕。“纪念今朝盛英京,万头攒孔遮墙牖。”叶圣陶发言中关于两次纪念会的对比,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柳亚子发言亦及此,并道出了个中缘由:“今年好了,在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先生来重庆和蒋主席握手言欢,使孙先生所主张的三大政策,很有复活的希望。”能举行这样一个不为当局所乐见的大型纪念会,这是共产党强大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衡执政的国民党的结果。但历史的遗憾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终于昙花一现,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古之痛。柳亚子乃性情中人,其发言与朗诵皆率性而为,亦见出非由庙堂主持的纪念会的生动活泼,不拘一格。
“记取明年九二五,生辰还祝迅翁寿。”由忌辰而念及生辰,诗人的悃忱溢于行间。读其诗想见其人,2017年是柳亚子先生130周年诞辰,真是“活在人心便永生”。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