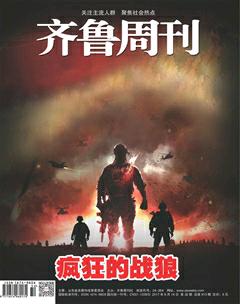民国时期的中日渔业战
陈祥
1930年春,定都南京不久的国民政府收到浙江、上海渔业群体的一堆请愿书。渔民们遭遇的难题迫在眉睫,日本轮船利用吨位大、航速快、设备新的优势,在嵊泗列岛海域大肆捕鱼,将渔获运到上海出售,这严重威胁到尚依靠传统技术的中国渔民的生计,毕竟渔业资源有限。渔业群体希望政府出面与日本谈判,保护本国渔民利益,洗刷渔业领域的国耻。
日本侵渔现象由来已久,但作为前现代政府的晚清不在乎现代渔业,治理失效的北洋政府则根本无力管理渔业,这一历史顽疾留给了新建立的南京政府。适逢日本渔业扩张时期,北至白令海,南抵马来群岛,都遍布日本渔船,遑论不算太遥远的中国沿海。
事实上,中国不乏有识之士注意到渔业危机。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3年出訪日本,目睹了日本渔业和航运业的巨大进展,他回国后给商部提交咨文,率先呼吁要启动古老中国的渔业改革。“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张謇的警告被一一兑现。
日本先进渔船如入无人之境
日本渔船的革命并不早,但现代化速度很快,背后是国家的工业化、海军扩张做有力支撑。1908年,日本才从英国购入第一艘金属船体、蒸汽动力的渔船,属于新兴的拖网渔船。中国江浙沿海第一艘由机器驱动的渔船,诞生早于日本,可惜沦为形象工程,政府无力推广使用。由张謇倡议组成的渔业总局,于1903年向德国订购了一艘小型机轮和相应渔具,取名“福海”号。前期由于实际作业时间少,每年亏损,直至辛亥革命后调整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扩大渔场活动范围、增加作业时间,它才发挥出机拖渔轮的威力。
新式捕捞法非常高效,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它在近海能将冬季潜伏海底的鱼群一网打尽,很容易导致渔业资源枯竭。这类新渔船很快在日本扎根,也迅速引起传统渔船操作者的不满。政府为息事宁人,在1911年限制新型渔船在近海作业,鼓励它们去远海,当然包括中国近海。
当时中国的渔船吨位小并且吃水浅,只能在近海活动。 1912年至1914年,为保护己国海域的生态,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禁止新型渔船作业的海域,加速逼迫它们来到中国的东海和黄海。对于从事远洋渔业以及去他国领海捕鱼的企业,日本政府不惜给予财政补贴。1917年,日本规定全国只能有70艘拖网渔船,新造船的排水量必须在200吨以上,航速至少11节,续航力在2000海里以上。1924年,日本规定内海及黄海、东海海域之外的渔船不受70艘的限制,这等于变相鼓励拖网渔船去南中国海。日本拖网渔船数量在1926年达到300多艘,在1937年达到1000余艘。
那时的关东州、青岛、上海、台湾和香港,成为日本渔船的后勤基地。出入中国领海的日本渔船,受到日本政府的纵容和保护。日本海军不时派军舰护渔,甚至直接向驱赶渔轮的中国军舰挑衅、示威。为争夺有限资源,占尽优势的日本渔船不惜欺负中国渔船,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破坏对方的网具。渔具一旦遭严重毁坏,中国渔船只能打道回府。最严重的情况,是日本渔轮撞沉弱小的中国木帆渔船,如1929年1月,“姬岛丸”号渔船在温州沿海撞沉一艘中国渔船;1931年3月,该日本船又在定海海域撞沉一艘中国渔船。
《申报》在1931年3月8日记录了日本渔船的野蛮状,“又闻该日轮在浙省洋面不但越海捕鱼,并且偷倒网舱之惯技,以至各钓船受害不浅,生计绝望。因日渔轮均装有柴油引擎,俟钓船下网后鱼已涨满时,只须渔轮在船旁驶过,连鱼带网均为叶子所卷,因此船家损失颇巨。”
中国的反击
“致我国沿海类(数)千百万之渔民,均受其欺凌压迫,以致渔场日缩,生计日穷,既乏相当渔业组织以谋抵抗,而政府又不为之后盾,含酸饮痛,莫可如何。”中国水产学会在1928年10月致电农矿部,“速令取缔,取消其协约,停止其进行,否则我国东南领海最优美之处女渔场,必尽为日人所攫取。”
当日本先进渔船以中国渔民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效率捕鱼时,中国渔民只能通过民间自治的渔业团体向政府申诉委屈和愤怒。工商业发达的上海对此最敏感,海员总会、水产学校同学会、总商会、江浙渔业公会、渔轮业公会及各鱼商团体,先后向南京政府的外交、交通、实业等部门请愿。势力雄大的上海总商会提出特别强烈的抗议,因为作为理事的镇海人蒉延芳拥有8家渔行。
实业部长孔祥熙、部里的渔牧司官员皆坚定反对日本侵渔行为,实业部管辖着江浙渔业管理局。1931年4月,孔祥熙参加上海渔业改进宣传会并作演讲,他对渔业提出一整套减税方案,倡议政府多介入渔业,保护渔民权益并提供种种支援。这套方案,之后被中国的渔业学者及官僚实践和宣传多年。
全世界当时对领海宽度尚无定论和共识,海军力量最强的英国奉行3海里政策,许多国家遵循英国的做法,但也有不少国家反对。中国国民大会在1931年初想将领海延伸到12海里,遭到海军部的反对,海军警告此举会在国际社会招惹来很多不必要的敌意。4月底,海军部、外交部、内务部审议后宣布领海为3海里。但确定领海距离后,中国并不能阻止日本渔船进出,吨位大、吃水深的日本船通常在离海岸至少15海里外活动。困境中,孔祥熙想到了一个妙招,从关税入手。
孔祥熙的办法在1931年2月由国民大会通过,开始执行。首先,中国外交部通知日本,两国尚未签订渔业协议,故日本渔船禁止入中国港口。接着,财政部通知海关,禁止日本渔船携带渔获进入港口,除非是正规商船,但征收每斤4.4元关税。孔祥熙还补上一条,禁止排水量100吨以下的小船来往于两国港口,名义上是堵上走私漏洞,实际是驱逐大批汇集在上海、小于100吨的日本渔船。3月底,中国政府免除了一切渔业税和鱼税,这是中国反击战的辉煌时刻。
这措施必然遭到日本的外交抗议,同时还遭宋子文的强烈反对,宋子文嫌税收有损失。又因为中国海上力量不足以常态化执法,偏偏日本又是得罪不起的海军大国,事实上执法时打了很多折扣,但侵渔危机总归改善诸多。日本人可以找到许多变通的法子,例如将满载渔获的船开往日据的旅顺和青岛,装入中国船的冷藏柜后转去上海销售,或船上借挂中国国旗,诸如此类的做法当然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日本渔品的竞争力。故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渔船借己方海军撑腰,抓住窗口期,疯狂在上海卸货。endprint
不幸的是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沿海主要港口首当其冲被占领。中国彻底无力抗拒日本的渔业侵略,以及背后的强大海军。
战争中的渔业
大肆侵占中国沿海地区后,日本成立大批侵渔机构,在华东地区就有华中水产公司、东洋贸易公司、中支水产炼制公司、中国水产公司、帝国水物株式会社。日本在华北、华南也有许多侵渔机构。以成立于1938年11月的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它垄断了上海的水产批发,并特许日本拖网渔船在附近作业。日本当局为垄断渔业编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指责中国渔民运输和经销水产品的方法低效又浪费,亵渎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事实上,上海所售水产的收入很大部分进入日本海军囊中,海军方面更是需要严控市场。
沦陷区渔民并未被禁止出海捕鱼,只是需要获得日伪当局的海关号簿。中国渔船若要在上海卸货,只能固定卖给日伪的侵渔机构,如华中水产公司。不幸中的幸运,难民潮水般涌入租界,导致上海水产需求远超战前水准,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让在舟山海域捕鱼的中国渔民多少能克服战争带来的苦难。
太平洋战争之前,能在中国渔业生意上与日本竞争的唯有西方列强。法国人看准商机,在1938年6月与上海水产市场的华人中间商合作建立中法渔业公司,专事沪上法租界的渔品销售。为了抢货源,这家新的合资公司豪爽地给舟山的渔民们贷款2万元,与沈家门的水产捕捞业负责人合作,协商将渔品运到上海。这匹“黑马”的背后不仅仅是法国,还有其他欧洲国家。
尽管日军占领了中國大部分港口,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浙江沿海仍有很多地区处于中国政府掌控下。中国海军在战争初期就损失殆尽,横行无阻的日本海军和混乱秩序催生的海盗,给国统区渔民带来很多危险。例如,在台州温岭县,冬季带鱼渔汛到来,曾习惯季节性去舟山海域的渔船,出于风险衡量只能忍痛放弃出海。更有国家大义让位给养家糊口的时候,1938年7月,上海的定海同乡会代表渔商向宁波市政府求情,希望获准让渔获从定海运往上海。战时的物资封锁是双向的,国民政府一样禁止物资流向沦陷区。
国统区的渔船出海时携带中国的海关号簿,但遇到日本军舰时须把号簿藏起来或扔进海中,否则日本人会没收、销毁渔获,或强制把船带到上海,强制把渔获出售给日方的营销机构。而当渔船来到尚未沦陷的镇海港时,需要接受军队和海关的检查,上缴给地方渔会1到5元,船然后才能获准去宁波卖货。宁波沦陷后,渔船需要获得日伪的证件,否则遭重罚甚至生命危险。
抗战胜利后统计,中国沿海地区在战时共损失渔船几万艘。以浙江地区为例,1937年前约有26000艘渔船活跃在浙江海域,随后到来的战火毁灭15000艘。损失方式包括日军在海上击沉渔船、日军焚毁当地渔船、海盗掠夺和毁坏渔船、渔船因长期无法出海而年久失修,等等。中国渔船在舟山海域的渔获量在1936年是93000吨,至1947年仅剩12000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