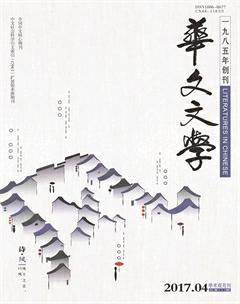论淡莹作品中的“新”华性
朱崇科
摘要:某种意义上说,淡莹相当成功的以诗作诠释了何谓新华性。她出生于马来亚,与新加坡社会共享类似的多元文化结构,她早年留学台湾,其诗作具有台湾型现代主义的风格,营构了一个有情的世界,这种气质与移民性吻合;而她留学美国后返回新加坡,又强化了其身上的文化中国性,因此她既涵化古典,又游刃太极。而步入中年以后,她对现实人生有着更为通达、圆润以及更为诗化的认知,比如她关注大千世界,也积极与自我对话,彰显本土情怀,同时她也具有超越性,并哲人般解释人生的课题。
关键词:淡莹;新华性;多元文化;诗化;中国性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067-13
作为新加坡最具影响力和创造力的女诗人,淡莹(1943-)的创作既引人注目,同时又有其内在的嬗变理路。原名刘宝珍的淡莹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江沙(Kuala Kangsar),16岁即发表诗作、散文等。1962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67年赴美,1971年获得威斯康辛大学(Wisconsin Madison)硕士学位,导师为周策纵教授,1971-1974年执教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SB),1974年6月返回新加坡,先后执教于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2004年退休。淡莹的新诗创作主要有:《千万遍阳关》(台湾星座诗社,1966)、《单人道》(星座诗社,1968)、《太极诗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发上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93)、《也是人间事》(台湾新地,2012),部分散文收入《淡莹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
整体而言,数十年创作累积成数册文本,淡莹的产出可谓厚积薄发,而1995年荣获东南亚文学奖,1996年再获新加坡最高荣誉的文化奖(文学),这既是对淡莹的高度肯定,同时反过来看也可谓实至名归。相较而言,有关淡莹的研究相对丰富:宏观的如文学史定位,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鹭江出版社,1999)②、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③等皆有论述。当然也不乏单篇论文,有对淡莹作品(尤其是《楚霸王》、《伞内·伞外》)的单篇赏析,如李元洛《亦豪亦秀的诗笔》(《名作欣赏》1987年第2期);亦有整体的分主题论述,如朱立立《爱·诗性·时间之伤》(《华侨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周可《浓妆淡抹总含情》(《华文文学》1996年第2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廖冰凌《存在之思——新加坡女作家淡莹作品中的哲理意蕴》(《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结合淡莹的最新诗作与散文进行处理,视角独特而厚重、论述有力。
表面上看来,淡莹作品中缺乏充分的本土性,而且其创作更多呈现出跨国的华人性特征,而实际上在我看来,淡莹作品中呈现出相当典型的新华性特质:其中一方面是明显的移民性特征,比如其台湾型现代诗创作,《千万遍阳关》、《单人道》;另一方面则具有多元性特征,比如她关于中华文化古典的现代表述,如《太极诗谱》等;关于现实世界的诗化表达,如《发上岁月》等。当然新华性中也包含一定的本土性视野,这在她的《也是人间事》、《发上岁月》中往往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实践。但不必多說,上述术语既有其边界,又往往犬牙参差,而结合其历时性发展,又别有一番繁复纠葛。这也是以(哪怕是繁复)观念统帅丰富个体的尴尬之处。
一、台湾型现代诗:有情世界
在《也是人间事·自序》中淡莹写道,“重读早期的诗作,特别是大学时期写的《千万遍阳关》和留美后期及刚回到新加坡时写的《太极诗谱》里的情诗,十分惊讶自己也曾经那么年轻多情过。年华似水,心境迥异,这类诗也算是在我人生中留下的一丝片影鸿爪吧!”(第22页)和“少年心事当拿云”不同,少女时期的淡莹往往多愁善感,在台读书时期,她得益于台湾诗坛甚多,如名诗人周梦蝶(1921-2014)的指点,罗门、蓉子夫妇的帮助,同时1962年和王润华、张错、林绿、陈慧桦等人创办星座诗社,她也从台湾型现代诗的汲取者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建构者,为此,她可以文字搭建起一个“有情”④(沈从文语)的世界。这里的“情”包含众多,毫无疑问,第一是指爱情,其次是指亲情、友情,第三则可以泛指普泛意义上的情感。
(一)西化的爱情。这里所谓的西化的爱情并非是指淡莹早期诗作中的爱情书写只有西化色彩,而是指她至少在两个层面展现出西化特征:其一是书写手法,无论是遣词造句、意象展现等诗歌技艺往往采用现代派技艺;其二是,在中国意象连缀时往往以西化意象衬托,而在观念取舍上往往也是西化居多的。比如《窄裙的边缘》“每个日落都激起一团圣火/燃亮你紧闭的双目/莎士比亚从此长眠不起/当你躺在窄窄的黑裙边缘//水光潋滟,照不尽旖旎/便睡到洞庭湖西子湖也枯竭/这是你永恒的归宿//下次我们再相望时/嘴里就嚼满了记忆/那个油腻腻的午夜/你在我的唇上绘半截彩虹”(《千万遍阳关》,第12-13页)认为,伟大的世俗爱情甚至可以让莎士比亚长眠。
《雨及千伞》“十月,我守住了特洛埃/城外长发的希腊人欲飞渡城墙和壕沟/宁静了半季的落霞道,此刻/竟飘洒起木栅的柔雨//我走出特洛埃的寂寞/撑着千伞旋入鏖战/风吹得我裙也飘飘,发也飘飘/那欲飞渡的人仍在千伞之外//威猛的Achilles以为操纵着胜利/忠实的Hector不知死神已步近/宙斯的目光没有比这时更冷漠/海伦却在一夜间哭湿了木栅的肩膀/轮回啊轮回,命运啊命运/你且来,千年,万年/在霹雳河畔或是在落霞道/我聆听流水淙淙,我不幻作落霞”(第34-35页)也具有浓厚的西化色彩,这首诗以希腊神话的典故映衬诗人对爱情的渴望、主动甚至是历尽艰辛的战斗。或许相当典型的则是《那一夜——之四》“那一夜,多瑙河呜咽/你遂遗失太多珍宝//远离传统下的嘲笑/化宇宙为纤指/与你交叉,十指交叉/共酌泛滥一秒钟的目光//我看不到现代,听不见古典/在音乐故乡的维也纳/史特劳斯偷啜暖暖的咖啡/偷啜情侣的疯狂//天火的炽焰在北极结冰/焚烧我们,复活我们/推开宇宙,你丑陋的笑/笑出一切无可奈何//那一夜,多瑙河呜咽/你遂遗失太多珍宝”(第48-49页)。诗人以相当雄阔的语言、西化的意象书写爱情的悸动,当然语句中间也偶有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影子。
当然,在淡莹吐露爱情的书写中,亦有中西结合相当圆润的诗作,如《今晚,我走后》“你将有重重凄楚/今晚,我走后/留下一阁回忆/半窗星蓝//立莲而降,并展开罗裙/覆盖你,自上至下,自左至右/你不栽莲,莲为你开放/开出馥郁,开出真真//然后缓缓下跪,膜拜/朝你,朝我/奉献一瓣虔诚/远方传来了肃穆的颂歌//今晚,我走后/回忆在你的床边丛生/你若子夜醒来,就默数半窗星蓝”(页50-51)以现代的手法,中国特色的意象(莲花、宋词里的真真等)连缀成一首雅俗共赏的佳作。需要指出的是,淡莹大学期间的诗显然相当西化而且晦涩,为此我们不能过分具体化其爱情所指,很多时候,诗作中的“你”可能是泛指(少女怀春的必然结局),也很可能是现实中的白马王子,当然有时也是幻化的缪斯的化身,为此解读时不可过分坐实。
1967年淡莹赴美并与王润华结婚。而她的《单人道》(1968)中的爱情书写在具体个人层面有了确指。此诗集中很罕见的暖意作品《今夕》也可以呈现出爱情的恒定性与彼此的思念,“从你的双目搭一座桥梁到我的双目/六十英里的惆怅和相思/今夕,你便是牛郎,我是织女/握掌的温暖,在桥的中站”(第55页),当然也有西化的痕迹,“我很倦,欲睡在希腊人的臂弯/梦已经平息的爱琴海/在阳光下跳出金刚钻,套着/那延伸至碧落至黄泉的无名指”(第56页)此间展示了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恒定性。有趣的是,诗作中还嵌入了他们彼此的著作名称,比如王润华《患病的太阳》、译作《异乡人》、淡莹《千万遍阳关》等。当然诗人也可以续写他离开后的孤独感,如《孤独梦》“他离去的脚步像吸水纸/吸干我洒在长亭的怀念//十里之外仍有十里/直到无涯处/相思树的浓荫成雾/推我入苍茫和孤寂中//那张弹簧铁床,蹦起/他小寐时的磨牙声/他屈背离开拓宝藏的书房/遗下数根莎翁的白胡须//我的目光常被扭曲/巡视空室,一如域外/只有延伸的地平线/而无古人,而无来者//他匆匆的脚步吸尽欢聚后/我是暂时枯萎的向日葵/串孤独梦,在长亭外”(第62-63页),同样是以中西合璧的意象(如莎士比亚、长亭等)表达思念、回忆和孤寂。
相当有趣的是,爱情也可以成为彼时相对青春的夫妇面对艰辛生活的精神支撑与凭借,这尤其体现在她在《太极诗谱》中那些书写当年北美生活的篇什中。比如《团圆》中就写道,“听你说/七年前缭绕在指南宫的一缕青烟/仍如我们的初恋缭绕在你心中/于是就有多少相思也被你握成团圆了//于是风雨之后的那晚/我被握成一朵睡莲/日夕等待/歌手行吟至湖畔/吟唱一曲/采莲谣”(《太极诗谱》,第128-129页),其中明显有一种对爱的回忆、确认与渴望。而《走在昔日的路上》(1972)则是人在加州工作的淡莹向王润华的浓郁思念诉说,“我是一缕孤魂/为追溯往事/独自飘来荡去/你说,我该在何处栖身?/你说,我如何燃亮三百个漫漫长夜?/行行重行行/每一步都踢起很多惆怅/与君生别离/你我的思念有没有归宿?”(第126-127页)当然,偶尔也会以过客的身份翻转思念和寂寞感,“十二月/我的怀念/像雪花洒在你双肩上/你是赶路的过客/漠视星光,漠视雪花”“雨打纱窗五更寒/你犹在三千哩外/犹在渺茫处/我却记取那夜共舞时/旋律把我卷入深深的寂寞里”(第123-124页)。而到了《伞内·伞外》时,这种爱情的焦虑感变成了诸多宁静与甜蜜、共渡与守候,“二月底三月初/我折起伞外的雨季/你敢不敢也折起我/收在贴胸的口袋里/黄昏时,在望园楼/看一抹霞色/如何从我双颊飞起/染红湖上一轮落日”(第90页),俏皮中显示出天人合一的爱意。如人所论,“情爱是文学史上永恒的话题,二十世纪文学中的爱情往往失卻了神圣的光芒……淡莹诗中的爱情醇厚深挚、健康而有活力,是相爱双方默契的应合和深情的关怀,这样的诗让我们对人类和生命产生信赖和依恋。”⑤
(二)过敏的悲情。罗门指出,淡莹的某些诗以“爱”为轴心,“向周围所辐射与波及到的种种属于人尤其是现代人的存在情境——如人的孤独感、失落感、绝望感、都市文明的空漠性,死亡的悲剧性、以及红尘剃度的情怀……等等皆是颇相一致的,且形成她独特的精神创作面”。⑥这的确是指出了《单人道》主题书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相较而言,《千万遍阳关》中的诗人偶有愁绪,但总为爱情所冲淡,如《五月在落霞道》“我是南风,旋转满林的相思树/红绒的裙子,折叠于片片叶面/你采摘后,夹在小杜的诗里/没有星光的夜晚,不围炉谈小杜的诗/遍读茎上的发香,泪眼及迷茫”(第27页),“泪眼及迷茫”已是诗化的存在,而且“发香”也透露了爱情的融合度;《任你缥缈远去》“自此不泣唱阳关,空余惆怅/任冷冷的风夹在衣袖里缥缈远去/我不回首,但似孤城,在洒着针雨的窗前”(第19页)亦有一丝“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甚至在《夜游指南宫》更显出一种体验丰富情感(包括忧伤)的主动追求,“以十指弹落廿三个红尘/掌吻掌,随你上山/回眸处,盆地列满星座//级级皆是一洼死水,皆有佛盘坐/闭目合十,任岁月劫尘世/任嫦娥的裙裾成炭,成灰//今夜上山,岂是禅悟/如来与我何关?我不圆寂/只伴你并坐石阶,唤醒愁结”(第9页)。
而到了《单人道》中,诗人呈现出相当强烈的悲剧情结,同时类似于疾病、死亡、绝望、虚空等意象频频出现,如《季节病》“满目皆呻吟,悬挂在铁床的四根支柱上/黑轰然陨跌至纱帐内/我是一条受伤的蛟龙,在血泊中/翻腾、辗转,与死亡作季节性的鏖战//绞痛和冷汗闯入了病榻/纠缠得呻吟声如火山之爆发/喷出红似熊焰的岩浆/狂吞一瓶又一瓶无辜的针药//死神每廿八天必打幽谷经过/透视埋着的宝藏是否很处女/而一切仍很奥秘,仍很处女/带着弓箭准确的征服者犹未降临//胜利与我彼此相属/季节病暂时痊愈后/我匆匆束装,往太阳的故乡旅行/让发育不全的生令,继续酝酿、破裂”(《单人道》,第51-52页)诗人通过处理痛经的经历观察周围病者,可谓细腻而深刻。
《钟声常鸣》是一首较长的诗,主要是涉及淡莹1966年返回马来西亚短暂的代课生涯,如“绝望是周期性的复发症/打上帝的指缝经过//每天,将时间装进公事包/以最低廉的价钱拍卖给学生/他们的头脑是刚写满又擦干净的黑板/常飘落一些粉屑到我的旗袍//划红色的死亡交叉,在堆积的作业上/把剩余的生令填入课程表/我不再是城堡里的贵族/而是向英国历史请求粮食的乞丐”(第15-16页)就是对她厌烦的工作的描述。不必多说,她绝望或愤怒也是其源有自,核心是“缪斯的精神被分裂吊在办公室的钟摆上/那规律的钟摆,摆不走千年遗憾//生令只是每支粉笔的附属/写满无数个黑板后又拭去/我将用剩的夹在拇指食指的短短希望/投入字纸篓的血盆大口/教室外,长廊以直线形的空虚迎我”(第17页)当然也有外在原因,学生们往往不动脑筋思考,“他们的目光系着一连串通向茔地的钟声/我就恨高跟鞋的细跟刺不进他们的神经/医治患了麻痹症的大脑小脑”(第18页)。诗人也写到彼此的煎熬与解放,“囚车已辗着时辰到来/耳膜炎即刻痊愈,只听钟声/像生令之虹,划过黄昏阳”(第21页)。
《终点》中书写颇多都市病,但即使是写诗人自己获得学士学位的判断亦显得触目惊心,“墓志铭铸制成的方帽子/如今被压缩得很扁/古罗马中国也被逼到坟场寻找立足之地/那两千个幽魂却飘游处处/以镜头猎捕光荣及辉煌/当很历史的钟声响自扁平的帽顶/我的约会永远在出口之内/绝路之外”(第22-23页)。而《数尽无奈》则把一种幽怨、无奈和绝望的意绪写得剑拔弩张,“绝望撒下如台北市万吨灰尘/自前窗闯入双眸的阴影/我踩不死传染病菌/它们在拖帚里繁殖复繁殖//每个毛孔都据居着绝望/拥挤、蛮横、阻塞/我被囚困于黑死病的磁场/无法冲出两极和传染区//眉睫再也织不进期待/只能抱膝面壁/任绝望像越战升级/像流行症蔓延//蔽天的神伤,纷纷降落/以千钧惆怅镇压我/我披发阖目,在雷峰塔下/数尽幽怨,数尽无奈”(第35-36页)而且调动了现实、典故和自我的敏锐感受轮番上阵。同样还有令人绝望的绝望,如《希望龟裂》,在用了不少诗人典故后,比如李白、陶渊明等,诗人开始夸大感受,“这是个空气也龟裂的日子/流弹苦闷到爆炸/豪雨的征兆虽已悬在半空/雨后,绝望却丛生如春笋”(第40页)。如人所论,“对存在状态和意义的模糊不定,导致焦虑不安的潜在愁绪,在《单人道》里愈见鲜明。此时淡莹已毕业并执教,刻板的教学生涯,离乡多年重返家园的调适困难,使她更敏感于自身存在的观照。这19首诗少了之前的淡淡愁绪,取之以鲜明具体的意象、澎湃激昂的情绪。纵观《单人道》,尽是生理和心理的疾病与痛楚,‘疾病(the Illness)可说是高度概括的喻体、象征物。”⑦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赴美一段时期,诗人和丈夫王润华过着相当艰苦的生活,他们不得不栖居地下室,还要到处兼职赚取生活费,而《太极诗谱》中的《火焰》就表达过愤怒得找不到出口的情绪,“很想仿芝加哥的黑人/以愤怒燃烧起一把火/燃烧起被放逐到异国的悲哀/可是火焰啊,火焰在何处?”(《太极诗谱》,第116页)《饮风的人》中也有灰黑的倾吐,困窘而无奈,“他是一只被追逐于视线之外的黑鸦/再愤怒也啼不醒万年青的绿意/乃挟两翼寒流徘徊至水穷处/环视域外而域外无一树无一歌”(第111页)。
但毫无疑问,诗人也书写其他情感,比如血浓于水的亲情,既构成了有情世界的宏阔天空,又是一种自我的释放,比如留美时期的《那比永恒更永恒的名字》就是献给母亲的诗作,“咬一口半生熟的牛排/咬一口千哩外你的声音/可口可乐的空瓶子底下/有一层薄薄的眼色沉淀”,这是以细节贯穿;也会直抒胸臆,“以爱叠起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渡过异乡深深的庭院/一刹那顿悟,那比永恒/更永恒的名字是/母亲”(第118-119页)。
《千万遍阳关》中亦有献给父亲的诗文,《常青树》“好比灯塔,照引七艘船的航程/又似燕语,衔去汹涛/无巨浪的臂弯里,我是第四艘船/泊岸吸满毅力后,便乘天风赶万里//你没有名字,你的名字是永恒/排列在我旅途的两旁/只要一仰睫,生活就蓊郁”(第8页)某种意义上说,父亲既是淡莹永恒爱的源泉,也是一种奋斗时期的精神支撑。《单人道》时期除了用可以确认的爱情稀释愁苦外,亦有友情滋润,比如《今夕》中提到羅门,“偶尔与罗门谈谈攻城的战略/说海伦如何被希腊人的精神感动/蓓蕾开放前,自己却寂寞躺下望云”(第58页)。而到了《太极诗谱》中,既有给知己白先勇的专文《五千年》“他是一抹独来独往的云/悬在五千年历史的上空/从一个朝代漂泊到另一个朝代/而归程是杜鹃嘴里的一只绝曲”(第114页)颇有激赏之意;当然也有为友人的诗作《无题》(第120-121页)。
罗门指出,“淡莹在创作时,思想与情绪的涌出,是颇带有那种感人的冲击力的,但还是嫌急了一些,如果能冷静与忍耐一点,使‘诗的本身执住绝对与所有的发言权,让思想与情绪默然(非消失)在诗中,则对其完成‘艺术优美的传达过程,与使诗接近乃至进入佳境是大有帮助的。”⑧这种批评自然有其道理,但作为更多是年青时代诗情与实验的产物,《千万遍阳关》《单人道》也有其激情飞扬、活力四射以及相对西化的特征,这种特征无论是对淡莹,还是对于后来的新华文学中的移民性特征而言都是可以理解的,往往也是难以复制的。锤炼与融入既需要时间、阅历,又需要更多的反思、反拨与实践,而这种变化要到她返回新加坡后才会有质的变迁或提升。
二、古典的现代表述:华化魂灵
耐人寻味的是,留美经历对于优秀的新马华文文学家往往都产生了相当深远而且内在的影响,如王润华恰恰是在其留美时期及稍后创作及出版了不可踵武的《内外集》,尤其是“象外象”系列。李永平(1947-)也恰恰是在留美时期创作出马华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吉陵春秋》,而相当别致的是,其中的吉陵镇富含四不像哲学,是一个颇具典型性的恶托邦⑨形象。毫无疑问,留美7年对淡莹也别具意义,其中之一就是再中华化(Re-sinonization)。而在1971-1974年她受白先勇推荐在UCSB讲授古典文学、中国文化、初级中文等,这都为她涵化中华文化的古典精华部分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是一种直接触发。
值得注意的是,淡莹的再中华化还有第二种机缘,就是1974-1980年她在风雨飘摇的南洋大学执教,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如她写于1984年的《惊变》就是描述她参观南大遗址的感慨,其中有纠结,“铲泥机、打桩机、起重机/一齐怒声呵斥/逼我立即走出/走出这幅青山绿水//风过处/落叶喟然无语/我使劲踢起/一些文化遗迹/一些胸中块垒”(《发上岁月》第34页);有对南大精神中团结一致、草根性的弘扬,“看!那如拳头粗的铁锁/寒光慑人,森森然/锁住了文、理、商学院/锁死了每间课室里的/春风。小草不能再生/所有根须都被刈除,包括/卖冰水、踩三轮的血汗/包括贩夫、走卒的感情”(第35页)同时也写到对这种所谓现代化建设破坏性的不满与质疑,“还有湖光,还有山色/一罗厘一罗厘被载走/日后回来寻觅/应以何处为起点?//夜的黑爪,霍地张开/我握着轴的两端/将心情 慢慢卷起/从满目疮痍中/一步一回首/走出这幅/这幅青山绿水”(第35-36页)。
(一)涵化古典。淡莹书写/重写古典的系列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写于美国的《楚霸王》系列;其二是,《怀古十五首》写于南大时期;其三是写于台湾时期(2004-2012)的古典乐器系列。
1. 《楚霸王》系列。毫无疑问,《楚霸王》是淡莹的成名作乃至经典之作,它相当娴熟的展现出诗人的多重书写面貌,如李元洛所言,“《伞内·伞外》这首诗,和《楚霸王》的情调风格完全不同,后者是金戈铁马的英雄豪气,前者是花前月下的儿女柔情,后者是烈火狂飙中,前者是人约黄昏后,充分表现了这位女诗人多方面的诗的才气。”⑩
整首诗霸气十足,如诗歌的开头,“他是黑夜中/陡然迸发起来的/一团天火/从江东熊熊焚烧到阿房宫/最后自火中提炼出/一个霸气磅礴的/名字”(《太极诗谱》,第41页)。同样在书写垓下之围时,诗人也别具匠心、对比明显,“此岸/敌军高举千金万邑的榜告/他那颗漆黑的头颅/没有比这时/更闪烁/更扎眼//彼岸/妇孺啼唤八千子弟的魂魄/纵使父老愿再称他一声/西楚霸王/他的容貌/已零落成黄昏/乌江悠悠”(第45页)。《虞姬》则又彰显出诗人的婉约气质和技巧,写她的生不逢时,“在那双重瞳里/她是一朵/开错了季节的/海棠花/饮罢酒/舞罢剑/就遽然化作一堆/春泥”;她的附属性,“营外是恨/营内也是恨/这一串血泪/该和在酒中/咽下/还是揩在/他宽阔的肩上”(第45页)。当然更写她的杀伤力,“绊住马蹄去向的/岂是一匝/又一匝的猛将悍卒/是她款款的眼神啊/不能仰首/那眼神”(第46页)以及勇敢率先赴死,“舞完这一招/已是登峰造极/她如凌空的剑花/倏然逃逸出/谣传纷纷的/重瞳”(第46-47页)。
《乌骓》则是另一种写法,虽然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它”,但此马却有主体性,比如其思考和对战争的小视,“自从东渡/它总以为对岸的鼓声/是一阵一阵春雷/顶多淋湿着苍白的杂毛”,其事功“它曾前蹄腾云/后蹄驾雾/驮着江东一股霸气/创下楚国江山”(第48页),其被主人送人并渡江,“风跟云/在水面悠悠地漂流/船在水上/骓在船上/悲哀坐在马鞍上”,其自杀殉主,“当对岸的鼓声/震落整个江山/他的长嘶/一直沉入深深的江底”(第48-49页)。
2. 《怀古十五首》系列。这个系列中的标题/主题大都是词牌名。耐人寻味的是,淡莹在处理时大致呈现出两种意象:一种是复活古典,以延续其韵味和意义指涉,如《声声慢》“终于走出/走出四弦/轻拢慢捻/将半生的沧桑/弹成一首/一首哀艳的绝响/从北宋唱到/南宋,唱到/乌啼,泉水瘖哑/唱到弦亦断,魂亦断…………”(第52页)有很强的历史感。《蝶恋花》“谁敢保证,三月/翻飞在花间的蛱蝶/梦见的绝对不是我//轮回以后/也许我超生为蝶/也许蝶沦落为我/也许什么都不是/你何尝听说过/十二生肖中,也有/一只羽翼斑斓/吮食花蜜的昆虫”(第61页),此中既有庄周梦蝶的典故化用,同时又重新诠释了“我”和蝶的化的可能复杂关系。《渔家傲》“我隐姓埋名/多年,却无一日/不纵情傲笑江湖/只有那对立于水中/瘦骨临风的白鹭/始终觉得费解/我晨昏泛舟/钓起的总是一片/浩瀚烟波”(第59页),其中洋溢着隐秘的尊严、孤独和清高感。
而另一种主体介入性更强的倾向则呈现出古典再现之后的现实性或哲理思辨。《武陵春》“纵使有桃花千株/我不妨小立此岸/观赏,何必问津/水流的来处及去处”(第52-53页)呈现出一种远观和更超脱的境界。《新荷叶》“几颗浑圆的露珠/蕴藏着大千/滴沥溜转/在刚舒展的荷叶上//明日滑落泥溷中的/是摇摇欲坠的露珠/还是正在摆渡的/我”(第54页)则是属于物我的同化;《满江红》“啊!请不要误会/染红了一河床鹅卵石的/是仇家淋漓的鲜血//在草本植物中/天生纤小的我/喜欢逐水而居/经常把胭脂般的面颊/探出水外/好奇地浏览/陆上明媚的风光”(第55-56页)此诗颠覆了其原有的壮怀激烈,而以紅色水草的淘气与习惯呈现出一种自然风光。
整体而言,淡莹的此系列书写呈现出她对有关古典文化知识的熟稔,但她又不是一种被动接受或吸收,而在其间介入了新的理解、现实感和鲜活的诗性,从此角度看,其书写呈现的是更具超越性的华人性。
3. 古典乐器系列。实际上,在1980年代淡莹在《发上岁月》里也有两篇古典书写/重写。《重逢》(1989)是书写唐婉重见陆游时的追问,回应《钗头凤》。她借唐婉之口发声,更强调二人的知己关系,“鹣鲽之乐像旭阳/穿透枝叶和寒雾/筛落心田/红颜,是我/知己,也是我/不妨帘外,婆婆有意/无意间的咳嗽/藏着几许嫉恨”(第186页);同时又比照陆游的矛盾性,可以阵前杀敌,“强敌当前,毫不惧惮/甚至梦中,亦驰骋沙场/向胡奴追讨河山/吐气如虹,愤慨满腔的/你,怎么会,怎么会/慑于无形的礼教/在严峻逼人的目光下/飒飒写下一纸休书”(第186-187页),却无法保留真爱,故二人婚姻最终也只能如花枯萎。《诗魂》则是重写屈原,其中既有雄壮气势,“三闾大夫显赫的身世/包裹在重叠的竹叶里/脉络分明,密实饱满/从汨罗江至江北江南/流至二千多年后的今天”(第189页);亦有细腻的现实与历史的交错书写,“绳子解开,叶子揭开/我双手捧着的/是一出有棱有角的历史悲剧/掌纹中隐约传来/深沉急促的鼓声/咚、咚、咚咚咚/击散所有水族的魂魄/击落楚国的猎猎旌旗/击痛无数翘首仰望的眼睛”(第189-190页);当然也奉献褒扬、提及屈原的自沉,“肝胆可以映照日月/情操可以印证山河/饮露餐菊之余/问了天,问了地/仍有许多吐不完的牢骚/乃行吟泽畔,任/湖水如谗言/及膝、及腰、及肩/淹没一颗被放逐的头颅”(第190页),也有诗人对屈原的真诚纪念,“水底的诗魂,不管/你是否涉江而来/我都飨你,以微温的雄黄酒/且趁着夕阳未下/人尚未酩酊/焚烧此三十行/成灰烬”(第190-191页)。不难发现,此一时段的淡莹在书写真爱与正气时亦颇有正气,同时往往以相对圆熟的诗艺正面建构。
而到了退休后旅居台湾时期的古典乐器系列,淡莹的书写又有了新境界。《琵琶》却是借助经典曲目“十面埋伏”将其战争化/武器化,“原来敌军就埋伏在十指之间/硝烟四起的刹那/周围一片漆黑/鸦雀无声//不知道一弹指/多少战马奔腾飞跃/一按弦/多少队伍相互厮杀/我蜷缩在角落/忐忑不安,屏息/凝视着琵琶上方/交错闪动的刀光剑影”(第25-26页);而且还细描其台上台下的巨大杀伤力,“杀戮声阵阵/自远而近,由疏到密/蓦地眼前一黑/我颓然倒下//血,从伤口/不止一处/汩汩冒出/染红了台上台下”(第26页)。《二胡》(2010)借助盲人阿炳的“二泉映月”重写旧文本,“一开始小巷就被拉长了/唏嘘之声自巷头延续到巷尾/孤灯下/那双充满凄苦的盲眼/正一步步探索呜咽的出路”,她巧妙的将半辈子的辛酸与琴弦挂钩,“梗在胸臆间的辛酸/被琴弦缓缓拉出来/再一点一点被推回去/推拉之间,不觉/过了大半辈子”(第27-28页),毫无疑问,二胡的演奏也有上佳效果,“寒月高照,泉水冰冷/我虽不喝酒,没抽烟/甚至拒吃高脂肪食物/心房还是揪在一起/抽搐了又抽搐/最终淌下两行清泪/一行留给来生/一行还给过去的自己”(第28页)。《古筝》则是借助“高山流水”的曲目,诗人着力书写二者之间的知己关系,“小溪淙淙,清泉潺潺/目的乃奔赴巨川/我的流向异于它们/我要永远依偎崖下/让澎湃的水声/见证一生一世的盟约”(第30页)。毋庸讳言,古典乐器系列更可以呈现出淡莹书写的收放自如,既可以刚烈铿锵,又可以细腻入骨,甚至这种巨大张力可以实现平稳而灵巧的转化。
(二)游刃太极。1971年淡莹开始在美国学打杨氏太极拳,1974年回到新加坡后,一段时间内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去空地上打拳,因此悟出一些人生哲理。1975年开始写《太极诗谱》,一直到1977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这40首诗。
淡莹写道,“在这一组诗里,有单写动作的如《白鹤晾翅》、《单鞭下势》,也有写动作兼蕴含我个人对人生的看法的如《抎手》、《金鸡独立》、《撇身捶》、《栽捶》。我较偏爱后者,不止是我写它们时注入了我的真实感情,同时它们也赤裸裸地反映了我的人生观。我不否认这些诗正如一些朋友所说含有很玄的禅理。佛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精神支柱,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世态度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一般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常常处在不知不觉中。”{11}从整体的角度看,太极拳的一套招式在认真处理后可以起到通体舒畅、强身健体之效,其中既有中华文化,如佛、道家的养生之道,同时又有诸多相生相克、吐纳自如、天人合一的大道理。淡莹的书写首先暗合了这一整套流程及其结构,如开头的《击掌问佛》“自丹田/徐徐地/呼出一部似懂非懂的/易经//一举掌/那朵洁白的莲/竟不选季节/吐蕊了//弟子在下/何谓阴何谓阳/何谓虚何谓实/何谓柔何谓刚/又何谓太极之初”(第7-8页)既有开始,又有疑惑,而结尾(四十)《左右揽雀 尾合太极》则对此有问题的对应答案,“打完最后一招/始大彻大悟/所谓太极/即一切阴阳之母/静则合/动则开/无声无相/生生不已”(第37页),同样还有一个相对圆满的回归,“这时我必须/回归本位/必须释放/栖憩在发丛中的/一对山雀/重返混沌的/太极之初”(第37-38页)。中间的38招,既是太极姿势,又是组诗的骨架。易言之,诗歌的整体结构和太极拳的程式合一,而某些招式和理念亦具有契合性,而更引人注目的则是浮游其上的淡莹的独特人生理解。
(十)《倒撵猴》其中既有对动作的描述,如可退,“你把如意棒/抡成又红又大的落日/紧随着我的脚步/下山”,然后反击而进,“再退便临渊/我运劲/如抽丝/源源递送”(第12-13页),但诗人最后还有对哲理的升华,也有对前文本《西游记》的调侃,“莫走/你愿意选择/水帘洞/或是/金、木、水、火、土”。(二一)《指挡捶》当然有对动作的描述,“敌刚我柔/敌柔我刚/敌进我退/敌走我粘/反正是这么回事/周旋下去/难免大开杀戒”(第21页)但亦有发自人性角度的批评,“这一招/何其毒辣/竟决意断绝/其命根子//历代传下的/家谱/从今以后/是不是一页/空白”(第21-22页)。(三十)《金鸡独立》“我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寻找/禾堆里/零零落落/被遗忘的稻粒/并无意/蓄劲在胸/把你踹踏成/大千世界中/一芥微尘”(第27-28页),书写颇出人意料,书写此招式背后蕴含的寡欲或无欲则刚的道理,而非是为了攻击或杀戮。(三四)《栽捶》“一捶下去/我突然变卦/把积压了/十五载的/冤仇/私欲/全埋在/这一小钵/净土里/到了春天/开发出来的/竟是三两株/菊花/及淡淡的/白莲”(第30-31页)亦有相当仁慈的心,把一个杀招转换成和谐之美(菊花/白莲),可以显出人格的高洁。
某种意义上说,淡莹对《太极诗谱》中人生哲理的感悟既有其相对鲜活、有趣的主体介入乃至独创性,同时又有在感悟太极博大浩瀚精神之后对不少世俗观点的超越,从此角度看,其诗性气质、道德品格与人生哲理三位一体,颇有价值,如人所论,“淡莹的《太极诗谱》含有很深的人生意味,而这种人生意味中又无不蕴藉着玄虚的禅理,这种禅理的获得不仅是诗人以超然之眼看人生、以平常之心感悟生命的必然结果,也是诗人将自己的个体生命体验融入中华传统的道禅文化精神血脉之中所修悟的人生与智慧的自然流露。”{12}
三、不拘一格:现实诗化
如人所论,“淡莹进入7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创作也就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风貌,具体表现为:审美视角渐渐从内心世界转向日常人生;情感表现从精巧浓密转为质朴素淡,有时直抒胸臆、直陈心迹,竟不惜以散文笔法出之;而意象营造也显得简明、疏朗——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其诗作的整体风格有了一种于灵动中见稳健,于敏感中见平实的气象。”{13}易言之,中年以后的淡莹更关注现实,同时也诗化现实的倾向开始增强,相较而言,淡莹的《千万遍阳关》与《单人道》,要么关注爱情主题,要么表达一种愤怒、焦虑、绝望意绪,加上语言相对晦涩,与现实关联性反倒显得疏离。从《太极诗谱》开始,尤其是其第三辑“鸿爪篇”有部分篇目开始呈现直接的现实性,而到了《发上岁月》与《也是人间事》则更是成为一种主流,淡莹在此中也呈现出其较强的包容性和多元主义。不必多说,亦呈现出其某一层次的新华性特征。
(一)关注大千世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大千世界当然不是指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世界,而是指可以呈现淡莹书写题材大气或霸气特征的世界,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一是对国际重大事件的观察及入诗;二、有关弱势群体的雕塑式的书写。
1. 快照国际政治。幸或不幸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时,淡莹正在中国夫唱妇随学术休假的王润华,而后他们于是年7月仓皇离开,并到了北美,但半年内难以忘记此事,所写四首诗皆与此有关主题有关。《此山非彼山》固然书写山势雄伟的洛矶山脉,但美景还是无法抵消屠杀的梦魇,“这一路上,山山水水/总难以跟心中的块垒认同/异国之土,他乡之水,毕竟/非我朝思、暮恋的神州/血,若非一夜之间/流成触目惊心的河/此刻我正在攀登黄山/沾一份灵秀之气/将全身浓浊的人间/烟火,清除得干干净净/绝不是在逶迤的山路/被来自千寻的庞大压力/震得遍体内伤,七孔淌血//巉岩陡然从眼睑拔起/险峻堪称险峻,却/哪儿有子弹,在体内/爆开一片鲜红的血景动魄?/山势的确峥嵘嵯峨/可怎及得上坦克车前/巍峨屹立的民族魂?”(第9-11页)《不必等我寄什么》原本想寄什么礼物给友人,但依旧难掩对有关惨案的愤懑,“艳红的枫叶使我想起/血,流自中华儿女身上/一行接一行,毫不畏缩/从英雄纪念碑前/汇流入每晚的梦中/怵然惊醒时/全部枫叶已萧萧/剩下光秃细瘦的枝桠/宛如早逝的千臂/奋起向苍天控诉”(第13-14页)。《断掌与合掌》则从枫叶想到流血事件,“俯身捡起/审视再三,赫然发现/叶脉清晰,一丝不苟/显示今年春夏/国运多蹇,黎民百姓/莘莘学子,难逃一劫/凑近断掌,我仿佛听见/血,不断冒出来的声音/骨碌骨碌,沿着长安街/直奔向全世界的良心”(第16-17页),同时也为他们招魂,“断掌入土以后/该我合掌,期待/以刽子手的腥血/在庄严的天安门前/写下慰魂的诗篇/我的梦魇、我的椎心/也要趁着祭奠的一刻/统统焚烧干净”(第18页)。《人间乐土》原本是写母校Wisconsin(Madison),却又由幸福的学生们想起天安门广场的惨状而加以不自觉的比较,“无需与坦克、机关枪对峙/幸福、青春、精力/尽可以任意摇摆出来/把鼓声擂到云霄之上/把金发抖成碎裂的阳光/把胴体扭成蛊惑的蛇/广阔的土地上啊/到处滋生着人权和平等/永远挥霍不完/六月的伤口累累/从夏至秋,始终未能复原/到了湖畔,被电子吉他/无意间一弹,立即迸开/血,如泉水般喷出/汩汩流满了校园一地”(第21-22页)。相较而言,这类类似于命题作文的诗歌(所谓“人文关怀诗”{14})不太容易写,更多是表达诗人的某种悲悯和愤怒情绪,成就并不太高,主题深度一般,但贵在记录诗人的即时心境与仁慈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