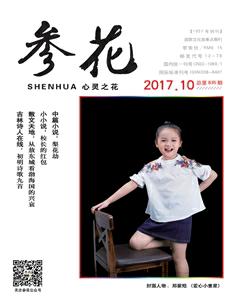乡村权力网络中个体存在的寓言
摘要:乡村社会内部有着严密而稳定的权力运行机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网络。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互动中,乡村处于明显的被动位置,乡村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受到了来自城市文明的强烈冲击。一方面,乡村传统的权力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权力之网也笼罩在乡村上空。叶弥在短篇小说《向一棵桃树致敬》中,以一颗悲悯之心谱写了一个乡村权力网络中的个体存在的寓言。
关键词:《向一棵桃树致敬》 乡村 权力 个体存在 寓言
杜赞奇这样定义权力:“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強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权力的各种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1]《向一棵桃树致敬》讲述了清潭村村民谭海五和妻子龙英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坚持拒绝卖树,守护自家大桃树的故事。在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暗含着当代中国乡村中个体在权力网络下的存在境遇。个体内心汹涌的欲望,无处不在的权力的网罗,人与人之间有形或无形的话语压迫,这都是叶弥所关注的人的存在现实。
一、艰难世事:权力网络的无处不在
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当代乡村,村委会成员成为乡村实际的政治权力所有者,成为人们恐惧又崇拜的对象。叶弥在小说一开篇就提到,清潭村里没有狗敢对着村委会主任陶云生狂吠,因此海五和龙英夫妇可以凭着狗的反应判断来人是否是陶云生。事实上,惧怕村委会主任的并不是狗,而是人。这种狗不敢吠、人不能言的局面凸显了权力的巨大威慑力,以及权力所有者对无权者的全方位规训。这种规训左右了人的存在境遇,更影响了人的思维模式。面对权力所有者以及攀附在权力所有者周围的人,人们本能地产生恐惧。而恐惧的背后隐含的则是来自权力的致命诱惑。权力之所以成为个体的理想追求,是因为在乡村世界里,权力就等于资源,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对资源的绝对占有力。这种占有力会荒唐到三番五次地敲开海五家的门,搬出村委会主任、镇长、市外经局主任等,只为买下海五家的大桃树。更荒诞的是,这种近乎强买的行为,其背后的力量竟然已经强大到令人无法拒绝的地步。海五说等桃花落了就卖,桃花就会在一夜之间落光,试问,还有什么是权力所不能为的?在权力场上角逐的人们,并不关心民主、法治,终被权力所异化。
与政治权力相配合的是文化性权力。对于文化性一词,费孝通这样解释:“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2]这种偏重教化而非强制的文化性权力,从古至今一直为乡村社会的运作提供有效的规则。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乡村传统的精神文化正被逐渐解构。这种解构使得乡村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尴尬位置,乡村中的文化性权力变得更加复杂。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已悄然深入乡村社会,渐成主流。小说中,在发现自己家“不起眼”的物件竟成为城里人眼中的“宝贝”之后,清潭村村民便竭尽所能地变卖一切。延年理直气壮地卖了爷爷种下的杏树,卖了老婆祖传的樟木箱子,换来了新家具、摩托车。在延年的眼中,只要能换钱,什么都可以出卖,哪怕是祖宗的牌位。这些满载情感与历史的不可复制的物件在金钱面前变得可有可无。乡村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否定。人们并非不知道这样的交换意味着什么,延年的老婆卖掉奶奶的奶奶传下来的樟木箱子的时候,也曾“哭得十分动情”,只是在趋利的、实用的观念的引领下,乡村重情的文化内核被消解掉了。当物质上的富足与否成为人们心中唯一的衡量标准时,人对内心完整性的渴求自然隐退。
对于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观念,不认同的少数人必然受到带有强制色彩的教化。这种教化让个体产生耻感,使之不得不将集体意志置于个人意志之上;而实施这种教化的主体则可以是社会中的任何个体或群体。小说中,海五因为执意不肯卖大桃树,不断地被人冠以“神经病”“不正常”“疯子”等带有侮辱性的称号,连带着妻子龙英也被其他人嘲笑。乡村社会的信息共有使得个体意志无处躲藏,作为少数人的耻感迫使个体不得不服从集体意志。对于卖树一事,海五虽有自己的观点,但在群体意志的压力下,他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拒绝。可见在文化性权力的教化下,个体的抵抗与坚守十分艰难。
二、人性坚守:个体存在的美好寓言
面对着政治性权力与文化性权力织就的权力网络,乡村中个体存在的自由之路举步维艰。叶弥企图通过人性的力量,为权力网络下的个体寻求出路。作家将此重任赋予了海五和龙英夫妇,以及大桃树。
海五是重感情的,他身上凝聚了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一面。作家并无意把海五塑造成一个斗士,海五只是一个平凡的、兢兢业业的普通人,他的可爱之处在于他宁肯看着小而破的电视也不卖掉大桃树换个大电视,只是因为舍不得。大桃树与海五日夜相伴,海五把它当作儿子一般,用海五的话说,大桃树带给他的快乐“比我那个闺女还多”[3]100。在海五看来,自己和大桃树之间的情感是金钱所不能比拟的。在狂风暴雨中,海五冲出门去看桃树和喜鹊,因担心桃树和喜鹊,海五竟然流下了热泪,如惦念孩子一般惦念着大桃树和喜鹊。同时,海五主张卖小树不卖大树,既是出于对生命生长的自然之道的尊重,更是要为清潭村保留历史与生机。海五的行为与清潭村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作为人们口中的疯子,海五实际上是在精神世界实现均衡的人。
海五的妻子龙英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面对海五在金钱和桃树之间的选择,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发现龙英的内心变化:当买树人第一次敲开海五家门时,龙英先是惊讶,接着皱起了眉,搬出海五来回绝了延年;听了延年的及时享乐理论后,龙英似乎有些动摇,但她还是关上了门,对海五撒谎说延年来借梯子;看着海五对着小而破的电视傻笑,龙英有些试探性地问海五要不要换个大的、新的,在得到海五否定的答案后,龙英便也说不要;在之后的日子里,龙英更是坚定地拒绝陶云生“我家不卖树”[3]98。面对村里其他人的奚落和嘲讽,龙英不争辩也不回击,正如谭二奶奶所言,龙英是个心里明白的人。相较于钱,她更在乎丈夫的感受。夫妻二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只是用情感去换取利益的事他们不愿意做。这种对情义的坚守是难能可贵的,亦是在权力网络下支撑个体的有力信条。
在整个故事中,大桃树作为情节展开的中心,隐喻了人性的坚守。从始至终,大桃树历经人祸与天灾,仍旧岿然不动。因着这份奇妙的力量,海五可以干净利落地拒绝卖树。作家用寓言的方式为海五和大桃树的故事画上了一个美好的句号。然而引人深思的是,生活并不是神话,也不是寓言,仅凭人性的力量能否完成个体存在的解脱?在权力网络的笼罩下,踽踽独行的个体又该何去何从?关于个体存在的思考似乎从未止息。
参考文献: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0.
[3]叶弥.恨枇杷[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赵禹佟,女,辽宁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文艺理论)(责任编辑 刘冬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