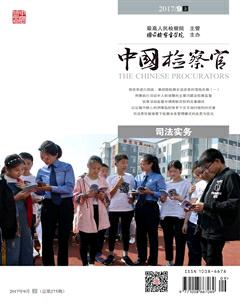自侦案件制作笔录常见问题探讨
齐钦 梁国武
摘 要:讯(询)问笔录是诉讼卷宗中不可缺少的言词证据,笔录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案件办理的质量,甚至影响案件的审理。检察机关担负着自侦案件的侦查,制作 讯(询)问笔录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实践中,侦查人员在制作笔录时能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认真落实相关要求,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笔录记载的内容不全面、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不明确、时间和地点记载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笔录制作的质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案件办理的质量。
关键词:职务犯罪 侦查 笔录制作 证据采信
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经常要制作各类笔录如讯问笔录、询问笔录等。这些笔录在案件的侦查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审查决定逮捕、审查起诉乃至审判活动的先决条件,是诉讼卷宗中不可缺少的证据材料。因此,笔录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案件办理的质量,甚至影响案件的审理。实践中,侦查人员在制作笔录时能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认真落实相关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侦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必须在合法场所进行”、“必须对犯罪嫌疑人或被询问人个别进行”等制度得到严格执行。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笔录记载的内容不全面、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不明确、时间和地点记载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笔录制作的质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案件办理的质量。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对自侦部门在笔录制作中的形式要件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提出建议。
一、关于笔录的抬头和名称问题
每一份笔录都应有明确的制作单位及反映笔录性质的名称。实践中,由于侦查人员的认识不够,笔录的抬头和名称往往是比较随意。如有的笔录出现“XX区人民检察院”的名称,没有使用单位全称;有的笔录名称出现“询问证人笔录”、“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等,有画蛇添足之嫌。鉴于自侦案件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讯问笔录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询问笔录的对象是与案件有关联的证人。因此,笔者建议笔录的抬头和名称应是单位的全称(与单位公章相同)加“询问笔录”或“讯问笔录”。如上述的“XX区人民检察院”应为“XX市XX区人民检察院”,对地市级检察院而言应为“XX省XX市人民检察院”,而笔录的名称应为“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不必再加上“证人”、“犯罪嫌疑人”等。
二、关于是否标注笔录次数的问题
自侦部门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往往需要几次、十几次甚至几十次,对一些证人的询问也需要好多次。对他们制作的笔录,反映的内容大多是不同的,有时即使相类似侧重点也会不一样,有时同一个对象的笔录内容上会出现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情况(如出现翻供、反复等)。实践中,自侦部门对笔录是否标注次数的做法是比较混乱的,有的笔录明确标注了次数,有的笔录就没有标注次数,有的笔录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标注了“第 次”的字样,但没有填上具体数字。笔者建议在笔录中应当真实准确的标注次数,特别是在笔录比较多的情况下,这项工作尤为必要。因为,一方面通过标注笔录次数能够体现笔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方便侦查指挥人员进行综合阅读,及时对案情作出判断并谋划工作;另一方面,通过标注笔录的先后次序有利于侦监部门、公诉部门和法院的案件承办人员阅卷,使他们更加直观了解案件的侦查过程,准确掌握被讯(询)问人的思想变化历程,为侦查监督、审查起诉、审理案件工作提供便利。当然,标注笔录次数有一个“后遗症”,即有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制作笔录是为了挖掘线索、拓展案源,而這些内容和材料往往不宜向检察机关其他部门及法院移送,这就会导致移送的卷宗材料中标注的笔录次数出现“断档”,容易给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及案件后续环节的承办人造成隐藏材料的假象。
三、关于时间记载的问题
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在许多环节上有时间上的要求。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中第134条及第195条的规定,说明侦查人员在制作笔录时记载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严格意义上讲,笔录记载的时间应该是笔录形成的全过程,即侦查人员开始制作笔录时至被讯(询)问人核对笔录后签名时为止。但在实践中,有的笔录能够反映包括被讯(询)问人核对笔录在内的全时段,有的笔录则不能。目前,侦查人员制作的笔录基本上是电子笔录,大多数情况下,有经验的侦查人员会在交给被讯(询)问人核对的笔录中结束时间上预留一段时间作为被讯(询)问人实际核对笔录时间,但即使这样做,笔录上记载的结束时间与实际上的结束时间还是会不完全一致,个别情况下甚至会相差很多。因此,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笔录形成的全过程,笔者建议在正常记载笔录制作的起止时间(即侦查人员从开始制作时间到停止记录时间)基础上,在笔录的最下端增加被讯(询)问人核对笔录的起止时间,具体起止时间由被讯(询)问人在核对笔录后签名时用手写的方式填写,如此就能比较全面地反映笔录制作的全过程。笔者曾遇到这样的个例,在两天三个时间段对犯罪嫌疑人制作综合笔录,总共历时11个小时,但侦查人员真正制作笔录的时间是5个小时,其余6个小时都是犯罪嫌疑人在不断核对并反复修改笔录,当时在这份笔录上就让犯罪嫌疑人用手写的方式标注了其核对笔录的时间,如果当时没有记载犯罪嫌疑人核对笔录的时间,就很难完整地反映出这份笔录的制作过程,甚至可能导致案件后续环节的承办人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四、关于地点记载的问题
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时也有场所方面的要求。如《规则》第1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检察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填写提讯、提解证,在看守所内讯问室进行。”;《规则》第205条规定:“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所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必要时,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提供证言。到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询问的,应当在笔录中记明。”等。因此,侦查人员制作笔录时的地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不分场合、不加选择地随意制作笔录。实践中,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笔录记载的地点比较模糊,有的笔录中只有“XX县看守所”、“本院”、“本院办案区”等模糊概念,这种对地点笼统表达到过大的范围往往会失去记录“场所”的意义,不符合要求。因此,笔者建议笔录中的地点记载应该具体到“室”,如“本院第一讯问室”、“本院102询问室”、“XX看守所第8提审室”等,只有这样才能客观真实地表达出制作笔录时被讯(询)问人正在何地、何处的具体地点信息。endprint
五、关于被讯(询)问人信息记载的问题
《规则》第197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要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贯、身份证号码、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及职务、住所、家庭情况、社会经历、是否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规则》第207条对询问证人作了相同的要求。实践中,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被讯(询)问人的信息记载不全面,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通常会根据个人的经验和常识来取舍被讯(询)问人的信息。如有的笔录会忽略被讯(询)问人的籍贯、民族、职业、文化程度等信息,认为这些信息不重要;有的笔录会省略被讯(询)问人的出生年月日,认为身份证号码信息已经能够反映其出生信息;有的笔录会忘记查明“是否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信息。笔者曾经看到过一份询问笔录,其中关于证人的个人信息记载只有姓名、性别、年龄三项,显然,这样的笔录是很不严肃的。事实上,笔录中记载的被讯(询)问人的每一项信息都是很必要也是很重要的。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行业背景的对象表达出来的实际文化水平和语言表达水平肯定是不同的。对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领导干部可以用语言精练、表达流畅、逻辑性强的表述来记录;而对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人则应用平简朴实、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法记录,包括地方方言、土话;对于特殊行业的专业人士,在言语中可能会出现特定的行业术语。因此,笔者认为在笔录中应当客观、全面地记载和体现被讯(询)问人的信息,除《规则》第197条规定必须查明的信息外,建议将被讯(询)问人的性别、曾用名、政治面貌、联系方式、身体状况以及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等信息都体现出来。特别是在制作第一次笔录及综合笔录时更应该非常详细地记载。在具体记载方式上,笔者认为可以比较灵活处理,如对被讯(询)问人的社会经历、家庭情况等信息量较大的内容可以在笔录中以问答的方式记载,其他比较简单的信息则可以通过填充的方式予以记录。
六、关于诉讼权利义务告知情况记载的问题
《规则》第197条、第203条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告知被讯(询)问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因此,被讯(询)问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告知情况在笔录制作中必须加以重视并予以体现。实践中,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即有的笔录非常详细罗列被讯(询)问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有的笔录则简单列举几条;第二种情况是完全没有体现,即笔录中没有被讯(询)问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情况的记载。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个别情况下侦查人员已经出示了《犯罪嫌疑人(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并让犯罪嫌疑人(证人)阅读后签名,侦查人员认为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再在笔录中体现了。二是侦查人员认为在制作笔录时已经口头告知了,同步录音录像中有记录,就不用在笔录中记载了。三是侦查人员认为第一次讯(询)问时已经告知过并作记载,以后的讯(询)问就不必再告知和记载了。那么,如何规范地在笔录中体现诉讼权利和义务的告知情况呢?笔者建议,在第一次讯(询)问时应当向被讯(询)问人出示或宣读《犯罪嫌疑人(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并由其在上面签名确认,同时将告知情况在笔录中予以记载。在以后的每一次笔录中仍应将“必须实事求是如实供述或陈述,不得扩大或缩小事实”等主要内容予以告知,然后再确认“你对犯罪嫌疑人(证人)诉讼权利义务是否已经了解?”,并由被讯(询)问人作出明确的回答,再在笔录中予以记载。也就是说,在每一次笔录的制作中都应当有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及被讯(询)问人员对此知晓情况的记载,只是记载的内容和体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另外,制作笔录时侦查人员应当主动向被讯(询)问人员告知他们的身份及姓名并出示工作证,告知讯(询)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将这些内容在笔录中予以体现。
七、关于签名的问题
《规则》第199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认为讯问笔录没有错误的,由犯罪嫌疑人在笔录上逐页签名、盖章或者捺指印,并在末页写明‘以上笔录我看过(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同时签名、盖章或者捺指印并注明日期……讯问的检察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规则》第207条对询问证人作了相同的要求。实践中,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笔录讯(询)问人员一栏只有一人签名,不符合要求;有的笔录签名字迹模糊,个别甚至无法辨认;有的笔录被讯(询)问人核对后书写的叙述不规范,出现“以上记得与我说的一致”、“以上笔录我看过,情况属实”等不严谨的用语。笔者建议在笔录的首页讯(询)问人员、记录人栏使用打印的侦查人员名字,然后在笔录尾部再由他们亲笔签名,这样既美观又符合法律规定,还便于侦查监督、公诉、审判环节的承办人阅卷和辨认。而被訊(询)问人核对笔录后书写的叙述必须按照《规则》第199条规定要求:“以上笔录我看过(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因为“相符”一词能够比较贴切地反映笔录制作中既忠于被讯(询)问人的原话,又有适度概括的实际情况。
八、关于笔录样式规范的问题
笔录制作具有明确的规范和严格的要求,如有违反这些规范和要求的情况出现,将导致该笔录的无效。实践中笔者接触到的笔录样式是各式各样的,不仅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内制作的笔录样式不一样,就连同一个办案组内不同侦查人员制作的笔录样式也不一样。除以上提到的一些问题外,还存在字体和大小不统一,数字写法不规范,有否下划线不一致等问题,一些笔录中还有案由、诉讼程序阶段、诉讼身份等信息的体现,有的就没有。因此,为更好地落实笔录制作的规范和要求,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笔者建议各个单位和部门针对各类笔录的不同要求对其样式进行统一和规范,从而提高笔录制作的质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