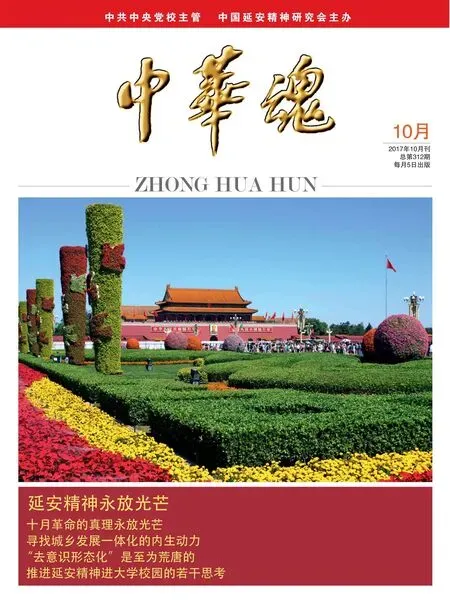何干之在延安的一段革命岁月
文/毛峥嵘
何干之在延安的一段革命岁月
文/毛峥嵘

何干之
何干之,1906年4月出生在广东台山县筋坑堡塘口村,先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修科和明治大学经济科,193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家。他从事教育工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培育了一批批革命青年,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1937年年“七七事变”后,党为了培养万千抗日干部以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党中央电报通知上海党组织,调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人到陕北公学任理论教员。
9月初,中央文化特派员冯雪峰通知何干之等准备启程。动身前,何干之、艾思奇、周扬、李初梨等4人到南京路华懋饭店秘密会见上海市委书记潘汉年。潘汉年说:“延安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成仿吾是陕公校长,招收各大城市青年去延安进行政治训练,急需教员,中央打电报来要你们去当教员。”临行前,冯雪峰取出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由队长李初梨携带,一封是党员介绍信,由何干之携带。次日晚,他们离开南京,由徐州转陇海路到西安再转道延安。
10月初,何干之等人乘延安派来的汽车北上,在蜿蜒的山道上整整走了一天,到延安城时已是万家灯火了。何干之把党员介绍信交给党中央书记处转组织部,李富春找他们谈话后,分配何干之、周扬到陕北公学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请他们吃饭。席间,他们报告了上海文化界的斗争和工作情况。毛泽东对何干之等人说:“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这次谈话给何干之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经常提起这些话。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研究,溶进整个革命事业中去。1938年欢送陕公毕业生上抗日前线,他代表教员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毕业上前线的同学,将用枪炮在前线与敌人肉博血战,我在这里就用笔和口来与敌人斗争,前线后方用一切武器和力量,要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去。”
延安的生活热气腾腾,工农翻身做了主人,积极参加选举、减租减息和参军等各种运动,进一步印证了何干之所阐述的工农是革命的主力的原理。他十分感奋地说:延安是一个旋乾倒坤、翻天覆地的新社会。特别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他认真学习了全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报告,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表示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王明路线。在延安,他获得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充分自由,那种为宣传革命真理而东逃西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何干之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写作热情空前高涨。他把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并征求意见。成仿吾对他说:“过去你在上海写了不少书和文章,现在到了延安,在党的领导下,应当写得更多更好,你自由写吧。你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放开手放开思想去研究吧。”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很艰苦,除伙食外,每人只发给5元零用钱,陕公校长成仿吾也是如此。为了优待何干之,中央决定发给他每月20元津贴费,并派一个警卫员照顾他,这在延安是很高的待遇了。
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旬邑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的土屋中,何干之一面进行教学工作,编写讲义,一面开展研究工作,著书立说。每天他窗口的灯光,总是亮到后半夜。何干之根据抗战的需要,一年内开设多门新课程,先后在普通班和高级班讲授《中国问题》、《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和《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陕北公学设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何干之任主任。他带领一批青年教员,开展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这些年轻的理论教员,后来都成长为新中国理论战线的骨干力量。为革命育英才,为革命的教育事业献力,正是他的夙志。过去在白区时,他曾对友人说,他的志愿就是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当一名红色教授。
1938年6月,陕北公学在关中旬邑县看花宫,开办了分校,扩大招生,何干之调到分校任教。教学之余,他开始写作由生活书店张仲实约写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于11月底完成,约八九万字,寄到武汉生活书店,1939年3月出版。这本书是何干之过去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设想中的一部分,是他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起点。他在这本书中创造性地结合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日本侵入中国后“经济界的新变动”,系统地评述了国民党十年来经济政策的得失,引述大量的经济资料,论证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指出中国必须在对日抗战的大转变时期“建立民族经济的基础”,以“迅速完成抗日战争的经济准备”,这就必须把抗战与民生统一起来,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必须“有日益健全的社会制度作基础”,“而民族革命战争是建立新社会制度的起点。”书中宣传了党关于全面抗战的经济方针和政策。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系统评议国民党十年经济政策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3月出版后,6月再版,10月就被国民党政府以“触犯审查标准”为名,下令“暂停发行”。
1938年10月,《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书尚未最后写完,何干之又开始着手撰写《三民主主义研究》,到1939年3月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是由于当时教学的需要,也是国共合作后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如何正确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共两党长期存在着分歧,特别是抗战以来一年中出版了好几种三民主义入门书,有的是好的,“也有若干别有用意的妄人,表面上装成一个神气十足的三民主义的研究者或信从者,而骨子里却到处贩卖私货,曲解阉割、湮没三民主义”。何干之认为:“对于这些有害的论调,每个中山先生的学友都应当联合起来发动一个思想上的消毒大运动。”这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对什么是三民主义的“真释”和“伪释”,从理论上历史上加以正确的阐述。何干之说他到延安后一年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研究欲望。他白天工作忙,花不出时间来,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把孙中山的著作、讲演笔记仔细地读了几遍。经过认真的思索,归纳整理了9个问题,然后动笔写作,两个星期写几千字,五六个月内写了10多万字。
《三民主义研究》一书,上海新中出版社于1940年4月出版,以后又两次重印,在国民党统治区颇有影响。何干之在教学、研究和紧张写作的繁忙日子里,创作的欲望如泉涌流。这期间,他正准备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史》,并拟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史概论》的研究大纲。关于中国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他曾谈到过这样的观点: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溶合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人民构成的,因此要研究社会史;而社会史的材料,大量地从民间小说、传说、笔记、野史和文物中反映出来,这些材料比“官书”价值还高。因此他用很多时间研究小说史,研究社会发展史。
1939年1月,他把自己写中国民族文化史的计划和想法函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复信,表示支持。信中说:“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对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态度,毛泽东也深表赞同,信中说:“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毛泽东在信中还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将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民主义研究》两本新书。何干之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他认为这是指出了学术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必须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重要原则。他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一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定要坚持这个原则。几十年来这封信始终珍藏在何干之的身边,一直到“文革”中才被送到中央档案馆保存,1983年年底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
何干之到延安后,曾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后来,党中央曾考虑调他到陕甘宁边区政策研究室工作,毛泽东也曾想留他做理论秘书。他考虑再三,感到自己是刚从上海来的文化人,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的锻炼,怕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的陕公分校受到军事威胁,中央决定分校撤回延安和鲁迅艺术学院等三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华北敌后,开展国防教育。何干之认为这正是自己接受民族革命战争锻炼的好机会,遂要求随联大到敌后去。经与张闻天、李富春商量后,党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华北联合大学的组织很快建立起来,下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等四个部,陕北公学改编为社会科学部,何干之任副部长。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大在延安正式成立后,中央举行了欢送联大上前线的大会。那时,刘少奇正在延安,特地请成仿吾和何干之到他住的窑洞里吃饭,为他们饯行。刘少奇知道何干之是广东人,会做菜,请他任主烹。何干之卷袖下厨,做了一桌广东风味菜,宾主畅饮,尽欢而散。这种革命的情谊,使何干之年久不忘。
何干之在延安度过了烽火战斗的8年,实践了自己“用笔和口与侵略者作战”的信念,不仅培养了万千抗战干部,还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撰写并出版了4本专著和若干篇论文,用以奉献给中国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