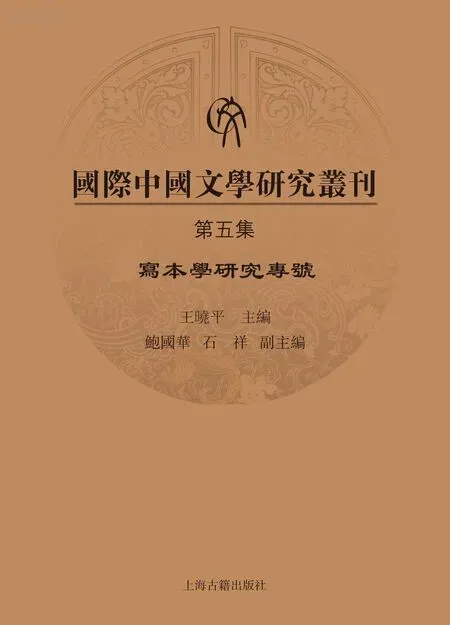中日寫本學術語的會通
王曉平
打通中國寫本特别是敦煌寫本研究與日本書志學寫本研究,是日本漢文寫本研究的當務之急。而打通這一領域的學術術語,更是急中之急,惟其如此,纔有利於寫本學文獻翻譯和研究中的互鑒。這裏將描述寫本内部與外部特徵的最基本術語,略加梳理,以便於論文翻譯和寫作中參照選擇。
用 紙 與 傳 本
西方研究拉丁文寫本和希臘、猶太、阿拉伯、波斯文原典的寫本學(Codicologie, Codicology, Handschriftenkunde),或譯作手稿學,從中日文獻的歷史發展來看,兩種譯法均有道理。就古代文化研究而言,以寫本學更爲妥帖。至於現代作家的手稿(日語稱原稿),自然也可納入寫本學研究的範疇,因爲在很多場合,它們的研究都離不開古文獻學的基礎。
寫本
寫本(写本,しゃほん),手寫的書,印刷技術普及以前的圖書製作方法。根據其成書的情況,分爲親筆本(自筆本)、稿本、清書本等。通常稱爲寫本的,是指轉寫本,或稱傳抄本。日本保存至今的古寫本,漢文文獻寫本自不待言,就是日本人著述的寫本,絶大多數也屬於傳抄本。也就是説,日本漢文古寫本研究的主體,就是傳抄本研究。手稿
草稿本(そうこうぼん),手寫的書,與印刷的版本相對照,也有時指草稿、底稿(下書き、したがき)。謄寫
亦曰謄抄。謄寫(謄写,とうしゃ),即複寫。所謂謄寫本,與寫本同様,指手寫的東西,特别是多用於公文書複製時。在中日兩國,相近的概念還有抄本(鈔本,しょうほん),除了有與漢語相同的指稱抄寫書的意思外,還特指中世接受講學時的筆記和摘抄本。拓寫本
影寫本(影写本,えいしゃほん),寫本之一種,指在親本上直接鋪上紙拓寫,是印刷技術普及之前的複製方法,可以較爲忠實地摹寫親本的字體、字的搭配、行數,而不容易出現誤寫。批注本
中日古代學者都有抄書讀的習慣,而且邊讀邊批注(書入れ)也不罕見。在刊本或寫本上留下可貴的文字,這様形成的批注本也具有不小的文獻价值,值得珍視。如日本南化本《史記》上面的批注,便保存了很多佚文。用紙
用紙,日語中稱爲“料紙”(りょうし),正如和田維四郎所説,古代書寫所用的料紙,最初大部分是來自中國的舶來品。如從推古天皇時起,日本也能造紙,從正倉院古文書中詳細記述的各種紙張的製造方法來看,恐怕是接受了中國傳來的造紙術,日本纔有了自己的紙。從敦煌出土的經卷看,其用紙與天平年間的寫經用紙幾乎難以區别,這説明天平時期日本用紙大部分是舶來品。當時的紙張是非常昂貴的。那時使用的紙張有白麻紙、黄麻紙、榖紙、斐紙、檀紙等,皆用於寫經。還有被稱爲荼毘紙的,僅見於被視爲聖武天皇真筆的寫經所用,但它是舶來品呢,還是日本專爲書寫此等經文而製造的,則不甚了了。到藤原時代,則使用雁皮紙、唐紙等。其中唐紙是指從中國傳入的紙,僅在藤原時代傳入日本,其前後均無所見,日本也有仿造的,其精巧不讓於舶來品。而雁皮紙,或者雁皮紙上以雲母刷出唐草、花鳥等紋樣,是用雁皮(がんぴ)造的紙。雁皮漢字又寫成“雁鼻”,並不是大雁的皮或鼻,而是一種主産於岐阜縣與滋賀縣的瑞香科矮樹,是造紙的上等原料。
所謂“和紙”,是日本古傳的手工漉製的紙,主要就是雁皮、楮(こうぞ)、三椏(みつまた)等原料造的紙,紙質柔韌,美觀好用。楊守敬在《日本訪書記》中對日本紙在保存古寫本中的貢獻讚歎有加,他説:“至於抄本藉用彼國繭紙,堅韌勝於布帛,故歷千年而不碎。”他所説的繭紙,是用蠶繭製作的紙。唐韓偓《紅芭蕉賦》:“謝家之麗句難窮,多烘繭紙;洛浦之下裳頻换,剩染鮫綃。”楊守敬所説大體不錯,其中或許也包括對和紙的誤解。
紙張
一張有字畫的紙稱爲一丁(丁,ちょう)。和本、唐本等摺頁綫裝(袋綴,ふくろとじ)的書(所謂和裝本),數其紙張數目時使用。在這種場合,正反兩面就稱爲一丁,也就是漢語中所説的一張。在日語中,帖(かきもの、ちょう)是數屏風、和紙、海苔的量詞,也是數摺本的量詞。在數摺本的時候,一帖就相當於一件。
證本
證本(しょうほん),可引以爲據的本子,可以傳遞來歷正當的原文、成爲他本依據的本子。内府藏嘉曆本《論語集解》奥書:此書受家説事二個度,故有先君奥書本,爲幼學書之間,字樣散散,不足爲證本。仍爲傳子孫,重所書寫也。加之朱點、墨點,手加自加了,即累業秘説,一事無脱,子子孫孫傳得之者,深藏匱中,勿出閫外矣。于時仁治三年八月六日 前參河手清原在判。
於時嘉曆第二閏九月 體於加州白山八幡院玉泉坊書之 禪澄之這些證本,就是家學的標準教材。在這一類證本的奥書中,有兩句話是不可或缺的,一句是不出閫外,一句是子孫永寶相傳。這種鄭重的叮囑,就是要告誡子孫後輩,外泄就是大錯,絶學則是罪惡。這樣的奥書,傳承的就不僅是證本的來歷,更是家學傳承的態度。或許也正是有了這種態度,這些久遠時代的本子纔能完好地保存至今。
摺本
日語中將採用經摺裝(將書頁反複摺合,整卷摺完,就變成重疊的長方形摺子的形式,在摺子的最前一頁和最後一頁,也就是書的封面和封底,再糊以尺寸相等的板紙或木板)的書,稱爲“折本”(おりほん),也稱作摺本(しょうほん·しゅうほん)。經摺裝比卷軸裝翻檢方便,在唐以及以後相當長一段時期之内,這種摺子形式的書很普遍,因而在平安時期以及其後的寫本中提到的“唐本”或“摺本”,大都是這種從中國傳入的經摺裝的書。由印度等地翻譯過來的佛經,都是這樣,所以人們稱這種摺子爲“經摺”,也就是與佛經有關係。室町時代的日本學人,還常常把從中國傳入的宋本書也稱爲“摺本”。清原宣賢等人用這種“摺本”與自家世代相傳的抄本對校的時候,就將“摺”字省去右邊的“習”,用“扌”來指代“摺本”,也就是新近從中國傳入的宋本書。奥書
書寫於書本卷末的文字。奥書(おくがき),《日本國語大詞典》解釋説:“文書等書寫物用紙左边末尾稱作奥,書寫在此處的文字稱爲奥書,特别是寫本等末尾有關年月、書寫者姓名、由來等的文字識語。”《日本典籍書志學詞典》説:“圖書的末尾,記敘著述、書寫來歷、著作者、書寫者、所藏者等的緣起文字,是瞭解圖書傳來的重要綫索。在寫本的場合,通常奥書也要原樣抄寫,這時從原本中抄寫來的奥書,稱爲‘本奥書’。奥書通常用於寫本,相當於刊本場合的‘刊記’。在現代圖書,是相當於版權頁(底頁、版本記録頁)。”寫經的奥書,有些有願文的功能。如伯爵田中光顯氏藏《觀世音菩薩受記經》奥書:
朕以萬機之暇,披覽典籍,全身延命,安民存業者,經史之中,釋教最上,由是仰憑三寶,歸依一乘,敬寫一切經,卷軸已訖,讀之者以至誠心,上爲國家,下及生類,乞索百年,祈禱萬福。聞之者無量劫間,不墮惡趣,遠離此網,俱登彼岸。
天平六年歲在甲戌始寫。寫經司 治部卿從四位上門部王
日語中把書後卷末的文章也叫“後書”(あとがき)或跋文。後書也可與奥書同義使用。不過,有時將所有後來添加的内容都叫後書,這就與奥書的意思不盡相同了。
袖書
與奥書相對的還有“袖書”(袖書,そでがき)。文書的末尾(左邊)稱爲奥,與此相對,開頭的地方(右邊)就稱爲“袖”,是原本執筆者以外添加的文字,内容多爲確認本文趣旨的文字。識語
識語(しきご),《日本國語大詞典》:“寫本、刊本等在本文之後或本文之前,記述有關此本的來歷、書寫年月等的文字。”義近於漢語的題跋。《漢語大詞典》、《辭源》均無此詞,但中國學者研究中已有使用。傳 承 與 校 勘
校勘
日本書志學中的“校合”(きょうごう、こうごう),也叫“校書”(こうしょ、きょうしょ),是指將自古相傳的諸本進行比較分析,以決定原文當有的面貌的工作,也就是校勘。中日兩國都有校勘典籍的傳統,校勘方法雖有相通之處,在用語、點校方式上則有所不同。在日本校勘是和訓點結合在一起的,校勘主要解決文字正誤問題,訓點主要解決文字讀解問題,但兩者顯然是不可截然分開的。由於日本學問的傳承方式自古以來以家族世襲的閉門傳授爲主,所以各家有各家的傳承系統,格外强調保持學説的純正與系統,一家的學説概不外傳。這一方面造成了學術的封閉和固化,一方面也養成了學者的嚴謹有恒而不屑於隨波逐流的品格。神宫文庫本《尚書》卷十三奥書説:
建長第八曆晚春十一日書點了,至此書者,以摺本書寫之,以古本校點之,凡虞、夏、商、周書者,壁中舊本,隸古之遺字也。雖然,改古字爲今字,唐本又如此,其上□高倉上皇御讀之本,又如此歟。(下略)
正和第三曆孟夏初五日,以家之秘説,授申生德才子,以十一代之學業終十三卷之詁訓,當時稀有者也。明經得業生清原長隆。
(上略)余偶得之珍藏有年,然今以爲希代之物,奉納勢州大神宫文庫,而貽萬世洪寶,表方寸微忱也。(下略)
貞享元年甲子夏四月上旬 島原城主從四位下主殿頭源忠房印
日語中還有“點合”“見合”等説法來表示校勘。如毛利本《吕后本紀第九》的奥書“延五正廿四辰書了,同年同月廿九日點合了”,“延五四一受訓了,學生大江家國”,“康和三年正月廿七日以秘本見合了,家行之本也”,“同年同月廿九日讀了”,“建久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黄昏讀移了”,從這些奥書可以看出,書寫者是一邊抄寫校勘,一邊聽講讀書,所謂“點合”“見合”都有校勘過程。
“家本”“家説”“秘本”這些詞語,充分展現了這種一家獨傳、學不出門的排他性。雲村文庫藏清家本《論語》卷第十奥書:
此書文增減異同,多本共以不一同,以唐本欲決之,未求得之,專以當家古本取準的書寫之,卒終朱墨功訖。
永正九年二月九日 少納言清原朝臣御判
文字增減,年來不審。以數多家本,雖令校合,共以不一揆。爰唐本不慮感得之間,即校正之處,相違非一,但古本之體法,今非可改易,仍脅注之兩存焉。就家説於無害之文字者,以朱消之,是又非憶(臆)説。黄表紙家本如此類有之,後來以此本可爲證者乎?
永正十七年九月廿三日 給事中清原宣賢
文中説“雖令校合,共以不一□”,其中最後一字衹可隱約看出像是“扌”,和田維四郎録以闕文處理,足利衍述《鐮倉室町時代之儒教》中的《皇朝傳本經籍奥書集》録作“揆”,可從。日本寫本中的奥書是寫本最直接可信的資料,有一些尚未準確讀解,有待於今後系統研究。
朱筆
、墨筆
中日典籍,均有經文墨書、注文朱書者。《經典釋文》條例有云:“今以墨書經本,朱字辨注,用相分别,使較然可求。”《五經文字》序亦云:“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不過,此亦並非全然如此。如唐代《周禮·考工記》零本,就如同後世經注本,注文爲墨書雙行細字。日本寫本在對原本添加批注或校勘文字時多用朱筆以示區别。置字
置字(おきじ),寫而置之不讀的字。漢語中表接續或語氣的詞在轉化爲日語時,没有適當的詞與之對應,而可以用格助詞或詞形變化來取代這些詞的功能的,便在訓讀中略去。這些詞主要包括而、於、乎、矣、焉、也、兮等,也包括凡、抑、又、將等副詞或接續詞。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清家訓點《論語》封底所書“置字大略不讀之,當讀之置字點之”,就是一般來説,這一類置字是不讀的,而有必要讀的時候,訓點者還是給它作了訓點。這樣,讀書的人遇到這些詞的時候,該讀則讀,不需讀的時候略過它就是了。和敦煌寫卷研究一樣,日本漢文寫本研究者也必須精通文字符號系統。關於寫本中的訓點符號、圈發符號、重文號、省代號,筆者在《日本詩經學史》及其他論文中已有介紹,這裏一邊與敦煌寫本對照,一邊着重概述幾種常見的校勘符號。
見消
日語“見消”(みせけち),是對誤寫、誤記以及異文等文字進行訂正、注記的方法之一。爲使底本文字清楚,在旁邊點上一點,或者在上面畫上一條細綫,而在合適的地方補寫正確的文字或者異文。它既是正訛符號,也用作補注符號。重文號
日文中的重文號至今仍在普遍使用。有=、々、゛、ゞ、ヾ、ヽ等多種形式。有的亦稱爲“蹦字”(踊り字)。封字號
〆,日語讀作“しめ”。爲文書加封的時候使用,在封口上作爲“封”“緘”的省代字用。據稱由“封”字旁變化而來。至今仍有不少日本人有在信封口寫上〆字的習慣。×號
日語讀作バツ、べけ。方角號
日語讀作カク、シカク。頓點號
表示占格,即空格無字。多見於雙行小字的注釋。兩行小字並列時,右邊的一行字尾尚有空,不再有字,補以頓號,以與前一行對齊。如高山寺本《莊子雜篇天下第卅三》:
卜字號
“卜”字號是分隔號與頓號的組合體,用於滅字,如伯2618《切韵唐韵序二》:九經諸子史漢三國志晉三國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
卜卜
文中“三國”兩字右側加卜字以示删除。在日本寫本中,也有以卜字號來滅字的,現代日本學者校稿時則用“トル”滅字。
分隔號
分隔號在寫本中使用廣泛,除了作爲連字號在兩字中間表示其爲一詞、不可分開解讀之外,還可在字的左邊,表示更改或有異文。分隔號亦爲專名號。天文年間古寫本《和漢朗咏集私注》用一分隔號貫穿兩字或三字中間,即爲人名,貫穿於字之靠右邊,即爲地名,兩條平行分隔號貫穿於字中,即爲書名。如後江相公《山中自述》“商山月落秋鬢白,潁水波揚左耳清”,“商山”“潁水”皆靠字右有分隔號,而注文中開頭一句裏的“綺里季”等商山四皓皆有分隔號穿於字中。該寫本中的書名、篇名如《關中記》、《文選》、《思玄賦》、《世説》等,則以平行雙分隔號穿字中。
分隔號還可表示隨機省代。前文出現的字詞,正文出現過的字詞,或者常用的專門術語,均可用一條或幾條來省代。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本《倭聚類名抄》中,注文中出現所釋詞語時均以分隔號省代。所釋之詞幾字,則以同樣數目的分隔號來省代。如所引書名中亦有所釋之詞,亦以分隔號省代。如雜藝類廿五的“投壺”一詞:

①袁暉、管錫華、岳方遂《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95。
高山寺本《莊子·雜篇·天下》“髁無任,而笑天子之尚賢”,其中“髁”兩字中間的分隔號表示兩字不可分讀,而其右側小字所注:
胡啟反。又,又奚、户寘反,丨丨,訛不止貌。
注中的兩分隔號,省代所注釋的“髁”二字。岩崎文庫本《幻雲史記抄》中大凡“史記”二字均以丨丨省代,如丨丨索引、丨丨正義、丨丨胡注等。
二短横綫號
表重文。亦特用於省代所注釋的字。如高山寺本《莊子·雜篇·讓王廿八》:楚昭王失國屠羊走而從於王。
二短横綫號寫於字中,表示廢字。詞與重文號的區别是不寫於字外。如高山寺本《莊子·雜篇·説劍第卅》末尾最後一句“三月劍士皆伏斃其處矣”,句有雙行小字的注釋:“心不見禮,皆自殺也”。這一句八字,每一字中皆有二短横綫,表示此八字當删。如果字中有短横綫,字外另書某字,則表示此字當改爲某字。
圓圈號
日語讀作まる、ゼロ、レイ。小圓圈在字下,表示字下有脱字,其所脱之字補書於其下或其右側。如高山寺本《莊子》:天能覆之,不能載,地能載之,不能覆。大道苞之而不能辨知。
弧綫號
弧綫號和小圓圈一起,用於補字。或表指示所釋之字。横拐號
在字左旁者,爲左横拐號“┌”,在字的右旁者,爲右横拐號,用以指示所注釋的字。《李嶠咏物詩注·坤儀十首·原》“帶川遥綺錯,分隰迥阡眠”,“川”字左旁注“野也”,“川”字與“野”字之間以横拐號相連,表示“川”之意爲“野也”,即平川、原野,與唐崔顥《黄鶴樓》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中的“川”同意,而非常見的河流之意。斜綫號
斜綫號在敦煌文獻中用於補入寫脱的文字。如伯2011《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末韻:
“妺”條原寫脱,於行右寫出來,以斜綫號表示插入。在日本漢文寫本中,斜綫號也有這樣的用法。
斜綫號還用來表示區分。更多場合斜綫號用作“合點”。“合點”一詞的基本含義是認可、認同、首肯、同意,而在文書中則指劃在專案右肩表示承諾、對照完畢的意思的鈎形綫條。在和歌、連歌、俳諧的批評中,則是指劃在佳作字句之上左右兩肩的鈎點,也就是批點。東野治之整理的金剛寺本《遊仙窟》的“翻刻凡例”中有一條説:“附有片假名的合點,在該訓讀的横向或下面,以(合)來表示。”而在校注者所有有注上(合)的地方,底本上原來都有斜綫號。和多數寫本一樣,這種斜綫號在字的左側的,爲/型;而在字的右側的則爲型,顯得自然和諧,在擁擠的字行間,也便於辨認其到底屬於哪一邊字的注。例如:

②東野治之《金剛寺本遊仙窟》,東京,塙書房,2000 年,頁86—87。
上文中“寇”字左側的“アタノ”和“兒”字左側的“ワレハ”,都是“合點”。松平文庫本《千載佳句》中的“合點”,有型和型,均在詩句首字的右肩。
鈎形綫
鈎形綫除了表示“合點”外,多置於一段首字之肩,表示另起,用於分段。如尊經閣本《古文孝經》第15行至18行:(逮)乎六國,學校衰廢,及秦始皇焚書坑儒,《孝經》由是絶而不傳。漢興,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
上文中的“逯”(逮)字和“至”字上的鈎形號,均表示另起。
其第37行:
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吾逯從伏生論。
文中“昔”字上的朱筆鉤形綫,表示新段落開始。長治本《冥報記》每一事(有個别漏劃)首字有鈎形綫“”,形更簡易,而功用不變。
彎鈎號
表示乙字。一般與上字下的小圓圈號一起,不難識别。小圓圈號表示下面的字樣應移至此字下。長方框號
長方框將字框於内,表示删除。圓黑點號
大圓黑點●表示篇目或一篇的開端。小圓圈號或小圓點用於句讀。如早稻田大學本《詩經述》卷之五:雅正是王室正樂之歌其篇本有大小之而各有正變之
有了小圓圈號,讀者便省去了很多腦力,順暢地讀完全文。
三角號
三角號△日語讀作サンカク。用於標明項目如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本《倭聚類名抄》第五册目録:
字號
“ヒ”字號在日本寫本中表示删補,用於文字修改。如松平文庫本《遊仙窟》:
① 松平黎明會編《漢詩文集編》,東京,新典社,1993 年,頁347。
上文在曰字左側,有ヒ字號,表示此字係誤字,在右側添加的“日”字是改正的字。
亻字號
“亻”是日語“一(イチ)”之省,用於校勘,一般書於字旁的某字下,意爲“一本作某字”。花押
花押是舊時文書契約末尾的草書簽名或代替簽名的特種符號。唐唐彦謙《宿田家》詩:“公文捧花押,鷹隼駕聲勢。”宋黄伯思《東觀餘論·記與劉無言論書》:“文皇(唐太宗)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朵雲是也。”日語中花押讀作“かおう”,一般指代替簽名的印章,即將署名圖案花的印章,亦稱“書き判”,採用將草書進一步打散而圖案化的紋様。讀符
有些寫本,卷末還有“讀符”,表讀過的遍數。讀過一遍,就寫上一個一字。宫内廳書陵部藏《群書治要》卷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卷末奥書之後皆有一個讀符。久原文庫本清原宣賢自筆自點《毛詩傳箋》卷二末尾的讀符如下:良賢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
業忠一一一一一
宗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一
良氏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
從上面的讀符,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原家幾代人研讀《毛詩》卷二的情況,其中良賢研讀七十有二,而最少的業忠也有五遍。
文 字 與 書 法
學問傳承的世襲性,對文字書寫的影響也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對於本文書寫高度用心,力求不改原貌,一方面對於校點文字,由於其流通範圍僅限於本家族内部,更會求簡省。
異體字
在日本漢文寫本中,存在大量異體字,其中不少屬於中國大陸流行過的俗字,特别是簡化俗字。寫本中用省文,或稱略字。江户時代的隨筆中,時而見到有關的記述。如村田春海《織錦舍隨筆》中有“寅字用刁字”一則:古寫本,有寅字作刁字者,此當出於衹略書字之頭者。如此省略文字之事,古來多有。此寅、同音之字,唐代通用,此方亦習得焉。字典上亦見寅、通用。
上文中的字,或爲夤字的訛變。這些的訛俗字在寫本中頗多。
點圖
從奈良平安時代起,日本學人爲了讀懂漢文、傳授漢文,發明了一整套簡便可行的訓讀方法,菅家、卜部(ウラベ)家、大江家等各家都自有一套辦法,訓讀中將一些最常用的字大幅簡化而符號化。漢字簡省,時有僅書起筆的一兩筆便代替全字的,如民作尸、爲作メ等;也有省略偏旁的,如時作寸等;用漢字表示日語讀音者,也求好寫,如タ作太、ツ作爪、ノ作マ作丁、セ作才、ヨ作(与)、和(ワ)作禾。類似的字寫半邊或“點到爲止”的字形,如權作木、孫作孑、從作彳、摩作广、等作ホ,這些被完全符號化的字,新井白石將其稱爲“點圖借字”(点図の仮字)。他把這些爲讀書之便而創造的“點圖”,視如“樂聲之譜,如按其譜得其聲調,按此點習其句讀”,他肯定菅原家、大江家在傳承這些不同方法的貢獻以及“經點”“記點”的作用,也特别提到,四聲圈點(平上去入聲)與中國用例相同,俗稱此爲“ヲコト点”。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字有些並不僅在訓讀中使用,在有些寫本正文中也可以見到它們。如將“雁”字寫成“厂”等。江户時代學問下行,簡省的文字更爲盛行,這些“點圖”方法也爲更多的人所熟悉。借用字
由於經籍中的俗字在限定的圈子裏,有些甚至讀者僅是自己的門下生,所以還不至於造成太大的文字混亂。社會上流行俗字則與漢字音義的日本化相關。新井白石《同文通考》中有借用一項,他説:“本朝俗書,務要簡便,凡字畫多者,或有借方音相近,而字畫極少者以爲用,其義蓋取假借而已。世儒概以爲訛,亦非通論。今定以爲借用。”他列舉的借用字有:若(ワカ) 若、弱音同,借作老若之弱字。○若,日灼切,擇菜也。一曰順也,又如也,又汝也,又語辭,又預及辭。
弁(ベン) 弁、辨音相近,借作辨、辯等字。○弁,音便。冕也。
沓(クツ) 沓、鞜音相近,借以作鞜字。○沓,音踏。沸溢也。
厂(カン) 厂、雁方音相近,借作雁字。○厂,音罕。山石之厓,巖人可居。

六(ロク) 六、録音相近,借作録字,如目録作目六之類。○六,力竹切,三兩爲六,老陰數也。
表(ヘウ) 表、俵方音相近,借作俵、裱等字。○表,標上聲。上衣也,又外也,又明也。
乃(ノ) 乃、濃方音相近,或借作濃字。信濃作信乃之類。○乃,奈上聲,語辭也。
木(キ) 借作藝字、議字,如安藝坐安木、參議作參木之類,蓋借木字方訓也。
番(バン) 蕃字通作番。玄蕃字蕃俗間作番,番亦訛畨,非。
甫(ホ) 甫、輔音相近,或作輔丞之輔。○甫,匪父反。男之美稱也。一曰大也,始也,又衆也,又我也。
包(ハウ) 包、庖音相近,借作庖丁之庖字。○包,班交切。容也,又裹也。
匀(イン) 匀,韵方音相似,借作韵字,匀注見上。

① 古屋彰解説《同文通考》,東京,勉誠社,1979 年,頁271—274。
文中所説的“方音”就是日語音,當時的日本儒學者視日本爲地方,故稱日語爲方音,稱日語訓讀爲“方訓”。日語“木”音訓作“キ”,所以可以借用爲音近的“藝”(げ)和“議”(ぎ)。其實漢語俗字中也有同類音近相借的例子。
上面列舉的有些字,至今還被列入當用漢字普遍使用。有些字詞的含義與漢語有别,如庖丁,在漢語中是指厨師,而在日語中却有菜刀、烹飪、厨師三種含義,使用頻率遠高於漢語。這些字由於屬於常用字,簡化借字可能最初衹是少數學者使用而後廣爲流傳的,也可能是民間首先使用而爲學者“拿來”的,不論怎樣,都已在寫本中站穩脚跟,使今人也不得不認真面對了。
合字
我國民間有將字合二爲一的所謂合寫字,它不同於合音字,而是對常用詞的超經濟處理,如問題作、圖書館作等,追根尋源,恐怕其來自佛家。在日本寫本中,既有漢字的合字(ごうじ),如灌頂作汀,勘定作賬,權利作,金椀作鋎,麻吕作麿等,還有一種假名合字(ごうじ),將兩個假名或兩個漢字合寫成一個,こと作より作、トモ作、さま作、人(びと)作、共(ども)作、多(だ)作、子(こ)作シテ作〆、こと作┓、トキ作等。下面這些字都是日本漢文寫本中出現頻率較高的。
字符
字是訓字的減筆字,用作加注訓讀音義。字符
字是音字的減筆字,用於爲字標注日語讀音。亻字符
亻字“イチ”(一)的略寫,爲“一本”之略稱,用於引用一本之佚文或異文。亻在《詩經》相關的寫本中亦爲“傳”字之省代字。乍字符
乍字爲“作”字之減筆字,用於某字作某字的場合。ケ字符
ケ字爲“竹”字之半字,在《詩經》相關的寫本中爲“箋”字的省代字。又,“箇”(個)字。古字
日本古寫本中常見的古字有旹、宲、等。俗字
日本古寫本中保留晉唐俗字寫法不少,有些至今依然沿用,如渇、葛、剣等,有些則多見於江户時代以前的寫本,如、、諐、舩、庿、嬢等。今天研究古寫本,則必須熟悉這些字,研究它們的使用規律,纔能準確識讀。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太宰春臺《楷書正訛》是日本漢字研究的必讀書,也是漢文寫本研究者值得多多鑽研的書;笹原宏之《國字的位相與展開》則是研究國字(こくじ)即日本自造字的專著,也是寫本研究者的必讀書。
定式
漢文寫本,特别是序跋與書函,文字布局亦有講究,如表自稱的字“余”“某”或本人姓氏,均需小寫,而對尊上則需空格書寫。太宰春臺著《斥非》,從細微之處比較中日兩國文人做法之差異,如:凡贈答詩書題引,或在詩前,或在詩後,皆可。必低一兩字爲定式。如題中有所贈官號姓字,必提之,或高於詩,或與詩平頭,雖詩中亦然。非唯官號姓字爲然。凡指所贈之詞皆提之,禮也。世儒乃有徒知低書題引,而不知提所贈官號姓字,雖提而低於己詩者,亦不達禮之過也。
寫本研究涉及多方面的知識,在整理時不可忽略的細節很多,整理者需如同一絲不苟的翻譯家一樣,細緻分析每一個字符以及它們的位置。
研究寫本,不能不涉及書法。日本書法整體上延續晉唐書風,鐮倉時代禪僧的“墨蹟”書法取法蘇軾、黄庭堅、張即之,但晉唐書風却一直在書壇上佔據主流,在風格上普遍表現出精巧、細緻、文雅之美。通行的是楷書,草書、行書也時有所見,但都多不過點綴而已。
日本漢文古寫本對於中國學術來説,無疑是一個跨文化問題,而凡屬跨文化問題,就要比單純研究一國文化複雜得多,有些看起來簡單的問題,甚至不成問題的問題,一旦具有跨文化性質,就必然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溝通障礙。學術術語的溝通就是其中的一環。跨文化問題最忌想當然,拍拍腦門,以此之心,度彼之情,就難免張冠李戴。寫本研究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而它的成果也一定會有益於兩國學術的融通。上文僅是初步整理,以應整理時參照,掛一漏萬,言説不周之處尚多,需在整理過程中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