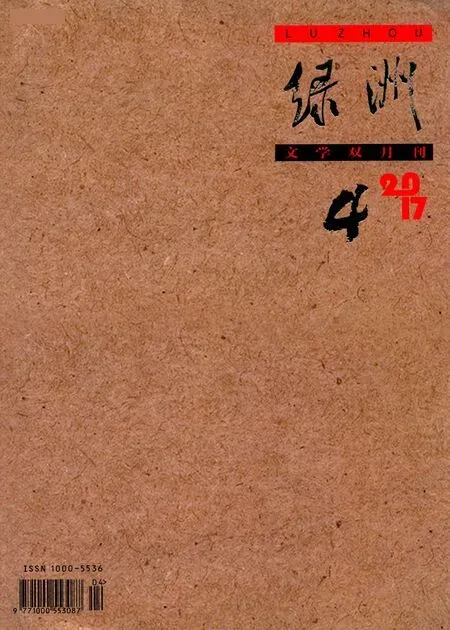如豆的灯火
黄孝纪
如豆的灯火
黄孝纪
灯盏的红焰
一粒谷,溅满屋。
每当想起这句儿时常挂在嘴边的谜语,脑海不由地浮现这样的场景:柴火在土灶里呼呼燃烧,火舌自锅底窜出,我们姐弟坐在宽板条凳上,烤火,添柴,叽叽喳喳,父亲喂猪去了,黑咕隆咚的狭小屋子里,母亲在黑暗中摸索着,一股煤油的浓重味道弥散开来。一阵响动,拉碗柜箱子的声音,母亲在摸索火柴。窸窸窣窣,“嗞”的一声,磷光闪动,一根火柴燃着了,把母亲的手掌映红。火柴伸向煤油灯盏,着了,屋子里顿时溅满了昏黄的光,把母亲模糊的身影浮雕了出来。
煤油灯下,是我们闲坐,母亲忙碌的时刻。乌黑的大水锅,水沸,咕咕作响,热气自木甑的圆木盖四周泄出,米饭芳香。母亲洗了粘有煤油气味的粗糙双手,清洗自家菜园里摘来的菜蔬。蒸好的米饭,母亲双手端了木甑,放在窗下宽板条凳的一端。换上乌黑的菜锅子,切菜,炒菜,放盐油佐料,装碗出锅。母亲动作麻利娴熟,我们习惯了观看母亲做饭做菜的过程,习惯了吃母亲做好的饭菜。
有一个细节,数十年来,难以忘怀,也是我们现时还偶尔的笑料。我的二姐贱花,小时候做农活是一把好手。那时,我的大姐出嫁得早,三姐和我都还读书年幼,二姐自然成了父母的得力帮手,主要劳动力。二姐脾气好,眼泪浅,吃夜饭若是受了母亲的责备,她不会吵不会闹,就气呼呼坐在木甑边,满心委屈,流着泪,一碗接一碗吃大饭,比平常要多吃几碗,以此作为对母亲苛责的报复。
夜饭后,母亲收拾碗筷,洗洗刷刷。父亲顺手从条凳角落摸起他的短烟筒,装了土烟丝,抽了灶台上的火钳,一俯身,夹一粒柴火子,伸向烟斗,吧嗒,吧嗒,呛人的烟气从他的嘴里鼻孔里吐出来,散成一片升腾的云雾,烟斗燃着,一红一暗。这个时候,灯盏可以归我使用了。我从窗台端下来,放在条凳上。拿来书包,掏出书本和作业簿子,或膝盖跪地,或坐在矮凳上,后背紧抵着灶身,我伏在条凳上翻书写作业。煤油的气味浓郁,灯罩里黑烟尾巴缭绕。
隔几天,灯罩子就熏得模糊了,尤其是灯罩口的四周,一片乌黑。母亲摘下来,拿一块小布片,洗擦干净,透明的玻璃顿时又光洁明亮。只是这个灯盏后来不小心打碎了,这在当时,是家里的重大财产损失。之后,我们家再没有买这样的灯盏。母亲拿了我的空墨水瓶倒入煤油,找来铁皮盖钉一小口,穿一根灯芯,盖上,就是一个灯盏了。只是,很多次,做作业的时候,稍不留神,我额前的头发就触到了火苗子,烧得嘶嘶作响,焦臭。
在这间老屋子里,我的父亲曾遭受过一次意外的头部受伤,血流得很厉害。那是一个深夜,隔壁邻居的大儿子偷树回来,树尾巴撞落隔墙的一块大土砖,正好砸在我熟睡的父亲头上。过后,有村邻先后从河对面的供销社里买了罐头来看望父亲。那些罐头,贴了鲜艳的水果纸贴,一瓣瓣果子在汁水中泡得鼓鼓胀胀,十分诱人。父亲吃罐头的时候,我们姐弟也有机会吃上一瓣两瓣,喝上一点汁水,甜。空罐头瓶子,成了母亲手下的灯盏。母亲手巧,找一截铁丝,做出“凹”形,挂在瓶口,灯芯在瓶内,点燃后,明亮又挡风。瓶口再拧一圈铁丝,加一个铁丝挂钩,既能悬挂高处,还能提着走。曾有好些年,村里流行这种罐头瓶子煤油灯盏。我的母亲喂夜猪,夜里去茅厕,出门串户,常是提着这样的灯盏,一粒微光,在黑暗里游移。
虽说供销社就在村对面,煤油基本上都随时有卖。偶尔的日子,我还是看到母亲向邻居家临时借一点煤油。过后,母亲赶了圩场,卖点自产的菜蔬花生豆子,提了空煤油瓶子,买了煤油还上。还煤油的时候,母亲总是笑呵呵地说着感激的话,多倒上一点。
家贫,不过,我的母亲对我的读书十分在意。母亲常有一句话总挂在嘴边:“养儿不读书,不如养个猪。”她对我的管束是严厉的,不准我看小人书,不准我跟吊儿郎当的伙伴纠缠在一起,文盲的她偏执地认为,唯有如此,我才不会误入歧途。我读书很为父母争气,小学里,我成绩特好,几乎每年都是三好学生,受奖励的对象。那时,任课老师夜里经常下村家访,昏黄的煤油灯盏下,我家这间又黑又窄的屋子却是老师喜爱停留的地方。黄秋德是一位和善的老师,年轻英俊,爱笑,他教我的数学。我的数学作业本上,经常是一个大大的红勾下,批注两个潇洒的红字和一个红色的惊叹号——“蛮好!”
“蛮好!”——这火红的批注,宛如煤油灯盏上跳动的红焰,它们一起燃烧着,照亮了一个山村男童对未来朦胧的向往和期许。
黑夜游动的火把
三月的春夜那时黑得真像一面锅底。水田犁耙过了,蓄着一层清清的浅水,阡陌交错,白天看来,宛如一面面连缀着的光亮镜子,插早稻已然临近。在这个时节的漆黑的夜晚,吃过夜饭之后,常有照泥鳅的青壮年男子,腰扎鱼篓,一手提着松柴灯笼,一手握着长柄的泥鳅叉子,在村前阔大的水田间缓缓游移。灯笼的松柴熊熊地燃烧,滴着油脂,火光通红,在无边夜幕的背景下,如豆,如星。
我家的楼上,也有这样的灯笼和叉子,铁锈斑斑。这是我父亲曾经用过的工具,在他青壮年的岁月里,也是一个喜爱照泥鳅的人。父亲成家迟,近40岁才生我的大姐,56岁生下我。因此,在我的童年里,父亲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不再照泥鳅。我也不曾有过亲自提着灯笼在春夜里照泥鳅的经历,只是远远地看着黑夜里游荡的灯笼,充满羡慕。
父亲曾是照泥鳅的好手,尤其是在我大姐童年的时候。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平素的日子,总要设法捉一些鱼虾泥蛙团鱼之类的荤腥,做我大姐碗里的菜肴。父亲左脚的大脚趾,就是在一次春夜里赤脚照泥鳅时,据说是踩着了蛇骨头,中了毒。之后红肿溃烂,无法行走,整整在床上坐了几个月,连脚趾骨头都烂掉了一大块。那段时间,母亲又忙又愁。忙着白天的农活,全家的一日三餐,父亲的护理。愁着父亲的病痛,愁着无钱又无药。为让父亲打发无聊的日子,母亲将上一年收的地里的棉花拿出了,要父亲每日里剥棉花籽。当年,经父亲一双手去籽的棉花足足弹了两床棉被。父亲脚趾好了后,严重变形。
大姐18岁就出嫁了,大姐夫是父亲相中的,住河对面的小村,忠厚老实,当过兵,后来转业做了工人。过年的时候,大姐夫探亲回家,到夜里,常过河来我家里喝酒吃饭,有时同我大姐外甥一起过来,有时就单独他一人。大姐夫可称得上是我父亲喝酒的知音,谈谈讲讲,细酌慢咽,自家酿造的红薯土酒,在炉火上热了一砂罐又一砂罐,菜也是凉了又热一热,往往要喝到夜深方罢,灶里的煤炭火渐成灰烬,灯盏芯开着了红星子的灯花。
一条石板路,一座石板桥,就把两个村子连接起来,中间相隔就一两里路。只是在严冬漆黑的深夜,伸手不见拳,独自走在村外,却也阴森可怖。何况,石板桥头两侧河岸,是村人去世后烧遗物床铺的地方,一滩方形的黑灰,常常要数月才消去踪迹,每每见了,心里难免发毛。而谈仙说鬼,也是村人日常的话题。由是,每逢喝酒夜深,大姐和姐夫必要母亲相送。
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已经从楼上拿了几根长长的葵花秆子或烟秆下来,点上火。
母亲拿着烟秆,走在前面,有时我也一道相送。大姐姐抱着外甥,姐夫拿着烟秆,随后跟着。一前一后两只火把,火光熊熊,在呜呜呼叫的寒风里,不时掉落绯红的余烬。村庄寂静空落,石板路上只有我们急促的脚步声,零碎的说话声。光晕随着脚步推进,推开前面厚重的夜色。
送至石桥边,母亲接火又点燃了新的烟秆,火把更加明亮。大姐姐夫拿了火把走向石桥,在河面投下火光的红影。我们站定,目送他们过了桥,融进无边的漆黑里。一火游动,绕过水田和溪水,上了高坎,直到对面的小村口。如豆的火把停住了,黑夜里传来姐夫的喊声:“你们回去吧!”
转过身,我走在前面,母亲举着烟秆火把跟着。
寒风呼呼刮着,火把游动。
点亮的神灯
过节,过年,家人过生日,早稻尝新,肥猪出栏宰杀,这些一年中重要吉祥的日子,母亲必定洗净双手,从厅屋的神台上拿下那只干渴蒙尘的白瓷调羹,添上金色的茶油,一根白色的灯草,重新放回神台搁板中央,点亮。空阔的神台,顿时充满了神秘和凝重。
母亲一脸肃穆,低着头,双手举过头顶,端着一只装肉的大碗,热气缭绕。她恭敬地站立在神灯前,嘴里念念有词,模糊不清。末了,她收手抬头,脸色和悦,端着肉碗,跨过门槛,回堂屋继续做菜做饭。
我曾经问母亲,敬神时嘴里说些什么?母亲微微含笑,说:“就是保佑你们啊。”
我也曾无忌地说,神台上是空的,又没有人,碗里的肉也没吃。母亲顿时有了愠色,责备我说:“要打你蠢子嘴巴!这样说话有过的。奶奶爷爷祖公祖婆都在神台上坐着。你不看见他,他们会看见我们,保佑我们!”
年复一年,母亲恭敬地点亮神灯,从黑发中年,到了头发花白的暮年。我们在母亲肃穆的祝祷中,成长,成家。
2001年暮春,门前的小溪清澈流淌,溪岸一排高过人头的橘子树,开着一树树细小白色的繁花,花气浓郁。曾有一个多月,我不停地往返县城和村庄之间。
这一次母亲病得很重,算是彻底病倒了。她的腹部鼓胀,剧痛。母亲预知去日不多,坚决不肯去县城就医。她担心死在外面,按祖辈传下的说法,这样的人,魂魄归不了家。好在我的大姐是乡村医生,大姐夫也在家。平时,白日里就由他们照料我的母亲,打针,吃药。晚上我父亲陪着母亲。我断断续续在单位上班,随时按照大姐的吩咐,买来针剂和药品。我曾经看到母亲痛得双目紧闭,大汗淋漓,几个小时双腿笔直地伸着,一动不动。我心如刀割,却又无法。我甚至默默地念叨,如果可以,我愿意缩短寿命,换回母亲的健康,少一份痛楚。大姐叫我赶紧去药店买杜冷丁,说母亲可能已是肝癌晚期。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剧痛就靠注射杜冷丁暂时压下去。
有一天,母亲气色好了很多,在床上躺了差不多一个月后,竟然能起床了,腹部也没那么鼓胀,似乎消了很多,只是脸上依然苍白而憔悴。她要大姐给她梳了头发,背了一条长凳,坐在屋外禾场上晒太阳。母亲虚弱地笑着,说已经好久没看到太阳了。她甚至拿出我买的药品给前来看望她的村邻看,说这些药要5元钱一粒,贵,是我孝纪买来的。“就是我这病啊,”母亲说:“阎王老子要你活好久,簿子上注定了的。”母亲头发花白,笑容平静,在她目光投向的远处,正是村前江对岸的我家的碧绿茂盛的油茶山,我仿佛看到了某种意味深长的暗示。
母亲再一次躺倒。几天后,离开了人世。甚至等不及看上我最后一眼。
我是黎明时分,在县城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电话中平静又简短地告诉我:“你妈妈走了。”我当即呆若木鸡,泪眼模糊。我匆匆赶回家,抱着母亲的遗体,泪流满面,长哭不已。没有守护在母亲弥留时刻,让母亲满含牵挂和思念而走,是我此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母亲的坟墓就在河对岸,我自家的油茶山上,这也是她和父亲事先就看好了的。很多年前,她就曾多次说过,她死后,要葬在自家的油茶山上,这里离家近,我们以后上坟也方便,而且她在山上一眼就能看见家,看见我们,回来也近。母亲每次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满含笑意,一脸平静。地仙择地的那天,我80多岁的老父亲,气喘吁吁,还特地跟了去,指定了大致位置。并留下话语,将来他也要葬在母亲身旁。
丧仪严格遵照村里的传统规制。出殡那天,母亲的灵柩停在村前的朝门口。我穿戴白色的长孝衣,抱着母亲的遗像,跪在母亲的灵柩前。黑色的棺木上,骑着一只纸竹扎制的大白鹅,八大金刚在捆绑抬棺的木杠。村人宾客围绕,花圈肃穆。我的身后,跪着一长串我的亲人,孝衣绵延。
三声炮响,喇叭咽呜,开道锣鼓敲响,时辰已到。一片痛哭。
“妈妈,您慢慢走啊!慢一点啊!”我不停说着,声音细小,只有我和母亲能够听见。我泪眼模糊,站起来,转过身,领着母亲一步一步离开村口。
安葬好母亲,脱下孝衣,一行人下山回家。家里的大门口已换上了红纸对联,厅屋打扫干净,神台前摆放了两张连桌,桌上端放茶果酒杯。按照风俗,司仪的礼生让我们入座,挂红传杯,并迎接母亲的遗像,安放在神台中央,点上了神灯。
白瓷调羹,白色灯草,神灯明亮,如豆,如星,如微小的太阳。
我凝视着母亲略带愁容的遗像,神灯长明。恍惚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儿时与母亲猜谜的情景。
“白龙过江,头顶一轮红日,是什么?”
“点亮的神灯。”
责任编辑 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