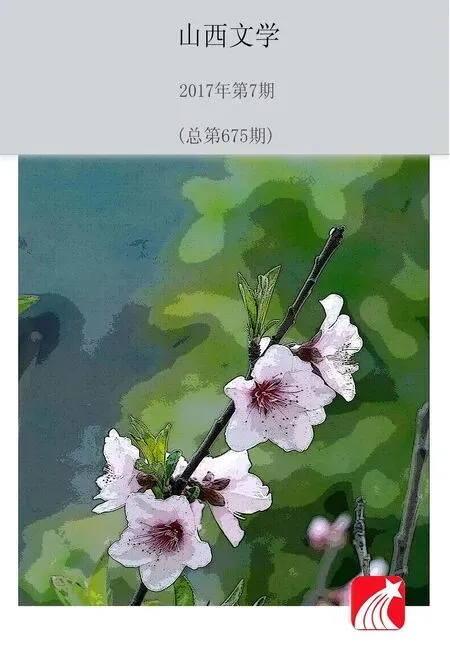民间语言的野性力量
吴 言
民间语言的野性力量
吴 言
确实,鲁主编说得对:苏二花能行!——意思我想有两层,一是苏二花的小说写得不错,二是苏二花还很有潜力。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苏二花的语言好,很有劲道。很多人写了很多年,语言还是绵软疲沓的,识别度不高。而苏二花的语言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干脆利落,形象生动,带着勃勃的生气。除了这些形容词,语言好会是什么样的阅读感受?就是你会被带着,像站在了传送带上,一节一节地就顺畅地读下去了,即便阅读是为了写评论,也不会觉得勉强。而到了《地狱图》这篇小说里,苏二花的语言已经完全征服了你,你已经不由自主跟随着人流去赴一场盛大的禳瘟会,并且汇入舞蹈的人群,舞得酣畅淋漓遍体通透!
苏二花对语言是有特殊感觉的,比如在《海拔八百米》这篇小说中,她这么形容女主人公:“黄再枫一直就是个浮夸的人,说话很少用简洁明了的名词和动词,而更多用的是形容词和副词。”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但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认识,是只有经验丰富的作家才能想到的。在小说《氢气球》里,苏二花这么形容小斌的妈妈:“小斌妈妈那是谁呀,巧,灵,手一份嘴一份的人物,虽然人长得瘦点、小点,但脑子不比风火轮转得慢,她吃这个亏?”这时语言又呈现出一种方言的生动。
除了上面这些星星点点,密度不低的散布在小说中的亮点,苏二花的语言还有另外一种很少见到的特点,就是非常善用排比句,比如形容心脏跳动:“这声音是春江上涨了的大潮,是群山颠定猛炸开的奔雷,是春天枝芽怒发的哔啵,是血浆在身体里生生不息的流淌。”这个特点在《海拔八百米》的结尾处有了一次集中爆发,营造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不依赖任何情节,仅凭语言就将小说推向了高潮。如果没有这样的结尾,小说只是提供了一个稍微不那么平淡的故事。但这个用语言构建的壮丽的结尾,反衬出现实中男主人公麻木暗淡的日常生活,提升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让人感到小说确实是语言的艺术,仅仅依靠故事情节,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艺术感染。
而在《地狱图》中,这样的特点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小说最后的三小节是对“禳瘟会”盛大场景的描绘,苏二花的语言终于找到了与之匹配的庄严仪式:
“人一重,灯一重,烟一重,鬼一重;唢呐一重,旺火一重,古老的榆树又一重;油灯一重、炮架一重、戏台一重、僧人的袈裟还一重;天一重、地一重、星光一重风一重;九曲阵一重、地狱图一重、十殿阎君是一重,万人舞蹈腾起的尘土是一重。在今夜,人鬼不分、人神不分、人物也不分;在今夜,生不分、死不分、明暗分不清;在今夜,哀伤与欢快不分、悲戚与欣喜不分、少壮与耄耋不分、天堂和地狱不分;在此时,人影憧憧、鬼影憧憧、月影憧憧、树影更憧憧;在此时,手在舞、腿在舞、腰在舞、衣袂在舞、头发在舞、整个身心全都在舞;在此时,男在舞、女在舞、老在舞、小在舞、整个龙泉都在舞。”
这时,所有的情节铺垫都淡退下去。小说前期提出的“生”与“死”的命题,都在盛大庄严的仪式中落定下来。仪式承载着对生之艰难的敬重,对死之必然的臣服,这就是宿命。与之相随的语言有着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不仅有华丽的外表,还是自带节奏韵律适合高歌吟唱的。语言自有力量。
《地狱图》这篇小说分明让人感到,若一个故事跟乡土、民俗结合起来,会有别样的小说面目,呈现出一种更为强大坚实的力量。我不由得想,青年作家也许都应该去“寻根”,从土地中找到自己文学的根脉,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长。
从苏二花的四篇小说,《秘密》《海拔八百米》《氢气球》和《地狱图》中,还是能感觉出语言上的潜隐变化的。事实上,如果小说中的情节太过离奇乖张,比如《秘密》中的强奸复仇之类,语言的特色反而被掩盖了。在《氢气球》这篇小说中,虽然是写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的被弃和死亡,但情节平缓下来了,语言的原汁原味反而出现了。在《地狱图》中,女女这一条线如果仅处理成平常普通的人生际遇,也不会有损小说的整体表达。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写作者要不要依赖故事情节?在我看来,太依赖外在的情节,达到触目甚至惊悚的效果,会把小说写得很外化、很外向。这不仅是写作新人身上常见到的,在一些很资深的优秀作家身上也时有表露。这当然跟我们光怪陆离的现实有很大关系,但我还是想把它归为作家的败笔,是创造力衰退的表现。
以“死亡”为例。它是很重要的文学元素,是戏剧性的,也是外化的。我一直希望每个作者都能慎用“死亡”。“死亡”是郑重的,值得用它来换取更多。就像福克纳的名篇《献给爱米莉小姐的一朵玫瑰花》一样,“死”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一击而中,升华了整个小说。
苏二花的这四篇小说,都写到了“死亡”。这样的使用率是比较高的。《氢气球》中小斌的死亡换来的是同情。类似的题材,史铁生写过《来到人间》。史铁生没有为患有先天性侏儒症的小女孩选择死亡,虽然父母有这样的机会。但 “死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生才是严峻的”。孩子活了下来,但需要承担生之艰辛和残酷。《海拔八百米》中,两个人的突然死亡有些随意,成了点缀,没有推进主人公对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的思考。而在《地狱图》中的“死”郑重了很多,它不仅经过了必要的生死挣扎过程,到最后还配有庄严盛大的庆典,这是“死亡”该有的模样,也换取了它应有的价值。
还要回到语言上,实际我想说,苏二花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完全可以写内敛、很内化的,有着内在力量的小说,而不必借助那些鸡精一样的外化情节。
我在心里一直在琢磨,苏二花这种语言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受武侠小说影响?受网络小说影响?(据说她曾经写过网络小说)。如若这样,我就要对类型小说和网络小说刮目相看了,难道自己真的OUT了?
正好在鲁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研班见到二花,我犹豫了一番,还是放弃了只对着作品书写评论的做法,向作者本人抛出了我的疑问。实际一个写作者受什么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大部分时候作家自己并不自觉。我首先问二花是不是受武侠小说影响?她迟疑了一下,说年少时喜欢读武侠小说。看来有影响,但还不是那么大。我又引导地问她,受哪个作家影响最大?她说以前很喜欢贾平凹,好些时候读得激情澎湃,但近年也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了,那样的感觉少了。我心里想,也可能是作家本身的语言能量减少了。民间的乡土语言,跟贾平凹学是对的。可是我没有特别感觉苏二花的语言像贾平凹。虽然同属北方方言区,但贾平凹的语言里有一种阴柔,苏二花的语言中却透出一种豪爽。看来这也不是答案。那么就是网络小说了。二花在网站上写过五六十万字小说,但因为类型化、同质化之类的问题放弃了。她肯定地说网络写作并没有影响她的语言,只是提升了写作速度。
还是不得要领。我问了二花的教育背景。跟我原先的预设不一样,原以为她上过技校之类,分配到铁矿工作,实际不是。她高中未毕业就去了运输公司工作。她小说里对话写得鲜活,很像她自己一直坚持的故乡方音。她说民间的语言才最是生动丰富,说得最好的不是老农民,是以前那种县城里的人,现在那样的人少了。她以前工作的运输公司的司机语言最是好的。司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生活放达恣肆,人生阅历和趣味最后都体现在了语言上。
《海拔八百米》这篇小说里有个细节写到了网络上的各种论坛贴吧,我想二花可能对网络挺熟悉。她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辞去了老家的工作。居家生活之外,网络成为她了解世界和介入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窗口。二花的小说之所以没有受制于单调闭塞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一种丰富性,除了她早期的社会经验,我想现在可能受网络的影响更多。但二花似乎没有那么热衷于网络,她说自己很少在网上论坛发言,只是看得多。
我心里的答案浮现了出来,但还是模模糊糊,似是而非。非学院化的教育,丰富的社会基层生活,网络世界,对文学的爱好,语言的天赋等,这些都成为二花影响语言的因素。但仍有疑惑,这足够吗?
正巧,二花和别人闲聊,听见说她很懂戏曲,是地道的戏迷。——噢!终于找到了!答案在这里!戏曲是造就苏二花语言风格最重要的因素!她那大段大段节奏铿锵的语言,让人想起舞台上急促的梆子声,锣声鼓点,铙儿钹儿,嘈嘈切切,一派人间歌哭与喧哗。
戏曲语言完全生发自民间,它在口语的基础上不断提炼、浓缩,成为语言的精华,带着声韵气息,保留了语言活生生的生命,没有成为书本上的文字标本。在苏二花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语言就像土地一样,为作家提供了滋养。问二花喜欢什么戏曲,她说什么都喜欢,最喜欢河北梆子。不像平常人那样只喜欢本地戏,晋剧或北路梆子,可见二花是戏曲的骨灰粉。二花说看戏一定要去场子里,那些老农民才真懂戏,即便他们大字不识。
我想起葛水平,她的语言就很有特色。即便是写石头和玄武的小文,也透着灵动和劲道。我不禁感慨,跟水平的文字比起来,我们的文字就像大棚蔬菜,盆栽植物,根本不见野生蓬勃。从苏二花身上,才恍悟到水平也是深受戏曲影响。她曾是戏曲演员,还是戏曲编剧。只不过,水平更像“婉转蛾眉”的花旦,苏二花则是铿锵飒爽的刀马旦。
我也想起了赵树理先生。张炜在《万松浦记》中有一篇短文《原汁原味的民间艺人》,虽然他没有点明,但一眼看出他写的是赵树理。赵树理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仅凭民间艺术滋养出来的大作家。跟其他的知识分子作家不同,书本对他的影响远远不及民间艺术。他也是深爱地方戏曲,民间曲艺,对戏曲的兴趣几乎超过小说。他的文学根植于深厚的底层文化土壤,所以才会抵抗时风,为自己保留了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创造出了能够穿越时光的经典。
《论语》有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的君子还是去写理论或骈文去吧。小说这种形式,我还是更喜欢“质胜文”,野性的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那些话都是自己跑出来的”,说到《海拔八百米》和《地狱图》最后的高潮,二花这样说。“我一般不设计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他们自己往前走。”——听了这话,我在心里都快哭了。当我还在苦思冥想怎么解构一篇小说时,苏二花手中的笔已经受到了老天的点化。
吴言,山西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
责任编辑/陈克海 chenkehai198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