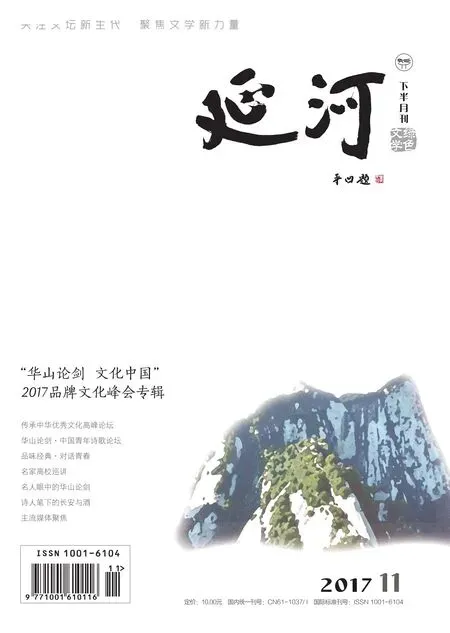寻 秦 记
□老四
寻 秦 记
□老四
1
山东人去陕西,会想起贾平凹的一篇散文《进山东》。秦人来鲁,颇多感慨,鲁人赴秦,亦有诸多想法。
对西安的印象,始于贾平凹小说中的西京。先看的《白夜》,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夜郎常在古城墙上吹埙,呜咽带有鬼气。再看《废都》,西京城里颓丧的文人,伴随着庄之蝶和他的女人们的故事,描摹出了西安城的一抹侧影。
围绕着陈忠实、贾平凹和路遥的作品、传说,这座城市被蒙上了一层文学的神秘气息。当然还有诗歌、摇滚、电影,昔日古都的文化影响力依然雄厚。
在历史的不同缝隙里,山东对于关中,意义各不相同。战国末期,秦与齐各领风骚,并称东西二帝,两极对立,展开冷战以及热战。最终,有渔盐之利而重商的齐国,因齐宣王、齐湣王几代帝王短视,缺乏战略眼光,尤其是燕国大将乐毅,差一点将齐灭国,齐国最终成为虎狼之秦的刀下之肉。
齐国的战略明显逊色于秦,当时,秦已然成为霸主,对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周天子并不放在眼里,它邀请齐国共同称帝,作为天下第二大国的齐国欣然应允,却不知自己从此便被放在火上炙烤。山东五国慑于秦的压力,又出于对齐贸然称帝的愤怒和恐惧,将矛头对准齐国,曾孕育了齐桓公的东方大国,就这样被敌人和自己搞死。
说完了齐,再说鲁。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如数,丧家之犬孔子,其利用价值大抵也是在坑与尊之间的不断转换。来自帝国中心关中的声音,一直在左右着以曲阜为中心的鲁文化,并在齐鲁交界的泰山抵达巅峰,起始于秦始皇的封禅,将这座并非极高却有着一览众山小独特优势的山丘打造成华夏第一名山。
我的老家,在距离曲阜不远的蒙山脚下。孔子登蒙山小鲁,登泰山小天下。我不太在意所谓的鲁文化,倒是对不拘礼节的齐文化颇有兴趣。齐与秦更相似吧,远古时候,两地都是边疆,所谓东夷西戎,是亚文化地带。
贾平凹说,八百里秦川农民视为生命的“五大要素”,除秦腔外,还有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羊肉泡馍。在关中行走,中午和晚上,我都泡在西凤酒里,在其刚烈而又绵软的润泽下,醉眼朦胧。能吃能喝能唱,秦人之豪放,不逊于山东大汉。“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唱秦腔”,只有亲临此地,才能真正体会到贾平凹、陈忠实小说里随时跳出的秦腔,那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命的一部分。
关中的寺庙和别处不同,既华贵又亲民,颇有一番风味。为了寻味唐诗与寺庙的隐秘关系,我们一帮人打车来到城南的香积寺。这个寺庙的大名,自然得益于王维那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地往南数里,便是终南山,隐士聚集之地。
香积寺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净土宗”祖庭,唐代著名的樊川八大寺之一。寺边的村庄,名为香积寺村。走在寺里,但见花木丛生,极具生活气息,说是寺庙,更是附近村民休闲修身之所在。
善导舍利塔,建于681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塔顶已经塌陷。寺院两侧,书法碑帖甚多,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弘一大师李叔同圆寂前手书的“悲欣交集”四个大字,一生况味集于其中,大师的境界,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如叶圣陶解释“欣”字,一辈子“好好地活”了,到如今“好好地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
在寺门口吃一碗面皮,一群诗人围坐成两个圈。吴小虫端着碗蹲在台阶上,恍若王维的另一张面孔。
可能,香积寺会成为我最喜欢的一座寺。
2
探究秦文化的起点,要到甘肃天水。我没有去天水,而是来到凤翔——秦之辉煌,自此地始。西凤酒厂也在这里,秦文化与酒文化混合在一起,颇有一种意味。
秦国的崛起,历经多次迁都,最初在天水,公元前714年迁都平阳(陕西宝鸡东南),公元前677年迁都雍城(陕西凤翔县南),公元前383徙都栎阳(陕西临潼),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陕西咸阳)。这其中,定都咸阳最为人熟知,有100多年,而在雍城,则有将近300年时间。
秦人迁徙的路径非常明确,即自西向东,从西部蛮荒之地,到肥沃的关中,步步为营,战略位置越来越重要。虽然最终定都咸阳,但雍城却是他们心中的圣地。作为十九代君主的宫殿和陵寝之地,这里是秦人祭祀上天的神庙。即便迁都咸阳100年后的秦始皇登基大典,也要回到雍城举办。
如果说秦国在咸阳开启了统一大业,那么雍城则是其称霸之地,在这里,他们终于摆平了西戎,稳定了西部边界。从此,历代国君只有一个目标,向东、向东、向东……去和中原诸国争锋,而不再是西部边陲小国。
相对于之前的都城,雍城有河流密布的水资源,有茂密的森林植被、丰富的土壤,发展农业、畜牧、渔猎都成为可能。发达的交通,多元的经济,秦国自此有了和山东诸国叫板的资本。至今,以此地为中心的西府地区,仍是文化昌盛之地,是秦腔的发源地,更著名的是岐山臊子面,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能吃到。
凤翔县发掘出大量先秦时期的历史遗迹,尤其以秦公一号大墓最为壮观。9月4日,当我站在秦公墓挖掘现场,俯身看到十几米之下的墓穴,时间瞬间把我拉回到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我仿佛走进了秦景公的生活现场,进行一场历史的对话。
1976年,凤翔县一个农民准备挖土修补院墙,在黄土层中,挖出了一些奇怪的土块,有黄有红,夹杂一些碎石,和周围的土明显不同。正是从这个农民开始,一个足有八层楼高、两个篮球场大的陵墓慢慢浮出水面。就在两年前,骊山脚下一个农民在打井的时候挖出了陶俑,即后来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中国农民为考古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不是他们对耕耘土地的热爱,很多文物将长眠地下。
从秦始皇上溯到秦景公,相隔300年的两代国君,在关中平原上相遇了。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被发现开始,考古学家就在寻找秦人东进的踪迹,凤翔秦公大墓的发现,将雍城这一历史名词标注于现实地理,经过长期的发掘和论证,一个东西长3.3公里,南北宽3.2公里的古城逐渐显出轮廓。
秦公一号大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古墓,墓内186具殉人是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椁室的柏木“黄肠题凑”椁具,是迄今发掘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的规格;椁室两壁外侧的木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
大墓中出土的石磬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最珍贵的是石磬上的文字,多达180多个,字体为籀文,酷似“石鼓文”。专家破解的结果,认定铭文记载了一次宫廷宴乐活动,大墓的主人,是活动的召集者。铭文里“共桓是嗣”几个字,说明了他的身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共桓是嗣”就是说共公和桓公的继承人,那么按照这个推测的话,它的继承人就是景公。
景公是秦第14代统治者,秦始皇的第15代先祖,自公元前577年起,在位39年。那时的秦国,已在雍城雄据百年,国力也日渐强大,从景公死后使用周天子才可享用的黄肠题凑葬式,可见秦的雄心,已经超出关中一带。
春秋时有两个景公,两人在位时间都很长,秦景公在位39年,齐景公在位58年。除了对当时各自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在死后两千余年再次引发关注,皆因墓葬。秦景公墓葬中发现了大量人殉,而齐景公墓葬中是大量的战马。
人殉,这种极其惨烈的殉葬制度,展示出一个时代的残酷背景。
我是鲁人,这些年更向往肆意纵横的齐文化。显然,齐文化虽然足够开放,却霸气不足,齐景公好马,更多是出于欣赏的目的,千乘之国没有顺利转化为虎狼之国。当然,齐文化中官与野随意转换的性格还是影响了后世许多年,所谓稗官野史,在《聊斋志异》中抵达巅峰,又在莫言的小说中得以呈现。
3
数百年的蛰伏和奋起,只为东进后的辉煌。可为什么“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 为天下笑者”?巅峰既是没落的起点,数十代的积聚,不及一人之挥霍。唐亦是如此,我们浸淫在盛唐的辉煌中,却不忍晚唐的没落。
《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诸多“唐朝的黑夜”,那些离奇的志怪故事,在中晚唐的天空下,暗夜中发出凄厉的嘶喊。不管是盛唐,还是中晚唐,一切故事的发生,总有一个风暴眼,这个眼,就是大明宫。
雨中逡巡于西安城。几次过大雁塔,想起韩东那首《有关大雁塔》,却从未停下脚步。沿着古城墙一路向北,城墙的巍峨让人赞叹,不觉想起许多城市被拆除的城墙,诸如北京、济南。曾看过一幅民国时期的老照片,韩复榘在济南城墙上修了一条环城马路,市民在城墙上骑自行车游览。今天的济南早已不复当年情景,而在西安,城墙则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雨越下越大,过了老城墙继续向北,撑伞走进大明宫,烟雨朦胧中,进入草木的世界。
这座未临其境早闻其名的著名宫殿,曾多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影视剧里的武则天、太平公主、李隆基等人,无数次在这里上演“最是无情帝王家”的故事。
大明宫是唐帝国的皇宫,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是当时长安城三大宫殿中最大的一个(另两个为太极宫、兴庆宫),自唐高宗始,17位皇帝在此办公,历时200余年。大明宫地处龙首原,俯瞰西安。相当于4个紫禁城,三个凡尔赛宫,十二个克里姆林宫,十三个卢浮宫,十五个白金汉宫,五百个足球场。
904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为兴建洛阳宫殿,拆毁长安城,将宫殿木料运往洛阳。自此,长安城彻底没落,至今一千余年。大明宫辉煌不再,后来成为西安的城中村,污垢横行,脏乱差,遍布的建材市场,占据了当年武则天们的生活轨迹。
直到2010年,此地再次建起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绵延五千亩地的区域内,一个类似于长方形的公园的出现,可见西安城之气魄。当年的城北,如今早已成为市区,周围高楼林立,让人想起纽约中央公园的格局。
公园的独特之处是,并未复原过去的宫殿,而是在每一处宫殿遗址上标明位置,建起框架式雕塑。同行的作家陈益发告诉我,每一处遗址都已经保护起来,在以后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会进行进一步考古发掘,或者复原过去的大殿。
我走上含元殿所在的一处平台,想象中,大殿拔地而起,周围的所有大殿鳞次栉比。这里是过去长安城的制高点,站在大殿里能够俯瞰整个城市,皇帝的威严在此处显露。王维曾有诗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高宗首次在这里听政,玄宗多次在这里大宴群臣、策试举人。
梨园静静矗立在宫殿东侧的一个湖边,这里原是一处游园,后来成为唐玄宗的娱乐场所,类似于国家曲艺中心,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在这里诞生。
作为帝国的中心,所有人和故事围绕着它,来自这座宫殿的消息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这里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命脉,大唐从这里出发,中华文化的制高点在这里酝酿。这一片石阶铺就的废墟,在重生中听取着一个民族的声音。
一个个皇帝,以及他们的时代在这里聚集。可惜武则天不喜欢长安,她钟情于洛阳,即使退位后仍长居洛阳,并死在了洛阳。也许是长安太具雄性气质,掩盖了女性的芳华,但武则天身上迸发的雄性气质确实够强,她要开创自己的时代,另选都城也就顺理成章。
如今的大明宫,是游人和孩子的世界,其地域够辽阔,走一圈下来,也需要花去大半天时间。已经被人熟知的故事在草木间流传,地下埋藏的诸多隐秘继续深埋地下,等待有一天重见光日,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大唐。雨中安静的公园,游人稀少,无数重叠的历史在此地交汇,又向着未来踏步前进。
很难用普遍的眼光来观察西安,汉唐气象是属于长安的,而对于西安,我们似乎只能用“夕阳残照,汉家陵阙”来感叹。这座在遗址上不断拓展的城市,还有多少“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有多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沉沦了千余年的老城,如何走向新生?
4
许多年前来过一次西安,我们几个人在重庆的山间游走,突发奇想要去咸阳机场飞回济南。于是,整个秦岭被我们洞穿。那时我还写了一首诗,其中几句是:
把这个村庄交给四川
那个山头扔给重庆
脚旁的小河随手赠与陕西
我手握重兵
三千汉字可轻取汉中
可越秦岭
在高速路上评点山川
把乱侃的嘴巴封为万户侯
把三省草民唤作良民
那天我同样醉酒,缩在车里昏昏欲睡,等到过了钟南山隧道,广袤的关中平原把我浇醒。山和平原如此分明,没有任何过渡,我已从隐士转身变为行者。那次,我们没有进西安城,而是从南外环绕到咸阳,去拜谒汉武帝的茂陵。
而此次,寻访秦和唐之外,独绕过了两汉。我的不太准确的感觉是,秦是陕西人的骄傲,汉唐是中国人的骄傲,唐更普遍而汉更高大。唐有唐诗做铺垫,汉代独缺了普遍性的文学。所以,汉代多是大国往事,犯我强汉虽远必诛,唐更亲民,有绯闻,有艳遇,有街谈巷议。
诗人也会重叠,在历史的夹缝中,同一座城,不同的人活成了一个人,一个人也活成了不同的人。就像我,以及我们这些游荡在西安城里的80后诗人,谈论的意义在哪里?争辩和反抗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早已踏过了某个时期,现在正以时间的速度向中年迈进,青春于我等究竟还有多少残留?在历史的夹缝中,一代人总会留下一些痕迹,我们留下了,并将继续留下。
与以十年为一个区域的代际划分比较,我更喜欢“同时代人”这个概念。所有活着的人,我们都是活在当下的人,接受着类似的信息,如果将文学比作赛场,我们有着同样的起跑线。在奋力诠释这个时代的道路上,耄耋之年的老人和十几岁的孩童机会是一样的。
秋风起,最后一天中午,我和几位诗人在大明宫外饮酒。关中人喝酒多用小盅,一口一盅,不多时便进入醉态。还有一种喝法,盅内倒满,酒将溢未溢,当地人叫“牛眼”。喝了满肚子牛眼后,细雨纷飞中乘坐远村老师的车回酒店。车过陕西作协门口,谈起作家路遥,我慌忙下车拍了一张照片,恍惚间感觉好似作家仍在这个院子里,躺在一把藤椅上,慵懒地晒太阳。
历史和现实在此交汇,前方不远是大雁塔,这几天所有的行走都会在车窗外看到它若隐若现的影子。这座城里曾有那么多诗人,现在还有那么多诗人,如果让我选择,可能最想出城向北,去黄土高原寻找一位作家的痕迹。可是,就文学理念而言,我与他早已背道而驰,但不能否认,他曾在我心里扎根,在外在的人生路径选择上,起到过一定作用。
一座城市要沉积多久,才能释放出久违的人性的光辉?活着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延续,就像大明宫里的那些宫殿遗址,皇帝们可以在里面吃喝拉撒,一介草民又有什么不可呢?只是时空不同,我所拥有的时空,在此刻成为人类永恒的经典。
返回济南后,某日,与陕西诗人、作家王刚微信聊天。他是路遥的清涧同乡,出版过几本关于路遥的书,恰好我曾买过其中一本。我从书架上翻出那本《路遥纪事》,时间再次重叠,现在的我,以及我们,不可能再沿着某一条路前进,却总会看到那条路上的风景。
同时代人走在这个世界上。我总会看到一些风景,此时,所有的人看到了同一个太阳,所有人都在描摹那个太阳。出现在每个人心里的太阳又是那么不同,有人的太阳成了上帝,有人的太阳成了阎王,有人的太阳成了石头、水、风、流水,甚至时间流动的某个支点、大雨降下的某个瞬间、激情时的某种体会都成了太阳的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