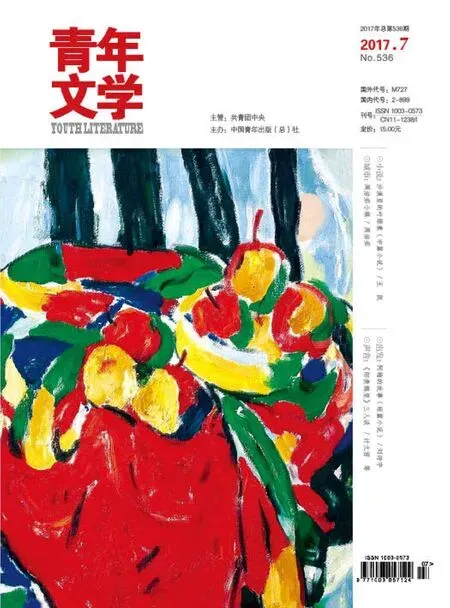周洁茹的此时此刻
⊙ 文 / 周洁茹
周洁茹的此时此刻
⊙ 文 / 周洁茹
【编者的话】
因为新增“城市”栏目,本计划和周洁茹做一次对谈,与她天马行空地聊聊她的生活和写作,她的城市和情感。周洁茹说,你看,你要问的,我能回答的,之前都有人问过,我也回答过了。在微信上,她立即打包发来了所有文档。周洁茹在写作上有个习惯,如果她准备改换她生活的地方,就会写一篇类似《到哪里去》的小说以提醒自己即将去或者已经去生活的方向。她强调,是生活,而不是旅行。一如她对写作的坚持,视若生命,也能断舍离;搁笔十五年之久,当她再次拿起笔依旧能洋洋洒洒。这是天赋。
如此,这个对谈变得更有意思,当然这也是基于周洁茹的原因,对谈变成了创作谈,她确实很别具一格。以下的文字也可以看作是一次隐去提问者的对谈,毫无例外都由周洁茹本人亲口作答,而且能反向推导出所提问题的大致面貌。所以,这自然可以视为周洁茹回顾城市生活经验的若干回忆。
到常州去
我出生并且度过前半生的地方,是常州。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写常州,这个小城市和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里的人和事情,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写,那时我还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香港,2016》)
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我固执地认为,写小说是我的事业,可是他们告诉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才是你的事业,小说创作只是业余爱好,我觉得我受到了打击,于是我开始想做点什么,但我只是在玩各种各样的花招,比如把头发染黄,并且希望他们在食堂里看到我的时候把调羹咽到肚子里去。我还干了点别的,比如穿着旗袍和木屐去上班,可是到年终我被评为了爱卫先进和档案工作先进,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成为那些先进,我认为所有的先进都是我的耻辱。我一直在想,换了别人,也许会对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心满意足,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幸福或者给了我幸福,我却痛苦。要么离开给我饭吃的地方,饿死,要么不离开给我饭吃的地方,烂死。我已经不太在乎怎么死了,死总归是难看的。……身在这个地方,却被这个地方漠视,是好事情。……如果说我身陷囹圄,写作就是我从栅栏里伸出来的一只手,我等待着它变成一把钥匙。(《头朝下游泳的鱼,1998》)
可以这么说,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生活。我关注我身边的男女,他们都是一些深陷于时尚中间的年轻人,当然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众多的新鲜事物就开始频繁地出现,我们崇尚潮流,自我感觉良好。(《现在的状态,1997》)
直到住在香港的第五年,我用了常州话来写《离婚》。我已经忘掉英文了我也没学会广东话,这期间我只去过一次香港书展,买了一本《繁花》,一夜读完。然后我用我的家乡话写了这个小说,我想我要向《繁花》致个敬。我真是太爱它了。(《我和我的时空比赛,2017》)
到美国去
我有轻微的电梯恐惧症和飞机恐惧症,每次我上电梯和飞机,都会发抖,担心它们会突然从高空坠落下来。有一次,一个坐在我旁边的男人说,飞机如果出事故的话会很快,几秒钟吧,什么都结束了,所以你根本不必要恐慌的。(《海里的鱼,1999》)
我离开中国,飞到了美国,整整一年,我都无法爱上我在美国的生活。我流了很多眼泪,可是用那么多的眼泪换心的平静,很值得。(《八月,2002》)
我在美国是不能写作的,像诅咒。(《八月,2002》)
我对美国有一些割舍不下的东西,一是BBQ(烧烤会),一是万圣节。(《大家与我,2015》)
我还看到《故事会》出现在纽约地铁里,但是,我没有在纽约的地铁里看到过任何一本《收获》和《人民文学》。当然纽约的地铁里也看不到《纽约客》。现在想起来纽约的那些日子,暗的,灰的,像漫长到没有尽头的隧道。我都没有去想纽约的地铁是什么样子的,也许纽约的地铁只是那样的,如果一个男人的书包带子从肩上滑落,落到邻座,邻座的男人不会挪动他的身体,邻座的男人直接地告诉那个背书包的男人,用坚定的眼神告诉对方,你的带子碰到了我。(《有时会写超短篇,2015》)
我没有写《到美国去》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现实,就是我在美国住了十年,而这十年,在我写作上来说,是完全空白的十年。(《在香港写小说,2015》)
我所有关于美国的小说都是离开了美国以后写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感觉好像就是,我最美好的时候,我爱的人都不在我的身边,或者我和“我老婆”离婚了,我才发现我最爱的人是“我老婆”,那种感觉。(《在香港写小说,2015》)
到香港去
对于很多人来说香港只是一个过渡的地方,或者是两块板中间的那一个区域,一个夹缝,我一直以为我在美国的十年是一个时间的缝隙,我走出来我还是我,只是世界都不同了。而我在香港这个地理的缝隙也待了接近八年,我终于可以承认这一点,香港是我的现在。我在香港。(《我们只写我们想写的,2017》)
我要感谢香港,给了我这样“准确”的生活。一切都是我要的,不喝酒,不开会,不睡午觉,这自由也是我给自己挣的。(《野心与慈悲,2017》)
在香港,我最常去的书店是沙田新城市广场的那间大众书局,后来搬走了,我就去商务印书馆。我对所有的书店都没有特别的喜欢,哪间书店离我最近,我就去哪间。如果去深圳,我去少年宫那里的深圳书城,因为从福田口岸搭地铁过去方便。住在香港,我就没办法在网上买书了,邮费比书贵,尤其当当网,用顺丰快递到香港,一百元的书五十元的邮费,上门再收偏远地区三十元,我住在香港的乌溪沙,快递要多收三十元令我意识到我住得实在偏远。(《阅读课,2014》)
作为一个香港居民,诚实地说,我对香港仍然没有很热爱。之前的六年,我都没有觉得我和香港有什么关系。因为不看翡翠台,因为不去街市买菜,因为一个香港朋友都没有,男朋友女朋友都没有,所以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当然我是一个特例,所有除我之外的新来港人士,都是在第一个月就学会广东话了。因为要融入香港社会,做新香港人。而不是像我这样,时刻准备着,要离开香港。(《在香港写小说,2015》)
不会广东话,是我的遗憾,要不然我就可以用广东话的模式来写我的香港小说,让它们成为“最香港”的小说。……所以我的香港小说,全部发生在香港,但是主角说的都是江苏话。当然我完全没有觉得我是一个香港人,但是我写了香港人的生活状态。就冷漠到残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一点确实也是没有地域的界限的。所以对我来说,香港人也是人,香港小说,其实也就是人的小说。(《在香港写小说,2015》)
到四十二岁去
成为一个专业作家的时候我二十三岁,那是一九九九年,祝贺我的人有一堆。但是我后来想想,要一个二十三岁只知道写写写的女孩,每天去过那种不坐班但是开会开来开去的生活,真是太残忍了。(《野心与慈悲,2017》)
我就出国了,背过的英汉字典刚好也用到了。二〇〇〇年,我二十四岁。如果你没有在二十四岁之前读完你应该读完的书,写出你最好的作品,你只能等到四十二岁了,至于这个四十二岁,你还在不在?你还写不写?就真的不能够确定了。我说的是真的。(《野心与慈悲,2017》)
二〇〇九年我从美国搬到香港,三十三岁,五年哪儿都不去然而又是准确的香港生活以后,三十八岁,我重新开始写作。也就是说,我还有足足四年恢复和适应的时间,让我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写出一部巨作。(《野心与慈悲,2017》)
到未来去
《进击的巨人》是一本日本漫画,由其改编的电影《进击的巨人》的海报上,一个废弃的岛屿,一道已经破掉的围墙,探进一个巨人的头颅。它要表现的,我倒觉得真是全人类的未来世界,污染,和人类的毁灭。也是文学世界的未来,污染和毁灭。(《过去未来,2017》)
二〇〇九年,有一部叫作《代理人》的电影,已经符合了我对未来的想法。真实的不完美的人类躲在家里,意识遥控机器人来代替上班甚至做爱,机器人的样子当然好得多,而且还不会死,大街上走来走去全是模特儿身体的代理人。这个电影造了一个最美的美梦给我这样的宅神。如果我可以购买一个美貌的代理人,她就可以代替我出去见人,又有谁能够说她不是我呢?但是代理人的问题就是,她还是会断线,如果我离开了遥控床,她就一动不动了,而且说到底她的身体也不是我的身体,即使快乐也只是意识的快乐,身体真是一点儿快乐都没有。我可能还是更喜欢自己的身体,老了很多也胖了很多的自己的身体。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死了,她也死了。(《过去未来,2017》)
二〇一五年,我重新写作的那一年,他们已经拍出了《查派》,查派是电影里机器人的名字。说的是机器人有了自我意识,然后帮助了人类,把人类意识上载到了机器人身体,于是人类也终于实现了不死。《查派》的评论可能很差,跟《未来水世界》似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提供了一个联系,人类与机器人真正的联系。死亡以后意识的存在和不存在,对我来说,我可能是相信在,但是它最终去到哪里我可不知道,所以又让我产生了一个不在的动摇。如果我知道它最终会去到一个机器人的身体,而不是随便一个什么地方,浩瀚的宇宙那种,我的信仰肯定就固牢了很多,这就是我喜欢电影《查派》的原因,我就是要一个肯定的,狭窄的,其实并不可笑的答案。(《过去未来,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