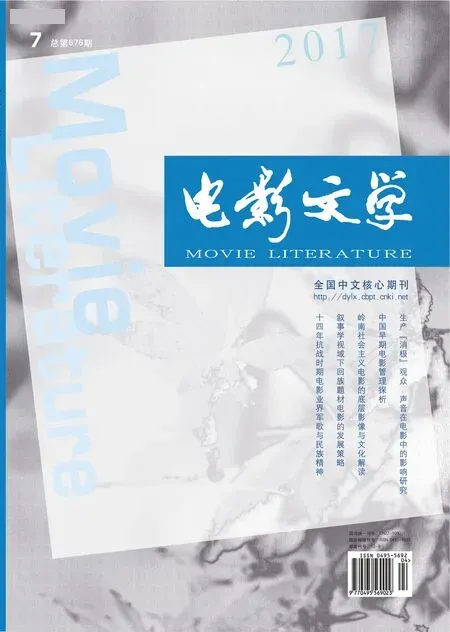中国电影的唯美主义艺术研究
申元东
(齐齐哈尔大学,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电影的唯美主义”指在影像营造中祛除意义、功利、实用的负载,直面艺术的纯粹和本质化的美感,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寻求境语的形式美和艺术技巧的美学流派。付诸感性形式的艺术表达,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复杂纷繁的审美世界里,找寻到可整合大众各异的审美心理趋向的共性原则,从而便于普遍理解、群体接受,呈现特殊的欣赏习惯、艺术趣味、美学命题乃至价值领域。一部电影的意义生产,首先来自于它的表现形态,其次才是表述内容。
中国电影在唯美主义艺术的营造方面也着力颇深,从费穆的《小城之春》,到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王家卫《东邪西毒》等片,精彩纷呈,表现不俗。而且因有着中国文化美学的深层熏染和无法比拟的表现优势,特别注重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物质载体之外的艺术本身的审美属性,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有着整体性色彩的审美情趣和美学品格。对于很多杰出的中国导演来说,银幕上打造的并不只是影像的情节意义,还有更为丰富的美学意义。因此,如果要展开关于什么是中国电影的讨论,引导大众深化对中国电影的认识,唯美主义的视角无疑是迈向通往东方电影艺术堂奥的通衢大道。
一、东方写意
唯美主义电影,在影像风格和艺术内蕴上倾向于镜头画面的纯粹美感和形式创造,视“美”为独立形态,抬高主观创造地位,几乎完全把社会因素,诸如时代科学、自然道德等成分排斥在外,显示出极端的主观形式倾向。塔尔可夫斯基的《乡愁》、费里尼的《八部半》等片都是典型作品。而中国电影在此基础上,又显然更加注重融会创造,凸显自身的特色。尤其将中国固有的古典美学方法和精神,内化为潜在的影像经络,并融会在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场面调度和题材选择等诸多方面,糅合现代电影形式讲故事的手段和格局,从内里生发出一种东方文化或中国艺术精神所独有的韵律和气质,以独特的民族风格自立。
首先,大量择取、发挥、渲染出古典山水画式的写意风格,把人物置于自然造化之中,达到天人合一,生发出寓情于景的唯美韵味。这是东方文化审美观念、手法和现代影像技术交融、发酵,呈现出的奇异视野和新颖角度,在影像与运镜的意境美上,浸透着中国文化、东方风情的基因记忆,并透过伦理/社会类型和煽情/曲折叙事,在古典美学与唯美主义之间搭建起内在关联性。费穆的《小城之春》是当时苏联电影“意识形态”和Montage构成原则、好莱坞工厂的“梦幻机制”和Continuity叙述方式、欧美唯美主义运动的艺术理想、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精神内审的多重影响下,创制“中国型电影”最成功的典型。该片借助小城里异乡人闯入从而产生情感纠葛的叙事,营造出了一种寄托遥深、独标高格的山水画电影唯美意境,其电影的构图,无论是深冬小巷、黄土高墙、垂斜白杨,还是矮屋围楼、依依人影,都是中国画之风格,是迁想妙得旨微于言象之外的“微妙境界”。这是中国电影在开创之初,就有意识地在运用现代创作技巧之下,把握民族风格,沟通中国电影与中国古典美学风格、欧美唯美主义理念的杰出尝试,并为后来的中国唯美主义倾向电影“立法”。
其次,普遍尝试在唯美主义画面感和深切的民族文化心理之间,寻求自身的叙事框架和题材资源,展现出传统抒情的艺术精神。所谓“抒情传统”,指有别于西方的戏剧和史诗的艺术特征和结构,而在艺术话语和内涵上专注于抒情特质的体系观念和实践。在影片里,影像的画面和节奏都内敛深沉,镜头的处理上节制、不逾矩的调性统摄全局,平衡、规范的全景构图渐渐累积起一种难以挥去的诗意情绪,仿佛是古典文化情感和现代唯美理念的传承和体认。这一点,典型的表现是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片子与其说是乡村爱情故事的叙事,不如说是完全中国式的“抒情传统化的唯美主义影像符号和中国阐释”。电影中的故事和人物表面上处于核心构件,实际上被“格式化后的简单化”,反倒是付诸唯美主义直觉的画面以抒情的形态和诗意的情感主宰和推动着剧情的进展,呈现出接近生命本身的、最诗意、最真实也最唯美的艺术形式。此抒情化的唯美主义表现形式其实是在创新电影语言。
二、民族风情
尽管唯美主义艺术观一贯地强调超然和独立,主张“审美不关联利害”,认为越抽象化、越理想化就越能表征社会特征,但另一方面,在其话语系统中,表意和隐喻或象征依然是其“形式内壳”。显然,任何的形式形态都无法完全超脱于物质存在和社会属性本身。对于具有唯美主义艺术倾向的电影来说也是如此。只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物,与一般的唯美主义艺术形态相比,其特殊性在于更加无法做到纯粹形式美感的要求,其内容叙事层面必然会涉及大众的精神、道德、情感等诸多因素,所有的唯美主义形式塑造最终都会对电影的价值传导目标予以必要的关注,并在不经意间成为某些价值观和民族/集体心理的指认对象。中国的唯美主义风格电影,其叙事特征也正是在这种“富于游戏的规范性和假定的唯美主义改造”中,不断有效地虚构现实,展现自身特色。
第一,唯美主义形式营造显示出鲜明的工具主义特性,而视觉语法则呈现民族风情的叙事表意美学原则。也就是说,在中国电影里,几乎所有的唯美主义元素都始终缺乏主体的独立性,这意味着作为独立的、形式中心的和言说的镜像主体并没有达到存在的现场,而是依附于表意的叙事存在,作为“民族寓言”的一部分展现。陈凯歌的《黄土地》,一方面蕴含丰富的静止长镜头、庞大的伴随着飞扬的黄土地灰尘漫舞的大全景、人格化的黄河和黄土地奔腾的画面、独特的民俗风情的安详直现等,这些唯美主义的形式营造以惊人的美感轰击着观者,使得大家在温馨的画面射线中漫游。另一方面,所有形式美感的元素构建最终都是为了沉挚而复杂的感情描述,并力图投入具有审视文化、重构历史的重大意图的情感结构之中,是一种带有强烈汉民族惯性思维特征的细腻、温柔、冷静、内敛的民族风情化叙事呈现。此后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晚钟》《孩子王》等片中都有传承。
第二,透过严密的“唯美形式元素链条”的营建来阐释主题,以探索性的象征和隐喻进行造型表意。基于中国文化精神思维结构无形或有形的牢笼,画面的形式链条往往会自然升华和延伸出影像内的或哲理或生活的意义内涵和象征指向,而画内的具象元素乃至人物言行,也几乎内指故事主题而非外涉观念、思想、哲理,并成为叙事链条有机与核心构成部件。张艺谋的《红高粱》就是最为集中的标签式展现。该片依据影音造型和银幕叙事,显现出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蕴含和民族特质的影像世界,并且这种充分的唯美主义格调视觉风格中不断地指涉具有“中华文化性格”的象征或隐喻叙事。电影有意让红色成为色彩主调,营造极端强烈的视觉印象和情绪冲击力,被阳光染成一片金黄的高粱、血红的太阳和天空、“颠轿”和“敬酒神”民俗的热烈狂野的仪式化画面等,无一不具有极致化的唯美主义风格,但同时也无一不是充满浓郁的民族文化密码的象征指涉。比如“野合”场景唯美化处理对生命意识的隐喻张扬;“颠轿”对性压抑和人性萎缩的封建指涉等,这些带有文化语境的唯美元素象征意图不仅使得影片的主题得到了最高层面的升华,而且也把这种象征后的民族文化特质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这样的风格在《菊豆》《英雄》《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片中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
三、东方想象的现代性重构
唯美主义艺术运用于电影,其价值就在于“向人们给予了另一种电影”,一种基于诗意的影像,并且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审美方式,那些唯美化的视觉载体重新挖掘出它那原生的、自然的、无秩序的特性,并不断地在历史文化语境中得到现代重构,从而解放了被传统叙事程式抹杀了的表现可能性。这种唯美主义影像实践,“理论旅行”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就很明显地呈现为刘欧梵教授所说的“东方想象的视觉载体和镜像的现代性重构”特征。 唯美主义艺术也成为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元语言,并以此与世界和现代性社会产生联系和认知。
一方面,感性、具象、诗意的唯美主义特征往往和“东方想象”构成比附关系,从属其中的特定的文化传统、族群或观念成为外部强加的概念、诠释和印证样态。系列带有民族特征的唯美主义画面镜头展示,与其说是被作为叙事的主要具象物呈现给观者,不如说是被表现为充斥东方想象的静物而出现在银幕之上。比如《卧虎藏龙》,其借助中国传统情调的江湖、武侠故事展开叙事,表面上是展现“中国风情”和现代社会已成绝响的中华侠义之风,但是影片在寄托着导演有关传统中国视觉美感和儒侠美好想象的画面和情感基调上,评判的中心,实际上是西方电影的娱乐趣味和审美标准。在霍建起的《暖》里,阴郁的色调笼罩全片始终,仿佛是披盖在中华文明身上的厚重帷幕,原始贫瘠的山河、低矮潮湿的瓦屋、厚重质朴的乡村农夫、粗粝坚韧以及苦难的静态观照。无论是中国大地的苍凉回眸,还是西方遐想的东方景观,这些唯美主义画面都伴随着银幕的徐徐展开而尽收眼底。可以说,在这些影片里,所有被强化了的有着中国想象的标志的唯美具象,都经过处心积虑的多重意象和符号设置,成为他者化的权力关系和欲望对象。
另一方面,电影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文化风采和品格,淫浸着涉及民族命脉及其现代性重构的创意和反思。与有造型画面“说话”的新鲜特征,实质上是主体性美学意识的觉醒和张扬,在电影镜像的美学风范及其诗学品格上,是以个性的张力和步向现代多元为艺术特色的。田壮壮的《猎场札撒》,以传奇性的蒙古大草原如诗如画的世界为背景,浓墨重彩地对草原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展开艺术的描绘,镜头所过无一不呈现出一股诗意浓厚的、富于视觉美感的唯美画面,写意、抒怀又沉重苍凉。经过唯美主义艺术视角处理和部署的影像背后,俨然可以感受到导演作为抒情主体的存在,也能感知到作者追求、引导、实践的根本是大写意的思辨。导演从现代性视域出发重塑的审美情思,是将唯美主义艺术的审美主体性融会到比拟现代性神话式的叙事之中,从而实现对一个古老、静止、唯美化的美学世界的超越,生发出新的现代审美、人文的意义。此手法,在《周渔的火车》《孔雀》《刺客聂隐娘》等片中也屡见不鲜,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电影整体性的代际接力。
中国电影的唯美主义艺术影像,不断地给我们带来奇妙的视觉体验和情感满足。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和创作现象,它究竟是从我们本土民族文化的原点中生长而起,还是被西方文明催生出的一枚“恶之花”,并对其特征、形态、内涵等诸方面,做出认真、理性、公正的探讨,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从全球化的视野来描述这些影片的现代性崛起、古典式继承及其文化、诗学风貌,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做出真实的呈现和文化透视,毫无疑问,又是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学和电影学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