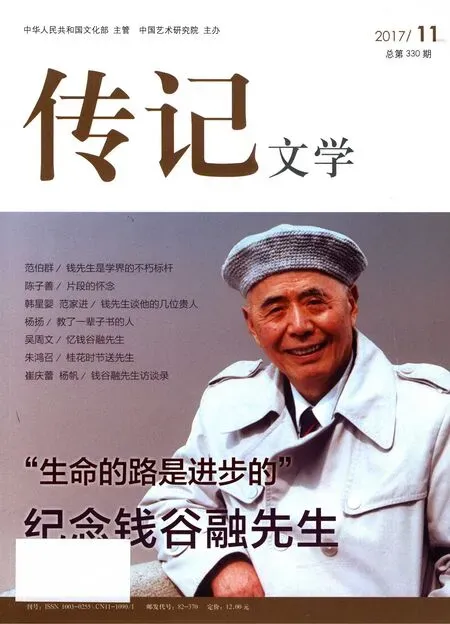他从几代诗人的身旁走过
—— 任洪渊小传
孙晓娅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白沫江水
白沫江从天台山的峰顶流下,流进岷江流进长江,流过平落古镇。这里留下了岩洞穴居的遗址,青衣古道的遗踪。来到白沫江畔,先秦先民“栖平坝而聚落”,“平落”,是他们对自己家园亲昵的称呼。
赭红砂石的乐善桥卧在江上,13株古老的黄角树排列在岸边,仪仗一样地,一株一重笼罩江岸,葱郁掩映着葱郁。桥,便坐落于这重重掩映之中。1937年夏历8月14日,乐善桥上游东岸,临江在第二株黄角树后的一户民居里,一个男孩出生了。他就是任洪渊。
任洪渊出生的时候,父亲任斌荣正在国民党的成都监狱服刑,不满周岁时,父亲已经远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他的童年,父亲不在场,母亲也在他6岁那年撒手人寰。一个没有父亲肩膀没有母亲怀抱的男孩命定地将温暖视为一生寻找的目标,或者,转过身,自己肩负自己。也许是一种宿命,今生注定他要靠自己的体温温暖自身,靠自己的体力支持全部的负累。
一个秋寒的日子,任洪渊跟随祖父、祖母回到他们位于大碑山中的山居。不到两年,祖父去世。祖父身后是71岁的祖母加7岁的遗孤。带着祖父的遗愿和遗产,他到县城三姑母家寄居上学。不到4年,甚至没有篱下了,三姑母败落了自己的家产,连同败落了祖父遗留给他的家业。
一段时间,任洪渊和祖母寄住在平落名儒名医郑春和先生家。那是新兴街一座新建的清雅庭院,连着三个天井的天空、阳光和轻风。小学课余,他在郑春和先生面前背诵完一卷《孟子》。40年后,他告慰先生:他没有见什么王,却见老,见庄,见惠。
任洪渊和祖母主要靠田租生活。闵老幺家两代租种祖父在闫镇子的6亩水田。骑龙山脚下的一带稻田,不涝不旱,白沫江的洪水在远处,山溪山涧汇聚的山潭却又在近旁,还有一纸租约,一亩水田和一担谷租,其中,包含了官定的田赋和各种名目的课税。
祖母每顿只吃一碗饭,任洪渊不知道,祖母顿顿都为他省下口中的粮食。除了过年时的腊肉,二姑母家插秧、打谷时的回锅肉,祖母月月常有的豆花、豆浆稀饭、豆面玉米馍馍,加上她家传秘技的甜面浆、豆腐乳、豆瓣辣椒,已经是美食了。
再贫苦,祖母也不愿砍伐祖父的山林,不愿卖出祖父传下的红豆木材。任洪渊11岁那年,祖母患了疟疾,并发呕吐、腹泻。他一夜、两夜,守住祖母。任洪渊忽然想起了《自然课本》上对症的金鸡纳霜。1948年年末,萧条的平落也只流通银元铜元了,在以物易物的市场,大米成为交换价值的中介,成为比纸币硬、比黄金软的通货。他提着两升米,到台子坝一家药店换取一盒奎宁丸。祖母病愈了。他到街前朝堤沟的石板上,冲洗祖母腹泻时穿过的长裤。站在水中,他长久望着自己的侧影……
平落的灯点亮了任洪渊的童年。他从乐善桥看台子坝的繁华灯树,看缭乱江面的灯影桥影黄角树影,听两岸环山间闪烁的灯在远远近近地问答。山中,祖父生前的那一盏灯没有人再点燃。
是昆仑神树若木——太阳树的投影?整个平落都欢笑在灯树下。那是平落人一个祈望丰年的明喻:春华,秋实,一株花果同枝的神树,年年生长在他们面前的土地上。树冠,是一盏红色的玉皇灯,在冠灯的左下和右下,两盏黄色的太极、太白灯对映着——与双灯相连、像繁枝四出的几十盏白色灯,灯连灯地在两侧悬垂着。
灯节固然是一场伴着鞭炮锣鼓舞龙舞狮的民间庆典,但是在平落,又是一场几十名僧侣拜灯的祭典。在方场中央,灯树斜倒在一排高过一排的梯凳上。灯树前,一列长香案供着满案的陶土灯钵。
平落子弟升灯的威仪,更像是一场阅兵和军演。由镇上的一百名子弟列队,排出一百年传承的方阵,呼喊着号子,抬起灯树——一起,一进,一停;二起,二进,二停;三……一列人梯接力一列人梯,灯树30度、40度……90度,在他们土地一样坚硬的肩膀和双手上树立起来。乐善桥的元宵夜,他在众灯中,也是一盏灯了。
文昌阁前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邛崃,在工业化之前,遥接着魏晋鹤林书院古风的新学,除了县中,开办了敬亭中学、蜀才中学、上智中学三家私立学校。
文昌阁原是古城东郊文昌庙的藏经阁,后来改做敬亭学校的藏书楼。30年代初,任洪渊的父亲还是四川大学学生。因在成都参加学潮、工运、罢市等地下活动被捕,幸赖张志和将军多次营救。被四川大学开除后,任洪渊的父亲到张志和将军创办的敬亭学校,以图书管理员的身份避居藏书楼。那一年,任洪渊的母亲(听说,她是当时的平落镇花——虽然他没有看见过母亲美丽的少女时代)还是敬亭女生。
若干年后,任洪渊也来到了文昌阁前。
蜀才小学是邛崃第一名校,实行成绩等级制:第一名承袭班主席。任洪渊的数学成绩很好,二年级期末算术考试,老师当场为他一个人命题,他突然觉得自己长高了一点。三年级,全校数学比赛,任洪渊在低年级组,总分第一,望着排名榜上的名字,他对自己笑了。没有一个可以报喜的人,他在欢乐的时刻四顾着无人的空旷。
一天傍晚,一个同学跑来叫他,他们偷偷爬上了蜀才中学的俄式钟楼。原来是一间大藏书室,彩色插图的开明版童话在任洪渊的膝上翻开,一页一页翻走了一个一个黄昏。但是,他的钟楼黄昏没有继续太久。
任洪渊回到白沫江东岸乐善桥旁的平落小学,读完了五、六年级。河岸,就在学校颓倒的墙外,黄角树绿荫下的白鹅卵石河滩,和跨河的赭红砂石大桥,也就成了他和同伴们的第二校园。
任洪渊不知怎么就开始在同学间讲起故事了,讲他在城隍庙前集市上、在新公园露天茶馆里站着听来的几剑几侠几义,讲完了,接着讲他自己演义的几剑几侠几义,一直讲到无穷剑无尽侠无限义。也讲《火烧红莲寺》,火烧成烟了,成灰了,就随便火烧什么,一场烧过一场。
他的故事也哗动了新兴街街邻老少的听兴,他们散坐在夏夜的凉风下听,挤坐在冬夜的篝火边听。
1950年夏天,他报考敬亭中学,仿佛是去应约。他走过几十里山路,走进古城东郊的敬亭校园。当时的人们叫敬亭花园。敬亭花园无墙,一条柳枝垂岸的未名小河流过校园,建筑师开渠引河水环绕四周,像装点一样,开放的栏杆和绿色的灌木围列在渠边,使整座花园向四面敞开。敬亭学校的创办人和他的建筑师居然能够在这座欧洲贵族庄园风格的校园,保持着中国周代官学辟雍带水环水的传统。
文昌阁在校河南岸,是一座塔形的三层红石青砖楼阁。12岁的任洪渊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走到文昌阁前,只不过他从小听来的飘忽的词语里,文昌阁,就像是一个意义不明的暗示,又像是一个走不进的久远的传说。
从解放军开进平落收编胡宗南残部那一天,任洪渊就一次又一次到台子坝看大戏台上的通告通令——他暗想在一个司令员的名字上找到传说中的英雄父亲。不过,像他失落在台子坝一样,他也失望在文昌阁下。
考试前夕,任洪渊在教学楼二楼大厅的乒乓台桌上无思无梦地睡了一晚。第二天,考试,交卷,出场。在校园的花木间,考生们在等待中乱步彷徨。张开阳校长派人叫任洪渊去面试。他看着书法家开阳先生提起毛笔在他的卷面上写了一个“A”字。发榜了,排列着长长名单的横幅长卷,张贴在文昌阁二层的墙壁上,他第一名。
清苦的中学生伙食也要每月交两斗米钱,一斗当主食,一斗换菜蔬。只有找闵老幺了——老幺,是祖父辈的称呼。但是8月,新谷还没有入仓,而且土改前二五减租的布告已经贴出来了。12岁,他站在街旁,一边一字一字细读告示,一边作数学的现实乘除:6亩,小土地出租,6×2.5……他满腹政治经济学,走进了一片水田间的闵老幺田家。不等他的加减实演,中年的种田人已经笑着一再点头。第二天,在台子坝粮市上,闵老幺把一担谷钱交到他手上,转身——又是一个背影。因为这个背影,他永远记着了他,记着了那一身风霜里的阳光。
第一学期快要过去了,到初冬的一个下午,任洪渊不知道为什么在校门口徘徊,突然收到了父亲从汉口寄到平落镇查询的信。信封上写着他的乳名——父亲在狱中为初生的儿子起的乳名,用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再结构一个祈愿字,听起来像是一声祝语。他流着眼泪,给父亲写了一封附带地址的信。后来,他的第二位母亲告诉他,他的父亲也是流着眼泪读完了信。自然没有人保存他12岁的手稿,一封消失的信,正好是他的一段故意留白的叙述。
在敬亭一年,任洪渊同样没有走进文昌阁一步。文昌阁始终是紧闭着的窗和深锁着的门,藏经、藏书,也藏着他没有文字的秘密。
1951年5月,他离别文昌阁,离别邛崃。
在长江和汉水相汇的地方
出夔门,在长江汇洞庭汇汉水的地方,登陆艇改装的客轮停靠江汉关码头,任洪渊父亲的警卫员接他和祖母上岸。13岁,他朝父亲和新母亲走去。
就在沿江大道上,祖母叫他给新母亲跪下磕头,一下、两下、三下。那是祖母唯一的一个命令句。40年过去,在这位母亲的追悼会后,他一下扑地,长跪在她的遗体前。她有4个亲生的儿女,也给了他母亲的爱。
任洪渊却一直没有能够走近父亲。父亲从来没有问过一句,他是怎样长大的。对他成绩单上印满的数学物理化学语文5分、加印的“优秀学生”红色铅字,父亲不过浏览一下。父亲自然不会知道他在实验中学的“数学家”名声了。经历了13年的英雄想象和期待,他心目中的父亲,却依然空位,近在身边的陌生和疏远让他害怕。
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任洪渊一遍又一遍笔录父亲的申诉,也就一遍又一遍倾听父亲的口述历史,他在父亲的历史中找到的是一位历史的父亲。他的父亲没有改变历史的一行字,历史的每一行字却都改变了他的父亲——
1928年,父亲在邛崃、蒲江、大邑三县联合中学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在邛崃被捕也被学校开除。
1930年,在四川大学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同年在成都被捕也被川大开除。
从1930年到1938年,多次被捕入狱。
1938年出狱,卖掉一部分家产作路费,只身带着一张重庆《新华日报》北上。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董老接见,随即被派往太行山根据地。
1941年,在延安中央高级党校第一期马列学院,始终走在同代的前卫者之列。
1980年,中央组织部和湖北省委作出审查结论:在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两个战场上的功绩被党肯定,党龄从1928年加入青年团开始,名字记载红军史册上。
父亲的余年,在手抄《毛泽东选集》中度过,一笔魏碑风骨的行书。从白沫江走到黑龙江,再回到长江。终年,埋骨在长江南岸,武昌东湖畔九峰山烈士陵园。
任洪渊为父亲写的碑铭比无字碑多了几个字:白沫江——黑龙江——长江。
1951年8月,任洪渊插班考进武昌实验中学。
校园在蛇山东麓,凤凰岭下缓缓斜落的北坡,近临江畔。在前工业年月,夜读时,静静的书桌边可以听到江声和隔江的江汉关钟声。校门前,只有那座全木结构的牌坊,和牌坊上重笔的“惟楚有材”颜体遗墨。从蜀才到楚材,他走到了牌坊下,而他一直没有完成一次才与材字体的离、合和字义的重组。
任洪渊中学生活的封面肖像,是数学家陈化贞先生(后来武汉师范学院建院,陈化贞先生是数学系建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主页是数学。二年级代数,由陈化贞先生开课。到9月,武汉还在火季中。陈化贞先生乘坐私家三轮车到学校,走进教室,一身中式绸夏装,对襟短袖上衣和过膝的短裤,白底浅蓝色细条纹,白色长袜,棕黄色凉皮鞋,银色的怀表链小数点一样一明一灭地在前襟跳动着。陈化贞先生站在讲桌旁,那双在镜片后的眼睛仿佛从远处注视着他,而且,从此天天注视着他,以至他的中学生活,也好像就是对那双眼睛的回答。
部颁的苏联代数教材,课本和习题本各一册,习题本比课本厚三倍。陈化贞先生的课后作业,不是从第几题到第几题,而是从第几页到第几页。一学期过去,班上渐渐形成了一种代数秩序:由任洪渊风一样列出方程,几个运数快手分别演算,最后答案共享。于是,陈化贞先生每次讲新课例题,都把任洪渊叫到黑板前,而他也每次解题如仪。于是,在一次课堂讲评时,陈化贞先生戏剧化地宣布,他可以不交代数作业了。
不知道最早是从哪个同学的口中传出:任洪渊是陈化贞先生特准不交作业的学生!成为新闻人物的感觉那么好,其他年级的同学们在他的前前后后指点着,交换着含义闪烁的手语、耳语、目语,还连着惊叹,连着女生脸上浅浅的笑意。从此,不管是自我肯定中的群体认同,还是群体认同中的自我肯定,任洪渊开始在数学中寻找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汽笛声响起,又一班渡轮从朝阳门码头离岸了,任洪渊还徘徊在黄鹤楼前。长江渐渐流过暮色,流进夜色。除了江声,一切都隐隐地沉没了,只有浪击浪的江涛声。在江上,他也有过一次轻舟放浪。两个汉口同学邀他坐小划子过江,他们说,风低、浪小,敢在江间弄舟的船夫们都有踏波行走的水性,我们为什么不随波漂流一回?10人满载,小舟被抛进了波浪。在岸边望江,水平一线,直到水天一线,现在,小舟边的浪花扑面,任洪渊在见水而不见岸的浩瀚里,只好故作神游,任凭波与波间起、伏,浪与浪下沉、浮。
他后来在江畔猜想,所谓古云梦泽,大概是长江的一场少年期泛滥吧。云的一半,早已滴落成巫山雨,滴湿过宋玉的青春,滴湿了宋玉高唐的朝朝暮暮,滴尽了——虽然他多次船进巫峡船出巫峡,也不再有那么一滴,两滴,滴落在他的舷边。
梦剩下的一半,应该是浩淼的洞庭沉思,容得下长江漫长漫长的回忆,排开龟山蛇山,排开天门,排浪千里——当太平洋的早潮涌入吴淞口,涌过京山,江海平岸,那可能就是他江潮与海潮满潮的中年。
吴淞口外,一水天涯。
两艘建设长江大桥的钻探船,泊在江心的波涛间。每一次过江,任洪渊都要读一遍船上白天漫展的旗语,或者夜晚摇荡的灯语。
升学前,听校长的动员报告,主题是号召报考中等师范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结束报告的召唤句是:青年团员应该站在第一线。作为团支部宣传委员,任洪渊填写了第一志愿: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
此后,他便在汉水边停留了三年。在这里,任洪渊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的《白夜》。白夜,北极圈的极地白夜,那迷茫在日色与月色之间的既是曙色又是暮色的白夜,也就是他青年早期的天色。
1956,中国大学新生专列
1956年,从8月25日到9月5日,中国大学新生专列纵横在几万公里的铁路上,北上,南下,东行,西去。
任洪渊坐在汉口—北京的专列上。
1955年,号召“向科学进军”。在湖滨师范校园,一位考取科学院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的老师和一位考取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的老师,成了他们一代人眼中另一类当代英雄。在工、农、兵为主语的话语年代,硕士、博士,这些重新出现的历史名词将带来什么,改变什么?
1956年,大学扩大招生——扩大到大学招生数大于高中毕业生数。动员青年干部、青年军官报考大学,准许应届中等师范毕业生报考师范院校。
高考报名志愿表也送到了湖滨校园。任洪渊对那么多大学的物理系、数学系,投去怅惘的一瞥,仅仅填写了第一志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好像哪怕只有一个名额也是为他预备的。不知道是出于谁的诗意,考生在交志愿表的时候,要交一个装录取通知的信封,自己写上姓名、地址,贴上邮票。他寻找到一枚青藏公路通车纪念邮票,画面尽现蓝天、雪峰、攀越世界屋脊的路。一枚他个人意义上的稀世珍藏。
7月的武昌考场是真实的火线。临场,任洪渊不得不在握笔的右手腕下垫着手帕,以免汗染卷面。一路畅行。他果然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启程了。在汉口—北京的专列上,任洪渊和一个北京大学数学系新生、湖北省高中数学竞赛第二名同车厢。他们交谈起来。未来的数学家告诉未来的文学家,他其实应该是第一名,因为评卷的数学家们算错了成绩,已经复查证实。一场记错了比分的数学竞赛和一个险些被加减法灭掉的数学家。他们大笑,笑声压低了车轮声。接着,未来的数学家对未来的文学家讲他的文学,未来的文学家对未来的数学家讲他的数学。他们的谈话,仿佛不是初遇时的期许和向往,而是分离前的回眸和别语。是的,他们,一个不过是在数学系门口告别他的少年文学,另一个也不过是在中文系门口告别他的少年数学。
9月1日,前门车站广场被数十面大学校旗翻卷摇动着。那是一次中国式的成年庆典,一代人的集合和出发。任洪渊朝一面选定的校旗走去。他有过自己的旗帜,有过旗帜下飘展的年华,旗上飘渺的明天与远方。师大仍然是那座几乎与世纪同年的“京师大学堂”的一部分。即使在半旷野的新校址,它那生命气息一样跃动的人文氛围依旧。因为“五四”后的人依旧,师与生依旧。
走进1956年的师大,任洪渊的第一堂古典文学课,在文史楼101阶梯教室。李长之先生,瘦削的身材上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夹着几卷书,迈着卡通人物的脚步,走到讲台上。长之先生开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叫李长之——就是那个在20岁的时候写《鲁迅批判》的人。这里,长之先生的“批判”用的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经典本意。

1994年,任洪渊全家福
晚秋的一个下午,是青年语音学家俞敏教授的语音课。101教室早早满座。几分钟过后,俞敏教授疾步跑进教室跑上讲台。一身秋装,黑皮夹克,黄卡其马裤,半高筒黑皮靴,麦克阿瑟式的黑色大烟斗和咖啡色贝雷帽。从国家语委普通话标准音会议上赶回来,迟到了,俞敏说着歉词。
9月15日,在数学楼和物理楼之间的小广场举行开学典礼。楼前的梧桐树还没有成荫。数学楼口的平台是主席台,同学们席地坐在裸露着沙土的广场上。
苏联专家顾问团到主席台就座,他们是来自列宁格勒师范学院的教育学家和教授们。
陈垣校长致词,历史学家开口如下笔一样地述往事。银髯陈垣在叙述青年陈垣:为了到几十里路外的一家庄园抄写清版二十四史,天天背着竹篓,提着灯笼,晨出,夜归;午餐编年史般重复着两个馒头,在偏远的山间田间,不管是星月夜的灯笼路还是风雨夜的灯笼路,都不是一种浪漫。二十四史是多么长啊——一语结束,陈垣老人和历史一齐笑了。
随后,任洪渊作为新生代表走到麦克风前。站着,满眼是北京9月的蓝和清丽,好像在静听远方许多演讲的回响。发言稿在衣袋里,把姿势、情态、语调都留给那些扮演他人的人们吧,此时此地,是18岁的他要说出的,他的同龄人要说出的。18岁,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开始了什么?鲁迅开始了什么?18岁,我们又从这里开始什么?……不知道是他在问台下的无数眼睛,还是台下的无数眼睛在问他。广场上涌起的掌声中断了他。
如今,18岁的演讲,已化作一曲历史的回声……
“迟到的诗人”
他是一个错过了年代也错过了年龄的“迟到的诗人”。1979年,任洪渊的名字才挤在几个朦胧诗人不朦胧的名字间,出现在《诗刊》上。也许从公开发表的诗龄上,他与他们同代,甚至同龄。他也曾有过不被遮蔽的出场:1979年早春,在《诗刊》虎坊桥编辑部门口,展示着两幅诗牌:一侧,是舒婷的《致橡树》;一侧,是任洪渊的《清明祭》,那时的青年画家王怀庆题图,一座由多组祭悼仪式拼贴的碑体浮雕。年末,主编严辰在编辑部会见“青年”诗人,任洪渊不无尴尬地坐在他们中最小的一个——顾城的旁边,身份不明地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的首场预演。如果没有严辰会见,他可能“冒龄”出席青春诗会了。
几年后,传来了台湾《创世纪·大陆朦胧诗专号》,任洪渊竟直接跻身在朦胧诗群里,时空又一次把远离的朦胧暗转成隔海的暧昧。需要声明吗?——又向谁声明“我不是青年”?他只好请朋友们原谅他这不是出于预谋的乱真。既然来自假面年月的人们都在换妆,他也没有什么理由藏老。何况今天流行的装嫩,又还不是昨天的风尚。
第一次坐到顾城旁边,任洪渊自语:“还能够与太平洋早潮般涌来的20岁一同开始吗?我是不能被淹没的。”朦胧诗潮澎湃的时候,他早已在自己的源流中。他选择“在他们附近”,因为“他们做了本该由我们这一代人做而没有做、不敢做的事情。他们走出了50-60年代中国‘学院’的高墙,在上山下乡的旷野读禁书,中国的和外国的,古典的和现代的……是他们延续了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并且,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回声才没有因为穆旦们的沉默而成绝响”。“在附近”,给了他距离,和距离后面的视野。任洪渊有了一个与诗潮中人同样远近的位置,他从这里开始。
1981年冬,评论家吴思敬设家宴,由此,江河、顾城和任洪渊有过一次小庭院的炉边诗会。他和江河初见,和顾城第二次坐在一起。炉边夜话后,一见面,江河就对任洪渊复述《太阳和它的反光》梦中得来的奇句,他也对江河复述《女娲》还未成形的“腹句”。他们是两个互相聆听诗歌“胎语”的诗人朋友——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只有一个江河这样的朋友。
1987年仲夏,在师大校园内的新居里,任洪渊等人为顾城和谢烨的远别饯行。送别,是在夏日的夜雨中,他对顾城和谢烨的回忆,最后停在他们穿雨走去的路上。对于任洪渊,这个雨夜永远遮断了他们前面新西兰激流岛的悲剧。
他们,30后40后的一代,是在1957年突来的风雨中过早离散的一代。离散了,不必说什么七子、八贤,什么林下啸傲的狂与狷,就连19世纪俄罗斯三四十年代赫尔岑小组别林斯基小组的少年梦语与誓言,他们也不曾有过。
文学的新时期毕竟开始了。他们虽然还没有迟暮,却也只能流连自己匆匆的晚春。他们——刘再复、施光南和任洪渊——美学、音乐和诗,不知道谁在呼唤谁,那么迟来、那么偶然地初逢。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三个除夕夜,他们相聚在刘再复建国门近旁的陋室里。长夜在刘再复《人物性格组合论》的构想中,施光南《海韵组曲》的旋律中,任洪渊《1966—1976组诗》火后残篇的余响中过去了,直到建国门断城上的晨曦映照他们的眼睛。他们在同一个太阳下笑了,哪怕此生只有这三个夜晚,三个早晨。
该为《人物性格组合论》撰写总论了,刘再复回顾世界文学半个世纪的现代演变。任洪渊为刘再复写了一段读劳伦斯手记,镶嵌在总论的一节,像一种装饰。那是他们暮春芸花的记忆,假如他们自己不忘却。
任洪渊也在施光南的钢琴旁低声念过他的一些断章,施光南的手指也或徐或疾一遍一遍敲击键盘。任洪渊知道,某一天,他的诗会碰响某位音乐家的和音与不协和音,照亮某一位画家的光与色,洞开某位雕塑家造型的空间与负空间。
1983年,任洪渊重回师大,像是放逐后归来。55级学长,第一代博士生导师童庆炳,到白广路他暂居的斗室探望。这是他与同代人少有的重逢。
1985年,童庆炳写出长篇《任洪渊论》,一万五千字,刊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据说,当年的校长王梓坤院士一看标题,竟以为这位大文艺理念家在评写某位古人。他的回应,是为童著的一卷文艺理论书补写二则当代文本解读。“北国的五条河,仿佛是五线谱从张承志弹拔的指间流响的五根弦……”也是一条长河,任洪渊的词语与童庆炳的词语,相汇相激,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之交。
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了首届作家硕士研究生班,任洪渊也忝列在汪曾琪等导师后面,与牛汉、谢冕分别指导几位青年诗人。《鲁迅文学院60周年纪念文集》第一卷选录了他的一篇讲稿,那大约就是他离鲁迅最近的距离了。
童门弟子的文艺家周末,让师大校园的一角敞开为世界文学学苑。坐在他们激辩的桌边,任洪渊静静聆听着百年文化思潮起伏的涛声。

任洪渊与女儿合影
任洪渊的文化哲学是同一主题的三重展开:在西方“语言转向”中重新发现汉语;在西方“时间再发现”中回到中国时间;在奥林匹斯众神前回望龙飞凤舞——中华文化原动的生命力。一方面,是对中国神话、《易》以及老子、庄子、惠子的“现代阐释”,另一方面,又同时是对西方从尼采到德里达的现代哲学、从普鲁斯特到米兰·昆德拉的现代文学的再解读,法语、德语、英语、俄语解读之外的“汉语再解读”。
他们,30后40后的一代人,是在世纪思潮的早潮和晚潮间两头失落的一代人,还是将晚潮澎湃为自己第二个早潮的一代人?拍岸的甚至裂岸泛滥的诗潮退潮了,上游冲出重山的喧闹已经汇涌成中游的深沉。当然有淘汰、沉沦、转向甚至逆向,但更多的是沉沙后的沉静和开远,这是源源不断的力。不然,怎么能够长流过广漠的平原并且准备荡开出海口?
回到师大,一个60年代的逃课生居然走上80年代的讲台,而且时时在讲台上布莱希特式自我间离地反问:现代文学教学,莫非就是一种破坏文学的最好方式?任洪渊改变了课堂: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不是发明老师而是发现自己。至少他的讲台不是复制未来博士——教授的流水线,至少从他的讲台下走出了逃离教室、逃离教授、逃离教科书的天才或鬼才,走出了震动诗坛的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诗人群,走出了小说家陈染和剧作家李静。在任洪渊看来,一个走不出作家和诗人的文学院是可疑的。

任洪渊著《女娲的语言》书影
2017年4月3日,在《伊沙诗集》5卷本首发式上,沈浩波主持了“任洪渊—伊沙面对面对话”。
伊沙处处尊称他的“任老师”。伊沙的诗歌语言与任洪渊的诗歌语言如此相异,“请任老师告诉我们,你们,任洪渊和伊沙,到底是怎样的师与生?”沈浩波迎面一问。他也直面回答:“我一直在读伊沙,读伊沙透明的深度,像阳光一样透明的深度。也许唯有自明的阳光才能够敞亮自己的深邃与无际。语言的自明也就是生命的自明。汉语太久远了,至少从唐代,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与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那是汉语诗一代一代嫡传的母语。因为诗,诗人们在道统的禁忌外,礼制的禁锢外,暂时解放了自己的生命也解放了自己的语言。他们生命自由中的自由的汉语。我和伊沙同在汉语诗谪传的母语中,再说一遍,像阳光,如果伊沙是透明的深度,那么任洪渊就是深度的透明。我们的诗歌语言都在哲学开始的地方与哲学终止的地方。这还不够吗?”
80年,任洪渊从几代诗人的身旁走过。一代一代诗人写出了他不能写或者写不出的诗篇,走过来了,他也写出了一代一代诗人不能写或者写不出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