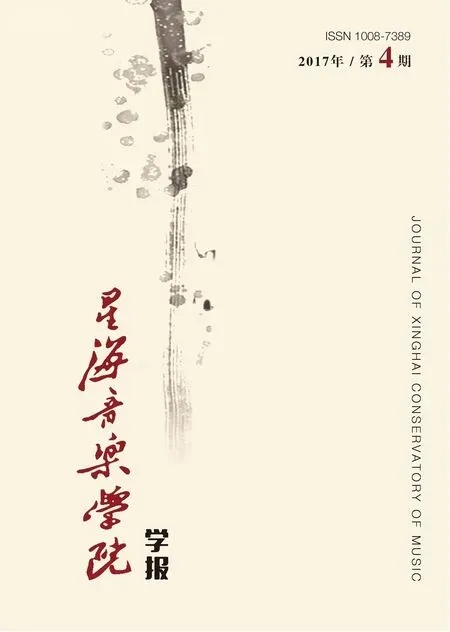施光南旋律思维与我国当代歌剧创作
居其宏
施光南旋律思维与我国当代歌剧创作
居其宏
施光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无论在其歌曲创作还是歌剧创作中,自觉强调线性思维,突出旋律在作品表现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以优美动情、动听动人的旋律语言为时代歌唱、为人民歌唱并获得广大听众的由衷爱戴。施光南的这一创作特点和成功经验,给我国当代歌剧创作以深刻警示和有益启示。
施光南;旋律思维;中国当代歌剧
施光南之所以与聂耳、冼星海一起被冠以“人民音乐家”的称号,除了他在自己的艺术人生和创作观念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通过自己创作的大量优秀音乐作品为时代歌唱、为人民歌唱之外,单从音乐创作上说,无论是他的抒情歌曲还是歌剧创作,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共同点,即根据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音乐审美传统和听觉习惯,在专业音乐创作诸多元素和手段中,自觉强调线性思维,突出旋律在作品表现体系的中心地位,将自己对时代、对生活、对外部世界和人的主观内界之种种情愫、感动和体悟,化为天才的、由衷的、动听动人的旋律语言,令歌唱家们唱来动情动容,广大观众听来过耳成诵,如此口耳相传,心领神会,至今不绝。恰是这一点,给我国当代歌剧创作以有益启示。
一、施光南歌曲创作中的旋律思维
施光南素以歌曲创作闻名于世。在他所有的歌曲作品中,《祝酒歌》《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多情的土地》等,尽管题材不一、风格多样、个性独特,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且极为显豁的特点,就是以独特、优美、如歌的旋律美质打动人心、征服灵魂,叫人过耳不忘,从而成为当代歌曲创作中万众传唱的杰作。
我们高度赞扬施光南歌曲中出众的旋律思维和天赋,并不等于说,这一切都是与生俱来或唾手可得的。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大量事实证明,在施光南短暂的创作生涯中,曾投入巨大热情和浩繁工夫,广泛收集、分析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音乐,深入研究其旋律之美、风格之奇、韵味之妙,把握其规律,体悟其精髓,如此日积月累,一座浩瀚的音调素材库就这样凝聚而成。一俟某个创作课题、某种创作冲动发出激情呼唤,过往那些音调素材积累便跃然而出,活脱脱鸣响于耳际,随后经一番融会贯通,将它们化为自己的语言和血肉,流泻于谱纸,于是,一首旋律优美独特、风格鲜明,听来既熟悉又陌生,明知其音调素材属地却又不能确指其具体来源的著名声乐作品便这样横空出世矣。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长期积累,偶一得之”境界。未经聚沙成塔的艰苦,便无信手拈来的自由。施光南在这个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鉴于此前业内许多同行对施光南歌曲创作有较深广的研究,2017年4月16日,在浙江师范大学举办的“施光南音乐创作与表演学术研讨会”上也有不少学者就此作了精彩发言和深入分析,故本文就点到为止、不再重复,而将论述的重点放在施光南歌剧创作的旋律思维方面。
但有一点必须强调指出,施光南歌曲创作中的旋律思维及其高度成就,为他的歌剧音乐创作奠定了最基本、最重要,也最具艺术闪光的高起点;换言之,施光南歌剧中大量声乐体裁,尤其是咏叹调、抒情短歌、重唱和合唱的旋律写作,从其歌曲创作长期养成的高超旋律锻造功夫中获益良多。因此毋宁说,施光南歌剧中的声乐体裁创作,是对其歌曲中旋律思维和写作的人物对象化定位和戏剧性发展。
二、施光南歌剧创作中的旋律思维
毫无疑问,歌剧音乐的表现体制是一个极为庞大而复杂的立体性、系统性工程,若论作曲家对其驾驭难度,远非一般歌曲作家和歌曲创作所能比拟;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欧美歌剧还是中国歌剧剧场审美的主潮,非但过去是,至今依然是,即便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必然是:以声乐为主、以如歌旋律见长;在歌剧音乐的表现体系中,“旋律第一”的核心地位永远无法摇撼,旋律思维和旋律美质永远是歌剧之声乐歌唱的灵魂,永远是决定一部歌剧音乐之成败得失的首要因素。正是在这一点上,施光南的歌剧音乐创作便充分展现出他那得天独厚的优势。
施光南的歌剧作品仅有1981年首演的《伤逝》和1998年首演的《屈原》两部,数量虽不算多,但在中国歌剧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伤逝》是一部抒情-心理歌剧。施光南在此剧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充分发挥旋律的抒情性特长,用来展现男女主人公曲折的心路历程以及彼此之间细腻深刻的情感冲突。在这里,施光南的旋律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近乎完美的表现。剧中的主题歌《紫藤花》,以及男女主人公的大段咏叹调《风萧瑟》《一抹夕阳》《冬天来了》《秋光,金色的秋光》《不幸的人生》等,它们的情感容量大,变化层次多,在美丽如歌的旋律倾诉中揭示出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戏剧性。
这些特点,在女主人公子君的咏叹调《不幸的人生》中表现得相当典型。
谱例1 《不幸的人生》(片段)

上例是子君咏叹调的返始部分。乐句开始完全再现咏叹调首句的宣叙性旋律,重新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拉回到冰冷的现实之中。不断重复的乐句,在子君寂寞无助中喃喃自语式的悲叹中将情感抒发推向全曲最高点(a2),以强烈音量唱出她内心的绝望与呐喊;进而激情消退,重新归于寂寥无奈的忧伤氛围并结束全曲。
联系到这首咏叹调中段所表现的子君对于往日爱情的温馨回味与追思,作曲家通过两种情绪的强烈对比来揭示人物心理戏剧性的成就和功力颇堪赞许。
与《伤逝》抒情心理室内歌剧的形式不同,《屈原》是一部正歌剧,音乐戏剧性思维的交响性和立体性是施光南的艺术追求,因此其创作难度较之《伤逝》更胜一筹。但两者也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旋律的浓重的歌唱性格和高度声乐化——这是施光南歌剧创作,乃至施光南全部音乐创作最为鲜明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在《屈原》中,不但几个主要人物如屈原、婵娟、南后、山鬼等均采用了不同程度的优美如歌的咏叹调加以刻画,一些重要的合唱(如“招魂”的合唱)、重唱(如屈原与南后、楚王、靳尚、张仪等人的对唱与重唱)分曲也充满了丰富动人的旋律描写。
尤为令人赞叹的是,在山鬼那首著名的花腔《无词歌》中,施光南的旋律天才得到了极为精彩的体现。
谱例2 《无词歌》(片段)

在上例中,独唱声部气息宽广的长音与花唱构成抒情的主旋律,而女低音则分成两个声部,在中高声区以密集的短句和变幻不定的和声与之作对比复调的穿插,形成立体化的综合音响。在女高音独唱声部,如歌的或器乐化的跳荡的音调上下翻飞,旋律线条曲折婉转,充满抒情浪漫的情调;加之它又十分声乐化,使花腔女高音轻灵剔透的歌唱技巧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和发挥,其舞台效果十分强烈,给观众的听觉感受颇为沁人心脾。
因此笔者与著名歌剧理论家刘诗嵘一致认为,施光南这首花腔女高音咏叹调,是我国正歌剧音乐中旋律最为出彩、音乐最为动人的歌剧分曲之一,即便拿它与西方经典歌剧中著名花腔女高音咏叹调(例如莫扎特歌剧《魔笛》中夜后的咏叹调)相比,也毫不逊色。
三、施光南旋律思维对当代中国歌剧创作的启示
中国歌剧在其诞生之初,根据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审美习惯以及对歌唱性旋律的特殊敏感,特别重视旋律在歌剧音乐表现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从早期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延安秧歌剧,到后来正歌剧的崛起和民族歌剧的繁荣,举凡在两次歌剧高潮中涌现出的那些经典剧目、那些经典唱段,无不以优美动人的旋律美质而令广大观众击节赞赏,传唱至今。
同时也必须指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歌剧,特别是正歌剧的音乐创作中,有一种鄙弃旋律的倾向开始抬头且呈逐渐蔓延之势,及至今日,益发普遍而严重,因而不得不察。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将瓦格纳的“乐剧”理论与实践视为圭臬,公开批评刘振球的歌剧《深宫欲海》“廉价地出卖旋律”。*1987年9月21日《人民音乐》组织的“歌剧《原野》《深宫欲海》座谈会”上,刘经树先生的发言。
到了21世纪之后,这种鄙弃旋律的倾向愈演愈烈,其具体表现在:被各种作曲技术武装到牙齿的作曲家们竟然写不出一首旋律动人的咏叹调来,相反,却让各种佶屈聱牙的、冗长沉闷别扭的、既难唱又难听的、洋腔洋调的宣叙性风格充斥全剧,非但与当代中国歌剧观众的听觉审美趣味距离甚远,就连绝大多数专业观众和歌剧同行也如坐针毡,难以卒听。
在这种情况下,施光南的音乐创作,尤其是歌曲和歌剧创作,以及浸透于其中的旋律思维和旋律天才,与当代某些鄙弃旋律的正歌剧相比,非但树立了一个标杆、一座高峰,更是一段艺术传奇、一种深刻警示。施光南用他的歌剧创作证明,凡是鄙弃旋律,也因此脱离大众审美需求的歌剧作曲家及其作品,必被广大观众所鄙弃。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歌剧界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向施光南学习的口号,学习他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学习他坚持在歌剧音乐创作中突出旋律思维的中心地位,学习他极具中国气派和中国风韵的旋律思维和优美动人的歌唱性美质,对中国歌剧的健康发展而言,极为必要且正当其时。
【责任编辑:杨正君】
2017-05-08
居其宏(1943-),男,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10.3969/j.issn.1008-7389.2017.04.008
J609.2
A
1008-7389(2017)04-0069-05
——寒窑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