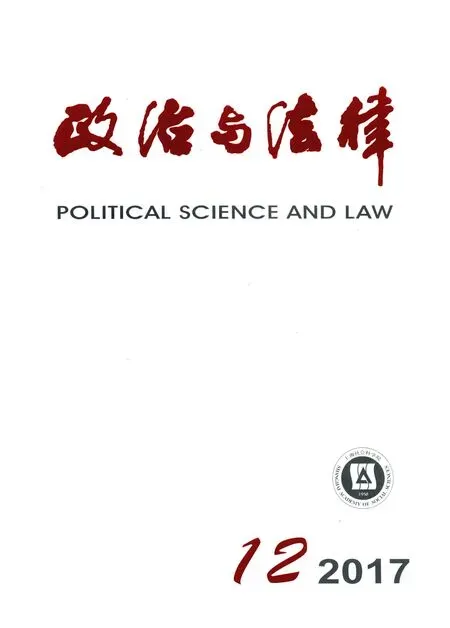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
杨继文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在我国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现实背景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存在规范和事实层面上的各种难题。污染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需要在其因果关系的事实意义基础上,从刑法实体规范、价值立场衡量以及司法程序的证据和证明意义来加以考察。明确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是一种混合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分层证明。它属于法证据学的概念范畴,需要精细的法证据学和诉讼程序的规范指引;需要法官居中进行自由心证裁量并做出裁决;需要在污染环境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找寻相关的证明对象和范围;需要注重证明的立体化背景和技术工具的综合应用与整体判断。它的证明度要求为确定性或者相对确定性,结果要求为证实结果与证伪结果。最终,在污染环境犯罪技术治理的背景下,要求对其因果关系的证明进行扩展。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据;证明;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污染环境犯罪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被“定制”出来的犯罪,随着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各国的刑事政策开始向保护环境的方向逐渐演进,我国近年来也开始重视用刑事手段保护环境。在对环境犯罪予以规制的过程中,其不同于传统犯罪的各个方面逐渐体现,目前学界对污染环境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罪的教义学解释上,但对其在司法实务中如何认定和证明则少有涉及。由于环境污染是一种与技术紧密相关的犯罪,追诉过程中往往涉及复杂的技术鉴定等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知识,因此相比于传统犯罪而言,其在证明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开放性,而目前我国的证明模式是否有提供这种开放性的可能,是本文研究的问题。
二、比较与定位:污染环境犯罪的界定及因果关系的位置
除了环境相关技术手段的更新和适用外,环境保护行为的经济奖励、治理污染的国家投入,以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切实履行将是我国未来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环节和基本内容。其中,对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和综合治理,将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主要抓手。污染环境的违法和犯罪行为,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负效应而产生和形成的,它具有技术性、政策性、间接性以及社会危害性。*参见杨继文:《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环境治理进路研究:理性化、社会化与司法化》,《环境污染与防治》2015年第8期。在环境刑法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存在规范和事实层面上的各种难题。例如,在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或者联系,直接影响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定罪和量刑,最终也会影响环境刑事法科学体系的建立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这就决定了,对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成为环境刑法关键技术环节所在。为了应对这些证明的难题,需要重新审视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因果流程的运行机制,明确对其证明的内涵、外延、特征、属性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等。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从证据学的基本学理来进行应对。对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不能仅从刑事法视角进行解析,而是应当同时借鉴环境行政法、侵权法等相关学科的证明方法理论。
环境刑法一般被认为是通过刑事制裁手段和体系来治理环境犯罪行为,以达到环境保护之最终目的的刑事法律科学。由于“环境”一词的含义界定存在主观性,导致了不同语境中的环境范围、治理体系以及技术内容也有很大不同。*参见杨继文:《环境、伦理与诉讼——从技术到制度的环境司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在德国,为了保护环境和惩治犯罪所为的刑事立法,主要是通过界定和承认环境法益与环境污染危险来源来予以规制的。在其立法中,把环境的概念明确界定为人类、动物以及植物的生活空间。*Wolfgang Schild, Umweltschutz durch Kriminalstrafrecht in: Juristische Blätter, 101(1979), S. 19.转引自郑昆山:《环境刑法之基础理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台北)1998年版,第24页。德国刑法分则不仅明确规定了各种污染环境罪的具体危险犯,而且规定了污染环境罪的各种基本形态的未遂犯。*参见李梁:《中德两国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立法比较研究》,《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这是一种主要以刑法典的修正和完善为方向的环境刑法模式。而在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则是采取了环境刑法的附属模式,以环境犯罪的行政刑法为核心,通过环境行政法等附属刑法的立法方式来应对污染环境犯罪。在日本,则通过《公害罪法》这一单行环境刑法的颁布和实施来对污染环境犯罪进行规制,该法不仅具有环境刑事实体法的属性,还在具体条文中规定了相关污染环境犯罪惩治的程序性规定和证据规则。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即在第5条明确规定了公害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以判例法的非法典化形式,将涉及污染环境的刑事部分、民事部分、实体部分和程序部分等内容有机地结合和相容在法律之中。如英国在1990年颁布并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即是一种系统性的环境综合立法。再如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应当将环境犯(环境违法)的概念与环境(公害)犯罪加以区分。前者系指凡与环境有关之不当或不法行为,得有现行法律规范,或为补(赔)偿、惩处或判决科刑者之谓。就不同法律领域而言,可以将其区分为民事犯(不法侵害)、行政犯以及刑事犯三种。而狭义的环境(公害)犯罪,一般是指人类的各种活动对环境的破坏,需要科以刑罚的严重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包括污染环境类型的环境犯罪,原则上系指触犯现行刑事法律之环境不法行为,以及涉及严重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政不法或民事不法行为,有必要提升为环境刑事不法在内。”*参见前注③,郑昆山书,第25页。
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犯罪之环境刑法,系指界定污染环境犯罪及其法律效果之人类社会生活规范的总和。要明确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证明模式,在做好对环境犯罪的界定之后,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因果关系在犯罪体系中的定位。笔者以新近较为流行的新古典二阶层体系来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成立进行考察(具体结构如图1)。

图1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
三、特性与因素: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独特性
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当然应当以刑法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为背景,但由于环境犯罪具有典型的技术发展和刑事政策交叉作用和选择的痕迹,故又有其独特性。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和根据被规定在刑法规范中的,它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事实意义上的联系,同时也被认为是基于法律的构成要件规定而产生的联系。*参见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是一种一般性的理论抽象和规范评价,需要在具体的各罪适用中,重点考量各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进行类罪和个案意义上的具体把握和分析,使得因果关系的相对性判断与一般性判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地紧密结合起来。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事实意义基础上,还需要从刑法实体规范、价值衡量以及司法程序的证据意义来加以考察,使其真正能够成为客观归责的根据。*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3页。
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损害结果,也许会随着自然规律的因果作用而显著体现出来,但也有可能因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的原因而被掩盖。*[日]野村好弘:《公害·环境の法律》,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99页。因此,污染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其结果性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者选择性,通过怎样的证据制度和证明技术予以固化也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例如,如果被告能够证明没有因果关系,他就能避免承担责任;但在一定情况下,这样的证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如许多年以前,原告的母亲在怀孕期间购买并使用了被告制造的产品。被告怎么去证明不是他的产品给原告造成了有害结果呢?这种类型的责任与下面保险责任很相近,即被告参与了一种活动,可能与许多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而引起了一种有害结果,他对这种有害结果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所以,关于因果关系事项的证明规则事实上是能够转换的,即由责任的因果关系根据而转换成非因果关系根据。当事实不言自明(res ipsa loquitur)学说被认为在一个过失案件中转移了说服责任时,其结果经常是把过错责任转换为严格责任,因为被告根本无法履行这种证明义务。还有,当法院采纳了一种推定,假若被告已经提供了一个安全保护器具,那么被害人就能用它达到好的效果时,这就是要加强一种政策的效果,这种政策事实上使得一种可能性的,而非概率性的因果关系能够足以引起责任。参见[美]H. L. A. 哈特、托尼·奥尼尔:《法律中的因果关系》,张绍谦、孙战国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属于犯罪构成中的客观构成要件之一,心理性的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例如,对于帮助行为之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应采取合法则的条件理论:当帮助行为在实际发生的事件历程中系属必要成分(即若将该行为从整体过程中删除,这个过程的说明就会变得不合理)时,便可肯定条件因果关系的存在。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物理帮助多半含有心理(精神)帮助的成分,但并非所有无效的物理帮助都必然可以转而透过心理帮助成立帮助犯。即便是在心理帮助的类型,帮助行为与主行为之间也必须存有因果关联才能成立帮助既遂犯,因果要求并不会随着帮助形式的不同而有差异。参见蔡圣伟:《论帮助行为之因果关系》,《政大法学评论》(台北)(2013年)第134期。这是因为在一般因果理论的讨论脉络下,当涉及他人内心的决定时,因为人类的意志自由与自然因果法则的必然性互不相容,所以在有人类的心理事实涉入时,就无法建立自然法则下的因果关系。这个问题其实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中就已经被提出:如果采取前置模式,法律适用者就必须说明自行陷入酩酊状态的前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间如何具有因果关系,此处会遇到的难题便是,没有一个自然法则可以告诉我们,行为人若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就不会犯该罪行。*参见上注,蔡圣伟文。
污染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其主要体现在行为上的综合性、时间上的潜伏性、空间上的扩散性以及结果上的复杂性。在行为意义上,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可能是一人或一个企业所为,但大多数则是多个主体或多个行为综合作用下导致的损害结果。例如,在日本大东铁丝有限公司盐酸毒气喷出案中,负责给公司运送硫酸的驾驶员松本一郎(化名)在灌装硫酸时,因疏忽大意,将同处一地、相隔只有1.2米远的亚盐酸苏打储藏罐误作硫酸储藏罐,把自己运来的硫酸直接注入其中,经过化学反应形成了320千克的盐酸毒气。这些毒气在内部压力作用下,冲开封口并迅速扩散至工厂附近的大气中。再加上当时风力的作用,导致该毒气影响的面积达到16000平方米。在附近生活和工作的居民,不同程度地突患急性呼吸道疾病、皮肤病、眼病等,大多数人需要住院治疗3日至139日不等。*参见冷罗生:《日本公害诉讼理论与案例剖析》,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2-373页。再如,在“上海垃圾跨省倾倒案”中,多名行为人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综合性,既有组织者,又有具体实施者,既有内部人员参与,又有被雇佣者的实施。他们将塑料袋、塑料瓶、编织袋、海绵块、泡沫盒等各种生活垃圾34000余吨,从上海运到江苏省苏州市,其中掺杂着大量建筑垃圾,混在回填土方之中,倾倒在其村委会承包的一个现代农业物流园内,造成垃圾场东侧断头浜小河因垃圾场渗滤液的污染而造成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高于吴淞江,且检出毒性物质挥发酚,其中垃圾场南侧小沟渗滤液检出镉、铜、铅等重金属。*参见马超、耿莉:《江苏一审宣判“上海垃圾跨省倾倒案”》,《法制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8版。在时间意义上,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损害结果往往具有一定时间上的潜伏性和滞后性,有的污染环境损害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而且这一时间过程不仅具有潜伏性,还有发生学意义上的叠加效应,损害的结果与污染行为往往难以清晰地认定和回溯。例如,在日本水俣污染公害案例中,首位患者是在昭和31年4月发现的一位5岁大的女孩,她表现出说话困难、行走困难以及狂躁不安等神经性症状。在此之前的昭和29年,其实就已经发现一名叫滨元二德的患者表现出手、嘴发抖、麻痹等症状。这种污染环境的公害行为,肯定不是突发状况。早在大正14、15年的时候,当地就已经发生了污染渔业的损害结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地的“氮肥厂”的污染环境行为。此外,空间意义上的循环影响及结果的不确定性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对污染环境犯罪法律上因果关系认定的复杂性。
除了上述事实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在刑事实体法和证据法的适用方面,还有一些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被重点证明的基础因素或者其他相关因素。它们的内容主要包括: “无之则不然”的条件或者原因;预见可能性;间接性;盖然性;充分性;常识以及(或者)政策考量;合理性;直接性;时间上的临近程度;近因;两方过错程度的比例性;行为所违反的规范的保护目的,等等(参见图2)。这些因素在因果关系的证明中如何系统性地得到考量,是此类犯罪区别于传统犯罪认定的重要体现。

图2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相关因素
同时,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具有依附性特征。也就是说,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司法审视,基本都需要相关的环境行政决定和环境侵权认定或鉴定意见,而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结果——“严重污染环境”,则往往需要通过环境科学和环境法的相关原理和制度进行辨别和处理,因此,污染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除了要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犯罪事实之间,跳跃于证据体系与证明技术之间,还应当坚持体系性、大证据学的思维方式,注重刑法与程序法、环境法、行政法及证据法的协调。*参见苏永生:《论污染环境罪的附属性》,《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四、理论与方法: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具体证明
(一)理论路径: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适当证明
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在我国刑事政策转向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之前,对污染行为导致损害结果的因果流程认定往往采纳严格证明的模式。这种因果流程的证明,因为前述污染环境行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实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因而对此类案件的认定往往不能定罪量刑,在能确定成立污染环境犯罪的案件中,实务部门的认定又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对于如何予以证明、采取何种证明理论予以证明缺乏一致性和充分的说理。在我国频繁修改污染环境犯罪相关规定,释放出以刑法加强环境保护的政治信息以来,实务部门则转向了运动式的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倾向,污染环境犯罪的数量激增,量刑整体趋严。在这种形势下,出于效率的考虑,实务部门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可能又比较隐蔽地采纳了自由证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知情权及异议权。
如前所述,与传统犯罪不同,污染环境犯罪具有更多的技术性,其证明的过程需要更多的开放性,这对侦查部门、检察部门和审判部门都是一种挑战,可以说对污染环境犯罪的追诉,实务部门的垄断性地位受到了一定的挑战,而更多地介入了如何对待专业鉴定、如何对待辩方的异议权等因素。污染环境犯罪的追诉将不仅仅是防卫社会功能的发挥,其可能还包含了如何恢复被破坏的法益等制度目的,因此控辩双方的责任分配和对抗程度都有独特性。这种特殊性从刑事政策的导向出发,在技术维度会当然延伸到证明模式的选择上。
依据证明力强弱程度,理论界一般将证明分为严格的证明和自由的证明。在通常的意义上,严格的证明主要是指用以证明犯罪而提交法庭的证据资料必须具有证据能力,且经过合法的证据调查程序,始得作为判断犯罪事实的依据。有了证据能力的证据,才会有法官评价证据之证明力的问题。与严格证明相对应的为自由证明,它是指无须使用具有证据能力之证据,并且证据不受限于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即可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从适用范围来看,严格证明主要适用于审判程序中,主要针对的是案件的实体事项和事实问题,如犯罪事实的有无,它的心证程度一般需要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确信”;而自由证明的适用范围主要在于审判程序之外的程序性事项,如法官的回避问题、起诉审查以及刑求抗辩等。*参见陈宏毅、林朝霞:《刑事诉讼法新理论与实务》,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15年版,第229-230页。随着我国证据法研究热潮的兴起,我国学者以大陆法系的证据法理论为借鉴,对刑事诉讼中的两种证明形式即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在这两种证明方式中,基于对我国证据规则体系存在很大欠缺 、证据调查程序亟待规范的考虑,学者们普遍偏重于对严格证明的探讨,而对自由证明着墨不多。这种对严格证明的倾向对污染环境犯罪这种关涉较多政策性、技术性的新型犯罪来说,往往牺牲了追诉活动的效率期待。对于自由证明的概念,基于对我国实务中证明的一定程度上的不规范性的反对,我国学者们往往有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的论断,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划分标准也过于简单化,这种研究的倾向性和不充分性给人一种印象,即自由证明仿佛是毫无限度、完全自由的证明方式,无需受任何限制。这种简单的研究模式则断绝了新型犯罪证明模式的更多选择,也忽视了自由证明理论自身的发展空间。
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理论的发展来看,自由证明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在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随着诉讼制度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化,不断扩大了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的范围,加强了对证据资格和证据调查方法的限制,诉讼证明普遍严格化。在自由证明的证据调查程序方面,一般也要求通过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并给予当事人争辩的机会,而不能由法官私下形成心证。作为推崇机能主义刑事法学的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教授从程序的特殊性出发,在这两种证明属性之间创设了另一种被称之为“适当证明”的概念。也就是说,他认为在传统的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之间的缝隙中,存在一种适当证明的理论和实践,其目的是充分强调对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尤其是他们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异议权。笔者认为,从适当证明的本质来看,它应当可以被划归为自由证明的范畴。这是因为,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划分标准来看,是能够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类的。严格证明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和完整的理论解释,而自由证明从对立的反面来说并不具备这样的要求。因此,不是严格证明的证明,就是自由证明。*参见康怀宇:《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具体运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适当证明本质上属于谨慎的自由证明,它的提出是为了更广泛的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抗辩权。故笔者将在发展的自由证明的概念基础上使用适当证明的概念,将适当证明等同于谨慎的自由证明。
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解释来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内涵和适用范围,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和第53条中规定了证据能力的审查认定标准——“查证属实”,并且需要进一步考虑所要证明的事实类型和它对于案件认定的争议程度等,因而可以被理解为严格证明方式在我国刑事法中的体现。*参见闵春雷:《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新探》,《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闫晶、万旭:《查证属实:严格证明法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规范表述》,《福建警察学院学院》2016年第2期。也就是说在我国,如前所述(图1),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系犯罪构成中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要素,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被重点地和严格地进行把握,相关证据材料在通过严格证明法则证明的过程中,需要被检验是否是证据条件所要求的证据,从而判断是否具有相应的证据能力。也就是说,犯罪事实主要是指待证事实中的主要事实,不需要认定的其他剩余事实一般无需证据进行证明。也就是说,除依法无需证明为必要者外(如公知事实),凡欲认定事实,皆需依据证据来进行证明;需要注意的是,重要的在于是否适用前述的严格证明,单纯从我国的法律表述来看,这种证明应该是严格证明。
从前述具体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因果流程运行视角来看,即从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到具体的因果流程,再从具体的因果流程到污染环境的损害结果,两次转化之间存在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间的“证明全等性”问题。这种“全等性”强调的是转化为相同的素材进行比较,将事实意义上的行为和结果转化为法律规范和概念,或者将法律规范和概念转化为行为事实和结果事实等。也就是说,在污染环境犯罪刑事规制的过程中,事实与规范之间在实然的意义上应该存在全等的关系。从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构成要素和证明属性来看,它的认定过程既包含严格证明,又包含自由证明,需分层分类证明。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事实认定,在待证事实的部分属于重要的和主要的部分,尤其与国家的刑罚权以及被告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因此需要经由严格证明方能予以认定。同时,由于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中的因果流程具有复杂性、技术性、综合性、潜伏性和扩散性等事实特性,需要在刑事诉讼的证明过程中进行区别对待,即需要借鉴环境法、行政法相关规定和因果流程理论,适当降低证明标准,从而使其具有区别于严格证明的自由证明的属性和品格,即谨慎的自由证明。

图3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适当证明
另外,从所要证明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本体视角来看,作为污染环境犯罪构成要件主要内容的污染环境行为(如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排放”、“倾倒”、“处置”等行为)和污染环境结果(如201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结果标准)需要采用严格证明的方式来进行证明。作为具体案件中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流程,应当采用谨慎的自由证明即适当证明的方式来进行。这也契合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事项均应采用自由证明的基本法理。例如,在持有型犯罪中,在保证诉讼公平和公正的情况下,由被告人承担适当的证明责任,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和正义的尽早实现。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过程中,被告人基于一些只有自己了解的因果流程事实进行辩护或提出主张的,也应当允许其进行自由证明。也就是说,系对于犯罪事实予以否认而由被告所提出之异议,不必限于有证据能力且经过适法有效之证据调查之证据,而可使用无法定证据能力或证据调查不受严格限制之证据,这种反转也将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蔡墩铭、朱石炎编:《刑事诉讼法》,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1年版,第87页。转引自罗海敏:《刑事诉讼严格证明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
综上所述,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相关要素的证明同时存在采纳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因素和环节。作为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要素和因果关系要件的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需要进行严格证明,以保证犯罪追诉的必要性和限缩犯罪构成;而基于对效率的追求和辩方参与权的保障,作为因果关系要件具体表现的因果流程,可以采用审慎的自由证明的方式进行证明。这种证明方式回应了司法实践中的诉讼价值需要和应对证明难题的实践需求,具有相对合理性。
(二)具体治理: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证明方法
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证明的本质是一种诉讼活动,因而属于证据学研究的范畴,需要证据学和诉讼程序的规范指引。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其实就是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对涉及因果关系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相关性的审查和判断。没有相关性的证据是不能被采纳的。在法证据学的运用过程中以及法院认定活动中,相关性问题通常被转化为法官理解的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之证明力问题,这时就进入到了诉讼和证据规范的范畴当中。同时,在司法实践的逻辑推理过程中,相关性也被认为是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和可采性的必要条件。可见,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同时接受诉讼过程中对证据相关性问题的二次规范指引,使得其表达的意思和内涵更加清楚。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将相关性界定为:“证据具有某种倾向,使决定某项在诉讼中待确认的争议事实的存在比没有该项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文版》,百度文库,2017年10月28日访问。有争议的证据是否对事实更有证明力经常成为激烈的争论对象,难以达成一致结果。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明相关性,与一般的推理及逻辑学中的相关性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一般逻辑学中的相关性只是证据能力和可采性的必要条件,在司法逻辑中并不能当然成为证据而被用来作为证明因果关系的事实。因此,判例法对相关性的概念进行了法律改良,无论是否接受对相关性(司法意义上)、实质性和可采性所做的复杂区分,具有逻辑相关性的证据的命运最终还是取决于审判的性质和目的。法官谈到的是“证明力”,而不是相关性。*参见[英]詹妮·麦克埃文:《现代证据法与对抗式程序》,蔡巍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这种证明的主体主要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控诉方和辩护方当事人,同时,法官居中进行自由心证裁量并做出裁决。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过程中,已经具备典型意义上的诉讼对抗及审判的三角形构造。由检察院为代表的公诉一方履行主要的证明责任,通过相关证据以及证明技术来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事实;辩护方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履行证明防御的义务,在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具备特殊情况时实施推定的证明方法,也承担适度的、相对的和置后的证明责任;法院作为最终做出裁决的司法机关,需要履行是否采纳或认可双方当事人的证明主张,并注重对于自由心证的裁量和最终的证明和裁判说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一方面,公诉方与法官由于“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可能存在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协同规制需要,这与检察官的客观证明义务和法官的居中裁判职责存在一定的混同和交织,使得检察官的“客观义务”难以承担起收集对辩护方有利的证据的“义务”。法官等审判人员承担的是居中审理和最终裁判的职责,应当是“裁判”而非运动员,因此,一般不承担收集证据进行证明的责任,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担负某种补充性的证据收集和证明职责。*参见龙宗智:《刑事证明责任制度若干问题新探》,《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无罪推定”的规范支持,导致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主体范围和责任上,由于“如实供述”的司法政策和司法惯性影响而不适当地扩大了,突出地体现在对辩护一方的责任的强化,这违反了刑事诉讼程序中公诉方承担主要证明责任的基本法理。
这种证明的对象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需要在污染环境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找寻相关的证明对象和范围。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对象,主要为涉及这种犯罪因果关系的各个基础要素和三大构成要素,即如图1和图2所示的各种要素。在污染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证明问题中,作为证明对象的要件主要是刑法规范中的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且在这里要强调犯罪成立事实的证明价值和意义,它决定着犯罪的成立与否,是量刑事实及其证明的前提和基础。*犯罪成立有实体法的要求,同样也有程序法的要求,所以要证明犯罪的成立,需要证明实体法事实,也需要证明程序法事实。而从刑事实体法的观念看,犯罪成立事实和量刑事实虽然都十分重要,但犯罪成立事实更具基础性。这是因为,犯罪成立是量刑的基础,如果行为不构成犯罪,自然不存在量刑的问题;而且,犯罪成立后罪名的确定对于与之对应的刑罚的运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参见赖早兴:《证据法视野中的犯罪构成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由于我国实体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将污染环境罪的构成界定为“行为+结果”的模式,因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证明过程中,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并不能截然地分离,在大多数情况下,量刑事实会随着定罪事实的证明进程而逐步明晰。正如前文所述,案件事实的证明需要在法律规范的指引下探寻事实与证据之间的相关性。因此,这种证明的对象必须回归到刑法具体罪名和案件的具体构成条件中去,而具体个案中的因果流程则可能依据污染环境犯罪行政刑法之属性而通过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规定和方法来认定。也就是说,证明的对象是涉及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各种行为标准、因果流程认定标准和结果标准。
在这种证明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方面,需要注重的是证明的立体化背景和技术工具的综合应用及其整体判断。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对大量的混合的证据材料和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分门别类地证明,而且在因果关系这一主题下“立体式地”投射到案件中已经发生的行为或结果上,并进行“整体主义”的思考,这项任务包括证明工具的综合应用和证明的立体化思考,即这种任务依赖于对所能获得的每项证据加以分析,依赖于对其加以分门别类并将每一项因素置于证明方案的恰当位置,还依赖于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进行的详细推论,最终就主要的待证事实获得一个结论。*[英]威廉·特文宁:《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莫尔》,吴洪淇、杜国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例如,在大陆法系国家,典型的程序性特征表现在作为事实认定者的法官在证据材料被提交后,才重点考量证据所包含信息的推理效力。而且在评估和衡量的过程中,他们需要综合地考虑这些证据材料和信息的证明价值以及它们的可靠性等问题。因此,对于这种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路径和方法,法官们会自觉地从证据载体和信息本身的角度进行立体化审视,侧重的是对行为举止证据的本能反应和包括其在内的整体判断。*参见[美]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这种证明的证明度要求为相对确定性,依据不同的因果关系要素而有所区别。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由于因果关系要素的特性导致其适用的证明程度要求存在差别,适用的结果接近于证明度的相对确定性。例如,在台湾桃园地方法院的一个判决中指出:“惟于公害诉讼案件,因公害之形成原具有不特定性、地域性、共同性、持续性与技术性之关系,其肇害因素常属不确定,损害之发生复多经综合各种肇害源而凑合累积而成,当事人举证甚为困难,若要求控诉方与一般侵权行为诉讼就行为与损害之因果关系为相同程度之确定证明,就衡平原则而言,并不适当。如依情况证据之累积,就与关系诸科学的关联,能为无矛盾地加以说明,即应认为已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之证明。换言之,控诉方对于因果关系存在与否之举证,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严密科学检验,只要达到相对确定性的盖然性举证即足,即只要有‘如无该行为,即不致发生此结果’之某种程度盖然性或确定性即可。”*姜世明:《举证责任与证明度》,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8年版,第387-388页。
这种证明的结果为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也就是因果关系证明的证实结果与证伪结果。一般认为,证明机制的结果主要存在于针对所有证据和事实的综合判断之中。当通过证据进行证明所得到的事实与社会常识等经验法则发生或可能发生抵触时,就需要人们采取行动去辨别这种事实与证据之间的关系的真伪,或者说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因此,对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明确的最终结果是寻找真理和避免错误,即所谓的证实和证伪。*Larry Laudan, Truth, Error, and Criminal Law: An Essay in Legal Episte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17.具体来说,证实的结果即证明的建立,是基于存在的事实而达到的对案件事实认识的满意程度。在司法实践中,向法庭起诉的条件需要首先确定这个事实,但是在具体的审判程序运作过程中,这个事实可能并不能达到证实所需要的满意度适用标准即所谓完美证据。这时就需要相关的证明规则进行“可能性平衡”或者“合理的怀疑”。而证据作为证明的一种手段或载体,需要明确案件中的事实问题和相关性效果,对其进行适用就是对法官产生心里说服的目的,进而肯定或者否定其他一些事实的存在。*William Twining, Rethinking Evidence: Exploratory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93.
五、技术与体系: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扩展
从概念的外延与因果特性的角度来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技术外延,主要是指这种证明的对象特殊性,以及它与其他传统刑事案件中因果关系证明的区别。如前所述,可以明确的是传统刑事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证明理论和方法,虽然可以应用于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活动,但是并不能彻底解决具有特殊条件和特殊背景的案件的证明难题。也就是说,对于某些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外延,需要以上述内涵为基础,构建和发展出与传统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方法以及证明模式理论相区别的新型证明理论(详见图4)。
第一,如前所述,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本质上是一种诉讼活动,因此对于它的证明不仅需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关注证据法上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还需要更加强调其他学科的证明原理和技术,实现跨学科意义上的证明论的融合,进而回归社会科学的体系思考。例如,污染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属于犯罪学共同的一个理论难点。需要从行为人的心理视角、犯罪结果的科学测量以及法律意义上的特定设置和特定时间、地点等方面,进行综合性和全局性的跨学科审视和理解。这种特点也决定了预测、证明和防止这种新兴犯罪的困难性。*Richard Wortley and Lorraine Mazerolle,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and crime analysis: situating the theory, analytic approach and application, edited by Richard Wortley and Lorraine Mazerolle,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and Crime Analysis, London: Willan Publishing, 2008, p1.
第二,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主体,决定了需要对证明责任的原理、制度和分配进行重新审视。例如,证明责任的分配当然应当尽量符合相关法律的规范要求和法律的安定性,但是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过程中,因诉讼双方的地位、资源和知识等方面的差距,可能造成程序上的不平等,进而影响实质正义的实现。故而在这类案件中,涉及因果关系的证明需要在特殊事件类型、诉讼公平性、个案正义等价值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以求对这些价值予以充分地衡量和兼顾。*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6年版,第9页。
第三,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对象,需要在刑法与证据法之间架构起沟通的桥梁,需要注意这一因果关系证明论的立体面,强调横纵立体关系中的刑事一体化基本面,注重在事实证明的基础上拓展证据要求与证明理念的关系范畴。例如,在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对象中,适用证明相关性的两个以上事实的相互联系,需要在刑事实体法中依据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顺序进行运作形成过程链。其中的一个待证明事实,无论是单独与其他事实或证据联系起来,还是综合性地联系起来,都在结果意义上存在证实或者证伪的证明理念,或者显示出因果关系的过去、现在或者将来存在与不存在的可能性。*参见[英]理查德·梅:《刑事证据》,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第四,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路径,需要在跨学科背景下进行社科法学式的拓展和层次化思考,需要注重的是大证据学背景下的心证方法、经验法则、逻辑推理和推定技术等的合理应用。传统型的证据法学教义性研究,关注的是通过排除证据或证明的异常和障碍的规则体系来实现裁决的确定性,而“跨学科”意义上的证据学则主张通过证据与事实关系的拓展来改进和提高准确性,这种路径虽然有些非常规的倾向,但是却可能成为当前乃至未来证据研究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要求,需要对证明标准的程度要求科学地进行要素审视和层次扩展,合理借鉴和吸收环境法和侵权法等学科的盖然性等理论。正如威格莫尔所认为的,“证明的科学”是先于证据的审判规则的,也就是说比证据规则更加重要。而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过程中,“证明的科学”却被忽略了。由于证据规则注定是要减少其重要性的,那么,发展证明的科学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所有的人为的证据可采信规则或许都要被摒弃;可是,只要审判依然是为解决法律纠纷而寻求真实的理性活动,那么证明的原则和科学将会永远存在。”*参见[美]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第五版)》,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第六,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结果,需要对证明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两面看”,重视正推也要强调反推,重视证实更要强调证伪。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困惑的问题所在即证据的排除和证明结果的得出。关于承认或排除的证据,需要在证明过程中进行形式反对或提供相反的参数标准,这最终可能导致证明过程的混乱增加。在逻辑上,假设一个“两面”的证明过程去寻求真理,当庭的观察者可能会减轻困惑从而明确明显相关证据的价值。有时,对此案证明可能有直接关系,但从证明的方向上看可能在审判过程中被排除。因此,对这种假设的理解,需要明确为什么某些证据的正推是被承认的,而其他证据却被反推排除在外,有必要研究证实意义上的证据,更有必要从反向来证伪进而排除一些不合理的怀疑。*Jefferson L. Ingram, Criminal Evidence (tenth edition), New York: Anderson Publishing, 2009, p7.从这个维度出发意味着,鉴定等其他学科的专业意见将从控辩双方的角度更多地不同程度地影响案件的证明和认定。

图4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技术治理体系
七、结 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同环境犯罪这种控辩双方对抗性有别于传统犯罪并更多地依赖于技术鉴定及辩方参与的犯罪类型将日益增多,社科刑事法学的合理因素应予以合理借鉴,在此类“定制”犯罪的认定中,实务应回应这种认定的开放性需求,并回归证明模式的技术维度和规范维度,以理论的指导避免政策影响下犯罪认定游走于严厉与轻缓之间的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杜小丽)
DF626
A
1005-9512-(2017)12-0077-12
杨继文,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师资博士后、诉讼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刑事庭审证据调查规则研究”(项目编号:16AFX012)之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