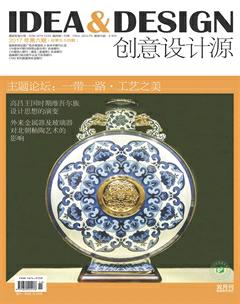古滇国青铜贮贝器造型艺术探究
刘利
[摘要]以类型学的方法将云南古滇国的青铜贮贝器分为提桶形贮贝器、束腰筒状贮贝器、铜鼓(形)贮贝器三大类,并依据现有出土文物做造型艺术上的分析,试图总结不同时期贮贝器的特点,以期为读者提供较好的辨识方法。
[关键词]古滇国;贮贝器;造型艺术
[Abstract]This paper from the money-box of bronze receptacles the forms of the bucket shaped receptacles, waist cylindrical receptacles, bronze drums (shaped) art characteristics of receptacles to do summary and induction. In order to judge from the modeling and shape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 casting age receptacles, provide better identification method for readers.
[Key words]The ancient Dian Kingdom;Money-box of bronze receptacles;Plastic art
“滇”是指战国至西汉时期兴盛于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古王国,西汉后期走向衰落,东汉初叶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1]自20世纪五十年代在云南滇池发现青铜文化以来,至今已发掘滇文化墓葬约1260座。在发掘的滇青铜文化的器物中,青铜贮贝器是研究古滇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形象资料,同时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贮贝器大约出现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早中期,经过战国、秦和西汉的发展,在公元前82年左右的西汉中期达到鼎盛。后来由于滇国的神秘消失,青铜文化消亡于东汉[2](图1)。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统计,可确定有34座墓共出土各种青铜贮贝器90件。本文根据现有资料将滇青铜贮贝器大致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即提桶形贮贝器、束腰筒状贮贝器、铜鼓(形)贮贝器和异形贮贝器(图2)。其中束腰筒状贮贝器又可以分为束腰形贮贝器和虎耳束腰形贮贝器;铜鼓(形)贮贝器又可以分为单鼓形贮贝器和叠鼓形贮贝器。异形贮贝器数量很少,有专家指出,异形贮贝器和一般的贮贝器形制相去甚远,可能是一种代用品,因此本文不作讨论。
一、提桶形贮贝器造型艺术
提桶形贮贝器出现的时间大致在战国中期,处于贮贝器的形成期。据马崧良《庄蹻王滇考》考释,滇国的开国之王庄蹻建都呈贡,死后葬于呈贡,呈贡天子庙M41墓应是庄蹻王墓。M41墓出土3件贮贝器,均为提桶形贮贝器。三件器形相近,只是纹饰繁简不同。其中一件五牛提桶贮贝器,高49.5厘米,盖径29厘米。
这件贮贝器器盖略鼓,中央铸有凸起的鼓形圆座,圆座周围有四圈铜鼓上特有的晕圈,圈内饰三角形齿纹及同心圆纹(图3)。圆座上站立一牛,形体较大,牛的身上以线刻的方式刻画卷草样的圆形花纹。盖边有首尾相接呈顺时针方向行走的四牛,形体较中央的牛体积小一些(其中一牛出土时已脱落,牛的位置靠近器盖折边的器耳),牛身同样刻有与大牛纹样一致的卷草样圆形花纹。五牛憨态可掬,站姿相近,有的牛角已断残。器盖有向下的短口折边,折边处又有两个左右对称的方形器耳,位置与鼓形圆座上立牛的头和尾相对应。
器身两侧近口沿处有犬形耳左右相对,犬的体积不大,以头朝上、四角垂直于器壁站立的姿势,焊接于靠近器身口沿的地方,与器盖器耳形成两两对应的关系,形成较为严密的上下一体。桶身呈倒梯形,其上铸刻纹样,用12道晕花纹对桶身进行分割,形成两个主要装饰带和三条几何纹样带,有主有次。两个主要装饰带上刻画着戴羽冠人、船纹、牛纹和水鸟纹等;几何纹样带刻画正三角形齿纹、同心圆纹和倒三角形齿纹,在器身的上、中、下部位重復三次。
器身底部有三足,足不高,稍稍缩进,45°角斜下视器物时不容易观测到足的位置。该器物出土时装有海贝。其它两件贮贝器在现有的文献描述中均为提桶形样式,关于器物造型的描述也很简略,器盖上无立体造型物。
铜提桶本来是滇国盛水或盛酒的铜器,并非用于贮贝。云南个旧东汉墓也有类似铜桶出土,但未见海贝。呈贡天子庙墓地出土的这3件提桶形贮贝器很可能也是代用品,主要是利用桶的空腹可盛物的特性来装海贝,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贮贝器。由此可见,古代滇国的海贝最初没有专门的容器进行储藏,随着对外贸易的展开,交易数目增多,海贝的数量越来越多,需要存放的空间越来越大,统治者才想办法用专门的青铜器来盛装海贝。提桶因为在造型上呈圆形,桶身较深,能够容纳较多海贝,出于对实用功能的考虑,圆形的铜桶就成为贮贝器的前身。
提桶形贮贝器身似圆桶,器壁轮廓造型呈直线形,器身装饰呈平面化,用阳刻方法描绘纹样,图案线条流畅舒展。器盖上只以牛的形象作为装饰,立牛壮硕有力,呈现出阳刚之气。然而古滇人对提桶形贮贝器在造型生动、财富展现、生活场景、宗教仪式等造型方面的表达还没有明确意识,或者还来不及想到可以利用贮贝器器盖上的空间还原和塑造滇国的生活面貌。古滇人对贮贝器的造型样式设计处于初探期和稚拙期,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造型与装饰风格。
二、束腰筒状贮贝器造型艺术
真正的贮贝器,以束腰筒状贮贝器的出现为标志。束腰筒状贮贝器出现在战国时期,延续至西汉,经历了贮贝器的形成期和全盛期。李伟卿先生认为束腰筒状贮贝器型制来源于竹节,竹节内腹腔的容积是贮贝器造型样式的起点,原因如下:1.滇国盛产“濮竹”,有使用竹器的传统,贮贝器的样式可以借鉴竹器的形状;2.石寨山的发掘简报中有“盛贝筒状器”的记录,在发掘遗址有明显的筒状印迹;3.江川早期墓葬中有成堆的货贝堆置,可能是竹器毁朽不存,贝币散落的结果[2]。由此可见,束腰筒状贮贝器的“祖形”可能是竹筒状竹器。endprint
束腰筒状贮贝器最终发展成为贮贝器的主流器型,数量也最多。这类器型不但在造型上产生很多变化,而且器盖上表达的题材和内容也变得多样化。可以说,束腰筒状贮贝器是贮贝器造型样式成熟时期的表现。束腰筒状贮贝器又分为束腰形贮贝器和虎耳束腰形贮贝器两类。从时间上讲,束腰形贮贝器比虎耳束腰形贮贝器早。前者出现在战国时期,后者出现在西汉时期。二者相比,虎耳束腰形造型相较于束腰形显得更为复杂。
(一)束腰形贮贝器
束腰形贮贝器高多在30厘米以上,盖径在15-20厘米之间。和战国时期的提桶形贮贝器造型相似,束腰形贮贝器器盖上的装饰物同样是牛,有的站立一牛(图4),有的站立五牛。仔细观察,束腰形贮贝器器盖上牛的形象刻画细节更多,对牛尾、牛蹄、牛角等的刻画更细致入微。如图5这件五牛贮贝器,器盖上牛的造型就各自不同,有的牛角弯一些,有的牛角往上翘;五头牛的体态有大有小,站立于中央铜鼓之上的主牛体形最大。器盖上的四牛以逆时针方向行走。可见,在牛的立体形象塑造上,束腰形贮贝器比提桶形贮贝器有改进,有多元化和细腻化的趋势。
器盖、器身两侧有上下对称的方孔器耳,对称的器耳保证了器盖、器身在扣合时必须有位置对应,形成正面、背面、侧面相对固定的观测角度。两两相对的器耳使古滇人在铸造器盖上的立牛形象时必须考虑将最佳的观赏角度留给正面,反映了滇国工艺匠人对造型审美的追求和表达。
束腰形贮贝器整体外形好似竹节,上下两端向外突出,下端突出比上端突出略多,中间缩进,仿佛罗马数字“Ⅱ”。器身保持了提桶形贮贝器外形舒朗简洁的特点,轮廓明朗干练。束腰形贮贝器上半部分呈直线形,到底端时才发散呈喇叭状,上口小,下口大,形成直曲并济的线条。器盖则相反,上口大,下口小,和器身对接的地方口径一致,上下贯通,连成优美的弧线。这条优美的弧线必须保证器盖和器身在扣盖处的口径完全一致,对造型精准和铸造工艺要求很高,否则器盖和器身就盖不上,影响实用和美观。
器身底部有三足,足较高,呈扁平状,以1/3段弧为节点焊接于圆形底部边缘,非常容易观测到足的位置和足的片状形态。可以说,束腰形贮贝器在造型和美观上比提桶形贮贝器更主观和自信,也更加重视贮贝器的实用功能。
(二)虎耳束腰形贮贝器
虎耳束腰形贮贝器高多在45-55厘米之间,盖径在25-32厘米之间,体量稍大于束腰形贮贝器。虎耳束腰形贮贝器器盖上的装饰物最富特色,有三个最突出的特点(图6)。一是造型生动而有力。器蓋上牛的造型明显比束腰形更健硕和富有动感,器盖上的牛均以逆时针方向站立行走,体态饱满壮实,个头较大,牛角向上弯曲,强健有力,牛身上的肌肉都清晰可辨,甚至连生殖器都做了刻画。二是量多而有序。和束腰形贮贝器相比,虎耳束腰形贮贝器在牛的量上明显增加:一方面是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是质量提高。比如八牛贮贝器,七头成年公牛以身体微斜向外的姿势站立,牛头略微偏朝外,紧紧围绕中间站在鼓面上的大牛,数量密集却秩序分明。另外,祭祀贮贝器上的人物形象多达129人,这些人分成不同的人群,分别进行着与祭祀有关的活动内容。除了人物,器盖上还刻画着建筑和大小不一的铜鼓若干,人们在主祭人的带领下,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有条不紊的祭祀活动。如此众多的形象分布在直径仅32厘米的器盖上,各行其是,各负其责,繁而不乱,在所有青铜器中是绝无仅有的。三是题材丰富。这是虎耳束腰形贮贝器最具特色的地方。除了牛的形象,还出现了反映滇国生产生活、宗教祭祀等题材的场景,大大丰富了贮贝器的表现内容。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不但有牛的形象,还对马和人物进行塑造。四头精壮的公牛围绕着中间骑马的滇国贵族统治者,为了强调贵族的身份,还特意对其做了通体“鎏金”处理。祭祀贮贝器更是将题材的丰富性推向极致,众多的人物形象在发型、服装、身体动态等方面各有不同。四面通风的干栏式建筑、排列有序的铜鼓、功能不同的道具和形状不一的生活器具更是将这件贮贝器塑造得极富故事性。可见,虎耳束腰形贮贝器不仅将财富的展示推向高峰,而且对滇人掌控财富的表达和对宗教仪式的记录也表现出非常重视的境况。
从器身来看,虎耳束腰形贮贝器的造型比束腰形贮贝器变化大。器身上下两端外突更明显,上下两端突出的程度相当,中间收缩更厉害,仿佛两个反向的括号 “)(”弧线形。有的虎耳束腰形贮贝器在器身的上下两端又有细微的外突,增加了线条装饰,使造型既保持整体感,又不失细节变化。束腰形贮贝器和虎耳束腰形贮贝器器身均不做深刻花纹装饰,一些贮贝器通体光素无华,另一些贮贝器器身上则有刻痕较浅的图案,纹样丰富多彩。比如八牛贮贝器,器身用四条较细的装饰带以水平方向将器身分割成四层,第一层为首尾相连的六只孔雀;第二层为六只雉鸡,其中一只在啄食蜥蜴;第三层为首尾相连的十匹长鬃马;第四层为首尾相连的九头长角牛[6]。每一层的动物分别按照逆时针、顺时针、逆时针、顺时针的方向行走。由于是浅刻,经过漫长的时间和空气的氧化腐蚀,器表的图形已不容易分辨(图7)。
另外,虎耳束腰形贮贝器的器耳也是引人注目的地方。器身上的器耳被铸造成虎的形象。器身的腰线最细处,左右两边分别焊接一只老虎,虎头朝上,虎视眈眈,虎口大张,四肢有力,一副随时一跃而起的登踏造型。二虎体形相当,左右相向而置。但造型略不相同,从虎尾的变化上能够轻易辨识二者差异,在大对称的布局中有小对比的变化。与束腰形不同,虎耳细腰形贮贝器仅靠虎耳判断器身的正面、背面和侧面。器盖上没有器耳,器盖的直径相当于器身上端的口径,锅盖一样置于器身上端,和器身没有上下扣合的关系。由于器盖和器身随机扣盖,没有精准的位置对应,不能判断器盖的正面、背面和侧面,而且会出现器盖与器身之间留有缝隙的情况。
器底有三足,同样以1/3段弧为节点焊接于圆形底部边缘,足较高,有的足呈扁平状,有的足呈兽类的爪状,爪足向外,牢牢抓住地面,比较容易观测到足的位置。综上所述,束腰筒状贮贝器的出现是贮贝器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专门为了盛放海贝而制作的器物。古滇人意识到贮贝器是一种可以象征财富、展示财富、记录生活的青铜器物。所以贮贝器在造型生动方面最具特色,牛作为财富的象征,反复出现在贮贝器的器盖上。数量上不但有所增加,而且在铸造工艺上也更加精良。贵族阶层以“火镀金”的特殊工艺处理方式出现在贮贝器上,表达对财富的掌控和拥有,不仅把自己的形象放置在贮贝器的中央位置,体量增大,而且还有意将自己的形象置于铜鼓之上,高出周围物象很多,形成绝对的视觉中心。另外,在造型美的形式上,充分表现出古滇国工艺匠人的审美创造性,一方面通过上下或者左右器耳的对称方式形成固定或者相对固定的正视、后视和侧视观看角度;另一方面通过器表图案逆时针、顺时针的方向变化形成有秩序、节奏的对比关系。endprint
三、铜鼓(形)贮贝器造型艺术
本文所说的铜鼓(形)贮贝器,包括直接用铜鼓改造成的贮贝器和专门铸造成铜鼓样式的贮贝器,因为它们外形都是从铜鼓外形而来,所以统称铜鼓(形)贮贝器。
铜鼓(形)贮贝器出现的时间集中在西汉,在时间上处于贮贝器的全盛期。据1956年第一期《考古学报》记载,在云南出土的贮贝器中,有11件铜鼓被当作代用品放置了货贝。《明史》记载,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击鼓山岭,群蛮毕集”[4]。铜鼓是古滇国各民族普遍使用的打击乐器,在祭祀、庆典仪式中使用,后来逐渐演变为上层统治阶级拥有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铜鼓由乐器演变为礼器,与中原鼎由炊具演变为礼器相似。[5]可以说,贮贝器除了进一步表达财富,还借用铜鼓礼器的神圣性来提升自身的价值,集财富与神圣于一体,使贮贝器具备了更深刻的象征意义。用击破的铜鼓改制成贮贝器,或是专门以铜鼓的形状铸造铜鼓贮贝器,都是这种象征意义的体现。
(一)单鼓形贮贝器
单鼓形贮贝器高在21-40厘米之间,盖径在22-35厘米之间不等,是由击破鼓面的铜鼓改制而成,属于再生型青铜容器。单鼓形贮贝器器盖和器身的铸造时代很可能不同,也许器盖是西汉中期铸造,而器身则可能是西汉早期或者是更早的战国时期。
单鼓形贮贝器的改制方法为:先将残缺不全的鼓面去除,另鑄一新盖,盖上焊接立体人物、动物形象。在原铜鼓的圈足处焊接一底,器身保持不变,这样铜鼓就改变了原来的用途,成为新容器,铜鼓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随之转移到贮贝器上。[6]
图8、图9和图10均为单鼓形贮贝器。3件器形的鼓面有非常明显的焊接痕迹,而且铜鼓和器盖的颜色差异显著,由此推断二者的铸造时间不同。铜鼓的胴部、腰部均刻画有纹样,有人纹、三角形齿纹、同心圆纹等,纹饰繁简不同。胴部与腰部连接的地方有器耳相连,以1/4段弧为节点进行焊接。
如果说束腰筒状贮贝器表现最多的是用牛来展现财富,那么单鼓形贮贝器刻画最多的就是各种生活场景还原以及与宗教祭祀有关的事件。比如农耕祭祀贮贝器(图8)的器盖上共铸35人,正中立一伞盖状铜柱,柱侧有四人抬的肩舆一乘,舆内坐一妇人,通体鎏金,另有男女执事人员若干,均围绕主祭人,有的执伞,有的骑马开道,有的在舆侧跟随伺候,还有的肩扛铜锄,手持点种棒,身挎籽种袋等,也有一些头顶成束的农作物,手捧坛罐或提篮系筐者,他们可能正在利用宗教场所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活动[8]。又如杀人祭铜鼓贮贝器(图9)和杀人祭铜柱贮贝器(图10)的宗教仪式感更强烈,农耕祭祀贮贝器是和风细雨的农耕祭祀和祈求仪式,杀人祭铜鼓和杀人祭铜柱就是鲜血淋漓的残酷牺牲和杀戮场面。这种强烈的仪
式感进一步巩固了贮贝器所具有的震慑力和神圣性。
单鼓形贮贝器有的器身底部有三足,稍稍缩进,足不高,起到架空的作用,形态没有特别讲究。有的贮贝器则没有足,铜鼓的圈足直接和地面相触,完全平置于地面。
单鼓形贮贝器是在铜鼓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在器身纹样装饰上没有更多创造的余地和发挥的空间,但在器盖的形象塑造上却加入了事件作为表现主题。一件贮贝器描绘一个事件,这些事件的场景很大,涉及的人物也很多。一些表示权利的器物,如立柱、铜鼓、铜柱等多次出现在器盖上,形制上也有意夸张和放大。贮贝器器盖上的事件主角,有的是古滇国的贵族精英,有的是主持祭祀的主祭人(多为女性)。这两类人拥有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权威,主持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劳作事件和重大仪式,也掌握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生杀大权[9]。通过刻画的事件场景,我们可以还原古滇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构成关系,甚至可以推导古滇国当时的族群阶层制度和社会状况风貌。所以,单鼓形贮贝器在造型方面最重要的不是贵族精英阶层对于财富的宣扬,而是利用铜鼓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将财富转化为统治者权威的表达,利用对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塑造展现滇国的社会状况。
(二)叠鼓形贮贝器
就现有的图片资料看,叠鼓形贮贝器有4件(图11),叠鼓形贮贝器高在39-63厘米之间,盖径在30-35厘米之间不等。其中纳贡贮贝器出土时上鼓已残(图11左上)。这件贮贝器高39.5厘米,胴径127.2厘米,由于上鼓缺失,无法统计盖径尺寸。如果器型完整,它是4件中最大的,高度应该超过80厘米,盖径也应该超过35厘米,体量比其他3件大得多。可以说,叠鼓形贮贝器是所有贮贝器中体量最大的,它比单鼓形贮贝器的容积增加了一倍,说明古滇国的统治者以二鼓相叠的方式来表现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权利。
狩猎贮贝器由上下两个铜鼓重叠而成,上鼓略小,去掉破损的鼓面后另配一盖,下鼓较大,于敞口的圈足处新接一底,器内装满海贝,上下两鼓焊接在一起。器盖上铸有狩猎场景,其中猎手三人,二人骑马,当中一人通体鎏金,另一人徒步,三人均佩长剑。骑马者左手持缰绳,右手执长矛(已残断),各自追逐一头鹿;鹿和骑士以间隔的方式围成圆圈,圆圈中间的徒步者双膝微曲,做好了攻击的准备。三条猎犬分别扑向二鹿,一只野兔似乎受到惊吓,蜷缩于一骑马者的左侧。
狩猎贮贝器上鼓圈足处焊接四鹿,下鼓的同一位置焊接四牛,均为立体雕铸,形象生动。胴、腰间均有四个绳纹条带耳,器身布满生动逼真的线刻花纹,上下鼓各三层,分别刻于胴部、腰部及圈足,刻画技法相同,内容有别:上鼓胴部刻十一只展翅飞翔的犀鸟,腰部用绳纹、三角形齿纹和圆圈纹组成的条带分为四格,其中两格为徒步狩猎图像,另两格为骑马猎鹿图像,圈足处有动植物图像一周,另有虎一只;下鼓胴部刻雉鸡七只,均作展翅扬尾飞翔状,腰部亦用绳纹、三角形齿纹和圆圈纹组成的条带分为四格,每格中均有小树1-2棵,另有虎、牛、野猪、鹿、鹰及人面兽身等动物图像;圈足处刻十二只孔雀,其中一孔雀嘴中衔一蛇(图12)。而纳贡贮贝器(左上)、战争贮贝器(右上)、狩猎贮贝器(左下)器盖上均有人物和动物的刻画。
战争贮贝器描绘了滇国与周边部落族群战斗,滇国获胜的场面。交战双方一方是椎髻的滇国将士,另一方为辫发的“昆明”人。虽说双方都在格斗搏击,但“昆明”人有的被砍去头颅,有的被击倒在地仍挣扎欲起,也有的双手被缚成为奴隶,显示他们败局已定。纳贡贮贝器在两鼓相接的边沿处,铸刻焊接立体人物和动物一周,首尾相接,以顺时针方向行走前进着。他们是滇国边部落和族群的人群,携带着礼物,向滇王献贡。纳贡的队伍可以分为七组,每组少则二人,多则四人,为首的一人皆盛装佩剑,衣饰较其他人华丽整洁,佩剑但不背负礼物,应该是部落或族群中的首领或头目。尾随其后者有的牵牛,有的牵马,有的抬扛贡品,有的背负贡品,缓缓向滇王走来。endprint
叠鼓形贮贝器器盖形象的塑造和题材与单鼓形贮贝器有很大不同。后者主要表现古代滇国以女性为主角,负责从事生产生活、宗教祭祀活动等的事项;而前者则主要表现以男性为主体,负责从事狩猎战争、部族统领等事件。单鼓形贮贝器的人物性别有男有女;叠鼓形贮贝器的人物性别则全部为男性。佟伟华先生在《滇国青铜文化中的珍品一叠鼓形贮贝器》中记述,叠鼓形贮贝器均出土于贮贝器较多的大墓,在出土贮贝器的大墓中,一般每墓只出土贮贝器1-2件,只有少量墓葬出土贮贝器3-5件,在发掘的34座大墓中,仅有4座出土了叠鼓形贮贝器,占所有大墓的11%。此外,出土战争贮贝器的大墓还出土了金质“滇王之印”。由此可以推断,叠鼓形贮贝器是与滇王身份相当的人才能拥有的,不但是身份地位的体现,而且是男性权威的显现,更是适者生存法则的再现。
另外,蹲蛙贮贝器的铸造年代晚于其他三件,约在西汉晚期。蹲蛙贮贝器上下两器对合,上鼓鼓面焊接一蹲蛙,鼓面与鼓身的形状和花纹与一般铜鼓相似;下鼓倒置,贴地的鼓面素净无纹,但焊接了三只矮足使铜鼓不直接接触地面,鼓身的人物和动物图像和上鼓相同,都是正立的。可见,蹲蛙贮贝器是为了满足存贮海贝的需要而新铸的器物。但造型与纹样大不及前三件贮贝器生动与丰富。此时已是西汉后期东汉初期,中原王朝郡县制在滇国逐步确立,滇王的政权有所动摇,一方面中原地区流行的金属铸币伴随着大量汉族移民和汉式器物涌入西南边陲,代表滇文化的贮贝器和贝币受到巨大冲击,贝币失去货币作用,储存海贝的贮贝器正逐渐失去实用价值和存在意义[8];另一方面铁器铸造技术的改进和锻造水平的提升使铁器成为主流器物,贮贝器由鼎盛转向衰亡的命运已成定局,因此蹲蛙贮贝器的造型与纹样就显得与其他三件明显不同。
结语
从以上三种贮贝器造型的分析来看,提桶形贮贝器用来贮贝不是客观需要,而是一种代用品。海贝的数量还没有多到必须要铸造一种专门的容器来盛放,因此提桶形贮贝器在造型上多借鉴铜提桶的样式,主要满足实用功能。贮贝器造型简洁,器身轮廓线条缺少变化,呈直线形。器盖所塑之物为牛,器身图案丰富,对财富表达的意识相对薄弱。提桶形贮贝器处于贮贝器发展过程中的萌芽状态。
束腰筒状贮贝器是为了盛放贝币而专门铸造,贝币的增多使古滇国统治者意识到贮贝器的重要性,并且借贮贝器来炫耀财富。束腰筒状贮贝器的造型最为丰富,有束腰形贮贝器和虎耳束腰形贮贝器两类。束腰筒状贮贝器器身轮廓优美富有流线的韵律,器盖所塑的牛不但数量增多,而且个头增大,强健有力。统治者表达财富的愿望十分明确,表达拥有财富的意愿也很强烈。除了表达财富,虎耳束腰形贮贝器还出现了反映宗教祭祀的题材,宏大的祭祀场景表明古滇国统治者不但要展現财富,还要将贮贝器题材刻画的内容范围扩展至与人有关的生活场景和事件中,通过事件来强调人的主观存在,兼具功能性和象征性。束腰筒状贮贝器处于贮贝器发展过程中的成熟和鼎盛阶段。
铜鼓(形)贮贝器不仅仅满足于贮藏贝币的功能性,而且从功能性走向象征性。造型基本和铜鼓一致,将铜鼓财富、权威的象征意义转移到贮贝器上。单鼓形贮贝器多在击破的铜鼓鼓面上重铸器盖,器盖上牛的形象消失,转而再现古滇国统治者主管生产劳动、宗教祭祀的场景,着重刻画统领者,并将其放置在醒目位置,突出权威的震慑力;叠鼓形贮贝器为二鼓相叠,有的贮贝器并非用旧鼓改造,而是专门铸制,进一步增强贮贝器的象征意义。器盖上展现滇国狩猎、战争、纳贡等场景,充分展现人与自然、部族与部族之间的优胜劣汰关系,突出权利的至高无上。后期的叠鼓形贮贝器受时代更迭和工艺变化等因素影响,造型由繁复转为疏简,是贮贝器发展由鼎盛转向落没的写照。
参考文献:
[1] 张增祺.滇国青铜艺术[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3.
[2] 李金莲.云南古代滇池地区青铜文化中的贮贝器综述[J].楚雄师范大学学报,2005(2):56-62.
[3]李昆声.云南艺术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4]肖明华.论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J].考古,2004(1):78-88.
[5]佟伟华.滇国青铜文化中的珍品——叠鼓形贮贝器[J].中国历史文物,2002(3):29-30.
[6]张增祺.滇国青铜艺术[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
[7]蒋志龙.铜鼓·贮贝器·滇国[J].中华文化论坛,2002(4):97-101.
[8]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5.
[9]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