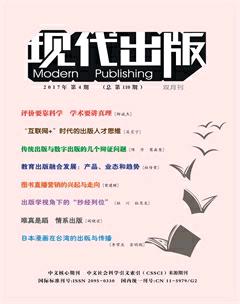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管窥
黄磊
一、供给侧改革的历史源起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之后,1979年英国执政的撒切尔政府、1980年美国执政的里根政府,针对西方需求提振乏力、经济“滞涨”的“凯恩斯陷阱”,吸收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大规模地将供给学派的减税、消减财政开支、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控货币供应量等政策主张付诸实践。这些政策实践都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提升了英、美的经济活力。
从中国历史上看,以减税为特征的供给端改革源远流长。春秋时期,管子提出“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人”“关赋百取一”“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等一系列放松管制的举措,为齐国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齐桓公以此“九合诸侯”,成为春秋霸主。此后,历代初立王朝,在供给端多采取“轻徭薄赋”、放松管制的政策,经济得以快速恢复。
结合中外实践可以看到,供给端改革的显著特征就是给予微观经济主体更多的选择权,从而在面对需求端的多样性时,能够根据市场做出及时和合理的应对。
二、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
根据开卷最新图书市场报告,2016年全国全年新书品种数为21.03万种,连续5年保持在20万-21万种之间。新书、重印书合计,年均大致在45万~47万种。过于庞大的出书品种,导致实体书店上架率低,上架图书的动销率基本在20%~30%,主动对接买方市场的能力较弱,企业经营“广种薄收”、经济效益较为低下。鉴于现状,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出版业而言,可谓恰逢其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三、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出版业与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水泥、钢材等高能耗产业相比,因其内容生产的属性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出版业在寻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时,要既重视目前大环境下存在的普遍性矛盾,也应该因地制宜地分析本行业问题的特殊性。
一是“去产能,强服务”。高产能是工业化社会流水线作业的产物。随着现代社会思维的多样化,由出版者单维度地提供价值判断的“现代性傲慢”,在社会的多样化背景下逐步解构,读者的阅读需求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个性化和小众化。针对这种状况,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在供给端面向读者进行自我调适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差异化要求更多地对市场进行细分,同时,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以当前出版的大学教材为例,纸质文本中,更多地从满足受众的学习体验出发,提供“案例导读”“知识链接”“微课”等多样化知识学习路径;市场型图书则更多地以读书会、微信群等方式,在服务增值和价值链延伸等多维度上进行开拓。
二是“去库存,轻资产”。自2004年以来,图书库存逐年递增,截至2014年,全行业库存总码洋为1010亿元,总库存数66.39亿册,年均增长2.5亿册。过高的库存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去库存是当前出版业供给侧改革“治标”的题中之义,“缩表”是压缩成本、维护出版业健康安全运营的必然选择。应当注意的是,部分旧版图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格、版本等方面的价值逐步凸显,在去库存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对这部分图书加以甄别、保留,切忌盲目操作。
三是“去杠杆,重研发”。“轻资产”的潜在含义,是出版者应当通过专业的策划团队,专注于核心价值,即内容生产。根据民进中央2015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国内现有35.7万家新闻出版单位,其中民营出版单位有32.4万家,占总数量的90.8%,资产总额占69%,营业收入占69.3%,利润总额占80.5%。毫无疑问,民营出版机构在文化事业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重要地位;但与之相对的国有出版单位,表现出“空壳化”的趋势。出版社过于注重码洋规模的外延式扩张,与社会民营企业“合作”较多,而自身选题开发能力在不断扩大的“合作”出版中逐步萎缩,甚至最终成为只能依靠收取“过桥费”维持生存的单位。为此,出版社应当摒弃短期思维,强化内容导向,重视研发投入。在2016年财报中,知识密集型企业的行业翘楚,研发经费投入在营收中的占比大致在15%左右。例如,华为的研发占比为14.65%,谷歌的研发占比为13.95%,脸书(Facebook)的研发占比为17.58%。相比之下,国内出版机构特别是国有出版单位在这方面的投入偏低。
除了提高比例之外,研发经费重点投向何处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方向不对,投入的经费很快会成为“沉没成本”,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看,研发经费的投入原则,应当密切对接需求端。需求端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府需求和市场需求。前者以各類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为主,后者以读者的市场购买为主。财政资金的扶持项目,往往具有规模大、周期长、社会效益显著的特点,对于此类项目,在内容、时间节点等各方面,应当做周密的规划和长期的安排。此外,传统出版社在内容生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也汇聚了一定的作者资源。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出版社应当有意识地向智库型、平台化的方向发展,成为政策制定的智力支持者和提供者。对于市场需求,则需要认真测度读者阅读偏好角度。在多媒体时代,优秀的市场型图书不仅在内容上有着上乘的质量,而且在传播方式上也往往具备“媒介融合”的特征,即传统纸媒借助于电视、网络等介质的传播内容,完成市场对纸媒内容的认知。例如,《人民的名义》一书,即借助电视剧的热播迅速畅销。此类的案例非常多,前些年的“百家讲坛”系列图书、《明朝那些事儿》等的热销,也是“媒介融合”的典型。
四是“降成本,新机制”。创新机制是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所在,也是在“三去”之后出版业起步的依托所在;否则,无效产能和高企的库存又将卷土重来。机制的创新是传统出版企业实现自我革新的重要举措。机制创新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引入外生性变量。根据《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按规定已经转企的出版社、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新闻网站等,实行国有独资或国有文化企业控股下的国有多元。”因此,就出版单位整体来说,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引入社会资本,激活内部存量,是盘活国有资本的有效举措。另一种途径,是通过改变固有的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约束条件,形成新的原动力。传统的编辑出版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具有强烈的流水作业特点和条块特征。生产者的价值,多体现为产品生产的某一环节。而当下的图书产品生产,更多的是依靠创意和策划。这一特点要求编辑从单一的生产环节中脱离出来,更多地从市场、读者、内容、装帧、营销等方面做综合的考量取合,编辑也由此逐步具备了“产品经理”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一批具备市场竞争力的策划编辑开始脱颖而出。出版业的供给侧改革,应当积极围绕这些市场敏感度高、产品驾驭能力强的策划人及其团队展开。目前,部分出版机构开始通过设立内部工作室、划小经营核算单位、下放用人权、实行全成本核算、提高激励比例等举措,最大限度地贴近市场。
五是“补短板,互联网+”。传统出版企业在新媒体兴起的浪潮下,除了要实现“媒介融合”外,还需要通过互联网这一介质,使其产品快速传导到市场和读者群中,并通过寻找产品内容的市场共鸣,迅速形成营销热点。就实际效果而言,要补上传统出版的“短板”,仅具有“互联网+”的手段,还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出版单位也开设了微博、微信等营销账号,但实际的效果不甚理想,大多成为“自弹自唱”的花瓶式窗口,有新媒体之形,而无其神。因此,“互联网+”这一手段,仍需要与机制体制创新融为一体,与内容的创作融为一体,真正释放其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