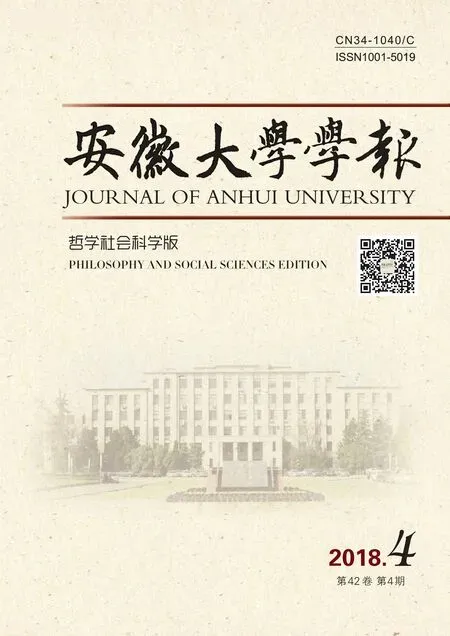《钦定本圣经》刊行后的另一种后果:英国散文风格的转型与本土化
王任傅
关于英国散文风格的确立国内外学术界已多有探讨,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影响英国散文发展的诸多因素,比如英语语言的发展、英国社会文化因素、法国文风的影响,以及当时盛行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精神的推动作用等。不可否认,以上这些因素在促成英国散文风格发生转变与健康发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综合所有这些影响力量,都远不及《钦定本圣经》(The Authorized Version of the Bible)的刊行与推广对英国散文风格转型和本土化所发挥的作用重大而深刻。
诚如美国学者、圣经研究专家约翰·加德纳(John Hays Gardiner, 1863—1913)所言:“(钦定本)圣经的风格确立了英语散文最终的标准,长期以来这作为一条毋庸置疑的公理为人所接受。”*John Hays Gardiner, The Bible as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 388.弗朗西斯·鲍恩(Francis Bowen, 1811—1890)教授也曾说:“实际上,英语文学许多最好、最具特点的品质主要来自对《钦定本圣经》有意无意的模仿。其措辞明晰、质朴,富有力量”,“只有当你的头脑和记忆已被我们(圣经)共同译本的散文所熏陶浸润……你才会掌握好的英语风格。”*Francis Bowen, A Layman’s Study of the English Bible: Considered in Its Literary and Secular Aspec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5, pp. 6, 16.两位评论家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道出了事情的本质。且不说“经过在教堂内外不断的诵读,‘钦定本’的内容连同它的文字和节奏早已深入英国人的灵魂”*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对于近代大多数英国作家来说,《钦定本圣经》都是他们启蒙的文学读物或终身不辍的文学范本,“直到二十世纪它一直起着一部教科书的作用,是每个人的教育的组成部分,不论他是一般老百姓也好,以至哲学家、革命家”*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众所周知,好的散文风格的形成不能只靠写作规则或章法,通过墨守成规而达到。一个人说话与表达的方式最终是在对身边榜样无意识的模仿中,在对最为熟识的书籍反复不断的阅读中悄然形成的*Francis Bowen, A Layman’s Study of the English Bible: Considered in Its Literary and Secular Aspec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5, p. 16.。这恰恰就是《钦定本圣经》发挥其巨大文学影响力的方式。
一、《钦定本圣经》之前英国早期散文的缘起、流变及特点
英语当中有两个单词表示了汉语“散文”的概念,它们分别是“essay”和“prose”。具体而言,“essay”对应于汉语狭义散文的概念,也被称为“随笔”或“小品文”;“prose”则相当于汉语中广义的散文。本论文所讨论的是广义散文(prose),即“包括诗歌以外的一切文学作品”*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这自然也包括小说在内,因为小说是“以一个故事为基础的一种散文记事”*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蔡文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38页。,或称散文体叙事文学。
英国散文有着悠久的历史。流传至今的盎格鲁-撒克逊散文最早创作于公元8世纪。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早期用散文体书写的作品并非出自英语,而大多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一方面,“拉丁文是中世纪欧洲各族教士和学者之间通行的文字”*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页。,“用它便于交流思想和学术”*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页。;另一方面,拉丁文在英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文化教育中心是寺院,而教会的正式语言就是拉丁语”*陈新:《英国散文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英国文学史家艾弗·埃文斯(Ifor Evans, 1899—1982)提出,开创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散文的人物可以确定的“最早的人是舍博恩的主教奥尔德赫姆(Aldhelm, 639—709),他用华美的拉丁文体写过女贞的赞美词”*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第8页。, 所以,奥尔德赫姆是迄今所知的英国第一位散文作者,而他的作品即是用拉丁文创作的。公元8世纪,英国历史之父——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 673—735)也用拉丁文撰写了他最重要的历史著作《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除此之外,比德还用拉丁文书写了30多本其他作品。
直到9世纪的下半叶,英国才真正出现了用英语写成的第一部散文巨著,即艾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 849—899)组织学者编纂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艾尔弗雷德是英语散文史上的重要人物。身为国王,他提倡使用英语,“试图通过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来改变人民愚昧无知的状态”*侯维瑞、李维屏:《英国小说史(上)》,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4页。。艾尔弗雷德曾说:“我们选择那些所有人都必须了解的书,把它们译成大家都能懂的语言,我认为这样才对。上帝慈悲,如果天下太平,这样英格兰所有拥有产业的自由青年就可以专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直到他们能够轻松而熟练地阅读英语。”*William Edward Simonds, A Student’s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Boston, New York, and Chicago: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2, p. 33.作为“英语散文中的第一部巨著”*A. W. Ward and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104.,《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文学价值,堪与《贝奥武甫》(Beowulf)在古英语诗歌中的地位相提并论。它的一些篇章,叙述简单朴素、生动有力,鲜明地表现出了英语语言和英国本土散文质朴风格的特点,堪称古英语散文的杰作。
虽然从英国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艾尔弗雷德大帝的文学成就极为重要,“在他统治时期,本国语言受到高度重视,这使得英国文学沿着自己的方式发展成为可能”*A. W. Ward and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 p. 106.,然而,由于基督教在英国社会的强势地位,拉丁语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知识界和文学领域的常用语言。因此艾尔弗雷德之后,人们继续使用拉丁文进行创作。于是,英国散文在诞生之初就形成了英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形式长期并存的局面;其中拉丁文的创作一直是主流。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用拉丁语写作还依然是英国文坛“当时的时代潮流”*陈新:《英国散文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不仅如此,在风格特点方面,早期英语散文也深受拉丁文风的影响,从而压制了本土散文的发展与壮大。古英语时期,最伟大的英语散文作家当推艾尔弗里克(Aelfric,约955—约1020)。他被认为是“有意识地从事散文写作并且有所建树的”英国第一人*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第12页。。艾尔弗里克重要的作品包括两卷本的《天主教道德训诫》(Catholic Homilies)和《圣徒传》(Lives of the Saints)等。艾尔弗里克的时代,拉丁语仍然是修道院里使用的语言,因此,拉丁式的句法结构十分普遍。起初,艾尔弗里克为了使文化层次低的人们也能看懂那些深奥的理念,努力避开晦涩难懂的词汇,力求用词简单、表达明晰。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写作中越来越追求语言形式,从而损害了自己的散文风格。艾尔弗里克也许觉得一种更为浮夸、华丽的风格要比平常口语更适于处理严肃的主题。但无论如何,艾尔弗里克后来在《圣徒传》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所采用的花哨风格,明显地逊于他最初的两卷本《道德训诫》*A. W. Ward and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128.。因此总体而言,艾尔弗里克的“散文风格比较雕琢”*李赋宁、何其莘主编:《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74页。,其大部分作品表现出了所受拉丁文风的深刻影响——结构严谨、措辞华丽,追求整齐的节奏感,因而显示出“一种有意识地矫揉造作”*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第339页。之感。
“诺曼征服”之后,英国文学进入了中古英语时期,此时的英语散文仍未摆脱外来语言文化的压制。最初的12、13世纪中,“英国的文学作品大部分都用法语和拉丁语写成,因为上流社会的诺曼贵族都说法语,而拉丁语则是当时欧洲通行的共同语言和诺曼底的官方语言”*李赋宁、何其莘主编:《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第112页。。在这两个世纪,英国本土的文学传统几近断绝。这段时间内只有为数不多的英语作品延续了本民族的散文传统,且主要局限于比较偏僻的边远地区。较为重要的作品有用来教育修女的《修女规箴》(Ancren Riwle)和用来记述圣玛格丽特(St. Margaret)、圣凯瑟琳(St. Catherine)与圣朱莉安娜(St. Juliana)的散文传记等。其中,用中西部方言写成的《修女规箴》独树一帜,被视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散文作品”,也是“整个中古英语时期最让人感兴趣的作品之一”*A. W. Ward and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 p. 230.。在语言风格上,《修女规箴》虽未能彻底摆脱古英语的束缚,以致表达不够灵活自如,但重要的是,它的语言清新、恳切,饱含真情实感——它朴素、率直,作者的文笔时而会触动读者的心灵,引人会心一笑*A. W. Ward and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 p. 231.。可以说,在英国文学发展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修女规箴》延续并保存了英国本土散文的质朴传统。
14世纪堪称英国文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首先,随着英语社会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宫廷、学校、法院和行政的语言,“在文学领域内英语也开始更多地代替了法语和拉丁语”,“到了14 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中东部方言(伦敦英语、牛津英语)已具有全英国共同的书写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性质了”*李赋宁、何其莘主编:《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第3页、5页。。其次,在英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这样具有世界声望的大诗人,他坚持用英语写作,有力地提升了英语的文学使用功能和地位。在英语散文方面,杰出的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 约1320—1384)及其影响下的罗拉德派(Lollards)建树颇多,他们在传教活动中积极推广了英语质朴散文的传统。威克利夫本人运用英语创作了为数不少的作品,包括布道文、论文和一些英文译作*Jean Jules Jusserand,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Putnam, 1895, p. 432.。他“致力于发展一种让所有普通人都能理解的英语,一种接近日常口语的风格;相比于乔叟精致文雅的风格特点,这显然更能代表普通民众的语言”*Charles Dudley Warner, Library of the World’s Best Literature: Ancient and Modern, Vol. 3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ociety, 1897, p. 16236.。 出于宗教改革的目的,罗拉德派还将《通俗拉丁文圣经》(The Vulgate)译成英文——《威克利夫圣经》(The Wycliffite Bible)。该译本通俗典雅、明晰有力的文风不仅传承了英国本土散文的质朴风格,而且达到了当时英语文学罕有的高度,被看成是最早的中古英语经典,与乔叟的作品比肩而立*William Muir, Our Grand Old Bible: being the Story of the Authorized Version of the English Bible Told for the Tercentenary Celebratio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1, p. 27.。但需要指出的是,乔叟、威克利夫等人的不懈努力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拉丁文在英国社会的强势地位,它依然是当时英国重要的学术语言。即使是威克利夫本人的许多重要神学著作也还是用拉丁语创作的,如《论圣餐》(De Eucharistia)、《论教会》(De Ecclesia)和《论圣经的真理》(De Vertitate Sacrae Scripturae)等。
虽然在14世纪人们看到了英语文学崛起的迹象和英国本土散文传统得以恢复与发展的希望,但是由于社会动荡的原因,15世纪的英国文学再次陷入了贫瘠,唯有民谣和与宗教密切相关的神秘剧、道德剧较为发达。同时,“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些严肃的著作仍然是用拉丁语创作的”*A. W. Ward and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286.。例如,亨利五世(Henry V, 1386—1422)的嘉奖是用拉丁语记录下来的;当时以拉丁语书写的编年史有20多份,而英语编年史仅约7份*A. W. Ward and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I, p. 286.;15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学者、神学家约翰·卡普格雷夫(John Capgrave, 1393—1464)的重要作品也都是用拉丁语创作的。
关于拉丁语在英国的主导地位从当时的印刷出版物中也可略见一斑。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 1422—1491)1476 年从欧洲大陆引进了印刷技术后,1478年和1479年在牛津(Oxford)与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分别创建起了两个出版社。它们所印刷的各类学术性书籍中,明显地以拉丁语作品为主。据统计,牛津出版社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出版的所有书籍当中只有一版是英语的,圣奥尔本斯出版的8种图书中,最初的6种也都是拉丁文的,只有最后两种才是英语书籍*A. W. Ward and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I, pp. 317-318.。因此,正如王佐良所言,总体说来英国文学“在古英语、中古英语时期,散文收获似乎不及韵文,而散文中的重要著作还是用拉丁文写的”*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第1页。。
16世纪到17世纪初,英国进入了现代英语时期;同时,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英国文学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英国散文蓬勃发展,但本土质朴、平易的风格传统依然处于外来文风的强势之下。首先,拉丁语在学术界和文学创作领域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乌托邦》(Utopia)是用拉丁语完成的。直到1551年莫尔去世之后,这部作品才被拉尔夫·罗宾逊(Ralph Robinson, 1520—1577)翻译成了英文。另一位重要散文作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甚至不相信英语能够持久,除了《随笔》(Essays)等少量作品外,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更为甚者,培根担心使用英语创作会“丧失其名誉”,在生前努力把自己最为重视的个人作品翻译成拉丁文,以图流传于后世。
其次,16世纪的英国文坛拉丁文风的影响也更为强烈。当时广泛流行的是带有强烈拉丁文色彩的华丽散文,如西塞罗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16世纪的英国文学界学习模仿拉丁文的风气“盛极一时,影响及于英语散文的写作”;读书人对拉丁作品字追句摹,形成习惯,以致他们使用英语的时候,“往往忽略拉丁语和英语的区别,把拉丁语的语法强加于英语,致使英文作品读起来似生硬的译作”*徐燕谋:《英国散文的发展》,《外语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2期。。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 1490—1546)就认为拉丁文要比英文优越,他在创作中极力追求拉丁文风,即使是用英语写作,也偏爱西塞罗式的圆周句,在词汇上大量使用源于拉丁文的长字和大字。
关于这种浮华矫饰的散文风格,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大学才子”派约翰·黎里(John Lyly, 1553—1606)的小说《尤菲绮斯或智慧的剖析》(Euphues or the Anatomy of Wit)所表现出来的“尤菲绮斯体”,这被看成是当时英国文坛绮丽、繁琐风格的极端体现。它的语言风格典雅华丽,文辞浮夸又多采用排偶句法:整篇文章犹如一块锦缎,花样套着花样,显得“富丽堂皇,然而真正说出的意思不多”*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第37页。。同为“大学才子”的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 1558—1592)不仅模仿黎里的“尤菲绮斯体”创作了传奇故事《潘朵斯托》(Pandosto),还采用这种文体风格创作了十五本“爱情小册子”*侯维瑞、李维屏:《英国小说史(上)》,第46~48页。。因此培根认为,整个16世纪英国文坛的主导风格就是“追求词语过于内容”;散文家们刻意讲究修辞手段而不关心文章的内容是否重要,这种文风必须加以改革*王佐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外国文学》1988年第4期。。直到17世纪前半叶,英国散文的主导风格还同样是华丽而散漫的“巴洛克”文风。《瓮葬》(Hydriotaphia, or Urn Burial)的作者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 1605—1682)即是巴洛克散文风格的代表作家之一。杨周翰曾评价布朗说,他的文章“隐晦而多义”;“行义曲折,信笔所之,很像浪漫派”*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4~175页。。
通过以上对《钦定本圣经》刊行前英国早期散文的缘起、流变及特点的梳理,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诞生之初英国散文就不仅在语言形式上存在着拉丁语和英语两种不同的作品类型,在风格特点方面也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表达模式:一种是矫饰华丽的散文,明显地透露出它所受拉丁文的影响;另一种则是较为简朴的散文风格,接近于一般英国本族语的节奏*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第339页。。虽然英国散文兼具这两种风格特点,但是拉丁语的散文作品和拉丁文风在英国文坛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以致本土的英语散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多受到贬抑。直到17世纪初期,英国大多数有教养的人都能说拉丁语或用拉丁文写作。因此,在《钦定本圣经》刊行之前英国散文尚不具有鲜明的文学自主性。
二、《钦定本圣经》影响下英国散文的转型与本土化
1611年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钦定本圣经》的刊行大大强化了英国本土散文质朴平易、通俗易懂的风格传统,有力地推动了英国散文风格的转型和本土化。这首先要得益于《钦定本圣经》自身的文学品质和风格特点。不可否认,《钦定本圣经》的文学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对希伯来和希腊语原文圣经艺术的继承,但同时圣经原文的风格特点极好地暗合了英语语言本身的特性,从而使《钦定本圣经》表现出了强烈的英国本土文风特点。了不起的圣经翻译家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 约1494—1536)曾深有感触地说:“比起拉丁文,希腊语与英语更为接近。希伯来语的特点与英语相近的程度则要超过拉丁文一千倍。圣经原文的说法与英语是一个样子,所以在一千个地方你只要逐字翻译就行;但若译成拉丁文,你则必须采取迂回的做法,要费很多工夫才能译得像样,从而保持原文的优雅和美妙,体现原文的意义和准确的理解。(圣经)译成英语,要比译成拉丁文好过一千倍。”*A. W. Ward and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 p. 40.也正因如此,加德纳指出,“在所有的英文书籍当中”,《钦定本圣经》无疑是“最具本土特色,最深入英国文学和英语语言”的*John Hays Gardiner, The Bible as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 11.。
在语言风格上,《钦定本圣经》的英语通常被人们称为“圣经的语言”,它“简洁、率直,虽有古朴之气却并不陈腐难懂。……通篇简单质朴、直截了当的风格极大地矫正了伊丽莎白时代辞藻华丽的散文风气”*Chen Jia,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p. 219.,从而“树立了我们(英国)的民族风格”*John Drinkwater,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London: Newnes, 1957, p. 75.。《钦定本圣经》的译者们吸取之前圣经各英译本的优点,译文朴实无华、明白易懂,且富于形象,韵律也颇有声咏之美,充分发挥了英国民族语言的特点。自刊行以来,它为英国人树立了英语语言“纯净风格的最高典范”*Eugene C. Sanderson, Our English Bible, Eugene: Church and School Publishing Company, 1912, p. 6.,成为后来的英国作家在文学语言和作品风格等方面竞相模仿的榜样。法国学者费尔南德·莫塞(Fernand Mossé, 1892—1956)评论说:“从17世纪起,英国人世世代代从这部书里取得养料。他们在这部书里找到了一种模范文风,既崇高又清楚,它使人能简洁地、纯朴地表达一切。”*费尔南德·莫塞:《英语简史》,水天同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年,第98页。王佐良也认为,“在不同程度上以这种‘圣经体’风格为特色的英国散文作家历代不断”,从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直到20世纪的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等,形成了一个悠久的质朴传统*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第265页。。
首先,17世纪伟大的散文作家约翰·班扬就是直接在《钦定本圣经》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在班扬一生所接触到的书籍中,对他影响最大、最深刻的就是《钦定本圣经》,乃至他的传记作者埃德蒙·维纳布尔斯(Edmund Venables, 1819—1895)称:“从根本上说,班扬就是唯独精通一本书的人,那本最好的书——英语圣经:不仅精通它的精神要义,而且精通它纯洁的风格。”*Edmund Venables, Life of John Bunyan, London: Walter Scott, 1888, p. 169.英国历史学家格林(John Richard Green, 1837—1883)也评述道:“圣经完全成了班扬的生活,以致让人感觉到圣经的词句就是班扬思想的自然表达。他生活在圣经之中,直到圣经的世界变成了他自己的世界。”*John Richard Gree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5, p. 614.
班扬学习《钦定本圣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风的简洁质朴与明晰易懂。在谈到班扬的代表作《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时,格林曾说:“它的英语是所有伟大的英国作家中最为简单、质朴的,但它是圣经的英语。”*John Richard Gree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5, p. 614.约翰·布朗(John Brown, 1830—1922)也认为,班扬在文体上继承圣经的最重要之处就是“语言的清晰、有力”*A. W. Ward and A. R.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VII,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11, p. 168.。其实,班扬早期的作品如《一些福音真理的开解》(Some Gospel Truths Opened)和他用以驳斥教友派信徒爱德华·伯勒(Edward Burrough, 1634—1663)的著作即已表现出了日后他持之以恒的写作风格,运笔轻松、言语直率,绝无生硬造作之感*A. W. Ward and A. R.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VII, p. 169.。而总观班扬一生的作品,它们无不表现出了这些特点,让人总是感到清新自然、通俗易懂。“你从不会感到他是为追求文学效果而写作,更不会感到他的写作仿佛是在完成一项志趣不投的任务。”*Edmund Venables, Life of John Bunyan, London: Walter Scott, 1888, p. 167.因此,班扬的语言,像《钦定本圣经》一样,堪称英语语言的典范。王佐良等人评价说,班扬的散文既不追求拉丁式散文的庄严华丽,也不讲究培根式散文的平稳对称,作者只是力求用大众的语言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是这种以口语为基础的风格最能反映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感情,有力地推动了日后英国散文的发展*王佐良、丁往道主编:《英语文体学引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年,第341页。。
在《钦定本圣经》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从17世纪中叶起英国散文就已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以拉丁文为代表的雕琢矫饰、晦涩艰深的外来文风日渐没落,而英国本土散文质朴平易、通俗易懂的传统风格日益突出,逐渐占据了英国文坛的主导地位。17世纪中叶之后,英国“不同类型的散文各奔前程,但又有一个主导方向,那就是平易,于平易中见思想,见艺术。这平易是一种文明的品质。”*王佐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外国文学》1988年第4期。
18世纪明晰平易的质朴散文进一步延续了英国文坛的主流风格。特别是作为英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和重要枢纽,斯威夫特对《钦定本圣经》的语言风格倍加推崇,并将英国本土“圣经体”质朴散文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在《钦定本圣经》的接受、传播及至走向文学经典的过程中,斯威夫特是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对该译本语言风格的赞誉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人们对于《钦定本圣经》的认识与崇拜。斯威夫特将《钦定本圣经》和《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视为保持英语稳定性的模范和榜样*George William Koon, Language and Character in the Works of Swif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1973, p. 25.。在斯威夫特看来,是英国国教的牧师通过这两部书使英语语言达到了它的最高标准*Ian Higgins, “Language and Styl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nathan Swift, Christopher Fox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54.。
《钦定本圣经》保持了质朴明晰、简洁有力的语言特点和卓越文风,它纯朴却不粗俗,它高雅却不浮华,它通俗易懂又饱含力量,这一切正是斯威夫特一生所勉力追求的语言风格和目标。因此,斯威夫特的作品极力效仿《钦定本圣经》,并出色地展示出了“圣经体”一脉相承的风格品质,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作家兼修辞学教授威廉·斯波尔丁(William Spalding, 1809—1859)就曾说:“斯威夫特的散文作品,没有一样不是原汁原味、强劲有力的撒克逊英语的杰作。”*William Spalding,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 1872, p. 321.乃至“几乎200年过去了,他最好作品的措辞与风格丝毫不显得过时。那时它是最上等的英语,今天它依然是英语中的精品”*Herbert Paul, “The Prince of Journalists”, Bloom’s Classic Critical Views: Jonathan Swift, Harold Bloom ed.,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 2009, p. 188.。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owden Clarke, 1787—1877)也认为:“在我们所有经典作家中,斯威夫特的措词和写作风格是最具英语特点,完全民族特色的。如果手边有一个本土词汇可以使用,他绝不会使用一个外来字眼。他也尽量不用连接性小品词、引入式短语和华丽辞藻,而使用最简单的句子结构。他是地道英语的大师,是利用潜藏隐性语言资源的大师,完美到几乎无人能及。”*Charles Cowden Clarke, “On the Comic Writers of England: VI.-Swift”,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Vol. VII, London: Grant & Co., 1871, p. 437.
循着光辉的榜样,斯威夫特几乎所写的一切都表现出了优秀散文的品质——语言清晰直率,意思朴素明白。抛开浓重的幽默讽刺特点,斯威夫特代表作《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语言就像《钦定本圣经》一样,堪称“简单平易、质朴优雅的典范”,它“非常值得每一位想要书写纯正英语的人好好学习”*James Beattie, Dissertations Moral and Critical, Vol. II, Dublin: printed for Mess. Exshaw, Walker, Beatty, White, Byrne, Cash, and M’Kenzie, 1783, p. 246.。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廉·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高度评价《格列佛游记》的文笔说:“它的文笔也精妙绝伦。至今还没有人能像斯威夫特这样,使用我们这种笨拙的语言,却写得如此简洁、明快而自然。”*毛姆:《读书随笔》,刘文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76页。
可以明显看出,斯威夫特在语言和文学风格方面的主张以及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延续了17世纪《钦定本圣经》的刊行所强化的英国散文的质朴传统。同时,斯威夫特在他说教性与讽刺性作品中对平易风格的提倡也反映出在英国一种关于语言与文学风格的主导的文化态度。他视《钦定本圣经》的语言风格为榜样用以改进和提升英语语言的呼吁,恰与17世纪中叶以降那些倡导简洁直率与朴实平易风格的作品同出一辙*Ian Higgins, “Language and Styl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nathan Swift, Christopher Fox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8.。
随着《钦定本圣经》成为英国专指的圣经,完全控制了英国圣经出版的市场,到18、19世纪,大多数英国作家自出生之日起就受到该译本的熏陶和浸润,其中不少人将其视为文学风格和英语措辞的权威*David Lyle Jeffrey, “The Authorized Versio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The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Peter France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71.。对于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 1816—1855)来说,虔诚的宗教思想及对圣经的钟爱贯穿了她整个的生命历程,这使其成为又一位优秀的“圣经体”散文作家。
正如约翰·梅纳德(John Maynard)所言,无论是从社会环境还是家庭环境来说,宗教对于夏洛蒂·勃朗特都处于她“生活和思想的中心”,具有不容选择的重要性*John Maynard, “The Bront⊇s and Relig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ront⊇s, Heather Gle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95.。夏洛蒂·勃朗特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她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是一位英国国教牧师,信仰福音主义。当时福音教派的家庭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他们对于上帝特别地挚爱与忠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而深厚*Marianne Thormählen, The Bront⊇s and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0.。因此,夏洛蒂·勃朗特自幼就接受了浓厚的宗教信仰的熏陶。夏洛蒂·勃朗特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曾多次表达她对圣经的无比喜爱。1836年5月10日,在她写给好友埃伦·纳西(Ellen Nussey, 1817—1897)的信中说:“我清楚《圣经》中的财富,我热爱它,也崇尚它。”同年12月6日,她又带着无限憧憬的心情向埃伦·纳西写道:“若我能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每天一起共读《圣经》;倘若我们的嘴唇能同时汲饮那同样纯净的仁爱之泉水,我希望、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变得更好。”就连谈到她与最好的两位朋友——埃伦·纳西与玛丽·泰勒(Mary Taylor)——的友谊时,夏洛蒂·勃朗特也以圣经作比。她写道:“事实上,我只有两个坚贞真挚的朋友:你和她。就像我对《圣经》具有强烈的信仰一样,我也深信你俩的忠实和真诚。”*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第10卷)》,宋兆霖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页、33页、129页。夏洛蒂·勃朗特不仅喜爱圣经,她对圣经的知识也极其丰富和深厚。在罗·海德求学期间,夏洛蒂·勃朗特对圣经的熟识与掌握令同学感到惊讶——“夏洛蒂对圣经中所有崇高的段落都极为熟悉,她尤其喜欢《以赛亚书》(Isaiah)。这一点没有那个同学比得过”*Marianne Thormählen, The Bront⊇s and Educ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0-101.。
夏洛蒂·勃朗特对圣经的知识自然带入了她的文学创作。阅读她的作品,人们能够清楚地发现夏洛蒂常常熟练地提及圣经的内容。基斯·詹金斯(Keith Allan Jenkins)全面考察了夏洛蒂使用圣经的情况后得出结论说,在同时代作家中几乎没人能像夏洛蒂·勃朗特那样从容自由地利用圣经*Marianne Thormählen, The Bront⊇s and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56-157.。除了思想内容之外,夏洛蒂的散文还弥漫着浓郁的《钦定本圣经》的语言风格。在代表作《简·爱》(Jane Eyre)中,她不仅反复地引用、暗指《钦定本圣经》,整个作品的风格也由其造就*Catherine Brown Tkacz, “The Bible in Jane Eyre”, Christianity & Literature, 1994 (44), pp. 3-28.。著名圣经研究专家大卫·诺顿(David Norton)曾说:“夏洛蒂·勃朗特不仅仅使用《钦定本圣经》,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其语言就是由它塑造的。”——对于夏洛蒂来说,《钦定本圣经》既是一座可供利用的资源宝库,又是一种风格影响*David Norton,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 as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6.。在诺顿看来,《钦定本圣经》在小说《简·爱》中所体现的风格影响远甚于其见之于约翰·班扬的作品*David Norton,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 as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7.。
19世纪的英国文坛,最能体现《钦定本圣经》散文风格深刻影响的著名作家当属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像班扬一样,罗斯金“几乎完全浸润在圣经里。在自传《往事》(Prterita)中,他列出了牢记在心的那些篇章;遍及他作品的圣经指涉又表明他对该书是多么的熟悉”*John Hays Gardiner, The Bible as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 p. 386.。在专门谈论罗斯金与同时代人阅读圣经的文章中,迈克尔·惠勒(Michael Wheeler)提出,19世纪的作家里面,约翰·罗斯金也许是“最具有圣经文化修养的”;他的散文风格举世钦赞,这“主要归功于《钦定本圣经》的影响”*Hannibal Hamlin & Norman W Jones, The King James Bible after 400 Years: Literary,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34.。事实上,罗斯金本人就将《钦定本圣经》的语言视为他个人风格的主要影响*Alister McGrath, In the Beginning: the Story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and How It Changed a Nation, a Language and a Culture, London, Sydney, Auckland: Hodder & Stoughton, 2001, p. 305.。他说:“要不是因为持续不断地阅读圣经,我有可能将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当成自己英语风格的榜样。”*John Ruskin, Praeterita Vol. I, London: George Allen, 1907, p. 344.
在他著名的自传中,罗斯金将自己圣经风格的养成归功于母亲对他自幼的教育和培养。“我母亲每天都督促我背诵大段的圣经;我要高声地朗读每一个音节,每一个难读的名字,以及从《创世纪》(Genesis)到《启示录》(Revelation)的一切内容,几乎每年一次。正是这种忍耐的、准确的和坚决的训练,不仅使我了解了那本有用的书,也让我获得了吃苦耐劳的力量和文学品鉴力。”*John Ruskin, Praeterita Vol. I, London: George Allen, 1907, p. 2.和夏洛蒂·勃朗特一样,约翰·罗斯金出生在一个福音派信仰家庭。母亲玛格丽特·罗斯金(Margaret Ruskin)具有严肃而坚定的、以圣经为核心的福音派信仰。儿子刚一学会阅读,她就每天教授他圣经,这一过程贯穿了罗斯金的整个童年,一直持续到他18岁进入牛津大学的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 Oxford)*Rebecca Lemon, etc.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Bible in English Literature,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09, pp. 525-526.。对于母亲的安排和教导,罗斯金坚信这是他“所受的全部教育中最宝贵、总的说来也是最必要的一部分”*John Ruskin, Praeterita Vol. I, London: George Allen, 1907, pp. 45-46,49.。因此,正如梁实秋所说:“罗斯金未出生时,其母即奉献他给上帝,使充教士。但是罗斯金天性倾向于艺术,幼时随母读《圣经》,从四岁到十四岁寝馈于新旧约者凡十年,以后罗斯金的散文风格,其丰富的辞汇,语言的语气,带感情的笔锋,都是于此时树其根基。”*梁实秋:《英国文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217~1218页。关于罗斯金《钦定本圣经》般简洁平易、明白晓畅的散文风格,王佐良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一文中有过细致的分析和举例*王佐良:《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外国文学》1990年第6期。,本文不作赘述。
可以说,18、19世纪是英国散文的辉煌时代,也是《钦定本圣经》在英国社会生活中最受重视、最有影响力的时代*Melvyn Bragg, The Book of Books: the Radical Impact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1611—2011, Berkeley: Counter Point, 2011, p. 135.。人们阅读圣经除了相信它是基督教的真理之外,也十分重视《钦定本圣经》的文学品质。此时的英国文坛,质朴平易的散文风格早已深入人心,这一优良传统又为20世纪的大作家萧伯纳(George B. Shaw,1856—1950)、毛姆和乔治·奥威尔等人所传承。当然,英国的文学也从来不是整齐划一、只有一种风格的,“虽说后来也曾出现过晦暗、艰深、堂皇、空洞的文风”,“但是明白晓畅的散文还是强大有力地存在着”*王佐良:《威廉·考拜特的〈骑马乡行记〉》,《英国文学论文集》,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24页。,并一直保持着英国散文的鲜明特色和主导地位。
综上可以看出,英国散文的发展,从17世纪中期之后就“形成了与前此截然不同的新风格,并为自己日后进一步的壮大和走向近代找出了正确的道路,奠定下结实的基础”*戴镏龄:《论科学实验对近代英国散文风格形成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这种“新风格”就是逐渐占据英国文坛主导地位的质朴平易、明晰易懂的英国本土散文风格,这在班扬、斯威夫特和罗斯金等诸多英国杰出作家的作品中一目了然。从此,英国文学具有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和自主性。在这个过程中,《钦定本圣经》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是它促成了英国散文在17世纪的深刻转型,树立了本土散文风格在英国文坛的主导地位,并最终使英国散文同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戏剧作品一样,创造了英国文学的骄傲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