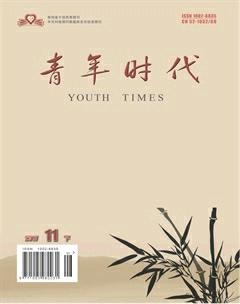在影像中重新发现中国乡村
谢周浦
摘 要:郝杰的电影三部曲《光棍儿》、《美姐》和《我的青春期》重新发现了中国乡村。一方面它不同于第五代导演镜头下与西方全球化对抗的、象征式的中国乡村影像,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第六代导演站在中产阶级立场上,精英视角下的边缘人状态素描。这三部曲构成了连续变化的主体,具有冷峻纪实的风格、通俗情节剧的因素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关键词:影像;发现;中国乡村
一、前言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苏牧对郝杰的长篇处女作《光棍儿》给予了极高评价:“如果说贾樟柯的电影让人们发现中国的城镇,那郝杰的《光棍儿》则让人们发现中国的农村。”近代中国的文学体系中,一直都有乡土小说这一派别,从废名到沈从文到汪曾祺一脉相承,新时期的贾平凹和莫言都依托于一方水土,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在电影创作中,乡土情结也曾风靡一时,1981年,作家刘绍棠曾经在《电影创作》杂志举办的座谈会上提出“乡土电影”的概念,《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老井》等一批作品,将乡土中国作为一个隐喻,完成了向世界输入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形象这一历史影像任务。可以说,中国乡村,曾经作为重要的背景,被中国电影浓墨重彩地描述过。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城市迅速膨胀,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截至2015年底,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了总人口数的56%,比1990年提高了26%。无论是精确到人头的数据,还是目之所及的现实,都揭示了一个现实:一面是城市飞速发展,一面是农村的不断凋敝,城市对农村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农村青壮年人口不断走向城市。这个过程对电影产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城市观影人群迅速扩大,城市人口人均观影频次已经达到中国人均观影频次的两倍。与此同时,都市题材电影幅度增长,而农村题材电影则相对萎缩。在这样的背景下,郝杰的“乡土三部曲”即《光棍儿》、《美姐》、《我的青春期》与传统农村题材电影有着全然不同的面貌,它们直白地揭示了当前中国农村的凋敝,将第六代导演以来的冷峻纪实推到更偏远的公众认知盲区。这是笔者之所以认为郝杰“重新”发现中国乡村的原因。
二、纪实的荒原
自第六代以来,冷峻纪实便成为中国独立导演的標签之一。郝杰的乡土题材电影延续了这个特性,这也是其与第五代导演的农村题材电影最大的区别所在。《一个与八个》、《黄土地》、《边走边唱》、《红高粱》等农村题材电影,通常具有很强的家国情怀,那些导演生活在现代化语境中,在意识形态里将现代与传统作为天然的戏剧冲突。而因为全球化意识的初步形成,他们在生活经验中接收到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的冲击,他们在学习经验中接收的是西方电影的系统化理论。因此,他们将现代性与西方社会建立了一种联系,而将中国视为其对立面——传统。因为近代西方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而将东方及其文化视为“他者”。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套说辞的第五代导演,在文化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主动将自己代入“他者”的地位中,并且试图寻求偏远农村地区的文化,以强化“他者”的异域感。于是,偏远地区的农村,成为第五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的缩影。而在郝杰的电影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国家隐喻。《光棍儿》讲的是城镇化过程中,被遗留在农村中失偶老人的现实问题。性资源与经济资源在这个狭小封闭的社会里虽然都非常稀缺,但却规则地运转着。导演没有像《暖春》、《那山那人那狗》那样,将这些现实问题以抒情的方式展现,而是以近乎自然主义的方式,将真实生活的细节暴露在镜头下。这些细节里涉及农村的性生活,毫不掩饰的脏话和俚语,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这是之前农村题材所无法触及的阴影,但随着郝杰从地下走到地上,《美姐》和《我的青春期》的纪实底色有所衰退,导演试图在前者中融入历史和时代背景,在后者中唤起“80后”的集体回忆,虽然在细节上仍然有惊喜,但在纪实性上,比之处女作退步了很多。
而与第六代导演相比,郝杰在空间上将冷峻纪实带到了中国乡村的角落,但抛弃了前者的中产阶级趣味和精英情结。具体在作品中,第六代导演的《流浪北京》、《安阳婴儿》、《日日夜夜》、《世界》等,虽然也是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但却因为高度个人化的情感表达、意识流的手法、大量隐喻的使用,整个电影显得晦涩难懂。而在郝杰的作品中,人们能看到纪实底色上的通俗情节剧基因。
三、在俗世
郝杰作品的通俗性首先就体现在主题上。这里并不是说选择农村题材就意味着通俗,而是它所关注的主题,不是第六代关注的精英阶层问题,比如《左右》的中年危机,《苏州河》中的存在焦虑,而是最根本的性欲解决。《光棍儿》中的四个老头,通过不同方式宣泄着自己的性欲,把它当作生活的日常;《美姐》主角铁蛋与三姐妹之间的关系,也交织着性欲的萌发和压抑,直到最后的戏剧高潮,矛盾冲突的双方是三妹用性作为诱饵勾引铁蛋,而铁蛋压抑着自己的性欲;《我的青春期》仍然如此,在这部郝杰的半自传电影中,男主角之所以要去当导演拍电影,就是为了和年少时候的性幻想对象共赴云雨。在三部曲中,性冲动成为主角的动机,性冲动的不断受挫或实现,构成了影片的戏剧冲突,串联起影片的叙事线。
这种通俗性还体现在叙事结构上。新生代新锐导演往往敢于在电影叙事上进行探索,如贾樟柯《二十四城记》和《海上传奇》里尝试将虚构与纪实相结合的叙事,《世界》和《天注定》的碎片化叙事,而郝杰更习惯传统的单线叙事,一方面让故事变得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因为受限于叙事角度的单一,往往很难让观众超越主角视角,对影像的思考也容易停留在故事层面,观众很难超越个人命运洞悉一个时代的特征。导演在《美姐》中试图强化故事的时代变迁,但因为叙事线的单薄,视野的局限,会让人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与叙事结构相对应,郝杰在镜头语言上也并没有太大突破,不同于“90后”导演毕赣在《路边野餐》中的长镜头尝试,郝杰对影像本身的实验性并不感兴趣。与学院派讲究章法的运镜方式不同,郝杰更加随心所欲,在《美姐》中运用上下摇摆的鱼眼镜头,及其夸张地隐喻男女之间的欢爱,给人造成一种生猛的直观印象,这让他的镜头语言更容易被大众理解,但相应地缺少一些回味。
四、浪漫的起点
在第六代的纪实基调上,郝杰讲了一个世俗化的故事,并且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更增添了作为个人色彩的浪漫主义情怀。他镜头下的乡村,看似冷峻原始,但这里的天地山水,都浸透着情感,是一种不同于第五代的,独属于导演个人的怀旧。导演明确意识到,“中国的农耕文化可以说是正在被连根拔掉,现在有很多农村都已经空了。我现在回到家里去,发现村子里已经没人了,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农村里没有小孩,也没有中年人,更没有青年人,农村生活已经是一种即将灭亡的生活方式,我回去之后已经没有童年的记忆了,大家都不在了,都出去打工挣钱了。在这些都没有之前,我想能够拍些电影,把它们记录下来。”。因此,他在《光棍儿》中选择记录,在《美姐》中,加入了对曾经农村生活的想象——民间曲艺二人台。作为符号,二人台的风靡景象,还原了导演对农村文化生活的想象。在《我的青春期》中,基于個人视角的留恋和不舍。但这些怀旧,与第五代将中国农村作为逝去的传统来缅怀又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是,在《百鸟朝凤》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被设置成矛盾冲突的双方,导演的价值观念和倾向性,在作品中表露无遗;在《光棍儿》中,郝杰并没有对传统农村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美化,转而采用一种自嘲和冷眼旁观的方式,记录下时光的轨迹。这种若即若离的羁绊,伴随着导演对自身身份的追寻,为影片带来言而不尽的复杂乡愁。
然而,这种个人化的乡愁在导演作品中被不断强化,从《光棍儿》的隐隐约约,到《美姐》中的集中展示,再到《我的青春期》中的大声宣告,以至于失去了其丝丝缕缕的美感,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或许这也是面对商业化市场不得已的选择——当个人情感被放大成集体回忆进行消费的时候,它就再也不属于个人了。
参考文献:
[1]贾战伟.从乡村到乡土的嬗变——郝杰乡土电影的美学特征[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2).
[2]刘绍棠.建立乡土电影[J].电影创作,1981(6).
[3]崔保国.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何英.粗粝影像下的生存真相——郝杰电影作品研究[J].电影新作,2015(2).
[5]萧薇.《美姐》:一曲乡间骑士的“告别”情歌[J].电影艺术,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