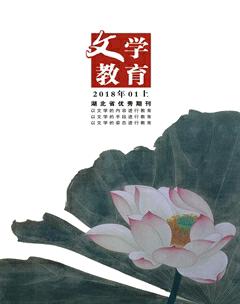我一直追求有诗意的小说
周聪
朱山坡,1973年8月出生,汉族,广西北流市人。早年主要写诗。出版有长篇小说《马强壮精神自传》《懦夫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灵魂课》《喂饱两匹马》《把世界分成两半》《十三个父亲》等,曾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上海文学》奖、《朔方》文学奖、《雨花》文学奖等多个奖项。现为广西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2017年岁末,我受《文学教育》杂志社委托,对朱山坡进行了书面访问。
周 聪:山坡兄好,感谢兄能接受我的采访。先说几句题外话,大约是九年前,我在中文系的课堂上读到了兄的短篇小说《小五的车站》,小五的返乡之旅让我回忆起一次雨夜回家时的情景:一个下午,我和两个堂哥骑摩托车去镇上打篮球,傍晚回家,发现摩托车车胎被钉子扎破了,镇上的修车店也都关了,顿时狂風大作,我们推着车子沿着河堤往回走的途中,闪电划过夜空,河堤两岸的野草像蛇的身子一样向前蹿。我想问的是,《小五的车站》是否“藏”有兄的某些童年经验?能否结合一两篇小说谈谈童年经验对兄的创作有何影响。
朱山坡:童年比较漫长,时间过得很慢,思想单纯,对经历过的许多事情印象深刻,而且历久弥新。童年记忆对作家影响很大。我的很多小说都受童年经历的影响。刚才你提到的《小五的车站》确实是来自少年时代的一次经历,第一次从省城乘坐火车回家,火车上的广播声音不是很清晰,我又听信了一个怀抱孩子的妇女的话,结果火车过了头,跑到另一个县去了。傍晚一个人在一个陌生而遥远的火车站,懊悔而害怕。还有一篇短篇小说《天色已晚》,是写小时候到镇上看电影的经历,电影散场后才发现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而且好久还不能从电影中走出来,站在寂寥的街头茫然四顾,不知所措。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里许多细节是童年记忆,比如台风、洪水、捕青蛙、卖冰棍、逃票进电影院等等,都是自己的经历。对跟我有类似经历的读者,记忆很容易被唤醒,从而引起共鸣。
周 聪:我注意到,兄的不少作品中都写到了“死亡”,比如《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小男人护送哥哥尸体回乡,《灵魂课》中寄存骨灰的“灵魂客栈”,《两个棺材匠》中“我”子承父业为死者做棺材,《送口棺材去上津》中“我”应母亲之嘱给临死的人送棺材……可以说,对“死亡”这一话题的思考一直贯穿在兄的写作之中。能否请兄谈谈文学中的“死亡”话题?
朱山坡:死亡是文学,还有电影、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说话。死亡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触目惊心,刻骨铭心,沉重,悲痛,难以言说。探索死亡真相使作家乐此不疲,因为这个话题是无穷无尽的,使人从中获得情感的力量和表达的深度。有人提醒我说,你“写死”了很多人。这让我也感到茫然。我能为自己辩护的也就是:我也“写活”了很多人。
周 聪:在兄的博客中,我读到了不少的诗作,比如《这棵树比另一棵树要高一些》《下午很大》《入侵者》《晨光中的泗水河》《你是我的太阳》《历史,在这里有点乱》等等,这些作品多为抒发日常生活的点滴感悟,或游历一山一水之间,或重温亲情的美好,或在阅读一本书时萌生出瞬间的思考,不一而足。我感兴趣的是,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在写作时带给兄的感受有何差异?或者说,兄在选择这两种文体时,语言修辞、叙事策略等方面是否会进行一定的调整和变化?请具体说说。
朱山坡:你应该已经发现,我的大部分诗都是叙事性很强的诗。我喜欢把一些无法形成小说的碎片化的细节和富有诗意的场景写成诗。写诗酣畅淋漓,语言轻快夸张,天马行空,富有弹性和节奏感,侧重情感的饱满和充分表达,不必考虑细节的真实和逻辑。写小说必须逻辑严密,语言简洁,讲究起承起合,注重细节的真实和故事的整体性。小说也可以有诗意,但必须服从于故事。有诗意的小说一直是我的追求。有一种情况是,我的一些小说是先有诗,然后再演绎成小说的。
周 聪:确实,兄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叙事诗,节奏感也不错。我们再来谈谈《十三个父亲》,这本书收录了兄的十三个写父亲的短篇,构成了一个父亲的文学形象谱系,他们慈爱、异想天开、颓废、愤世嫉俗……我尤其喜欢其中的《鸟失踪》《骑手的最后一战》《爸爸,我们去哪里》三篇,那个与鸟为伴、去南方寻找死去的儿子喜宏的父亲,那个骑着马追火车消逝在黑暗之中的父亲,那个让给女人观看死刑犯吃喝场面机会的父亲,都给我带来极大的审美震撼。这些虚构的父亲形象,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光辉伟岸父亲的刻板印象,父亲变回真实的人,他也有喜怒哀乐。在兄接下来的写作中,是否还在继续捕捉“另一种父亲形象”?能否透露一下这个系列的创作计划。
朱山坡:关于父亲的小说我已经写得够多了,差不多都集中在小说集《十三个父亲》里,各种个性的,我奢望其中一个能成为经典形象。文学史上关于父亲的小说汗牛充栋,我只是努力添枝加叶。但我不打算刻意写更多的父亲,除非有新的发现,因为我有更感兴趣的人物需要呈现。
周 聪:兄的长篇小说《我的精神,病了》一直以来是我钟爱的作品,因为它揭示了当下这个时代的群体症候。这个长篇讲述了一个从农村走出的青年马强壮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保安王手足的那一耳光,给马强壮以重创,马强壮从此在精神困境的迷途中迷失了,他开始在城市生活中走上了一条自救与自弃的道路。兄说这部小说“真正关注的是人的内心,是一部纷繁芜杂时代的精神荒诞史”,我是非常赞同的。我想问的是,在兄看来,马强壮(个体)被时代碾压后的精神出路在哪里?一个顶着强壮的身体的个体在纷繁复杂的时代面前是孱弱不堪的,那么,其精神对抗的意义在哪?
朱山坡: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像马强壮这样的出身于农村的人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他们有自尊,有追求,有责任心,任劳任怨。但是,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不少人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个体在强大的秩序里微不足道,无从反抗,一旦沦落,便滑向枯萎。马强壮努力过,奋斗过,但屡战屡败。他还可以继续挣扎,奋斗到底,可是他选择了放弃。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脑子里“兵荒马乱的”,连自己都掌控不了了。我们既鼓励百折不挠,屡败屡战,也允许有人中途放弃。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胸怀容纳失败者,原谅自暴自弃。我想说的是,放弃是一种“软对抗”,意味着跟理想、跟现实妥协,跟自己达成和解。endprint
周 聪:细读兄的一些作品,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那篇2010年发表在《文学界》上的短篇小说《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它与卡佛的短篇《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和《学生的妻子》在情节上就有相近之处。具体说来,《我可以看见最细小的东西》讲述了“我”听见细微的声音无法入睡,起来发现山姆在撒药粉杀鼻涕虫,和山姆交谈几分钟后“我”回去睡觉,躺下了却发现院子门还是没有闩。《学生的妻子》中主人公南因为迈克的呼吸声而彻夜失眠,她可以听见许多常人无法觉察到的细微的声音。兄的《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讲述了一个老太太多次听到呼救声并报警,却找不到声音的源头,最终民警小宋经过排查找出声音来自一个废弃的小水塔。小说中老太太对声音的敏锐感知,与卡佛的这两篇小说如出一辙。事实上,对于声音敏感的捕捉也同样在卡佛的其他作品中有着呈现,比如诗歌《窗外的人》,就可以印证《学生的妻子》这篇小说,体现出卡佛对细部的敏锐观察和感知能力。我知道兄读过不少卡佛的作品,能否请兄谈谈对卡佛作品的理解?
朱山坡:我读卡佛小说时更在意他的叙述,他很简洁,点到即止,意味深长。我寫《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时没有联想到他的上述几篇小说,但也许有神似之处。我这个小说是出自一个真实的新闻故事,说是一个人老是听到有人呼救,但又不知道来自哪里。别人以为他是幻觉。但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找声音的来源。其实它是一个寓言。因为我们知道,世间呼救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在呼救。声音来自内心,也许是来自邻居或远方,也可能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向卡佛致敬。
周 聪:再来谈兄的《鸟失踪》(《天涯》2009年第3期),在我看来,那个对鸟无比迷恋的孤独父亲形象,颇有点柯希莫的固执和倔强,这个短篇在氛围的营造上与《树上的男爵》第24节中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也曾注意到,兄在《把世界分成两半》的“后记”《向着经典写》中表露过对川端康成的推崇。可以说,这些小说大师是兄写作的精神参照与坐标,能否请兄推荐一两部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家作品?
朱山坡:我曾经对川端的《伊豆的舞女》推崇备至,常常反复阅读。他的其他小说我读得不多,但有一篇就够了。我更喜欢马尔克斯和奈保尔。马尔克斯的全部,奈保尔的短篇集《米格尔街》。天才式的叙述。
周 聪:我曾在《南方文坛》上读到过一篇题为《为民间野生人物立传的叙事探索——朱山坡小说创作论》的论文,该文梳理了兄的小说创作轨迹,但我注意到,其中没有涉及《我的精神,病了》,这个长篇后来被改名为《马强壮精神自传》在漓江出版社出版,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呼应了之前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懦夫传》。我很好奇,书名的改变是受那篇文章的影响,还是另外的原因?
朱山坡:修改书名是因为出版审查员的意见。
周 聪:最后一个问题,在《风暴预警期》后,还有没有在写新的长篇?如果有,能否透露一下题材。谢谢山坡兄。
朱山坡:《风暴预警期》是我的重要作品,到现在我仍然没能完全从它的创作状态中走出来。但近来还是完成一个长篇小说《绿珠》的初稿。写晋代美女绿珠的爱情故事,是一部命题作文式的写作,不过,还是有点成就感和获得感的。正在构思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还在自我论证中。每一个小说写之前我都得自己反复论证是否有意义。如果构思被自己否定了,就另起炉灶,直到找到值得写的故事。
周 聪:谢谢山坡兄的回答,我们也期待兄的《绿珠》早日面世。谢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