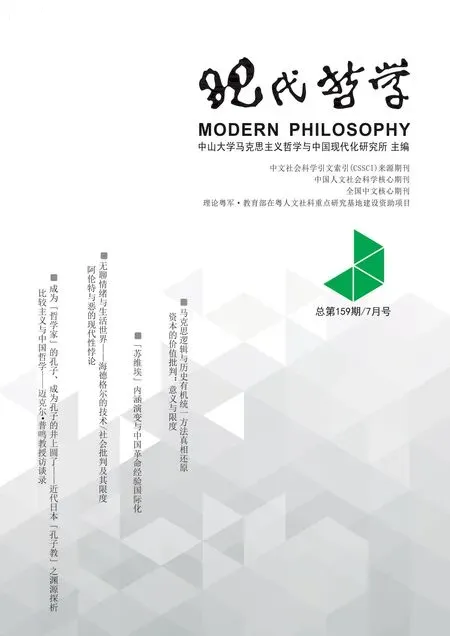《中论》说诸法不成的两个理路探析
袁军荣
《中论》广说诸法不成以显无生之义,大致理路概括为二。首先是对治性的,重点在于说明对手何以是不正确的。这是通过展示各种边见内在的矛盾来说诸法不成。比如《观涅槃品》开篇说:
若一切法空,无生无灭者,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槃?
若诸法不空,则无生无灭,何断何所灭,而称为涅槃?*龙树菩萨造、梵志青目释、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中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1995年,第184页。相似的偈颂可见于《观成坏品》:“若法性空者,谁当有成坏?若性不空者,亦无有成坏。”(同上,第152页。)《观缚解品》:“诸行往来者,常不应往来,无常亦不应,众生亦复然。”(同上,第115页。)常与无常亦是两边,无论业行(或众生)是常,还是无常,都不成相续往来的流转。吉藏云:“往来之本不出人法,此二若实,要堕断常。常则天人无交谢,静然不变,何有往来;无常则体尽于一世,谁复往来耶?”([唐]沙门吉藏撰:《中观论疏、中论科判》,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 1986年,第278页。)
第一颂的一切法空,是外道见,这里的“空”就是一无所有;若一切法无所有,如“第二头”*“第二头”指子虚乌有之事,出自《观三相品》:“若法是无者,是则无有灭,譬如第二头,无故不可断。”(《中论》第2卷,前揭书,第72页。)一般,自然没有生灭可言。第二颂的“不空”是与一无所有相对的“实有”,实有则自在恒住,也无生灭可言。如此,实无、实有俱是两边,均不成生灭。诸如此类的论破方式广见于《中论》各品。这样的论破方式在破斥邪见方面有其殊胜的作用,但很容易引起这样的想象:实有、实无二见固然与生灭相违,但在实有实无之外,是不是还有生灭可求呢?或者说,在破邪之外,是不是还有正见留存呢?因为它不能让人免除这样的想象,所以若按吉藏“三中说”*《三论玄义》立“四中”,《中观论疏》说“三中”,所谓对偏、尽偏,及绝待中。《论疏》曰:“此三何异?答:玄意(笔者按:应为玄义之‘义’)已明,今重略叙。”(《中论序疏》第1卷,[唐]沙门吉藏撰:《中观论疏、中论科判》,前揭书,第3页。)可见《论疏》中的“三中”说是《玄义》的撮要,今权且采用《论疏》的说法。来判定,诸如此类的论破可谓只得“尽偏中”、未达“绝待中”,尚不是中道的究竟处。之所以说“尽偏中”不究竟,是因为“虽尽于偏,而有于中”*[唐]沙门吉藏撰:《中观论疏、中论科判》,前揭书,第3页。。《中论》则是“尽偏而不留中”的。这尽偏而不留之“中”,吉藏强名其为“绝待中”。对此,龙树到底是如何做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把《中论》说诸法不成的第二个理路展示出来,它不同于前一理路的地方在于:它以缘起本身为考察对象,在世间共许的缘起法上直接显示诸法不成。
一、《中论》中的一组特殊论式
“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是对缘起最适切的说明,这一偈颂恰当地表达了诸法彼此相待的缘生性,《中论》确有许多文句是以此形式出现的。但还有一类颂词,说的虽是缘起,但这类颂词的落脚点却是“缘生”的“不成”。通过这些偈颂,龙树似乎表达了对诸法缘生性的极大怀疑。比如,《观因缘品》中,龙树在广说四缘生*四缘是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所谓“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中论》,前揭书,第28页。)四缘是诸法生起的四个条件,又是诸法生起的四种方式。在《观因缘品》中,龙树谍定“四缘”之后,广说四缘生不成以显无生之旨。不成后说:
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出。*《中论》,前揭书,第32页。
在本品结束,龙树又总结到:
果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以果无有故,缘非缘亦无。*同上,第32页。
在第十七品《观业品》中出现了和上一颂相似的论式:
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同上,第128页。
第二十品《观因果品》也有一颂:
是故果不从,缘合不合生,若无有果者,何处有合法。*同上,第148页。
倘若认为诸法是因缘生的,论主为何说“果(业)不从缘生”,为何说果不从缘的“和合”生呢?这让人颇费思量。下面的几句颂词,说的是彼此相待的因缘性。和上面偈颂不同的是,它们探讨的只是彼此相待的互生,并不涉及缘合生果的问题。但论主对彼此相待的因缘同样表示了怀疑。《观六情品》中,龙树说:
离见不离见,见者不可得,以无见者故,何有见可见。*同上,第44页。
一般认为,“见”和“见者”是相待而成的,“离见”无“见者”可得,这不难理解。但是,怎么“不离见”,“见者”也“不可得”呢?相似的论式还有第二品《观去来品》:
去者则不去,不去者不去,离去不去者,无第三去者。*同上,第35页。
第六品《观染染者品》:
若无有染者,云何当有染,若有若无染,染者亦如是。*同上,第53页。
第十品《观然可然品》:
因可然无然,不因亦无然,因然无可然,不因无可然。*同上,第90页。
“去者”的“不去”,“染者”的“无染”,“因可燃无燃”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更耐人寻味的是,论主得出结论的方式。且看《观去来品》中的一颂:
云何于去时,而当有去法,若离于去法,去时不可得。*同上,第34页。
此颂后半颂说的似乎是“去法”与“去时”的相待而成,前半颂却是对“去时去”的反诘,其意思是“去时无去”。而且,论主是以后半颂作论据来证成前半颂“去时无去”这一结论的。按一般的理解,“去法”和“去时”是相待而成的,论主怎么能以“去法”和“去者”的相待来说“去时无去”呢?《观颠倒品》中,这一论证方式更加明确:
不因于净相,则无有不净,因净有不净,是故无不净。
不因于不净,则亦无有净,因不净有净,是故无有净。*《中论》,前揭书,第167—168页。
这两颂的前三句都在说“净”与“不净”相待的因缘,但第四句的结论却是“无有净”“无有不净”。而且“无净”“无不净”的结论都是从“净”与“不净”的彼此的相互因待得出的。《观时品》也是如此,对过、现、未时间三相,龙树说:
不因过去时,则无未来时,亦无现在时,是故无二时。
以如是义故,则知余二时,上中下一异,是等法皆无。*同上,第140页。
第一颂的前三句说因过去而有现在、未来,第四句的结论却是“是故无”现在与未来“二时”。像“不离见,见者不可得”、“去时”的“不去”、“去者”的“不去”、“染者”的“无染”、“因可燃无燃”等诸如此类的偈颂都是在彼此相待的因缘上直接说彼此的不成的。诸法“相待而成”,这本是世间所共许的,但这些偈颂分明在说“相待而不成”。
二、《中论》对彼此相待的难问
若从彼此相待的一般性来总结论主的论证,可把上面的论式写作“因此有彼,故无彼”,或改写为“因彼有此,故无此”。不论如何,“因此有彼,故无彼”这一论证显得过于简单。下面结合《观然可然品》*“燃”和“可燃”的关系就是“火”和“薪”的关系,由波罗颇蜜多罗翻译,清辨所做《般若灯论释》中,把该品品名译作《观薪火品》。相较而言,鸠摩罗什的翻译更能凸显“燃”与“可燃”的相互因待性:“燃”因“可燃”才能成“燃”,“可燃(薪)”因“燃”才能成“可燃”。的相关偈颂,进一步说明龙树是如何从彼此相待的因缘着手,来说明彼此俱无的。该品虽然就然可然立论,但依论主之义,该品的论破是通一切法的,因为在本品最后,论主曾经明示:
以然可然法,说受受者法,及以说瓶衣,一切等诸法,若人说有我,诸法各异相,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味。*《中论》,前揭书,第91页。
可见,论主此处是以可然(燃)和然(燃)为喻,类比五阴和我、泥和瓶、缕与衣、受与受者、作与作者等一切具有相待关系的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本品的论破方式当作一个范例,来论破一切相待关系和一切“相待而成”的法。龙树对彼此相待的论破是通过设置三组两难困局进行的。
(一)“复成”与“无因”的两难
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先定有何法,而有然可然。
若因可然然,则然成复成,是为可然中,则为无有然。*同上,第88—89页。
第一颂前半就是“此有故彼有”的标准论式。这里,龙树并不把“此有故彼有”当做一个无须论证的前提,而是把它当作有待考察的对象来难问:如果说是因“可燃”而有“燃”,因“燃”而“有可燃”,那么到底是先有燃而后有可燃,还是先有可燃而后有燃呢?
接下来的一颂,龙树对此中潜在的矛盾进行展示。如果说因“可燃”而有“燃”的作用,那么就有问题了:既然“可燃”是因“燃”而成为“可燃”的,在“可燃”之前必有“燃”法已经成就;既然“可燃”前已有“燃”法成就,还有必要用“可燃”再去成立“燃”吗?这样做岂不是多此一举(复成)!这里,龙树说的“复成”之过,类似于逻辑学的循环论证,像在偈颂中所说的,在论证中总有人会犯这样的错误,即用一个尚待成立的“此”法去成立“彼”法,又用“彼”法成立“此”法。龙树指明其中的问题:你本想用“此”成立“彼”,但又说“此”的成立本就离不开“彼”,“彼”若已成,何必再用“此”成立“彼”呢?
第二颂的后两句,颂词太简单。若展开来讲,应是这样的:如果要避免“复成”之过,除非承认“可燃”的成立不需要“燃”法;如果“可燃”不需要“燃”法就成为“可燃”,那么“可燃”的成就便成“无因”的了。若无因,则断不可成。同样,如果用“燃”法成立“可燃”,也会出现相同的问题。论主想避免“复成”之过,却出现“无因”之过;若要避免“无因”之过,却会出现“复成”之过。在“复成”和“无因”之间,论敌一定会出现一个,这是对手不得不面对的第一个两难困局。*《观去来品》中,龙树用了相似的论证:“若言去时去,是人则有咎,离去有去时,去时独去故。若去时有去,则有二种法,一谓为去时,二谓去时去。”(《中论》,前揭书,第34页。)第一颂的“离去有去时”说的是“无因”之过,第二颂中的“则有二种法”说的是“复成”之过。
(二)“未成”与“已成”的两难
若法因待成,是法还成待,今则无因待,亦无所成法。
若法有待成,未成云何待,若成已有待,成已何用待。*《中论》,前揭书,第89—90页。
如果像“燃”“可燃”的关系一样,此法因待彼法而成,彼法因待此法而成,龙树认为还会出现另外的问题:既然彼此是相待而成的,那么在此法、彼法成立之前,就应该没有“法”来成立“相待”的关系;反之,既然“相待”的关系无从成立,怎么可能有因“相待”而成的此法、彼法呢?这又是一个两难的困局:既然法是相待而成的,在没有法的情况下,是什么作为相待的对象呢?没有相待的对象,怎么会有“相待”的关系呢?如果说先有法后有法的相待,那么既然已经有了法的存在,还用得着相待来成立此法、彼法吗?
在这两个偈颂中,龙树批判了相待的彼此二法的实存性以及法的相待关系。不仅“此”与“彼”是相待的,而且“相待的彼此”和“彼此的相待”也是相待的。“相待的彼此”尚不得成,“彼此的相待”焉能成就?或者说,“彼此的相待”尚不得成,“相待的彼此”焉能成就?
(三)“俱成”与“非俱”的两难
如果说的相待而成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先有此法然后以此法成立彼法,也不是先有彼法然后以彼法成立此法,而是彼法和此法在相待中同时成就,就没有以上问题。这个辩驳看似有道理,实则对问题的解决没有帮助,虽然在《观然可然品》中龙树没有对燃与可燃的“一时俱成”做出批评。但是在《观染染者品》中,论主提到了这个问题:
染者与染法,俱成则不然,染者染法俱,则无有相待。*同上,第54页。
染者和染、可燃与燃的相待关系是一样的。此颂中,论主说如果染者和染法同时成就,则失“相待”之义,青目解释说:“若染法染者一时成则不相待。不因染者有染法,不因染法有染者,是二应常,以无因成故。若常则多过,无有得解脱法。”*同上,第54页。这种解释的核心是“一时成,则不相待”。依青目之意,若说二法是相待的,此二法必有相生的关系;若二法同时但不相生,则失相待而成之义;若失相待而成义,染者与染法则有“无因”而成的过失。再者,若同时但不相生的二法就是相待,同时存在的法那么多,岂不都是相待关系吗?因此,只要是相待的,就是相生的;只要是相生的,就不能是同时的。*龙树所谓的因果是就法的相生关系而言的,若是相生的,就不是同时的。这不同于西方哲学谈论因果的方式,即把因果放在两个层面来谈,一是事实层面,一是逻辑层面。以父子关系为例,从事实说,一定是先有父亲,再有儿子;但就逻辑而言,如果没有儿子,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父亲的,因此父与子应是同时成立的。严格来讲,说“从逻辑层面来说,父与子是同时成立的”也不对。因为西方的形式逻辑与时间无关,它们是一套先验的符号系统,与经验无关,也无涉于时间,谈不上“同时”或“不同时”。龙树所谓的因果是就着众生误认为真实的、因缘和合的世界谈的,他对逻辑层面的“同时因果”并无太大兴趣。如果相生的二法不能是同时的,也就无法从上面的两难境地中逃出来。最后,龙树的结论是:
因可然无然,不因亦无然,因然无可然,不因无可然。*《中论》,前揭书,第90页。
综上,通过这样三组两难困局,龙树以世间共许的缘起为考察对象,在彼此相待的缘起上抉择彼此的不成,否认了缘生彼此的真实性。
三、《中论》破不破缘起
看了上面的论破,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龙树的做法是不是破坏了因缘法?缘起是佛教各宗共许之义,相传佛陀也是体悟十二支缘起入道的,龙树真的破了缘起吗?对于这个问题说是说非,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缘起虽为佛教各宗所共许,但依佛所说,缘起的甚深处却是难知难了的。《杂阿含经》二九三经说:“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倍复甚深难见,所谓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寂灭、涅槃。”*[南朝宋](印释)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6页。依佛意,这缘起的甚深处是寂灭无生的涅槃。在龙树看来,依文解义的声闻学者并没理解缘起的甚深义,因其不见缘生甚深处之无生。“谓有定性之生,此是不知第一义谛。既不得第一义,亦不知世谛。”*[唐] 沙门吉藏撰:《中观论疏、中论科判》,前揭书,第98页。龙树作《中论》的目的之一,就是引领声闻学者回小向大,令其领悟缘起的甚深义。对于《中论》的旨趣,青目这样说:
(佛陀)先于声闻法中说十二因缘,又为已习行有大心堪受深法者,以大乘法说因缘相,所谓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一不异等,毕竟空无所有……佛灭度后,后五百岁像法中,人根转钝,深著诸法,求十二因缘、五阴、十二入、十八界等决定相,不知佛意,但著文字,闻大乘法中说毕竟空,不知何因缘故空,即生疑见……龙树菩萨为是等故,造此中论。*《中论》,前揭书,第24页。
在对缘起的看法上,大乘学者和声闻学者的所见确有深浅之分,声闻学者以“缘生缘灭”说缘起,大乘行者以“不生不灭”说缘起。具体到“彼此相待”的关系,声闻学者虽然看到彼此的相互因待性,但认为实有彼此、实有彼此的相待,没有看到彼此的相因相待和彼此实有性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从这种矛盾出发,进一步领会“相待的彼此”和“彼此的相待”的“假名”义。另一方面,声闻学者虽然也承认“此无故彼无”,但认为彼此还是可以有的,彼无只是因为此无,此有彼自然就有。在这种理解中,“此无故彼无”似乎是条件从句,他们并没有对彼此的相待做更深入的考察,也不能免除对相待诸法实在性的想象。在大乘学者看来,彼的无不是因为此的无,彼此相因相待的当下,就是彼此俱无。《观因缘品》的一颂,是对这一问题最简明的概括,该颂说:
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说有是事故,是事有不然。*同上,第31页。
《青目释论》说:“诸法从众缘生故自无定性,自无定性故无有有相,有相无故何得言有是事故是事有?”*同上,第32页。偈颂中“有是事”是因有,“是事有”是果有,“有是事故,是事有”是“此有故彼有”的另一版本。诸法无自性,所以说“有是事故,是事有”是不然的,即说“此有故彼有”是不然的。“此有故彼有”的“不然”,当下就是“彼此俱无”,这与广见于《般若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分明是同一理路,五蕴的不成当下即是空。
正是因为“深著法相,但著文字”的声闻学者耽在定性缘起上,龙树才把世间共许的的缘起作为考察对象,在“因此故彼”的相待上直接说彼此的不成。至于《中论》破不破缘起,吉藏给了很好的回答:“斯乃是观正因缘明中道,云何名破因缘耶?”*[唐] 沙门吉藏撰:《中观论疏、中论科判》,前揭书,第11页。在对《观因果品》的疏释中,吉藏又自问自答:“此品为破因果,为申因果耶?答:品品之中,皆有申破二义。求内外大小性实因果皆悉无从,故名破因果,以计性实之人,即破因果义,故论主须破之。二者,性实因果既除,始得辨因缘因果。即称因缘,则因果宛然而常寂灭,故因中发观,则戏论斯忘也。”*同上,第328页。依吉藏看来,不是龙树破了缘起,倒是“计性实之人”不解缘起。
话虽这么说,但显示诸法不成的第二个理路毕竟不同于第一个理路,第一个理路以邪见为考察对象,而第二个理路则以缘起为考察对象,它的申与破都是在对世间缘起的考察上进行的,因此不免引起这样的担心: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有“所破太过”的危险?正因有这样的担心,后世某些中观师认为:在辨破世间法之前,有必要对“所破事”进行抉择。他们认为:要破除的不是缘起诸法,而是对诸法“自性有”生起的“实执”,“若未了知所破量齐破太过者,失坏因果缘起次第,堕断灭边”*更敦群培著、智严译:《中观甚深心要善说——龙树意趣庄严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附录第135页。其中的“量齐”就是界限的意思。。这样的担心固然不无道理,可能龙树也不会反对:要破的不是缘起,而是对缘起诸法产生的“实执”。问题是:无始以来的实执心普遍存在于众生的一切认识中,这种直感的实在性无时无刻不在缘起法的显现中起作用,对处于凡夫位的众生来说,如何能从栩栩显现的缘起法中拣择出“自性”来破除呢?举例而言:假如一个人想从盐水中煮出盐来,他直接对盐水加热就可以了。若此人想,我要得到的是盐,千万不能把盐毁了,我只应直接对水加热,方能不坏吾盐。试问:若盐水未分,如何只煮水不煮盐;若盐水已分,又何必加热以求盐?“只破自性,不破缘起”,这样的想法看似有道理,在实际操作上根本行不通。在《中观甚深心要善说》中,更敦群培引章嘉国师《证悟之歌》的话反讽这些中观学者,真是“栩栩显现任其存,偏寻兔角来破除”*同上,第20页。。他认为,在抉择性空之前,无需对栩栩显现的法作“自性”简别,要一并以正理检验其真实性。
如果把黄金、石土、草木等不加分别地一齐投入火中,能燃烧的就会烧掉,不会燃烧的就会余留下来。同样地,把所有的显现毫无分别地用正理破除,剩下的就只能是如幻之物。既然留了下来,它们必然会继续存在。既然正理不能伤害到它,那又为何要把如幻的缘起法从一开始就拣择出来呢?*同上,第21页。
如果不明“所破事”,会不会落入“断见”的泥潭?更敦群培认为,这样的担心也是多余的。
有些人害怕如果瓶子、柱子等被正理破除后,什么都没了,就会落入断见。这是一种毫无必要的担心。亲见瓶子就在面前,凡夫俗子的心里怎么可能产生“此瓶根本不存在”的断见想法呢?就算有这样的想法,但他明确地知道这个瓶子是可见、可触碰的东西,如果同时有“此瓶虽现于我面前,但却根本不是如其显现那样存在”的想法,这即是空有不二的中观见,也就是明白,事物并非如其显现那样存在——这怎么可能是断见呢?*同上,第20—21页。
从佛教学基本格局来看,众生因被无明障蔽才有生生世世的流转,佛教修行的目的就是消除业障超越生死,使众生不再在生死中流转。因此,三期佛教无不广说无常、无我、无生之义。若从佛教本怀去理解《中论》的两种论破方式,就能明白《中论》为何对世间缘起的批判得如此彻底了。《中论》虽以缘起为论端,但却无意捍卫世间缘起,世间自然有世间人来成立。龙树的任务反倒是要指出,世间错认为实的诸法何以是不成立(性空)的,若没有对世间法毅然决然地拒斥,对无常、无我、无生的法印是很难生起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