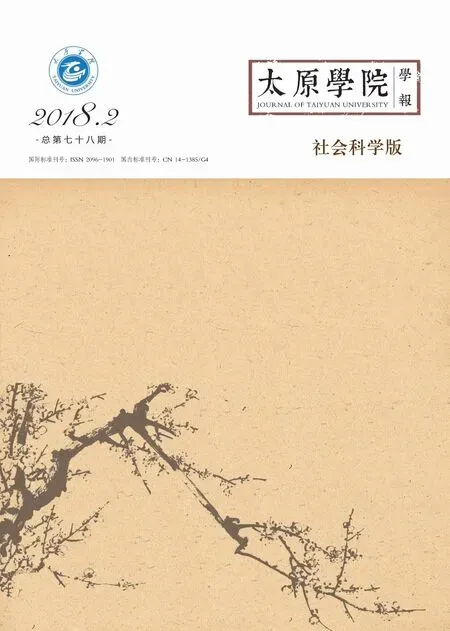质疑动产让与担保制度的三个通说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革新经济体制以来,市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金融交易运作渐趋频繁。出于对信用授受的担忧、风险规避的考虑,实践中萌生出大量以设定担保为基础的交易,除典型担保外,尤以让与担保为甚。然而,法律具有滞后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以动产让与担保为基础的信用交易,俨然成为物权法定主义统摄下的“法外空间”,与现行的定限担保物权体系“格格不入”。与此同时,司法实践对于“无法可依”的动产让与担保之认定亦莫衷一是,“同案不同判”现象催促着物权法学界对此的回应。毋庸讳言,此背景下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动产让与担保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作为非典型担保的代表,动产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之履行,与债权人约定将动产所有权先移转于债权人,如嗣后债务人不能履行到期债务则债权人可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之担保方式。从历史沿革角度看,让与担保制度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其雏形为信托质,端绪由此萌生。信托之适用并不限于担保,其亦广泛应用于诸如亲权等涉及人身的民事活动。信托质系信托于债的关系中的担保化应用,其运作表现为以担保为目的的所有权移转,具体而言:债权人先于形式上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若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债务,则债权人可处置该动产或主张以物抵债,但应返还超出债权额部分之价款;反之,若债务人如约履行,则债权人被课予返还标的物所有权之义务。值得注意的是,信托关系存续期间,债权人以占有改定之形式对标的物施以管领控制,债务人仍直接占有该动产并对其使用、受益[1]。由于此制度能很好地平衡双方利益,故信托质一度风靡,成为早期担保的主要形式之一。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继受让与担保制度,然其并非明定于成文法,而系于判例中表彰。德国法院于1906年以判决的形式肯认了让与担保之债的合法性,后又于《租税调整法》中对此予以细化明确[2]。受前述德国判例影响,日本法院于明治45年对让与担保的态度出现更迭,由原先的“因其系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转变为“基于内外效力有别而对内有效”,据此承认了让与担保制度。随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了德日学说,对于让与担保制度的抵触逐渐松动,仅以禁止流押作为对其的限制。至此,不论是理论抑或实践,让与担保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制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反窥我国立法,物权法定主义下让与担保制度的生存空间极为逼仄。因其于制定法中无迹可寻,故迄今为止让与担保并未取得担保物权之名分,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其的立场亦显骑墙。然而,学理上的论争无法阻遏信贷实践的飞速发展,动产让与担保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日益凸显。时至今日,学界对动产让与担保制度已作较为充分的研究,但笔者认为,其中的三个通说观点值得商榷。
一、质疑“动产让与担保不可成文化”之通说
通说观点认为,“动产让与担保不可成文化”。首先,让与担保本质系通谋的虚伪表示。纵观动产让与担保设立始末,债务人并无转移动产所有权于债权人的意思;易言之,所有权移转仅为形式外观,而以此为对价担保债的履行却是实质内涵,故动产让与担保系双方基于通谋而为之虚伪表示。其次,让与担保明显有违现行法中“禁止流押”之规定。禁止流押的设立初衷系遏制债权人乘人之危之行径,保护立约时处于窘迫境地的债务人,避免其因“城下之盟”蒙受巨额损失。而不论从形式抑或实质上看,让与担保与流押契约几无二致。再次,让与担保与现行担保体系相冲突。物权法定主义下,担保物权的定位系定限物权,即其仅享有部分所有权的权能,其由所有权派生并起限制效果。而让与担保具备“完全所有权”属性,故如若将其成文化,无疑将构成对现行担保体系完整性的破坏,逻辑上亦难以自洽[3]。最后,动产让与担保成文化既无比较法上的先例,亦无迫切的实务需求。一方面,比较法上承认动产让与担保的国家大多未设置动产抵押制度,某种程度上,前者是后者缺位时用以弥补漏洞之法的续造;另一方面,实践中可通过对动产抵押进行解释以处理动产让与担保纠纷,故无立法之必要[4]。
笔者认为,“动产让与担保不可成文化”这一通说观点值得怀疑,理由如下:
(一)动产让与担保的“让与”并非虚伪表示
民事主体凭借表意参与民事活动,内心意思与外化表示相结合即形成意思表示,此为法律行为成立之核心。意思表示系表意人表达内心意愿之产物,属法律概念。表示行为与内心真意不一致时即引发真意保留与虚伪表示两种样态。虚伪表示适用于双方通谋之情形。所谓通谋,其成立须同时满足以下三要件:其一,双方的意思表示均欠缺效果意思;其二,表意人效果意思缺位之情况为对方所知晓;其三,双方串通,故意作出非真意之合意[5]。
需澄清,动产让与担保中“让与”并非虚伪表示,而是基于真意所欲发生之权利移转行为。如前所述,虚伪表示之“伪”以效果意思欠缺为前提。就动产让与担保而言,双方移转动产所有权之际即确切地达成以此作为担保之合意,该合意系真正的效果意思,并无构成虚伪表示之嫌隙[6]。退一步讲,即便“让与”构成虚伪表示,由于“以供担保”为隐藏其中之意思,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之规定,虚伪表示无效并不牵连于包裹其中之隐藏行为之效力,故当事人可主张适用隐藏行为之规定,排除虚假意思适用之余地。比较法上德国判例即借助罗马法的信托理论对动产让与担保之“让与”作出有效性解释,从而颠覆了先前因“让与”被误读为虚伪表示而无效的观点。
(二)动产让与担保并不违反“禁止流押”之规定
前述已及,立法之所以对流押条款持否定态度,缘其保护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债务人,以阻遏债权人利用债务人穷困之窘境逼迫其签订流押条款进而巧取豪夺。多数学者认为让与担保“披担保之衣行流押之实”,本质仍是变相的流押。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一方面,就法律性质而言,流押系债之履行的实现方式,而非担保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押与让与担保分属不同范畴,并无交集。与流押即直接以物抵债不同,让与担保之设立着眼于标的物的交换价值,担保之债到期不能清偿时,债权人负有强制清算义务,仅就担保物清算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故从实质上看,让与担保能很好地平衡双方利益,避免流押可能引发的恃强凌弱之不平。另一方面,就当事人享有之权利义务而言,由于流押发生于抵押担保中,故物权法定主义下双方享有之权利义务已为实定法所明确。相形之下,让与担保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多源于习惯或法理,譬如担保物变价后,债务人有权请求债权人返还超额价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司法实务不断深入,“禁止流押”规定的弊端也逐步昭显。首先,“债务人处于弱势”这一预设即存在疑问。当下大多数借贷关系并非以债权人为主导,而系互利共赢之合作:债务人举债融资,通过抬高财务杠杆激进式经营,增加每股收益,以博得报表使用者青睐;债权人收取本息,通过将闲置资金投出获取收益,从而为企业创造利润。由是观之,“债务人处于弱势”之预设在当下显得以偏概全、不合时宜。其次,“禁止流押”规定有悖于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禁止流押是手段而非目的,其设立旨在遏强扶弱,匡扶公平。借贷双方实力均衡背景下,“禁止流押”规定之适用应逐步限缩,让位于意思自治。最后,实践中抵押权的实现多为经双方协商后将抵押物折价,故从法律效果看,其与“以物抵债”的流押并无二致,故规定“禁止流押”之必要性亦不如前。
(三)动产让与担保并不与现行担保体系相冲突
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多采潘德克吞体系,遵循体系的内在逻辑一致性系维护法典形式理性的应有之义。现行担保制度下担保物权均为定限物权,而让与担保所让与之权利并非“完全所有权”,其行使以担保目的为限,实质上仍属定限物权,故对其作创设并不悖于担保体系的内在逻辑。有学者指出,承认让与担保即突破物权法定主义,有违所有权内容法定和担保物权种类法定。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作为所有权担保的他种形式,所有权保留与融资租赁均以成文化,列示于合同法分则中,此二种担保均对所有权内容作限缩,皆有僭越物权法定主义之嫌,故将同为所有权担保的动产让与担保成文化亦无可厚非。至于“承认动产让与担保”存在违背担保物权种类法定之嫌的观点,笔者认为,此恰恰印证了动产让与担保成文化的必要性,宜将其法典化示于典型担保之列。毋庸讳言,前述冲突之化解端赖于立法始竟其功[7]。
(四)动产让与担保于比较法上有迹可循且有迫切的实务需求
研究一项制度是否应予立法,其肯綮在于其是否与我国国情相匹配。域外立法例仅具参考价值,以他国未创设动产让与担保制度得出我国亦不应对此成文化之推论,显然难以令人信服,遑论比较法上确有将动产让与担保成文化之先例。譬如日本通过《假登记担保法》之颁布,以立法形式承认了卖渡担保的合法性;韩国亦颁布专门法调整让与担保当事人间法律关系。放眼更广阔的视域,不论是《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抑或《联合国动产担保交易立法指南》,其中均存在针对让与担保立法所作之论述。
此外,就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之取舍而言,有观点认为,二者功能相当,取其一即可。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一方面,前者具有后者所不具备之突出优势,集中体现于实现方式的灵活便捷。现行物权法下,动产抵押权之实现主要通过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完成,且须以当事人间无异议为前提。实践中抵押人动辄以实体权利义务尚存争议为由延宕抵押权实现之进程,此无疑将增加抵押权的实行成本,于债权人不利。相较之下,动产让与担保权的实行无需司法公权力介入,不论采处分清算抑或归属清算,债权人均可依约定及时获得债之清偿,而不必劳神费力,周旋于旷日弥久的司法程序。另一方面,“迳以动产让与担保取代动产抵押”之观点亦不可取。动产抵押权变动无需公示,此有违我国物权变动长期以来所恪守的债权形式主义,实属异类。而动产让与担保虽能解决上述问题,但仍具有体系异质性,以此代彼的方案并不适妥[8]。笔者认为,应同时规定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二者并无非此即彼之对立关系,两项制度可以同时存在。随着金融交易数量逐年攀升,金融担保前景广阔,动产让与担保的实务需求愈发迫切。不断催生的金融交易手段如融资融券、信托收据的广泛应用足以证成动产让与担保应用前景之广阔,立法理应对此作出回应。综上所述,由于动产抵押与动产让与担保实行机制有别,适用领域各有侧重,故我国即将编纂的物权法编中宜将两项制度同时规定,使二者各司其职,服务于相应的经济活动。
二、质疑“动产让与担保采所有权构造”之通说
通说观点认为,“动产让与担保采所有权构造”。首先,让与担保权无价值权性。让与担保虽形为担保物权,然其以权利转移为先决条件,并无变价可言。所有权权能不可随意拆分,债权人受领“让与”即取得完全所有权,对外效力上物权变动已成,对内效力上债权人仅受内部信托关系约束。其次,动产让与担保以占有改定为其公示手段。作为交付形式之一,占有改定能够充分发挥让与担保“保守商业秘密”之功用。当下,随着社会分工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占有与本权相分离之现象显得稀松平常。明确占有改定的公示效力系大势所趋[9]。最后,采所有权构造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利益。债权人取得动产所有权后,可在不超过担保目的范围内对担保物施以处分,从而大大提升债权实现之可能。
笔者认为,“动产让与担保采所有权构造”这一通说观点值得怀疑,理由如下:
(一)动产让与担保权具有价值权性
担保物权的设置以服务于保障债务清偿为目标,以支配担保物交换价值为手段,价值权性是其根基。动产让与担保权亦是如此。根据定义,债权人受让担保物所有权时,虽于表面上形成“权利外观”,但基于双方真实意思可知,此“让与”仅供保障债务清偿,债权人不得对该动产作出超过担保意旨范畴之处分。就实质而言,债权人所受让之所有权并不圆满,得受担保目的之限,如若嗣后担保权实现程序启动,债权人将仅从该标的物清算价值中优先受偿。由此可见,动产让与担保中债权人仍是对标的物交换价值作支配,其价值权性不言而喻。至于“所有权的权能无拆分之依据”的提法,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权能系权利所分解之能力,特定场合所有权项下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分离,恰恰是“权尽其用”的表彰。某种程度上,担保物权即是所有权交换价值凝结成的独立权利,让与担保权亦是如此[10]。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所有权构造”动摇了动产让与担保系担保权属性之根,而惟有对其采“担保权构造”方能体现其实质。
此外,亦有学者指出,“担保权构造说”将让与之所有权定性为非完全属性,系对“所有权让与”要件之忽视,这种企图通过模糊所有权与定限物权之边界进行解释的做法,实乃牵强附会之举,不足为训。笔者认为此观点欠缺说服力。一方面,动产让与担保中“债权人于形式上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担保权实现时允许归属清算”等足以证成该制度并未忽视“所有权让与”;另一方面,定限物权本就是由所有权派生,将动产让与担保权理解为仅具备交换价值之所有权亦应无可非议。
(二)动产让与担保不应以占有改定为其公示手段
权利的静之拥有和动之行使须以外化形式得以呈现,物权概莫能外。物权的直接支配性、普遍对世性要求其变动须以特定机制显现,由此,公示制度应运而生。
“所有权构造”理论下,动产让与担保的公示手段系占有改定,此为德国判例所采纳并沿用多年。然该做法饱受学界诟病,理由是:占有改定虽为交付形式之一,但因其过于隐蔽,对善意第三人保护不周,故其公示价值微乎其微,所有权变动之形式要件亦名存实亡。笔者对此深表赞成,我国动产让与担保之公示如若采占有改定,则物权变动构造无疑会向意思主义倾斜,其结果是将从实质上撼动债权形式主义之根基,此应避免。
既然公示手段不应采占有改定,那么还有哪些其他的可供选择之公示方法呢?一种观点认为,可借鉴日本,以明认作为公示手段。明认源于习惯法,日本判例在林木、温泉等自然资源物权变动场合对其予以承认,效力等同于登记。简单易行是明认之优点,然其内容过于粗略,难堪记载复杂物权变动之重任,故不宜采纳。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效法动产抵押制度,以登记作为公示对抗要件。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一方面,动产让与担保受追捧的原因之一系其隐蔽性特征,不论是所有权让与时的内部约定抑或担保权实现时的清算方式选择,当事人均可自行协商,外人无从知晓,此无疑增加对举债经营的债务人商业秘密保护之力度。而如若采登记,则上述优势将荡然无存,针对债务人的商业秘密之保护亦被摧毁。另一方面,动产种类层出不穷,纷繁芜杂。加之其价值量通常较小,移动频繁,故以登记对其公示将招致不堪重负的工作量,巨额成本的耗费亦是必然,从制度设计的成本收益权衡角度分析,此做法无疑得不偿失[11]。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一方面,评判某项制度的优劣,关键着眼于其运行是否能平衡好各方利益,减少偏颇之虞。“陌生人社会”模式运作下,贸易往来以信用为其基石,以缓和人际隔阂带来的信任危机。作为信用评判的关键依据之一,交易参与者的财务状况应以合理方式予以外现,其真实性务必依仗健全披露机制之运作。诚然,商业秘密系企业之隐私,债务人设法对其施以保护无可厚非,然而制度设计应作通盘考虑,以实现各方利益之衡平为宗旨。除债务人外,债权人、第三人利益以及维护交易秩序之稳定理应予以观照,不可顾此误彼、失之偏颇。如是思忖,借助登记公示动产让与担保权之变动恰是考虑周延的中肯之举。公示对抗模式下,借贷双方让与担保权之设立依约定而成就,经登记可对抗善意第三方。此制度的优点有二:其一,有利于衡平债务人与债权人之利益。债务人可出于隐蔽商业秘密之虑选择不予登记,此情形下担保权自合同生效时设立,双方即受担保关系约束。若让与担保人无权处分,使担保物所承载之交换价值减损,债权人可对其主张违约责任。其二,有利于保护不知情第三人利益,从而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并重。在动产让与担保权未登记场合,债务人在继续占有担保物之际,可能为无权处分之行径。通常,占有系权利人享有动产所有权的表征,不知情的交易相对人基于债务人占有动产之事实,合理信赖其乃真正权利人,而后基于此信赖与让与担保人订立买卖合同并支付相应对价。登记对抗下,善意第三人原始取得动产所有权。准此,交易安全得以保障,个益与公益亦达致衡平。
另一方面,登记并非一概采书面形式,文件登记已不再是唯一选择。于比较法视角观瞻,美国法上除传统书面登记外,亦施行声明登记制。与前者有别,后者不以文件为载体,且内容上无需记载合同详情。笔者认为,声明登记制可资借鉴,理由有三:其一,隐去债务人部分隐蔽性信息,缓和因采登记导致的对债务人商业秘密保护之不周。声明登记下,对外公示的内容仅为最基本信息,有关所担保合同的详细情况均会被过滤,债务人资力状况亦仅是简单陈述,其细枝末节处无登载之需。此方式能于使外界周知的同时尽可能地保障债务人秘密信息,实为衡平之举。其二,减少成本,消解动产登记耗资繁重之不足。动产易移动,地点的更迭将会导致登记内容的频繁变更,此诚大幅增加交易成本,存在本利悬殊之虞。文件登记下,该不对等之境况还将被进一步放大,当事人基于对本利的权衡选择对动产让与担保不予登记,其结果是该登记制度名存实亡。相形之下,若采新型登记,由于声明内容不涉及担保细节,仅显示最基本信息如主体身份、标的物价值等,故“登记内容因动产移动而频繁变更”之疑虑可予消弭。此外,随着资本市场的变迁,金融担保异军突起,作为担保物的动产,其价值亦不可同日而语,“动产价值量小”这一成见应当摒弃。其三,与时俱进,声明登记的电子化更契合时局。随着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其应用已广泛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纸质化的文件登记有赖于人工对信息的逐字填写和比对,文件归档与整理即嗣后保管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的投入,此自不待言;对比之下,电子化登记不以纸为载体,无纸化操作在简化流程的同时,节约了资源,也为第三人查询担保信息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鉴于交易成本的减少,担保权人更愿意办理登记以保障其清偿时的顺位,债务人亦可于不过度披露其自身秘密的同时从担保权人处取得融资,电子登记下双方利益皆被考量,均衡局势始现。另外,比较法上法国、韩国、澳门地区等均对动产让与担保采登记对抗模式,运作优良。动产让与担保登记机制的建立无需另起炉灶,扩大现行动产抵押登记系统的适用范围,使之涵盖包括动产让与担保在内的动产担保登记,不失为上策之举。
(三)动产让与担保的制度设计应兼顾好各方利益
前述已及,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为动产让与担保制度运行之归宿。“所有权构造”理论下,担保权人基于信托法律关系所享有的担保目的范围内的所有权,其在对外效力上和完全所有权无异,对于担保目的所对应的交换价值部分,其可自行处分,此无疑对担保权人有利。然而,“所有权构造”保护债权人过度,而对他方保护不足。该理论下,担保人于动产上设定担保后将“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债权人无权处分。债权人仅受合同内容拘束,效力不及于外部第三方。故若债权人果真无权处分,符合善意取得要件时第三人将无负担地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而担保人只得主张违约责任以获救济,其地位之薄弱可见一斑。相反,“担保权构造”理论下,所有权于实质层面并未从设定人处移转,此大大削减债权人无权处分该动产之可能。债权人可于条件成就时通过清算程序优先受偿,利益得以保障;设定人仍支配着担保物,无需惴惴而栗,寝食难安。由此可见,较之于“所有权构造”,“担保权构造”更能照顾好各方利益,契合衡平法理。
三、质疑“动产让与担保权实现采处分清算”之通说
通说观点认为,“动产让与担保权实现采处分清算”。一方面,采处分清算可回避被认定为流押条款之嫌。担保权的实行以债之不履行为其启动前提。就实行方式而言,存在公私之分。“公的实行”借助公权力,通过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程序予以实现,司法干预性是其特征;“私的实行”依当事人约定展开,不必历经繁琐的强制执行程序,灵活便捷是其优势。就担保权实行而言,动产让与担保权显属后者。前述已及,动产让与担保制度最鲜明的优势系清算环节的简单便捷,无讼累之烦扰。就“私的实行”而言,其清算方式存在处分清算与归属清算两种备选方案。处分清算指担保权人从将标的物变卖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而归属清算指担保权人确定地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并将超额价金返还于担保人。从表征看,归属清算与流押实现几无差异。另一方面,基于动产让与担保权的价值权性,采处分清算更契合担保权普遍特征,也有利于厘清当事人间的实体权利义务[12]。
笔者认为,“动产让与担保权实现采处分清算”这一通说观点值得怀疑,理由如下:
(一)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处于优位
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意思自治鲜明地体现着民法本质以及私法自治理念。在无禁止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场合,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应优先被尊重,动产让与担保权的清算方式选择亦应遵循此理。通说观点将处分清算视为唯一方式,排除当事人约定的做法诚不可取。贯彻意思自治原则下正确的做法应首先考虑当事人针对清算方式的选择是否有约定,惟有无约定情形下,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方有适用之余地。
(二)采归属清算无流押条款之嫌
如前所述,规定流押条款之禁止在抑强扶弱方面有其功用,但应有所缓和。归属清算下,担保权实现时虽有所有权确定性的移转,此与流押相似,但债权人应返还超额部分价金,其结果是担保权人仅就债权额部分变价受偿,并无偏颇受偿之可能。故“归属清算与流押实现几无差异”的观点过于片面,不应采之。
(三)采归属清算更能凸显制度优势
动产让与担保的制度优越性显于其高效便捷。该优势借助归属清算可彰显得淋漓尽致,此处分清算所不能比。有观点认为,处分清算系变价清算,而动产让与担保采“担保权构造”,变价受偿乃其清算之核心,因而处分清算与其更为匹配。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处分清算固然围绕变价展开,紧扣担保权构造逻辑,然其并非唯一之选。归属清算下,债权人对超额价款负返还义务,从其受领的绝对金额看,并未超出其应得额,准此,债权人受偿结果与变价清算下无异,并不存在“处分清算与动产让与担保更为匹配”一说。在承认了归属清算与变价清算在与动产让与担保匹配程度无高下之分后,对于清算方式的取舍理应回归动产让与担保的机制本身之营运。事实上,动产让与担保法律关系中,担保人于设定时已有以物抵债的心理预期,担保权人亦有到期取得担保物完全所有权之期待。由是,某种程度上采归属清算更吻合当事人设立该担保权之初衷,同时也能最为迅捷地达致债权实现之目的。比较法上,法国即规定了当事人间无约定时归属清算优先适用,制度优势由此凸显[13]。
四、结论
动产让与担保之“让与”系真实意思,该制度不抵牾流押禁止之规定,能很好地融入现行担保体系之中,且存在大量实务需求,因而动产让与担保制度成文化诚有必要。鉴于价值权性之特征,动产让与担保采“担保权构造”,并以声明登记为公示手段,如是,方能兼顾好各方利益。就清算方式而言,应首先尊重当事人意愿,以约定为先;无约定时,应采归属清算方式以突显动产让与担保的制度优势。
参考文献:
[1]周枏.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91.
[2]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5.
[3]胡绪雨.让与担保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兼译我国物权法是否应当确认让与担保制度[J].法学杂志,2006(04):126-128.
[4]王卫国,王坤.让与担保在我国物权法中的地位[J].现代法学,2004(05):03-08.
[5]施启扬.民法总则[M].台北:三民书局,2001:246.
[6]谢在全.民法物权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105.
[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97.
[8]高圣平.动产让与担保的立法论[J].中外法学,2017(05):1193-1213.
[9]向逢春.动产让与担保公示问题研究[J].求索,2013(05):165-168.
[10]高圣平.金融担保创新的法律规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242.
[11]向逢春.让与担保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72.
[12]谢在全.民法物权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921.
[13]叶朋.法国信托法近年来的修改及对我国的启示[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 121-127.
——以债务人不知悉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