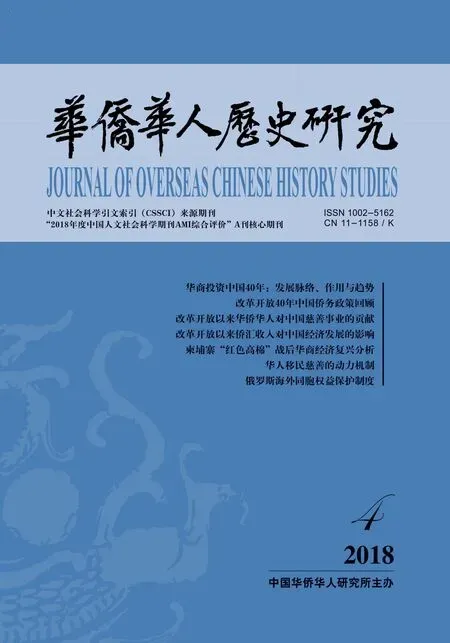柬埔寨“红色高棉”战后华商经济复兴的人类学分析*
罗 杨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北京 100007)
“一座鬼城,曾经繁忙的中国商业区看起来像一场灾难性风暴后的场景,每个房子和商店都被洗劫一空”。[1]1979年,越南攻入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首批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描述刚刚经历红色高棉劫难的柬埔寨。然而,短短20多年后,柬埔寨被喻为“亚洲经济新虎”,[2]近年来,它的GDP平均保持着7%的年增长率。[3]从百废待兴到飞速崛起,华商是实现柬埔寨战后经济转折的“中坚”力量。[4]2001年,时任柬埔寨新闻大臣吕来盛曾表示,80%的柬埔寨华人是商人,华人控制了柬埔寨80%的经济命脉。[5]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柬埔寨的战乱、排华,同样使华商经济经历了从零开始、浴火重生的过程。柬埔寨华商经济如何在战乱废墟上恢复重建?在战后的几十年中究竟经过哪些发展阶段?为何是华商从柬埔寨众多族群中脱颖而出,使柬埔寨的国民经济在短短20年间实现“凤凰涅槃”?种种有关柬埔寨战后华商经济的具体情况,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学界尚缺乏细致而深入的个案研究。①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柬埔寨华侨华人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例如,顾佳赟《“一带一路”视阈下柬埔寨华人华侨的群体特征分析与政策选择》一文分别从语言、教育、社团三方面归纳了柬埔寨华人的群体特征,黄晓坚《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变迁(1991—2017)——兼论柬埔寨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一文系统梳理了1991年柬埔寨恢复和平以来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变迁,陈世伦《柬埔寨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传承与发展》一文对柬埔寨华人社会中的社团与乡缘认同组织作了开创性研究,郑一省《柬埔寨土生华人婚俗探析——以实居省狮子桥村为例》一文基于婚俗探讨了柬埔寨华人的文化适应,代帆、刘菲《柬埔寨华裔新生代的认同及对华认知》一文通过实地访谈分析了柬埔寨四代华人的认同特点。
近年来,笔者赴柬埔寨华商最为集中的金边、历史上和现今最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西哈努克港(又名磅逊港)及其毗邻的贡布、戈共等地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调查中,笔者访谈了30余位在柬埔寨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华商,他们有的在红色高棉期间被赶入森林开荒种地,有的则逃往海外,战后重新回归。他们是红色高棉战后柬埔寨华社和华商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的亲历者。笔者试图通过第一手的访谈资料和个案研究,探讨华人尤其是华商在整个柬埔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功能,分析他们如何将自身社会嵌入本土社会结构之中,怎样适应并能够占据如今的位置。
一、理论综述
与柬埔寨华人及华商经济相关的民族志调查和结构性分析,主要有三种富于启发性的解释范式。
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学生威莫特(W. E. Willmott)在柬埔寨金边、暹粒等地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1967年,威莫特基于其博士论文出版了《柬埔寨的华人》(The Chinese in Cambodia)一书,首次将柬埔寨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总体进行社会人类学的分析,[6]1970年,他又出版了《柬埔寨华人社团的政治结构》(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一书,对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内部结构展开专题研究。[7]对于战前柬埔寨的总体社会结构以及华人与柬埔寨社会的关系,威莫特借用了英国东南亚史学家富尼华(John Sydenham Furnivall)的“多元社会”概念。富尼华所谓的“多元社会”是指由不同族群构成的一个社会,每个族群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这种社会缺乏共同的社会价值,因此,每个族群只在市场中发生联系。基于柬埔寨华人的特点,威莫特在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和补充了富尼华的“多元社会”概念。首先,他强调只有当某一个特定族群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即阶层的划分沿着族群的分类,这样的社会才能称为“多元社会”。根据威莫特当时的统计,华商控制了柬埔寨的农业经济、城市商业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华人既是一个族群的分类,也构成经济上的主导阶级。其次,在“多元社会”中,真正引起社会冲突的是当另一个族群也在经济领域崛起,并与之前掌控经济的族群产生矛盾,例如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新兴国家独立后,土著族群对华商资本的排挤以及对其进行民族资本化,但柬埔寨并未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对于柬埔寨上层而言,是通过华商而不是取代华商获取其经济利益;而对于柬埔寨下层民众来说,倘若没有华商,他们既无法出售自身生产的农产品,也没有渠道购买所需的日用品。因此,柬埔寨没有形成一个与华商竞争的柬埔寨土著阶层,在这个“多元社会”中,或许“缺乏共同的社会价值”,但正是不同族群间的经济关系将这个多元社会的各部分捆绑在一起。
施坚雅在同一时期对泰国华人的研究,[8]与威莫特的论点形成反思性的对照。柬泰两国毗邻,在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借鉴关系,两国华人在发展模式、社会地位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施坚雅对泰国华人社会及华商经济的分析值得参考。施坚雅深入剖析了华人何以能够控制整个泰国的经济生活。传统上,泰人的社会划分为贵族和平民,平民属于他们的保护人,每个人都在其固定的地位上履行明确的义务和权利,受到限定的社会地位使其失去在经济竞争中必需的个人自由和地域移动。但华人脱离于这套人身依附关系之外,华人勤俭、重商的精神正是泰国文化中所缺乏的,所以在泰人社会结构中,在最顶端的保护人和最底层的受保护人之间,为华人留下多样的填补空间。但是,施坚雅并不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泰国也是一个“多元社会”,尽管它也有职业沿种族分化的趋势。泰国社会的顶层总是泰人,但不像华人在西方社会,华人在泰国被完全同化是可能的,泰人通过封爵等保护制度,将顶层的华人吸纳入自身的圈子。在这之外,新兴起了另一个上层阶层,如中泰商业联盟中的华商和军政权贵,他们比传统的贵族更加西化。而在这两个上层阶层之下,似乎有两个中间阶层,由华人和泰人分别构成,华人阶层的骨干人物就是华商,他们保持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又倾向于现代世界,泰人的中间阶层主要是政府雇员或商业白领。泰国社会的下层既包括华人技术工人和劳工阶层,也有正在形成中的泰人工人阶层。因此,施坚雅认为,阶层的界限并不与族群的范围相连接,泰人和华人间重叠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业地位,以及介于泰人社会和华人社会间的许多中间分子,都对“多元社会”的概念提供了反思。
荷兰泽兰德大学魏维尔博士(Michiel Verver)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在金边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主要探讨了战后柬埔寨社会是否依然能够被称为威莫特所谓的“多元社会”。[9]他认为,虽然经过战乱,华人在战后依然重新占据了战前的经济主导地位,但“华人”的范畴和边界变得混杂而灵活。首先,华人的来源日益复杂,战前柬埔寨华人根据来源地分为福建、广东、海南、潮州、客家五帮,而今战时逃往西方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柬埔寨华人作为二次移民乃至多次移民重回柬埔寨,无论其国籍还是身份认同都更为混杂。其次,柬埔寨华人的代际差异逐渐扩大,战时强迫中柬两族通婚而形成的大量混血儿、中国新移民、从国外重新回来的柬埔寨华人、土生土长的华裔等不断增多,使得华人的构成十分复杂。第三,柬埔寨华人的商业网络随着当地社会的资本主义转型和融入全球化进程,不再局限于柬埔寨国内,正如施坚雅所说“他们倾向于现代世界”,同样使得“和世界做生意”的“华人”边界难以廓清。因此,威莫特所谓的“多元社会”因为“华人”壁垒的日渐模糊而消解。
上述学者聚焦于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定位“华人社会”。正如施坚雅提到,在当地社会中,有许多中间分子,在某些社会场合自认为是华人,而在其他社会场合又自认为是泰人,能讲流利的泰语和华语,社会关系有华人也有泰人。这样一个横跨双方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的混杂群体,虽然无法将之归入“多元社会”的一个组成范畴,但却是上述学者都提及的“中间层”(intermediary sphere)[10]。无论是威莫特还是魏维尔考察的时代,柬埔寨的商业大多由华人经营,而华商构成柬埔寨华人社会的主体,他们是当地社会上层官僚、贵族和下层民众之间,当地社会和外部世界之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海外非儒家文化国家之间的中间层。华商无法被纳入多元社会的模糊性和混杂性,恰是他们作为“中间层”的特性。
二、历史的断层
“3年8个月20天”、“20年的断层”,这是笔者所访谈的每位华人都会强调的历史记忆。柬埔寨国运多舛,华人的命运随之起伏,经历过好几个“断层”。
14—15世纪,柬埔寨历史上最伟大的吴哥王朝的都城被暹罗攻陷,迁都金边。深居内陆的吴哥王城曾是中南半岛上宗教文化的核心地,面向海洋的金边却处于西面印度文明与东面华夏文明的夹缝,柬埔寨史学家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称它是一个“文化断层带”。[11]金边位于四条河流的汇聚点,源于北部内陆的洞里萨河和上湄公河在此交汇,又分成百适河和下湄公河流向南部海洋。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文化断层带”成为联接内陆稻作农业区、森林山地与广阔海洋世界的枢纽,各方物资交换转运的辐辏之地。从吴哥迁都金边,地理和行政中心的转变意味着柬埔寨从深居内陆、依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依靠世界市场和海外贸易的深刻转型。[12]这一时期正是柬埔寨华人社会形成的关键点,17世纪成书的张燮《东西洋考》中辟专章介绍柬埔寨:“篱木州(一说为金边),以木为城,是华人客寓处”,“市道甚平,不犯司献之禁,间有颐者,则熟地华人自为戎首也”,[13]当时金边的华人社会已经形成。柬埔寨从依靠农业经济转向发展海洋贸易,这种转型受到元明两朝中国与东南亚海上贸易扩张的影响,华人大量移居柬埔寨,既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又是这一转型的推动者。随着柬埔寨从相对封闭自足的农耕国家转为依靠对外贸易,17—18世纪柬埔寨华商在这一“断层”中崛起。
1863年,法国开始了在柬埔寨的殖民统治,面对陌生的东南亚土著社会,最令他们头疼的是总与当地最实在的商业领域隔着一层距离,因为传统上是华商充当柬埔寨社会中上层王室贵族与底层民众的中介:一方面,他们购买从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为王室贵族提供奢侈品;另一方面,他们替王室贵族收税、代办经商等,为农民提供必要或急需的贷款。19世纪法国海军军官、探险家弗朗西斯·加尼叶在柬埔寨探险时多次在沿途村镇遇到华商:“华商之有恒产者,每娶土人之女,握商贾之权”,[14]“南掌人爱杂货铜锡器肥皂棉货,番人爱铜丝料件火药,向例贸易以官吏居间,必馈以礼,诸货均经官吏及华商之手,其价定之于华商。”[15]法国殖民柬埔寨后,不得不采用买办制度,找华人作为中介,根据华商掌握的当地商情,告诉西方人该购进什么货物,然后通过华商的销售渠道很快便把这些货物分发出去,利用华商掌握最全面和最直接的市场网络。柬埔寨华商因填补了西方外来者和土著社会之间的“断层”而发展壮大。
1953年,柬埔寨王国独立,在柬埔寨民族国家的建构时期,作为“非我族类”的华人虽然遭致一定的排斥,但依然得以发展。当时柬埔寨70%的商店仍由华人经营,80%的对外贸易由华人掌控,金边3000多家商店中有2000多家属于华人。[16]然而,1970年,美国支持的军官朗诺发动政变,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实行清空城市、废除货币、消除私产、将包括华人在内的民众赶进森林开荒等极端措施。1979年1月7日,越南入侵,推翻红色高棉,1989年才陆续从柬埔寨撤军。1993年,柬埔寨在国际社会斡旋下成立王国政府,进入和平重建阶段。“3年8个月20天”是指红色高棉统治的这段黑暗时期,华人成为柬埔寨的“资产阶级”,华人社会被摧毁殆尽,“20年的断层”则是70年代朗诺上台到1990年重新恢复和平前的战乱年代。
笔者访谈的华人以第三个“断层”来划分自己的生命,感觉已经死过一次,而今获得重生。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命运同样如此,多年战乱打断了它原本的发展轨迹,华人要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构起一个新的社会。因此,“断层”后的柬埔寨华人社会,完整呈现了一个海外华人社会如何从零开始建构起来的面貌,也正因为有这段“破”和“立”的独特历史,相比其他绵延发展、未曾中断的海外华人社会,“断层”后柬埔寨华人社会的重建及其华商经济的恢复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
三、现实的轮回
(一)区域性的贸易体系
“20年断层”后,柬埔寨华商经济的恢复同样始于“夹缝”。“那个时候,刚从红色高棉出来,华人都是空手起家,什么都没有,每个人的耳朵在听,缺乏什么东西。”①为尊重和保护访谈人隐私,依照人类学田野调查惯例,文中所引用的访谈内容隐去了访谈人的姓名及身份。“越南打了几十年仗,什么都没有。泰国什么都有,做什么出来都能卖。”华人“什么都没有”,越南“什么都没有”,从森林中走出来的华人,再一次崛起于这两个“什么都没有”的罅隙之中。
“一个国家还没有安定的时候,赚钱的机会很多,我们华人就抓住这个时机。”柬埔寨和越南在从无序的战乱进入有序的发展轨道之前的这段“中间”转折期,在华人眼里却是充满各种可能性和能动性的混沌阶段。此外,钱德勒认为,夹在泰国和越南之间的地理位置对柬埔寨政治和社会有重要影响,这两大邻国使柬埔寨的统治精英要么两强选其一,要么借助区域外大国的力量企图保持中立。[17]或许他忽略了处于泰国与越南夹缝的地理位置,对于柬埔寨的经济的影响,以及它与泰国和越南之间的跨国贸易,乃至在东向中国、日本、韩国,西往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广阔地带构建起的“区域性的贸易体系”。这一经济网络的建构不是凭借“区域外大国的力量”,而是柬埔寨国内的华人以及他们与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和中国同胞之间的各种联系,他们形成了柬埔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中间层”,也使地缘的“夹缝”转变为贸易的“中转站”。
在这一“区域性的贸易体系”内,柬埔寨对外交接的途径分为陆路和海路两种,陆路是走柬泰边境,海路则通过戈共、贡布、磅逊这些海岛或战前的边境港口。“泰国有些华人买东西到边界那边,柬埔寨华人踩着脚踏车,从泰国那边买来布、香烟、日用品,那个时候很惨的,没有交通工具,踩脚踏车要四五天才到金边,来回要一个星期。”“那时候,有一波华人在边境和金边之间来来往往。一天几千个人,骑着单车,从泰国边境过来,然后带到金边,再从这里到越南。”
相较于陆上华人依靠脚踏车“单枪匹马”式的转运方式,海上贸易规模更大,也是被二十年战乱打成一盘散沙的华人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身社会的方式之一。首先,第一批敢吃螃蟹的人涌现出来,“一些人胆子大,从香港、新加坡买一些东西后就在那里的公海交换,当时管理不是很严,给当兵的一些钱,住在磅逊港捕鱼的船就跑出去公海。没有货币,就用黄金交换。”“从越南运出去咖啡、鱼、肉桂、虾皮、蛇皮等等,越南封闭久了,这些东西都囤积在国内卖不出去,我就安排卖给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交货的时候就在公海,约个时间,到公海,给个信号,到什么位置,用罗盘、对讲机,对讲机的号码大家讲定。”
这种自发式的贸易形式逐渐被更有组织的方式取代。一种是“港主”式的垄断贸易,“在戈共,海南人在那边起家的,有个海南人,谭延和,他越南语、泰语都懂,和当地的高官熟,当地官员也需要经费,就委托一个人去开港,就让他去开,联系外国的东西到那边来卖。他包了整个戈共军队的物资开支,所以才畅通无阻,全部的泰国货都进这个岛,政府给他独家优惠。他先垄断,下来的货靠他们海南的小集团来分发去卖。”谭延和的继任者名叫徐光秀,也是海南人,“那时候,在戈共港,一丝一线都离不了他,差不多每一样东西都是他过手的。他以前是一个小皇帝。他赚到钱,所有军人的费用都是由他负责,负责政府的开支。”另一种组织方式是“钱会”式的合股经营。[18]“我跟朋友开公司合作,10个人凑500两黄金,把这500两黄金分成10股,但每个股究竟有多少人我们都不清楚,每股可能有很多人,我这股就有2个人,我跟我朋友每人出25两。”“我们从红色高棉出来,当时大家都没有本钱,都是叫朋友、靠关系凑起来。”
磅逊、戈共是泰国和金边之间的“中转站”,负责将泰国的货物接进来,金边则是这些边境港口和越南之间的“中转站”。“那时候越南不能直接从泰国进口,交通方面、政治方面,种种方面的原因,就到金边来买。”而在金边转运的主要是潮州人,“海南人去泰国走私,我们潮州人从边界那边买过来,就在中间买卖,越南来这边买过去。”金边的潮州人同样组成“股份”,“我们组成一个个小公司,有人在这里卖,有人去磅逊、戈共那边拿货,哪个好赚我们就订哪个。”“慢慢找线嘛,金边什么都没有了,什么货都可以进来,什么来都可以卖,只是赚多赚少而已,所以你联络上一条线就不错的。没有钱就先垫一点,赚了钱慢慢还,转来转去,就是这样过日子啦,转来转去,越做越大。进出口就是靠关系,靠来靠去,你做得有信用了,你的朋友、别的货也可以介绍,就越做越大。”
柬埔寨华人在这一“区域性的贸易体系”内的中介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它与上文提到的14—15世纪柬埔寨从吴哥迁都金边,从内向型的农耕之国转变为外向型的海洋贸易之国的第一个“断层”息息相关。1679年,广东的一位将军杨彦迪放弃反满斗争,率7000部下来到时属柬埔寨的越南岘港等地,1778年,高棉人迫使他们迁往西贡,杨彦迪和部下们建立起华人聚落,并很快成为印度支那的商贸中心。自法属殖民时代到柬埔寨独立后,华人掌控着金边到西贡的出口贸易。1675年,年仅17岁的雷州人莫玖来到柬埔寨,后率众在河仙地区建立市镇、村庄,将本是荒地的河仙经营成“华夷杂处”、经济繁荣的国际性港埠,一说他建立起以华人为主体、颇有影响的“国中之国”,其范围横跨今柬埔寨西部的西哈努克港、南部的贡布,东至越南南部的整个海岸线。通过莫玖家族的关系,海南人大量移民邻近河仙的贡布,在越南、泰国之间做起跨国贸易,这个“区域性的贸易体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朗诺发动政变前。
无论是摇着渔船出海的华人,还是踩着脚踏车翻山越岭的华人,抑或是在金边和越南之间一站一站转运的华人,其生活世界并未囿于戈共、贡布等海岛和暹粒等边地,他们面向广阔的海洋和内陆,将孤岛、边地转变成海、陆物产集散、分配的“中站”,也实现了柬埔寨华商经济的初步恢复。
(二)“土能生白玉,地可出黄金”
如果说“20年断层”后,柬埔寨华商经济的重兴始于“什么都没有”,即在泰国、柬埔寨、越南构成的三角贸易体系内,乃至在整个向西拓展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向东延伸到日本、韩国等地的“区域性的贸易体系”里,利用各地在有无之间的差异,“转来转去”,那么,它的第二次腾飞则是因为“有人来了”。
从1970年朗诺政变到1989年越南撤军,这20年间柬埔寨国内政局混乱,各方势力林立,对外闭关锁国,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逐步恢复和平,步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正轨。“开放”对华商经济而言,具有两重影响:一是进出口货物的“常态化”,这就使得磅逊、戈共、贡布这些地方,地利仍在,但华人最为看重的“时机”已变。20世纪90年代初,磅逊港正式开港,国家给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颁发正规牌照,谭延和、徐光秀这些时势造出的英雄们再无垄断之力;其次是“开始有人来了”。正如一位华人所说,“只要有人,就有买卖,有买卖就有用钱,有用钱我们就可以联络,我就知道,我们活了!”
“土地成为商机,最早是联合国的人带进来的,20世纪80年代末华人开始买地。”1991年,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由联合国驻柬埔寨人员负责监督巴黎协定的实施,主要是解除各派武装,遣返在泰国的难民,为全国普选成立制宪大会等。联合国成立多国参与的联合部队,约有1.3万名士兵和超过7000文职人员、警察等入驻柬埔寨。[19]据说,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行动,总共花费了20多亿美金,这些工作人员的薪水占了总花费的很大部分。“联合国派来几万人,这些人吃喝拉撒都要,华人聪明,捕捉商机也快,再学几句英文,他们要找房子,华人马上去找房子。第一拨走私者聪明,转得快,不走私了,风险太大,转行了,有房地产可以做,就买地买房子。这是90年代的转型。”
第二拨外来者是来柬埔寨投资设厂的外国商人。“美国对柬埔寨有最惠国待遇,来这里开厂生产再出口,很划算,工厂需要土地啊,所以地价的上涨跟外来的工厂有关系,有一个当地的需求。”“最初来的是新加坡人,接下来马来西亚人、香港人,大陆人慢一步,90年代台湾人也来很多。”当时,欧美等国为援助柬埔寨,使其经济恢复发展,规定柬埔寨出口欧美的服装、鞋类等,有一定的免税配额,其他国家的商人到柬埔寨设厂生产,再出口欧美,可以降低成本,这刺激了柬埔寨制衣业在过去20年间的繁荣。
华人作为柬埔寨社会的“外来者”,将土地视作自身在当地社会的“根”,所以本地华人喜欢囤积土地,就如同他们在此扎根得越深、越牢。而柬埔寨人作为土著,从未将土地视为己有。历史上,柬埔寨没有现代的土地“产权”概念,国王是全国的土地之主。平民百姓的土地通过实际的耕种得来,清理出一块荒地并开始在上面种庄稼,只要这种行为持续,这块地就是耕作者的,倘若这块地被荒废了三年以上,其他人就可以来开荒种地。[20]这种土地占有方式长期以来适于地广人稀的柬埔寨,它无需对土地所有人信息进行登记和记录,税收制度也是基于收获物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土地占有量。直到现在,这种获得土地的方式依然留存于柬埔寨乡村和一些城市。
柬埔寨华人利用这种文化差异,很快嗅到土地“增殖”的奥秘,他们发现原本是“死”的地皮,竟然可以实现“钱生钱”。他们先从柬埔寨人手中买来土地,“柬埔寨人,包括农村里,从2001年和2002年开始也卖地,柬埔寨农民,不是说他笨,而是没有这个知识,他先卖田地,有了一笔钱就买汽车,后来汽车没钱加油,就卖汽车,最后什么也没剩下。”“华人很多时候的做法是,这个地,我跟地主讲好,我买是1块钱1平米,你卖我1块钱,我卖多少钱是我的事情,我再去告诉另一个人,说这个地2块钱,那个人一想太便宜了,那就跟你合股,各出50%,但其实我没出本钱。”“这是空手套白狼的形式,但华人有他的社会关系,才有他的无形资产。”无论柬埔寨人还是华人,虽然都对土地怀有“增殖”的观念,但前者是基于农业经济的土地本身的丰产力,后者却是根据商品交换的逻辑,使土地本身变为可交换之物,并通过不断地交换实现“钱生钱”的目的,正应了柬埔寨华人供奉的“神位”和“祖位”神龛或供奉土地公的神龛上的话——“土能生白玉,地可出黄金”。
同样作为外来者的马来西亚人、台湾人和大陆人,在柬埔寨做土地买卖,也不得不通过本地华人作为中介。“华人有当地的眼光、信息,外来人财大气粗有什么用,当地市场不是太熟。”中国大陆来的移民与柬埔寨本土社会的接触也得通过本地华人,他们又成为新侨与柬埔寨社会之间的中间层。“本地华人跟官方有关系,拿批文,拿大项目,新侨跟他们赚钱。”一些新侨试图绕过本地华人进入柬埔寨社会,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融入,但是被骗的很多,一些柬埔寨高官收了钱,但不给他们办事。相比新侨的“自上而下”,本地华人“自下而上”的策略与他们在柬埔寨打拼的历程一脉相承,如同在经济上的逐步增殖,他们稳步地编织起一张从底层至上层的关系网络,而这张关系网络依然是新侨融入柬埔寨社会必需的纽带。
在殖民时代,正如施坚雅在对泰国华人社会的研究中指出的,“西方人总是感到没有办法估量当地市场以及跟当地零售商直接打交道,只有很有限而间接的商情资料。每家西方商行都要物色一位华人充当其商行的中介人。他熟识当地市场的情况,还处理西方商行和泰国政府之间的一些日常关系的事务。”[21]而法国统治时期的柬埔寨同样如此,华人将偏远的柬埔寨山区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依靠他们作为中介,才得以实现本地土特产和外来商品之间的交换。“20年断层”之后,联合国军、马来西亚人、台湾人、大陆人,作为外来者,或许他们同样感觉自身和柬埔寨社会之间“隔了一层”,本地华人眼中的“时机”和“商机”恰是使这些外来者得以在当地社会“落地”的中间环节。
四、结语:互为“他者”的柬埔寨社会与华商
威莫特、施坚雅和魏维尔分别从族群、职业以及认同的角度反思了“多元社会”概念,上述学者围绕的主题及其争议的焦点,实则在于在当地社会中,是否存在一个“华人社会”以及如何定位这个“社会”——在联接当地社会和后续新移民之间具有何种功能,何以嵌入当地社会之中。
红色高棉后,重建柬埔寨华人社会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断层期间留在柬埔寨的,另一种是断层期间逃到国外后重新回来的。这两种人并非毫无关联,他们在重建柬华社会、重振华商经济的过程中密切结合。他们的结合使得现今柬埔寨华人社会的人员构成具有亦旧亦新,亦内亦外的特点,没有出去的这群人,虽然是“老华侨”,但他们自认为是断层后柬埔寨华社的“新一代”,有的很快瞄准时机,踏出国门,在跨国贸易中崛起成为华社“大佬”;出去的这帮人,他们虽是战后柬埔寨华社的“新移民”,在国外打拼,多已加入外籍,有的积累起巨额资本,却带着“老一代”华人对柬埔寨难以割舍的情分回归。这两种人都认为他们才是柬埔寨“真正的华人”,不同于父辈,后者没有在这里长远居住的打算,也不同于21世纪后从中国大陆来的“新侨”,新侨称这些华人为“本地龙”,他们自己是“过江龙”。由这两者构成的华人群体,是红色高棉后柬埔寨华人社会“承上启下”和“沟通内外”的关键,他们联接了断层前后两个时代,是从华侨到新侨的过渡,即两种“过客”之间的中间环节,既是真正“扎根”柬埔寨,又与祖籍国和再移居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两种人继承了红色高棉前华人在柬埔寨经商的悠久传统。柬埔寨华商经济深嵌入柬埔寨本土社会,它们的历史在断裂中延续和轮回。从吴哥王城到金边港口,在柬埔寨历史的分水岭上,华商既是柬埔寨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转为依靠外部市场这一深刻变革的受益者,也是其承担者,因为柬埔寨人“从事种稻、僧侣或当官”,“销售、园艺和对外贸易掌握在华人或华裔手里”。[22]而经历“20年断层”后的华商经济,依然是凭借在上述柬埔寨历史的转折时期构建起的“区域性的贸易体系”。柬埔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这是其历史的又一个分水岭,西方殖民者与土著社会之间总是“隔着一层”,这一层便是华商,作为外来者的西方人,不得不依靠华人在当地的商业网络,才得以和土著社会衔接,使柬埔寨偏僻乡野出产的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将世界市场上的货物销往柬埔寨农村。20世纪90年代,当柬埔寨的国门重新打开,联合国军、台湾人、香港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等作为新的外来者,小到他们的“吃喝拉撒”,大到巨额投资,也需要本地华人的接引,才能在柬埔寨社会落地。华商,对外,使柬埔寨经济融入外部世界;对内,使外来者适应本土社会,正是他们介于内外之间的“中间”角色,以及他们的“中间层”发展模式,使他们成为柬埔寨这个“多元社会”中的“中坚”力量。
华商在柬埔寨社会结构中的这种位置和功能,也是其作为“他者”,与柬埔寨社会长久以来互动弥合、相辅相成的结果。柬埔寨人大多习惯生活在农村,扎根土地,靠天吃饭,城里的柬埔寨人更愿意做官而不想经商,加之其宗教强调个人的修行与解脱,笃信佛教的柬埔寨人,其生活观是朝向未来的超度,而此世的生活则眼光向内,面向土地与佛寺,于是,它早已把世俗的经济活动交给华人。其次,不同于中国社会中的等级与升迁方式,传统上,诸如柬埔寨、泰国这类东南亚社会只划分贵族和平民,平民不属于土地,而属于他们的保护人,每个人都在其固定的地位上履行明确的义务和权利,但华人作为外来者,脱离于这套人身依附关系之外,因此,在土著社会结构中,在最顶端的保护人和最底层的受保护人之间,为华人留下可以填补的“断层”。
地处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夹缝”的柬埔寨,正是巧借来自东、西两边的“他者”之力,使吴哥王城一度成为中南半岛上的宗教中心,也曾使繁华富庶的金边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经历20世纪20年的战乱后,一片空白的柬埔寨想要浴火重生,同样需要他者。1989年,越南刚刚从柬撤军,柬埔寨谢辛亲王便召集十一位华人去他家,这些华人是战后利用金边百废待兴、亟需小手工业的时机第一批重新从商的华人。谢辛亲王让他们筹备恢复华人组织:“大多数高棉人想在政府里当官,不喜欢也不善于经商。你们应当组织起来,联系在海外的亲戚朋友,吸引外资,当好发展经济的桥梁。”[23]而独揽柬埔寨军政大权几十年的洪森,早在担任首相之前,就礼贤下士,亲自去请战乱时逃亡海外、积累起丰富资源的一些柬埔寨华人回归;出任首相之后,更加意识到华商对于柬埔寨经济恢复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无论是踩着脚踏车奔波于金边与泰国、越南之间的崇山峻岭,划着小木船颠簸在暹罗湾的风浪中交接货,还是将被中国农民视作安身立命之“根”、被柬埔寨人奉为神圣的土地作为“生金”的媒介,柬埔寨华商总是在各种历史的断层之中,在各国贸易的夹缝之内,“转来转去”、“靠来靠去”、“换来换去”,形成断层和夹缝之间的“中间层”。他们在“来”“去”之间,在“内”“外”之间,与土著社会和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互为他者,认识和理解不同的社会文化机制,并思考如何使自身融入其中而又超脱其外。
[注释]
[1] Milton Osborne, Phnom Penh: A Cultural and Literary History, Signal Books Limited, 2008, p. 184.
[2] “亚洲经济‘新虎’——柬埔寨”,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2018年8月31日。
[3] 《中国与柬埔寨:政和商通》,《柬华日报》2017年6月15日。
[4] 黄晓坚:《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变迁(1991-2017)——兼论柬埔寨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
[5] 顾佳赟:《“一带一路”视阈下柬埔寨华人华侨的群体特征分析与政策选择》,《亚非研究》2016年第1期。
[6] W. E.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ublications Centre, 1967.
[7] W. E.Willmott,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0.
[8] 施坚雅著,许华等译,力践等审校:《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9] Michiel Verver, “Templates of‘Chineseness’ and Trajectories of Cambodian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Phnom Penh”,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Vol. 1, No.2, 2012, pp. 291-322; Michiel Verver and Heidi Dahles, “The Institutionalism of Oknha: Cambodian Entrepreneurship at the Interface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45, No. 1, 2015, pp. 48-70.
[10]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1] [12] [17] [19] [22]大卫·钱德勒著,许亮译:《柬埔寨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5、89、2、277、117 页。
[13]张燮著,谢方校注:《东西洋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52页。
[14][15]晃西士加尼撰,丁日昌督译:《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广文书局,1978年,第16、39页。
[16]庄国土:《二战以来柬埔寨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
[18]Maurice Freedman ,“The Handling of Money: a Note on the Background to the Economic Sophisti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William Skinner,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4年。
[20]Sokbunthoeun So,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 of Land Registration at the Grassroots”, Cambodi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ited by Caroline Hughes and Kheang Un, NIAS Press, 2011, pp. 139-140.
[21]施坚雅著,许华等译,力践等审校:《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第108页。
[23]谢辛亲王召见这十一位华人的过程参见柬华理事总会主编:《柬华理事总会成立十三周年纪念特刊》,柬华理事总会出版发行,2003年,第62、72页,以及笔者对其中几位当事人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