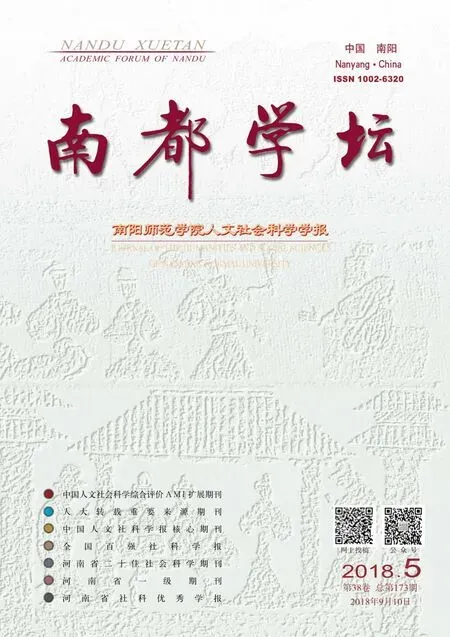李鸿章与何如璋的“球案”三策
刘 韶 军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清朝光绪初年,中日之间发生了影响琉球国命运的“球案”,李鸿章在处理“球案”时,从当时清政府派驻日本公使何如璋于光绪四年(1878)的来函中提出的上、中、下三策中选择了其中的下策①何如璋发给李鸿章的信函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的《李鸿章全集》第3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后引《李鸿章全集》,均为此版本)内附于李鸿章给总理衙门信函之后,但不是何如璋来函的全文,而是节录,作为李鸿章函的附录。此函的全文收在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的《何如璋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内,以下引用何氏论处理“球案”三策的原文,都据《何如璋集》此版本的第95—97页。。何氏提出的下策是“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评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侥幸图存”。与上、中二策相比,下策可简称为“言之复言之”之策,而上、中二策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要言,而且要采取行动,可称为言行兼举之策,下策则是只言而无行的策略。
选择下策与日本交涉琉球问题,最终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让“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侥幸图存”的目标。而日本早在中国采取此策以前就已经为实际吞并琉球而采取了不少行动,在何如璋提出处理“球案”的三策之前,清政府并没有针对日本对琉球采取的一系列吞并行动而采取对应性的有效行动,也没有对此进行交涉。这种反应迟钝的态度,使中日双方在处理琉球问题时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即日本步步得手,中国初期没有反应和交涉,到日本对琉球“阻贡”之时,中国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状态之中。因此,何如璋虽然根据他对日本国内各方面情况的了解而提出了三策,但李鸿章综合各方面情况考虑,已经没有魄力采取何氏提出的上、中之策,只能选择其中最为无力的下策。这一选择使得日本有恃无恐,更进一步地采取更多的吞并琉球的实际行动,而在与中国进行口头上的外交交涉时,则横生枝节、蛮不讲理,最终使得清政府在琉球问题的处理上不得不接受琉球被日本吞并的实际结果。虽然在条约的签署问题上清政府采取了延宕之策而不与日本最终结案,但这种无可奈何的办法也不能改变日本吞并琉球的既成事实。
更严重的是,日本通过观察清政府处理“球案”的态度与手法,更进一步摸准了清政府处理外交问题时的脉搏,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制造朝鲜问题,逐步扩张自己,削弱中国,使中日两国在琉球问题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从而使两国在其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本文分析李鸿章根据何如璋提出的三策在处理琉球问题时的种种想法及其逻辑,探讨影响李鸿章之所以如此考虑的各种因素,并以日本方面的言与行作为参照,由此看出李鸿章在处理“球案”时的无奈、无力、无策的尴尬状态。
一、清政府对琉球问题的麻木不仁
日本决定对琉球采取吞并行动,早在何如璋向李鸿章提出“球案”三策之前。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已经由天皇发布诏书废琉球国王为藩王,这对改变琉球国家性质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但中国方面对此没有采取交涉行动。到同治十三年(1874),为平息日本出兵台湾事件,中日签署了《台事专条》(即《北京专条》)。之后,参与此事的日方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回到日本后就向政府上书,建议及早对琉球采取措施,其中说:“琉球两属形态,自中世以来,因袭已久,难于遽加改革,以至因循至于今日。”[1]100这一说法与后来日本与中国进行“球案”交涉时根本不承认琉球“两属”的说法完全不同。这一情况也说明了琉球国本来对于中日双方是“两属”的状态,而这是历史形成的现状,日本既不能否定,也难于遽加改变。但日本后来改变说法,不承认琉球的“两属”,而硬说琉球本来只属于日本,则反映出日本政府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赖账的流氓态度。大久保利通当时还承认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现状,因此提出了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断绝其与中国之关系,自刑法、教育以下以至凡百制度,逐渐改革,以举其属我版图之实效”。日本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逐步采取措施,以达到改变琉球两属的状态,使之变成专属日本的目的。这一事实也反映了日本早就有心改变琉球两属的现状,而清政府对此则没有应有的警惕,更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到光绪元年(1875)三月,大久保在东京接见琉球三司官池城安规等人时说:“琉球藩尚成两属形式,今日若不改革,则将受中国干涉。”[1]101池城等担心中国政府不予同意,没有答应大久保的提议。日本政府于是马上发出命令并着手实行,包括:废止琉球对中国的朝贡和派遣使节等;撤销琉球在福州的琉球馆;琉球与中国的贸易业务由在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琉球藩王更迭之际接受中国册封之例予以废止;琉球与中国的事务交涉,由日本外务省管辖处分,同时还在琉球设置了兵营。此年六月,日本派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到琉球传达上述命令,琉球方面表示不能奉命,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因此停止改变琉球现实状态的脚步。光绪二年(1876),日本政府就在琉球施行了新裁判制及警察制,并对琉球民众施行海外护照制,彻底施行日本对于琉球发布的一系列新政之令。
到光绪三年(1877)三月,琉球王尚泰派其姐夫向德宏(日方称其名为幸地朝恒)到福州,谒见清廷的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哭诉日本禁阻琉球向中国朝贡的事件;又向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控诉,并请求美、英、法三国公使出面仲裁。到这时,何如璋才向李鸿章发信提出上、中、下三策,所以,日本方面认为“至此事态渐呈表面化”[1]102,由此进入中日双方为“球案”进行交涉的阶段。
对这一阶段有关情况的发展变化,李鸿章是否知道呢?他在光绪四年(1878)四月二十九日复何子峨的信中说:“迩年以来曾未认真议及。”据这一说法,似乎是说他知道近年以来的相关情况,只是没有认真商议如何应对。但他在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二十八日复丁雨生的信中却说:“琉球距闽台较近,今仅得何子峨东洋来信,究未知琉球实在情事。若执事为闽帅,必早专人确探回报。”[2]429这又表明福建方面的大臣没有派人探听情况和向李鸿章报告,所以他对近年以来日本对琉球的各种行动并不知道具体情况。但他并不是说对琉球的事情毫不了解,只是知之不详。
之所以会如此,表明清廷对琉球事务并不关心,所以日本人在《对华回忆录》中就说:“从来中国政府对于琉球,并不十分关心。”[1]104日本人所以会这样说,正反映了清政府对于琉球的命运确实是不十分关心的。所以李鸿章说“迩年以来曾未认真议及”,“究未知琉球实在情事”,而闽帅也没有早派专人探听确实情况而向朝廷报告。这是事实,毋庸置疑。而这种不十分关心的态度,就使日本从同治十一年以来就敢于对琉球一步步采取各种吞并措施,而中国却不闻不问。作为总理衙门大臣,难道不应该督促闽帅及驻日本使节随时探听日本与琉球的情况,及时掌握相关变化,而随时因应吗?清朝的大臣及官员们对此类事务都不放在心里,这就说明了当时清政府及其官员们在外交事务上是何等的把国家利益不当回事,反映了他们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是何等的短浅。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日本政府及其官员对于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增长与发展又是何等的重视和有远见。当时的中日双方的这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他们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会怎样做以及会形成怎样的不同结果,这对于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又是具有多么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何如璋在事态公开化以后所思考的对策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事态公开化以后,虽然清政府对于此前日本各种行动不曾关注和详细了解,但当琉球向德宏等人来华诉求中国出兵救援之时[注]据何如璋的报告,向德宏向中国诉求时也对日本在琉球的一些行动避而不谈,所以通过向德宏等人的诉求也不能详细了解日本在琉球都做了什么。,清政府仍有机会采取有力行动阻止日本,使之不能最终吞并琉球。
仔细考察从事态公开化到日本最终彻底吞并琉球,这一段时间还有两年,即从光绪三年(1877)三月向德宏来华求援,到光绪五年(1879)三月,日本政府发布对琉球的废藩置县令,并命松田道之率“步兵半大队”到琉球宣布此令[注]现在有些文章说松田道之率警官及警部巡查160人,或说率兵500人。与日本方面出版的《对华回忆录》对比,至少是士兵500人,不可能只是警官和警部巡查160人。20世纪的抗日战争时,日军陆军编制是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一个步兵大队约1215人,则日本人的《对华回忆录》说的“步兵半大队”就应当是500-600人左右。又据《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34页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的“与美前总统晤谈节略”:“日本今春遂派兵四百名入中山,掳其世子、大臣至东京。”400之数亦与500接近,而与160人相差较多。,到四月四日以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名义布告废止琉球藩,设冲绳县,并任命县令,到六月,最终逼迫琉球王移居东京。只是到了这个程度,日本人才说“琉球完全统一在日本的府县制度之下了”[1]103。
在从事态公开化到日本完全把琉球统一为它的府县制度之下,李鸿章及清政府又做了什么呢?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实际上又浪费了一年时间,即到光绪四年(1878)四月,何如璋才向李鸿章提出了著名的上、中、下三策,而这一年时间内,清政府仍然是无所作为。
考察清政府向日本派出正式使节,是在光绪二年(1876)八月中,许钤身为正使,何如璋为副使,但许钤身实际并未成行,所以到此年十二月初,又任命何如璋为驻日本正使。也就是说,在向德宏向华哭诉求援之时,何如璋已为驻日大使。他为什么到光绪四年(1878)四月才向李鸿章报告有关情况并提出上、中、下三策呢?考察这一过程,又可看出当时清政府的官员做事是如何拖沓,完全不能适应当时世界各国相互来往的最新潮流。
据何如璋《使东述略》[3]68-78记载,虽然何如璋在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就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日正使,但他到次年光绪三年(1877)七月才接到正式的敕命和国书,这中间就拖延了半年多的时间。之后又拖了三个月,这是何如璋为了前往日本赴任而做各方面的准备,即准备成行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到了十月,何如璋才从上海乘船出发,在日本登陆后,前往东京的途中,又经过了许多地方,每地都要停留,与当地人士交往应酬。这不禁让我想起南宋时的陆游从家乡绍兴前往四川夔州赴任的情况,为此他写了一本《入蜀记》,前后也是绵延了大半年,他在《入蜀记》中仔细记载整个准备成行以及一路上的见闻、与各地官员人士相互交往应酬的情况。这与何如璋赴日本出任正使时的情况非常相似,所以他也会写成一本类似《入蜀记》那样的赴任日记。这也说明了中国古时历代官员的文人习气及其拖沓作风已经成为传统。
何如璋直到十一月二十日[注]吴国仪《略论清政府开始向国外派遣常驻使节》(《外交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中说何如璋于此年11月30日到达日本,这是不确切的。仔细阅读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就可知道。才到达日本首都东京。也就是说,何如璋作为清政府派驻日本的正使,是在向德宏哭诉求援的八个月后才正式开始他的外交使命的。然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可以理解为在这一段时间内是要了解日本的各方面情况,之后到次年即光绪四年(1878)的四月,才写信给李鸿章,论及救援琉球之事。
据这封信所述,可知何如璋是在用心了解日本国的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才向李鸿章写信提出具体建议。正是在这一期间,日本抓紧实施了吞并琉球的计划。前面说到清政府对日本从同治十一年(1872)将琉球国王废为藩王,到光绪三年(1877)事态公开化,五年之间,清政府对琉球的命运不予关心,置之不问。而事态公开化之后,又因如上所述的缘故而使事情的处理拖延了近一年时间。一方是紧锣密鼓地采取种种吞并措施,一方则是按部就班不慌不忙地做着官员的事务,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政府在处理琉球问题上的主动权就一点点消失了。
即使这样,日本方面也还没有走到最后的地步。清政府还有一年的时间来采取有效的措施挽救这已经极不乐观的局面,在这个时候,扭转局势的关键是何如璋给李鸿章的来函及其中的上、中、下三策。
何如璋在光绪四年(1878)四月二十八日给李鸿章发来了“与总署总办论球事书”[3]95-97,这封信向李鸿章详细汇报了何如璋来到日本后所了解的相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日本在中国开始交涉琉球问题后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最后向李鸿章提出了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仔细阅读何如璋这封信,才能了解何氏提出的三策是否可行。
何如璋认为中国如果开始与日本交涉琉球之事,当然必须慎重,“稍有不慎,边衅易开,是事大且有关于安危利害”,但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是最好不要因为琉球之事而引起中日间的战争,这也符合李鸿章的想法。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处理此事才好呢?何氏说明他到日本后“细揆日本近情”,发现此前福建大臣的有关说法“有未尽得其要者”,而这种耳闻之说,会影响李鸿章的决断,所以何如璋要为李鸿章做尽量详细而可靠的报告。如前所述,李鸿章曾对丁雨生说过他对福建方面未能及时提供相关情报有所不满,而这也印证了何如璋所说不虚。何如璋信中所说的日本各方面的情况,都是李鸿章为处理琉球事件所急需的情报资料,但也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及其官员对日本的相关情况的掌握是多么匮乏和多么迟钝,这无形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在做出决断时的无奈。
何如璋为了提出上、中、下三策的可行性,首先分析了日本方面不敢“遽开边衅”的四个原因,这是对于整个形势的基本分析和采取何种对策的基本前提,也是符合慎重处理又不引起边衅的根本宗旨的,应该说也符合李鸿章主持整个外交事务时的基本思路的。
何如璋判断日本“不敢遽开边衅”,其根本前提是对日本国情的实际了解,即他在信中说的:“论国事者,百闻不如一见。闽中向时所传东耗[注]“闽中向时所传东耗”,这一句如实反映了当时清政府是如何了解日本相关情况的。“东”指东国,即当时清人称日本的一个名称。耗指消息。“东耗”即关于日本的消息。通过这一说法,可知清政府是通过福建官员的汇报而了解日本情况的,虽然这不是唯一的消息来源,但既被何如璋特别提起,也可看出是当时清政府据以获得日本方面的相关情况的重要来源。而下一句说明福建方面进行汇报的信息大都是来自商贾的传说和报纸的报道,又可证明清政府及福建方面都没有派人前往日本进行实地的考察与探知。只有等到何如璋到了日本之后,他才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日本的一些比较具体的情况,这就比福建方面向朝廷汇报的信息详细多了,但就国家决策的需要来看,这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也说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一向是极为疏略的,这背后就是中国一向以大国自居,而不把周围小国放在眼里的自大心态的充分表现。,皆出自商贾无识及日报夸大之词,多非其实。”如前面所说的“闽函所言,有未尽得其要者”,即出于这一因素。何如璋首先说明这一点,也是针对当时国内对日本实情不能真实了解而有夸大以生恐惧的心理,而这就会引导人们在处理相关外交事务时会产生误判而采取不正确的对策。
何如璋根据他所了解的日本实际情况,理出四个理由说明日本“不敢遽开边衅”,第一是因为“日本疆域不逾两粤,财赋远逊三吴,民细而质柔,惟萨摩、长门人稍称才武”,即日本与中国相比,是“大小悬殊”,所以日本的“执政知时局艰危,深维唇齿,欲倚我为援”。这是说日本当时的国力与中国不能相比,日本执政者也不想得罪中国,还想维持中日唇齿相依的关系。这是何氏到日本后通过“旁观目击[注]“旁观目击”四个字,说明何如璋了解日本的情况也是非常肤浅的。这都说明当时的清政府对于日本根本没有专门的机构与人员和相应的办法去搜集和掌握相关的各方面的情报资料。这也可以说是李鸿章在处理“球案”时感到非常没有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了解到的日本方面的“情伪”之一。
第二是日本的财力情况,何如璋说:“日人自废藩后,改革纷纭,债逾一亿,去岁萨乱[注]“萨乱”,即明治十年(1877)萨摩藩反抗明治政府的叛乱。,以民心不靖,复议减租,国用因之愈绌。顷下令借公债一千余万,以继度支,闻民间未有应者,其穷急可知。迩年赖以敷衍者,纸币耳,若兴兵构怨,则军火船械购自外国者必须现金(故去岁有向我借枪子之事)。东人虽巧,恐不能做无米之炊。”这是说日本当时的财政情况也不允许遽开边衅。其中说到的“现金”,不是日本国内使用的纸币,而是真金白银,所以说日本就算是想开战,在财力上也不能支应。
第三是日本的军力情况。何如璋说:“该国近更军制,寓兵于农,常备额陆军三万二千人,海军不及四千人,兵轮十五号,多朽败不堪使者,大炮数十尊,不尽新制。定购英石兵轮三号,以费绌,仅一号始抵横滨,名为铁甲,实铁皮耳,每船价值仅三十余万金,非钜制也。其驾驶、兵法亦未精,尚非我军敌。全国口岸纷错,自防不暇,何暇谋人?”何氏通过自己到日本对其军力的实际了解,包括上面提到的“去岁向我借枪子”,认为当时日本陆、海军都还不是中国的对手,所以认为日本当时也不敢以琉球之事而与中国开战。
第四是日本国内的社会及民心情况。何如璋说:“废旧藩时,收田土偿以家禄,限十五年为期。近将届满,失职者日就贫困,怨望益深,故十年来祸乱迭起。若复倾国远争,内变将作。且常额不敷征调,势必役及番休,无故兴师,徒滋众怨。彼谋国者皆非轻躁之人,此种情形,谅筹之已熟。”这是说日本国内也不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具备与中国开战的高昂士气。
基于这四点分析,何如璋认为:“四年以来,日人不遽肆恶于球者,虑我与之争,或开边衅,是以徘徊未发。”这说明自日本对琉球逐步采取一系列行动以来,日本还是担心中国与之强力相争的,所以到何如璋发信之时日本还没有采取最后的行动。
当时中国人对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出兵台湾之事怀有恐惧心理,何如璋认为也不应因此而担心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就令败约寻仇、空国来争,试思彼兵船几何?海军几何?能令我沿海防不胜防乎?”他还分析了日本人对于出兵台湾的实际想法:“若台之役,则西乡隆盛实主之,非执政本谋,长崎临发,追之不及,因将错就错,使大久保来中议结……西乡后复议攻朝鲜,执政痛抑之,遂去官称乱,自灭其身,即此一端,可知东人之不敢轻易生衅。”由此认为日本当时执政者也不想马上与中国翻脸用兵。
何氏并进一步分析事态可能会怎样发展变化:“若以为日人无理如瘈狗焉,时思吞噬,果尔,则中、东之好终不可恃。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已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这说明对于日本的要求,不论是听之还是拒之,最终都不可能保持“中、东之好”,最后结果都对中国不利,所以在处理“球案”时就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抑制日本不断扩张的野心,如果处理“球案”软弱无力,最终的结果必是“边衅究不能免”。所以他提出的对策是:“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凡事皆然,防敌尤急。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日争衡,犹可克也。隐忍容之,养虎坐大,势将不可复制。”
这一分析判断,是有先见之明的,说明当时中国对琉球的处理如果决策不得当就会引起更多的连锁反应,使中国更加无力应对。何如璋对事态发展的这一逻辑,是符合事实的。而他的对策的基本点是先发制人,采取主动行动,占据主动地位,而其依据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不是狂妄自大和一味好战。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何如璋提出的上策是“一面辩论,一面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慑”。这一对策,是既要与日本辩论,又要采取派出兵船的实际行动,是言行并举的方案,目的是向日本表示中国对于琉球的“必争”态度,“即因此生衅”也“不能不争”,表示中国即使因此生衅也不会退让的强硬态度。这一对策之所以是上策,是由于中国采取主动行动,主动权在我,如何应对,让日本去选择。在采取行动的同时与日本辩论(言),言行兼举,言则有力,行必有果。
次一等的中策是“据理与争,止之,不听,约球人以必救,使抗东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东人受创,和议自成”。这一对策是让“球人”来对抗“东人”,中国“出偏师”进行策应,对日本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最后促成“和议”的结果。这一对策,中国有半主动权,日本仍是被动,而且中国的半主动随时可以变成全主动,日本必须考虑自己的实力来选择与中国抗衡的方案。
第三策是下策,既然称为下策,就是最不好的对策,是上策、中策行不通之后才可采取的对策,而不是一开始就放弃更为主动优势的上策和中策,自动选择最差的下策。这是人们之所以把对策分为上、中、下三等的道理所在。下策就是“言之不听,时复言之”,中国对日本言而不听,再“援公法邀各使评之”,这是让其他国家来言,希望让“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侥幸图存”。第三策之所以是下策,就在于全是靠言,希望通过中国不断地“言”,加上各国根据援引“公法”的“评”,来达到“日人自知理屈”的目的。对这一策略,如果是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一定会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
何如璋之所以提出三策而分为上、中、下,当然是要让李鸿章明白哪种对策最好,哪种最差。下策之所以最差,就是因为“言之复言之”是毫无用处的,各国的“评”和“日人自知理屈”,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可以说,这根本不是一策,只是做样子自欺欺人罢了。一个国家的外交事务如果这样来办理,会是什么结果,谁都能想象得到。
何如璋提出三策之后,也替李鸿章考虑了他的为难之处,但天下事不可能都那么好办,为难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在为难之时拿出正确的决策,才能挽狂澜,救中国。何如璋说:“如璋明知今日中国与诸国结约,决非用兵之时,况值晋豫旱饥,尤难措手。第揆之日本近情,其不能用兵,更甚于我。”即日本也有它的为难之处,两者相争勇者胜,谁敢先发制人,抢先采取主动行动,谁就占据了优势。这时不能只想到自己的为难,而应考虑今后的结果。所以何如璋实际上是不赞成采取下策的:“若徒恃口舌与争,则日本亦深悉我情实,决不因弹丸之地张挞伐之威,往反辩论,经旬累月,必求如旧日之两属,诚无了期。”这是告诉李鸿章,不能采取下策,不然就是“无了期”,这正应了后来李鸿章采取延宕之法所造成的不了了之的结果。
何如璋认为外交上的“言”不能是孤立的“言”,必须有其他条件的配合。他说:“窃谓各国纵横之局,必先审势,而后可以言理。”“审势”就是综合考察各方面的情势,包括双方国家的国情、实力、执政者的能力与性格、会采取怎样的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性以及其他国家与双方国家的利益关系等。对这些情况审查不清楚或有遗漏,不能利用这些实际情势,在言理时就会处于被动。所以下策的言之复言之,不能只是在口头上与对方交涉,而是要根据情势的变化与实际情况选择如何言,言什么。
中国是有漫长历史的国家,在历史上曾有许多例子告诉后人,如何在外交上与对手“言”。李鸿章和何如璋等人,都是熟读中国古书的人,对于《左传》中各国之间为了各种争端而进行外交交涉时所使用的“言”以及“言”与当时各国的情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与日本进行琉球问题交涉时,如何“言”也是一门高级的学问。根据历史经验,光靠“言”,没有“行”,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总之,何如璋为李鸿章提出的上、中、下三策,不是泛泛之“言”,而是他在了解日本国情的基础上,考虑到中国的为难之处,然后进行了周密考虑的结果。他的本意是不能采取“言之复言之”的下策,而应采取上策或中策。但李鸿章为什么却选择了最不好的下策呢?他在做出这一选择时究竟做了怎样的思考呢?对这些问题也需要加以分析。
三、影响李鸿章选择下策的各种因素
李鸿章之所以选择下策,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距琉球远,且全是海路;第二个是当时中国的铁甲舰不足。
李鸿章在光绪四年(1878)“复何子峨”的信中说:“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昔春秋时卫人灭邢,莒人灭鄫,以齐、晋之强大,不能过问,盖虽欲恤邻救患,而地势足以阻之。”[2]312
但地远不能成为理由,所举的历史上的例子也不充分。春秋时齐、晋等国并不是因为地远就不派兵到其他国家进行作战行动,如齐桓公在幽地与鲁、宋等国进行会盟,攻打山戎直到孤竹而救援燕国,会同宋、曹等国共同救邢而重建邢国和卫国,到召陵攻打楚国,在洮地与诸国会盟而扶助周襄王即位,到葵丘与诸国相会等,以及晋国与楚国在城濮、泌、鄢陵等地发生大战,这些地方距齐、晋都是地远,而齐、晋仍然要采取应该实施的军事行动,这都足以说明李鸿章所说的春秋时齐、晋之国因地远问题就不出兵恤邻救患,是不足为据的。
关于铁甲舰的问题,何如璋信中说到当时日本购于外国的军舰,“仅一号始抵横滨,名为铁甲,实铁皮耳”。李鸿章在“复何子峨”的信中说:“所购铁甲船,闻甲有四寸,似非铁皮五六分厚者可比。”这里说到的日本所购铁甲舰,即日本从西方购买的第一条铁甲军舰“甲铁号”。此舰为木制战舰,外包90至140毫米厚[注]据这一数据,1寸等于3.333厘米,90—140毫米即9—14厘米,约合中国的3—4寸多,可知李鸿章说的“四寸”是符合事实的,而何如璋说的“铁皮”则不太准确。的锻铁装甲,1863年建于法国波尔多拉芒兄弟船厂。经多国转手后,同治六年(1867)以40万美元出售给日本德川幕府,同治七年(1868)五月到达日本。但当时日本正处于戊辰内战状态,明治政府与处于日本东北地区的幕府势力正在作战,西方各国处于中立,美国公使将船扣留在横滨。当时幕府和明治政府的海军都是木制军舰,所以幕府和明治政府都想得到这艘船。同治八年(1869)三月,此舰被移交给明治政府,取名“甲铁号”,同治十年(1871)改名“东”号。同治十三年(1874)在长崎因台风沉没,后打捞出来修复后作为预备役舰。到光绪三年(1877),日本已有3艘二等铁甲舰[注]一等铁甲舰排水量在8000—10000吨以上,后来中国的“定远”被称为“遍地球一等之铁甲舰”,二等铁甲舰排水量在5000—7000吨,如日本的“扶桑”“比睿”铁甲舰,当时中国又称之为“小铁甲船”。,海军实力超过了中国。
中国方面,同治年间,在福建设船政,建有船厂,又在上海建江南制造局,也有造船厂。到同治末年,二厂造出兵船近二十艘,都是仿西方的三桅兵船[注]早期的铁甲舰也有三桅,还要依靠风力航行。,属于木船,但都安装大炮数十尊,如同治十一年(1872)江南制造局造出的第5号船,长30丈,置大炮26尊,英、法人称为中国最巨之船。同治十二年(1873)福建船政造出的7、8号战船,安装的大炮,既有前膛炮,也有后膛炮。据记载,这些新造的兵船,都能出洋巡历,南至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北至辽东。但这类兵船还不能与日本的“甲铁号”一类的铁甲舰相比,所以李鸿章一心想通过购买西方最新式铁甲舰的方式建立新式海军来与日本对抗。但每艘铁甲舰需银100万两,清朝廷在拨款上一直不太重视,如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的信中说:“南北洋海防经费,第一年尚解百余万,次年已不及百万,今更不及数十万。”[2]429这就使李鸿章建设新式海军的愿望迟迟不得实现。
当时李鸿章曾受光绪皇帝接见,也谈到铁甲舰与处理琉球问题的关系,见前述“复丁雨生”的信中说:
上(指光绪帝)询:“琉球事当若何?”
(李鸿章)对:“惜我无铁甲船,但有二铁甲,闯入琉球,倭必自退。”
上谓:“外廷皆力言铁甲不可购者,糜费无益。”
对:“至此可知有益,但既无巨款,亦来不及也。”[2]429
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定远”“镇远”两舰才从德国建成回国。二舰的装甲、火炮口径虽不是当时世界之最,但在远东无与匹敌,被称为“遍地球一等铁甲船”,在海军实力上才超过日本。
在处理琉球问题时,除了何如璋,也曾有其他大臣提出用兵之策,如李鸿章在复丁雨生的信中提道:“郑玉轩献议:借洋债购中小铁甲船4号,配以闽厂所造兵轮16号,分为4队,专派熟悉军务、船务大臣为统帅,管辖海面数千里,闽、津、沪三机器局制备药、弹、煤油等物。”李鸿章认为“其言殊有条理”,但举借洋债一事,在当时也难以实行。李鸿章此信说:“农枢久以洋债为厉禁,左公二次假洋商为华商,利息一分三厘,各省重受其累,洋人永著为例。于是中外更讳言‘洋债’二字。玉轩此议,当轴闻之破胆,然非如此则铁甲断不能购。”为此李鸿章不由感叹:“无钱逼倒英雄汉。”[2]429
考察到这些情况,就可理解李鸿章为什么不敢采纳何如璋用兵的上、下二策了,也就能理解李鸿章在处理琉球之事时的无奈与无力了[注]关于当时中国的海军情况,查有关论文,有人认为:清朝海军在1861-1884年间发展迅猛,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1867年到1876年,江南制造局共制成6舰,1869年到1874年,福州船政局共制成15舰,见侯昂舒、龙方成:《论清朝海军后期停滞的深层原因》,《军事历史》,2006年第6期。也有文章说:自1874年丁汝昌建议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在向英、德、法等国购买舰艇、炮械的同时,又在福建马尾设立船政,建船厂,设学堂,不到十年,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建成,共有各类舰船100余艘,约9万吨,见袁瑛:《清朝海军兴衰初探》,《海洋开发与管理》,1999年第2期。戚其章对此的统计数字不同,见戚氏《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齐鲁学刊》,1982年第2期。此文说:到1884年,三洋海军初步建成,福建海军有舰只11艘,9857吨;北洋海军有舰只14艘,10980吨,南洋海军有舰只18艘,21287吨。按吨位来说,这似乎是一支可观的海军力量。这些文章对当时中国海军的论述,都不够详细,还无法证明当时中国的海军就强过日本。。就以上所述两个因素看,第一个因素受第二个因素的制约,如果铁甲舰的问题解决了,地远而力不及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当时中国的海军实力不及,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经济落后。
除了这两个最主要的因素,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影响着琉球问题的处理,如在何如璋与日本外务省的交涉陷于僵局之时[注]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记载,何如璋到东京后,于光绪四年(1878)9月3日到日本外务省会见外务卿寺岛宗则,为琉球事件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其中说道:“不顾琉球多年臣事中国之事实,禁止其对中国朝贡,其故安在?宜令率由旧章。”寺岛对此竟然说:“我国(指日本)以前对琉球外交虽默许,但(琉球为)无独立权之国,恐有为他国所并吞之虑,故今禁其私交。”这与大久保与中国订立《北京专条》后的上书中明确承认琉球为两属之国的说法完全相反。何如璋又在10月7日向日本外务省送出照会,其中援引了两国订立条约的第一条,而寺岛在11月21日对此照会提交“复文”时明确说:“该岛数百年来皆为我国之邦土。”又因为何如璋的照会中有“我政府以为日本为堂堂大国,恐不至无视邻交,轻侮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的语句,寺岛竟以此为借口,说照会中的这种说法是对日本的无礼,于是反向中国提出要求:“如前言不撤回,我不欲商谈。”见该书第104至106页。,格兰忒建议两国另派大员会商,以避开外交官层次上的纠缠不清。但李鸿章认为中国方面竟然没有可用的人才,见李鸿章光绪五年八月初六的“复丁雨生中丞函”:
子峨照会,语太过火,此时未便先撤,倘日本肯另派大员来华商办,自无不可俯就之理。若欲中国派人前往,不特无大员可派,亦虑难以收场。[2]481
另派高级大员相商的办法不是不可行,但令李鸿章为难的竟是“无大员可派”,中国缺乏处理这种外交难题的专门人才,也对李鸿章采纳下策产生了不利影响。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让日本有机可乘。即当初中、日订立条约时,对“两属”的“邦土”的说法过于含混,给日本留下了狡辩的机会。如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与美前总统晤谈节略”中说:
(向美国前总统格兰忒)指示中国、日本修好条规第一款:两国所属邦土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安全。毕副领事(毕德格)云:可惜立约时未将朝鲜、琉球等属国说明。当告以:邦者,属国也;土者,内地也,即是此意。[2]434
两国所立规约中使用这种还需要另加训诂的文字,而不是明确指明其所含的意思,应该说是中国方面在订立条约时的一个疏漏,日本方面肯定知道中国古代文字在使用时的这种特定情况,所以也不在订立条约时专门提出,这说明日本在订立条约之时就有故意模糊有关文字之含义的用心。所以日本后来可以不顾事实,否认琉球是中国的属国,硬说数百年来琉球都是日本的属国。如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的《对华回忆录》所载:
何如璋于光绪四年(1878)10月7日向日本外务省送出照会,其中就援引了两国订立条约的第一条,而寺岛在11月21日对照会提交“复文”时就说:“该岛数百年来皆为我国之邦土。”
这不仅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也是利用中日条约对两属邦土说法的漏洞,而采取了另一种解释。此后日本与中国交涉琉球问题时,就一口咬定琉球历来是日本的邦土,而不是承认中国理解的琉球为中国属国的解释。虽然中国方面可以用中国传统对文字进行训诂的方式说“邦”指属国,“土”指本国内地,但在条约中并没有明确说明“邦”所指的“属国”究竟是指哪国,所以日本后来也可以说琉球是属于他们的“邦”,而不是中国所属的“邦”,这就使中国无法再利用当初的条约来反驳日本。就算中国方面此后利用大量的历史文件证明琉球一直为中国的属国[注]《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312页载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复何子峨”,其中说:“密请总署转咨礼部,将琉球数百年朝贡成案钞备崖略,可以应答不穷。”此即中方搜集相关历史资料以备与日方交涉时作为历史证据。,但日本方面也找了一些历史上的材料主张琉球一直是自己的属国[1]107-109,这就为中国向日本交涉琉球问题时另外衍生出一个复杂的问题[注]《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99页“与日本竹添进一笔谈节略”中说:“琉球属中国自昔已然,天下皆知,非一时一人之私言。即使亦属日本,中国上下向所未悉。前日本与我定约时,第一条所属邦土,实指中国所属之朝鲜、琉球而言,当时伊达大臣及嗣后换约之副岛等,皆未向我声明琉球系日本属邦。今忽谓琉球专属日本,不属中国,强词夺理,深堪诧异。”这一问题的出现,就因为当初与日本订约时中国以为琉球属中国是天下皆知的事情,所以认为日本方面也会这样理解,就没有在条约中明确指出朝鲜和琉球是中国属国的事实。但日本方面心里明白,这样模糊的条约用语,正是后来可以做文章的漏洞,他们当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中方当场核实清楚,而是作为以后可以利用的地方。所以在琉球问题上,本来没有琉球是不是中国属国的问题,在经日本这样耍弄一番手段后,就成了琉球问题中的一个新生问题。。
总而言之,在琉球问题上,中方一开始并没有特别予以重视,给了日本几年的时间推进自己的吞并计划,当事态表面化之后,中方完全有理由出兵来解决双方的争端[注]《李鸿章全集》第32册“译前美总统幕友杨副将来函(光绪五年六月十一日到)”中载美国前总统格兰忒的副手杨越翰的说法:“以琉球既有臣服日本几百年之凭据,不难一查即可明白,何不先与中国说知,交出凭据,乃先做此失和之事。况两国各有驻京公使,遇有交涉大事,须照万国公法办理。此等重大事体,应照公法规矩公道商量,何必诡行霸气?我前在北京听恭亲王说,日本并未与总理衙门商量,又未与何钦差妥商。即将此意向日本大臣说:日本如此举动,中国不即决裂动兵,是中国大度含忍仁厚待人,不欲遽然失和。若西国遇有此事,必早动兵。”可知当时中国完全有理由向日本动兵来制止其吞并计划。,但由于李鸿章认为日本已有铁甲舰而中国尚没有与之相当的海军实力,故而没有信心动用兵力来实施强有力的制止手段,致使日本各种诡计全都得逞,而中国方面只言不行,全面被动,只能应付,没有一点反制手段,终于造成琉球被日本吞并的恶果,虽然李鸿章后来采用延宕之法不与日本结案,但琉球被日本吞并的事实则已形成,后来再想改变这种历史事实,就比当年有了更多更多的困难。而当时何如璋提出的上、中二策,本来也是在对日本各方面情况有所了解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但李鸿章在所有情况中最为看重的铁甲舰的铁甲厚度与何如璋所说的不符,也就使他从根本上丧失了采纳上、中二策的信心,只能寄希望于与日本进行言语交涉的方式上。而只言不行的办法,丝毫不能解决问题,这也被历史的进程所证明。此后,中日双方加紧海军建设,李鸿章也基本实现了他要建设强大海军的目的,手上有了“遍地球一等铁甲船”,却又因其他方面的建设不能与海军装备的建设同步,而使中国虽然有了比日本更先进的铁甲舰,也仍然在10年后的甲午海战中战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先进的新式海军,也遭到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