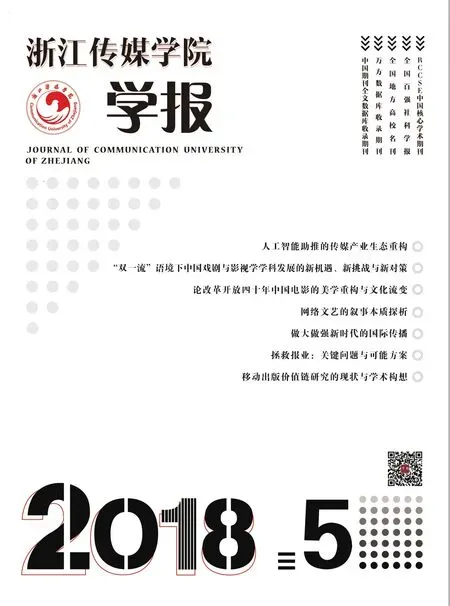当代动画电影对童话精神的重新审视和发现
徐洲赤
好莱坞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里,有一个核心情节是如何拯救家族记忆——曾奶奶已是垂暮之年,患有老年痴呆症,如果她就此死去,那么,亡灵世界的曾曾祖父冤魂将永远消散。最后关头,主人公将曾曾祖父的歌谣从亡灵世界里带回来,唱给曾奶奶听,终于唤醒了她的记忆,找回了照片……这个情节耐人寻味,它似乎表明:在拯救家族记忆方面,歌谣从来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西方动画电影曾呈现两种创作风向:一种是以迪斯尼以及欧洲动画为代表的讲述性传统,遵循渊远流长的童话精神和理念,保留着某种歌谣性的风格,体现出传统的童话叙事特征,比如《冰雪奇缘》《狮子王》《美女与野兽》这一类;另一种则是那些锐意求变的新锐动画公司,以颠覆性的主题诉求、反转性的情节构思和人物设定以及各种怪诞的画面造型来吸引观众,表现出某种“反童话”叙事的特征,比如试金石的《圣诞夜惊魂》、皮克斯的《神偷奶爸》《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但有意思的是,迪斯尼与皮克斯的合拍片《寻梦环游记》恰好体现了两种典型风格的融汇。笔者估且将之解读为当代动画电影的一种心理症候与反思。
一、歌谣性传统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种古老的讲述方式我们并不陌生,这种家族讲述式的叙事方式,建立起了讲述者与倾听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好莱坞梦工厂动画《疯狂原始人》生动地反映了原始人类与故事之间的依存关系,那位对家庭深具责任感的父亲瓜哥,每当家庭成员有离心迹象时,他便会使用这一招:“下面我们开始讲故事。从前……”
这让我们强烈感受到,我们的世界和记忆从来没有断裂过,我们仍然生活在同一条古老的河流里。正如民间童话故事的搜集、整理者安吉拉·卡特在她的《精怪故事集》序言中所说:“死者了解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情,尽管他们守口如瓶。”[1]这像是一个悖论。知晓一切者已经长眠,他所掌握的秘密随肉体一起腐烂;他懂得一切,却毫无用处;生存者需要那些秘密,却无法让死人开口。但事实并不那么让人绝望。因为还有大量的口头传说和故事在民间流传,它们带着讲述人的体温,倾听者会感觉那就是讲述者人生的一部分,讲述者本身也是童话的一部分,而这些讲述者往往是自己的亲人或长辈,因而,那些故事中的人和事也就化作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在故事的讲述中,虚幻与现实融为一体,化为听者的童年记忆,不可分割。
这个熟悉的讲述人既是童话故事的叙述者,也是童话中所包含着的丰富世界观的传承者、演绎者。不同的讲述者,倾注了对童话世界的不同理解。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在其著作《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中,曾引用儿童作家莱莉蒂埃的话说:“你们一定会向我承认,我们最好的故事就是最接近保姆讲述风格的简洁的那种。”[2]
那么,什么是保姆讲述风格?这是传统童话叙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即相同对话和情节的重复出现,简洁中透出繁复,繁复中延缓叙事的展开。以白雪公主的叙事为例,当白雪公主被遗弃在黑暗大森林里,发现了小矮人的小屋,故事是这样展开叙述的:
一进门,她就发现房子里的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十分整洁乾净。一张桌子上铺着白布,上面摆放着七个小盘子,每个盘子里都装有一块面包和其它一些吃的东西,盘子旁边依次放着七个装满葡萄酒的玻璃杯,七把刀子和叉子等,靠墙还并排放着七张小床。此时她感到又饿又渴,也顾不得这是谁的了,走上前去从每块面包上切了一小块吃了,又把每只玻璃杯里的酒喝了一点点。吃过喝过之后,她觉得非常疲倦,想躺下休息休息,于是来到那些床前,七张床的每一张她几乎都试过了,不是这一张太长,就是那一张太短,直到试了第七张床才合适。她在上面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这七个小矮人的出现的确是出于叙事复杂性的需要。首先,这七个小矮人本身就是超现实的,他们出现在白雪公主的困境中,对主人公命运转折起了铺垫作用,而不是直接让王子出现。其次,这个数字是一个不多不少的常数,如一个星期有七天,北斗七星等等,它给人们一个暗示:世界是有规律的。七个小矮人的数量,它既不影响故事的简洁性,又能够适当制造叙事上的繁复性,从而在叙事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悬念。我们将这种童话叙事的特有手法称之为童话叙事的悬宕性。比如:“她觉得非常疲倦,想躺下休息休息,于是来到那些床前,七张床的每一张她几乎都试过了,不是这一张太长,就是那一张太短,直到试了第七张床才合适。”按说,七个小矮人身高应该比较一致,他们睡的床不会长短不一。但是,假如直接交代说:“她在小矮人们的床上睡着了。”那么童话的趣味便被削弱。同样的道理,接下来小矮人出场:“第一个问:‘谁坐过我的凳子?’第二个问:‘谁吃过我盘子里的东西?’第三个问:‘谁吃过我的面包?’第四个问:‘谁动了我的调羹?’第五个问:‘谁用过我的叉子?’第六个问:‘谁用过我的小刀?’第七个问:‘谁喝过我的葡萄酒?’”这种有意制造的叙事上的繁复所造成的悬宕性能让儿童读者更好地享受故事的节奏,满足某种期待心理。
那些“漫漫长夜里讲故事的人”,他们的口头讲述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即兴创作的过程。“根据欧洲的习俗,讲故事的人大多是典型的女性,比如英语和法语中的‘鹅妈妈’,她是个坐在火炉边纺线的老太太——真的是在‘纺纱线’……”[1](3)而英文中“纺纱线”(spin a yarn)也有“编故事”的意思。[1](3)就像纺纱线一样,编故事者把不同出处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形成了集体创作与个人体验相结合的叙事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为了打发时间,另一方面是利用孩子急于获知故事结局的心理,有意延宕谜底的揭晓,于是,故事往往就采用此种铺排方式来进行。结果,这反而赋予故事传说一种特有的形式感,类似于修辞中铺排效应。它在情节叙述上的特点不是层层推进,而是徘徊反复,从而经过充分的铺垫,达到心理层累的效果,最后把情节和情绪推向高潮。同时,也无意中体现了童话叙事的目标:努力寻找可以把握的世界规律和本质。这个规律和本质可以概括为几个元素:可爱的好人、有秩序的世界、有规律的节奏和可掌控的未来。
二、“后来”的追问
但这种由讲述风格形成的、可以被把握的规律和本质在当代动画电影中正遭到挑战。童话的结尾通常是——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小孩子会不断追问:“后来呢?”而成人都知道,这样追问下去很危险:恢复的平衡有可能被打破。因而,“从此”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后来了。
在这些语境中,与乔字组合的词语,均是“装模做样”的意思。“乔势”、“乔样势”、“乔驱老”、“乔龙画虎”、“乔张致”、“乔张做致”、“乔声势”、“乔腔”,虽然它们的用例不同,但是其核心义却是一样的。
但当代动画创作却越来越多地追问起“后来”——童话面临被终结的危险。比如,《怪物史莱克》改造了公主与王子原型,开头就拿童话的温馨气氛来开涮:“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她被可怕的魔法控制住,只有真爱才能解救她……美丽的公主被关在城堡最高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待她的初吻。”看上去,一个关于爱情和幸福的美丽童话将走向预料中的美满结局。但是,温馨的童话氛围被突然打破:一只粗暴的大手撕掉了童话书——“这是不可能的。”随着一阵抽水马桶的冲水声,长相怪异的绿皮肤史莱克拎着裤子走出厕所。
这种改造从艺术童话的创作即已开始——“在民间童话中假定的愿望成真、惩恶扬善,在艺术童话中往往被一种带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冷冷的现实所取代。民间童话天真的大团圆结局模式也往往被突破。”[3]只是在当代动画创作中,创新和颠覆的意图更加明显。传统童话在长期流传中凝固下来的一部分东西在松动,不断被新的趣味和观念所解构。
1.“坏主角”
当代动画创作反童话叙事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常常以童话经典角色为戏仿和调侃对象,让传统童话的人物关系实现倒置和互换,并出现越来越多的“坏主角”动画电影。
如多年以前,宫崎骏动画电影《天空之城》里即出现过一位彪悍的海盗奶奶朵拉的形象,角色一改传统的慈祥祖母形象,精通天文地理和密码破解,横行天空,却面恶心善。但这里朵拉奶奶并非主角。到了蒂姆·波顿,他在《圣诞夜惊魂》里让一群幽灵世界的怪物做了主角,它们的目标是吓人——“我是会变脸的小丑/突然出现突然又溜走/我是你看不见的幽灵/像一阵风拂弄你的头发/我是夜晚月亮中的黑影/让你做噩梦一直吓到醒……”而在皮克斯的《神偷奶爸》里,主人公更是世界第一大坏蛋格鲁,他为了夺回这个头号坏蛋的称号,决定建造火箭升空盗取月亮,堪称偷天大盗。接着,这部皮克斯动画电影在拍了续集后,一不做二不休,把电影里的恶人帮凶小黄人开发成主角,拍了《小黄人大眼萌》。影片一开始,这些小黄人就明白宣示,他们的生存目标是能够傍上超级大恶人,为他服务,一起做坏事,否则种族将要毁灭。其中充满了夸张、妄想、蠢萌与搞笑,这都是十足的儿童趣味。因此,看起来这样的构思是反传统、反童话的,事实上却是儿童趣味的回归。
法国动画电影《王子与公主》,曾用传统的公主与王子关系,对传统童话角色的倒置和互换进行了一系列演绎:国王提出,如果有人能够打败女巫,他就把公主嫁给他。于是,王子勇敢地进入女巫的城堡,却发现女巫是个美丽女子。当国王派人来接王子去与公主结婚时,王子宣布,他爱的是女巫,他要留下来和她永远相伴。故事结局完全反转。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结束后,电影随之出现字幕:“休息一分钟,讨论一下吧。”此时,我们以为接下来会是讨论场景,但是,画面真的定格了,时间长达一分钟,以此来强调并且让观众去思考故事的反常性。
一分钟的空白画面之后,出现了另一个故事:王子和公主按照传统故事模式,亲吻结婚,但亲吻之后,男孩变成了青蛙,似乎人生在倒退。青蛙不断恳求女孩再次吻他让他变回来,谁知亲吻之后女孩自己变成了一只蜗牛,作为青蛙的男孩只能再亲回去,结果又变成一条鱼,双方只好不断地亲下去,又不断地变成各种意想不到的生物,比如腊肠狗、跳蚤、长颈鹿、大象等等。最后,他们各自变成了对方,就这样手拉手去结婚。这大约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最好结果。
在传统童话里,亲吻和变形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两大要素,亲吻是爱的象征,爱可以拯救一切,被魔法所困的童话人物往往需要在爱的解救下脱困。而在爱的作用下,变形意味着好人身份的恢复,以及爱的回报。但是,在这里,亲吻这个行为被解构了,其中的爱的力量意义被消解,爱意味着盲目的行为,将导向不可掌控的未来。甚至,正是爱的表达引起坏的结果,引起一连串的无法预知的变形。在这样不断的变形中,秩序彻底颠倒,而人们也在不同的视角变换中体察这个世界,或许这才是这个作品的真意,同时,也是所有反童话创作的真实意图。
2.反规训
成人化的规训是大多数童话主题的表达意旨。比如,童话故事中常常有一些情节,是故事主人公自己造成了命运的逆转,与眼看到手的幸福失之交臂,陷入困境。这是告诫人们该如何抗拒诱惑,或改变人身上某些不好的品性。如童话故事《太阳东边月亮西边》中,妻子不听丈夫的劝告,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一定要在晚上看清楚丈夫的脸,结果给自己和丈夫带来灾祸,到手的幸福生活消失了;在另一个故事里,主人公获得解救后,被吩咐快快往家的方向奔跑,千万不要回头看。但是,眼看就要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听到身后的声音,忍不住回头,于是,主人公重新被黑暗所囚禁。这些故事都在告诫孩子们要听话,要安分,不要自作主张。但是,当代动画作品的规训性叙事被抛弃,不再仅仅教导孩子们做一个乖乖女、好孩子,而更赞赏冒险和求知的勇气。
例如蓝天工作室系列动画电影《冰河世纪》中,那个跑遍地球、紧追松果不放的松鼠,以其可爱的造型和执着的精神令人开怀,以其丰富的寓意触动人心,那颗到处滚动的松果似乎代表着人们的欲望,推动世界走出冰冻时代。梦工厂作品《疯狂原始人》中,父亲瓜哥不肯离开山洞,认为传统的穴居生活才是安全的。当一家人在灾变中失去山洞,他的所有念头就是重新寻找一个山洞。他有许多来自传统的信条:“恐惧是好事,改变是坏事。”“任何的娱乐都是不好的”“不要不害怕”。这些信条在传统童话中依稀能够感受到。他的女儿小伊则对一切充满好奇,希望走出山洞,寻找光明,寻找新的生活。甚至,《寻梦环游记》中的主人公为了追求音乐梦想,进入了亡灵世界。显然,其中都蕴含着对儿童心性的肯定和张扬。
3.不完美
在这个颠覆传统的过程中,创作者有意突破了童话的完美模式,强调了不完美之处,包括人物性格的不完美、命运的不完美和结局的不完美。“我认为观众对于角色的认可度来自于他们的不完美,而不是他们的优点。”[4]在《怪物史莱克》中,所有的一切都在突出不完美,英俊的王子和美丽的公主这样的完美模式被解构了。前来解救公主的是一个住在肮脏沼泽里的自私怪物史莱克,他不是为了爱,只是为了自己的领地不被打扰,才答应国王去完成一项使命。公主也不像传统童话中那么矜持美丽,尤其是在故事的最后,丑陋的史莱克并没有被解除魔法成为帅气的王子,而是让公主也变成了丑陋的怪物——但从此他们却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动画电影《玛丽与马克斯》,主人公带有某种生理与心理的残缺,且他们的世界观也是“残缺”的。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主人公是两名通信长达20年的笔友。40多岁的马克斯是一个阿斯伯格症患者,有人群接触恐惧症,和小女孩玛丽的通信就成为他和这个世界的唯一交流。玛丽给素不相识的美国人写信,想知道美国人的孩子来自哪里?她认为孩子是从啤酒杯里生出来的,马克斯回信告诉她:“很不幸,美国孩子不是从啤酒罐里发现的。”这时候,我们认为马克斯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但是,接下去他告诉玛丽:“我四岁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她说小孩子是犹太祭司下的蛋孵出来的。如果你不是犹太人,那就是修女下的蛋孵化的。”马克斯经常在纽约的街头捡烟头,第一次给玛丽写回信那一天,他捡了128只烟头。他之所以捡烟头,以我们正常人理解,大概是为了防止火灾,或者环境卫生等等,但这是成人的想法,马克斯则如此解释:“这些乱扔的烟头很危险,它们有可能随下水道冲进海里,海里的鱼就会去抽它们。”在这样的世界观交流中,一个儿童和阿斯伯格症患者的世界就此相通了。
但玛丽和马克斯的世界不像传统童话那样绚丽,而是带着灰暗色彩,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封闭的精神世界里。作为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马克斯一旦接触现实世界就会崩溃。在现实世界里,他基本无法和人沟通,对语言之外的所有表情达意方式都无法理解。对女性抛过来的媚眼,他手足无措,或者毫无反应,因为他不能理解其中的意图。这样的“残缺”世界观会影响儿童观众的观感吗?电影的创作者似乎并没有为此担心,因为这种“残缺”恰恰体现了丰富的童趣。
三、颠覆中的融合与回归
反童话的叙事何以能够成立?细究起来,传统童话中的儿童世界观,其实是掺杂了成人希望儿童接受的世界观,而非纯粹的儿童世界观。比如,告诫孩子要听话、守规矩、遵守秩序、做个好人等等。但是,就儿童心性本身,他们是希望捣捣乱、恶作剧、做点坏事乃至天下大乱的。这样的想法,在成人讲述童话里会被隐藏和屏蔽,但在当代动画电影里得到了发现和开发。这是“坏主角”动画电影出现的心理基础。
事实上,在儿童的世界观里,其秩序是否真的如成人想象的那样井然有序呢?在反童话的动画电影里,童话世界的逻辑往往是破碎和非理性的。比如,法国动画电影《大坏狐狸的故事》,背景是一个秩序大乱的疯狂农场:一只想吃鸡想到发疯的狐狸被迫成了“鸡妈妈”,而三只误入歧途的小鸡一心想当“嗜血狐狸”;一只鸭子和兔子因为“误杀”了圣诞老人,不得不扛起拯救圣诞节的世纪重任……我们细加考量,这种破碎与反秩序恰恰是对规训化的农场秩序的颠覆,是一种自然秩序的回归,诗性世界的回归。诺瓦利斯将童话世界概括为“自然的自然状况——世界之前的世界。”[3](4)这才是彻底意义上的回归。
在对传统童话精神的重新审视和发现中,原初性的儿童世界观得以凸现。所谓“世界之前的世界”,便是要实现人的尊严的回归。安徒生说:“我真希望能够生活在童话世界里,能够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过一种奇妙的生活。”[5]“玛丽与马克斯”是在照着自己的心意生活,虽然在外人看来,这样的生活是灰暗的,但自有其奇妙之处。因为,他们不需要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来表达。
再如好莱坞动画电影《驯龙高手》中,破坏自然秩序的真正敌人是那个超级大恶龙。它住在一个巨大的山洞里,像一个蜂王那样,控制着全部飞龙,让他们每天给它提供食物。只有消灭它,才能让世界恢复平等相处的天然秩序。这揭示出,真正的自然秩序,必须摧毁所谓的权威和统治,才能使人的心性获得解放。正如《霍顿与无名氏》的结局:“从此,霍顿和呼呼族以及森林里的所有动物,包括袋鼠妈妈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件事教导我们,万物生而平等,无论他们多么渺小。”这就是原初性的儿童世界观的真意所在——“万物生而平等”,人人拥有尊严。
因此,当代动画电影的叙事风格在发生变化,但真正的童话精神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融合中实现新的回归。比如,讲述性叙事的代表迪斯尼动画,其画风越来越像皮克斯、蓝天工作室甚至漫威,但它的内在仍然是浓重的童话情结。比如《疯狂动物城》,灵感来自于童话名著《柳林风声》,人物也保持了迪士尼特色的可爱造型,情节上没有大的颠覆,但又有必要的反转,既是“童话喜剧”,也是“寓意电影”,还有动作、悬疑、政治和犯罪等元素,达到了迪斯尼风与反童话风的很好的平衡。有意思的是,以反童话姿态出现的《怪物史莱克》,无意中也暴露了创作者对童话的热爱:有一天,所有童话中的人物,包括灰姑娘、白雪公主、木偶匹诺曹等等,都逃到了史莱克的沼泽小屋前来避难。因为,这里的国王仇视童话世界。于是,怪物史莱克承担起拯救公主和童话世界的双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