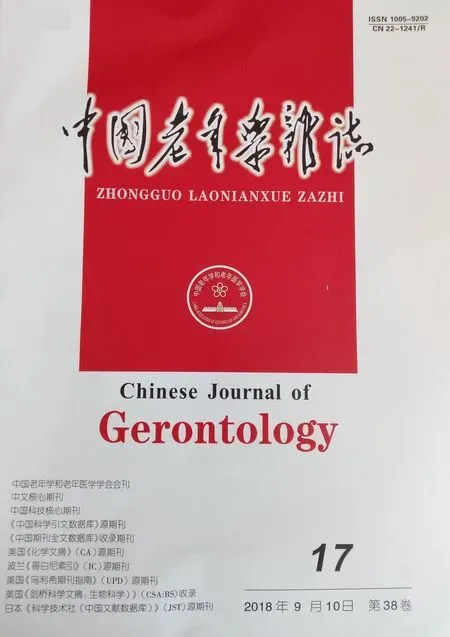缺血性组织损伤中内皮祖细胞的作用
蒋月丽 梁 冬 余靖一 庞明武 何超明 王源江 赵振强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老年医学中医科,海南 三亚 572000)
组织缺血损伤在临床上十分常见,如心肌梗死后心肌损伤,缺血性脑卒中所致脑组织损伤及肢体缺血损伤等〔1~3〕。造成缺血性损伤的关键因素在于组织供血不足〔4〕。大量研究表明,内皮祖细胞(EPCs)在缺血性组织损伤中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如促进缺血组织血管新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等。本文以EPCs在缺血性组织损伤中的修复潜能为主题,对现有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探讨基于EPCs临床治疗的潜在问题和应用前景。
1 EPCs及其生物学特性
1.1EPCs来源 EPCs是来源于机体骨髓的一种特定的造血祖细胞(HPCs)〔5〕。该细胞是未成熟的内皮细胞(ECs),可通过骨髓动员进入外周循环血液中。1997年,Asahara等〔6〕首次从人外周血中分离出EPCs,并进行体外培养。目前已经能够从多种组织样本获取EPCs,包括循环单核细胞群、脐带血及骨髓〔7~11〕。
1.2EPCs的表型特征 迄今为止,对于EPCs的表型特点尚无明确的定论。Asahara等〔6〕发现,EPCs能够表达造血干细胞表面抗原CD34。EPCs还能够表达CD133表型分子〔8,12〕。此外,这类细胞表达一些内皮特异性的细胞表型分子,包括:血小板内皮细胞黏附分子(CD31/PECAM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KDR/Flk-1)、内皮细胞特异性酪氨酸激酶受体(Tie)2、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及血管内皮钙黏蛋白(VE-Cadherin)〔13〕。
1.3EPCs的生物学功能 体外培养的EPCs呈贴壁式生长,细胞形态为梭状,能摄取乙酰化低密度脂蛋白(ac-LDL)〔14〕。ECs分化潜能是EPCs的重要功能特性〔6〕。另外,EPCs还具有其他功能特征,包括:迁移、黏附和小管形成〔15~17〕。EPCs对于维持血管稳态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并受到了广泛关注〔5,18〕。一方面,EPCs具有内皮分化的潜能,直接参与内皮再生〔8〕;另一方面,由EPCs分泌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血管紧张素(Ang)-1等〕和相关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L)-1β、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在血管新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19,20〕。
2 EPCs在组织缺血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大量动物实验研究表明,EPCs能够向缺血组织部位迁移,并分化形成ECs,参与血管新生〔13,21〕。同时,EPCs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等旁分泌物质,在缺血组织部位构建保护性微环境,促进缺血组织损伤修复〔20,22〕。目前,有关EPCs在缺血性组织损伤中的保护作用研究,主要涉及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肢体缺血损伤〔13,23,24〕。
2.1缺血性心脏病(MI) MI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心血管病(CVD)中常见类型之一,主要表现为心脏局部组织血供减少或停止〔25〕。据报道,在美国,每年约有79万人发生心肌梗死〔26〕。最近,《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6》发文指出,我国CVD危险因素流行趋势明显,CVD发病人数增多(约2.9亿),其中大陆MI患病人数约为1 140万,且急性心肌梗死(AMI)死亡率总体呈上升态势〔27〕。目前,人们已经在心肌梗死动物模型和临床患者中对EPCs的作用进行了相关研究。
在心肌梗死动物模型中研究发现,采用体外扩增的EPCs移植治疗后,动物心脏供血明显改善,心功能明显提高,同时,心肌瘢痕形成明显减少〔23〕。Kawamoto等〔28〕研究发现,对心肌梗死大鼠进行心肌内自体EPCs移植治疗后,缺血心肌部位微血管密度明显增加,同时,动物左心室射血分数增加。
研究表明,EPCs数量及细胞功能与心血管危险因素呈负相关〔18,29〕。临床研究表明,循环EPCs水平对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及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30〕。目前,一些临床试验正致力于研究EPCs在心肌梗死中的作用。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试图通过观察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患者,论证外周血循环EPCs与心肌梗死后再灌注损伤和心脏重构的关系,目前该项目已处于完成状态〔31〕。另有临床试验曾试图研究局部EPCs移植治疗心肌梗死,然而,这些项目最终因某些原因而终止试验〔32,33〕。EPCs保护心肌梗死的分子机制尚未阐明。多数研究认为与细胞功能性分子有关,如一氧化氮(NO)和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等。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对参与心脏康复计划的CAD患者血中EPCs数量和NO水平进行检测发现,执行心脏康复计划的患者循环EPCs数目增多,同时,部分患者血管内NO水平升高,提示NO生物活性可能与EPCs功能相关;据此,该研究所在CAD(包括心肌梗死)患者中进行了一项临床观察性研究,试图从基因水平上探索影响EPCs动员、内皮分化和血管修复潜能的内在因素,目前,该临床试验项目已处于完成状态〔34〕。由加拿大渥太华医院研究所发起的名为ENACT-AMI(the Enhanced Angiogenic Cell Therapy-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Trial)的随机对照试验(RCT)研究,首次对基因与细胞治疗相结合治疗AMI进行了临床探索研究,该二期临床试验企图通过eNOS过表达的方式,提高自体EPCs功能,促进心肌梗死后血管新生,目前,这一项目正在受试者招募阶段〔35〕。虽然,大量的临床前动物模型研究已证实EPCs在心肌梗死损伤中具有保护作用,但是尚缺乏直接的临床证据,仍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关临床试验以阐明EPCs在心肌梗死患者中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2.2缺血性脑卒中 脑卒中是致死致残常见的原因之一〔36〕。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占脑卒中总数的70%以上〔37〕。溶栓是目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唯一有效的方法,然而由于治疗时间窗窄,尚不能满足大多数患者的治疗需求〔38〕。近年来,干细胞移植研究备受瞩目。EPCs作为一种新型干细胞,不仅能参与血管新生,而且参与维持血管稳态,有望成为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新方法。在实验动物模型上,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基于EPCs的缺血性脑卒中治疗研究。给予缺血性脑卒中小鼠EPCs输注治疗后,动物脑梗损伤明显减轻:脑组织梗死体积显著减小,伴随着明显的行为学功能改善〔13〕。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移植的EPCs能够归巢于缺血损伤的脑组织部位,并参与形成新生血管,其机制可能与基质细胞衍生因子(SDF)-1/趋化因子受体(CXCR)4信号通路有关〔13〕。EPCs能分泌多种促血管形成生长因子,如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VEGF和肝细胞生长因子(HGF)等〔20〕。将EPCs条件培养基通过尾静脉注入缺血性脑卒中小鼠体内发现,梗死部位血管新生明显增多,同时伴随着神经功能明显改善〔22〕。目前,尚缺乏EPCs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的治疗研究及相关临床试验。由德国Charite 大学发起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内皮功能及内皮祖细胞水平变化前瞻性队列研究试图研究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急性期循环EPCs水平是否会增加〔39〕。另一项由中国南方医科大学发起的AMETIS一期临床试验试图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进行自体EPCs移植治疗研究,以评估EPCs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可行性、有效性及安全性〔40〕。然而,目前这两项临床试验尚处于停滞状态。仍需要对EPCs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保护作用进行更多的研究分析,尤其是相关临床试验的开展。
2.3缺血性肢体损伤外周动脉疾病(PAD) PAD是一种心脑外围区域的血管疾病〔41,42〕。引起PAD的发病因素有很多,如吸烟、糖尿病、肥胖和高血压等〔43~45〕。据报道,PAD在40岁以上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3%,60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会增加一倍〔46〕。其中,缺血性肢体损伤(LI)是PAD中最严重的类型。其发病机制为,患侧肢体动脉血流受阻,尤其是下肢〔47〕。在一些地区,每年每一百万人中就有500~1 000人遭受肢体缺血疾病的困扰〔48〕。肢体缺血病变常引起足部或脚趾疼痛,并进一步发展为肢体或足部溃疡和坏疽,甚至导致截肢或死亡,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47〕。超半数LI患者在确诊后5年内出现死亡〔3〕。目前,外科手术干预是处理肢体缺血病变的主要方式,如血管搭桥再通、摘除堵塞的动脉。然而,由于多种现实因素,超30%的患者不能从中获益,最终选择截肢〔47〕。再生医学的发展为缺血性肢体病变带来了新希望:通过诱导患肢血管新生,恢复缺血组织血液供应。在众多再生治疗研究中,EPCs的作用受到了广泛关注。
采用裸鼠和大鼠进行临床前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从动物外周血单核细胞群分离培养的EPCs,能够促进动物下肢缺血后组织血管新生〔10,23,49,50〕。另有研究报道,采用人源外周血和脐带血EPCs治疗后肢缺血后,动物缺血组织部位微血管密度显著提高〔10,50〕。目前,尚缺乏EPCs治疗缺血性肢体损伤的临床研究。Arici等〔46〕对8例重度肢体缺血患者进行EPCs细胞治疗研究发现,自体移植外周血来源的EPCs后,有6例达到伤口完全愈合,静息痛得到抑制,同时步行功能恢复;超声造影结果显示所有受试者患侧肢体血流均增加。虽然早期的临床试验表明,EPCs细胞治疗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并能促进LI患者伤口愈合。然而,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人体试验,以确证EPCs细胞治疗是否能延长LI患者免截肢生存期。
3 问题和挑战
目前对EPCs在缺血性组织损伤中的保护作用主要源于动物模型的验证结果,还未能实现临床转化。
3.1EPCs促肿瘤形成 EPCs与肿瘤的形成可能存在一定联系〔51~53〕。Vajkoczy等〔51〕的研究表明,EPCs可归巢于肿瘤组织中,促进肿瘤血管新生。采用小鼠人神经胶质瘤移植瘤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体内注射EPCs能够促进小鼠移植瘤生长,并增加肿瘤组织血管密度〔52〕。乳腺癌患者肿瘤组织中存在EPCs,且EPCs水平与患者血液中促血管生成因子VEGF呈正相关〔53〕。EPCs的促肿瘤效应将影响基于EPCs的治疗应用,尤其是伴有癌症或有潜在风险的患者。因此,为了排除潜在的致癌风险,需要对EPCs促肿瘤作用做深入研究,这样才能确保基于EPCs治疗缺血性组织损伤的安全性。
3.2EPCs生产标准化实现 EPCs细胞治疗在临床缺血性组织损伤中的常规应用,需要使用大量的细胞。同干细胞一样,EPCs作为一种先进疗法中的医药产品,其分离、培养扩增及处理过程需要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54,55〕。GMP的实施将为大规模生产满足临床质量要求的EPCs带来新挑战,包括EPCs细胞的分离获取、培养基和血清的使用、细胞培养的密度及必要的封闭式生物反应器系统。从人体骨髓中采集EPCs通常需要进行介入操作,而外周血和脐带血将为EPCs的采集提供可行的替代来源。此外,为了避免引入异源性物质,可使用血小板裂解液或者人血浆和血清替代胎牛血清对EPCs进行体外培养。封闭式生物反应器系统相关技术的应用,如微载体技术〔56〕和固定床细胞培养系统〔57〕,将为从EPCs含量稀少的样本中获取有效的细胞数提供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EPCs生产过程需要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包括:维持细胞表型及功能特性、避免细胞转化及监测微生物安全性,如此才能保证人体安全性,同时获得稳定的临床治疗效果。
综上,虽然目前缺乏EPCs在缺血性组织损伤修复中的临床研究,但是EPCs的这种保护作用在动物模型中得到了广泛验证,并且在人体试验中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基于EPCs的治疗方案有望成为治疗或预防缺血性组织损伤的新策略。一方面,针对内源性EPCs,可刺激骨髓动员,向外周血释放EPCs,促进内源性EPCs归巢至损伤组织;另一方面,可采用自体或异体移植技术进行EPCs移植。这将为临床上难治性组织缺血损伤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EPCs在多种组织器官缺血损伤中具有保护作用。在人体进行的EPCs细胞治疗研究结果提示,采用动物模型所获得的临床前实验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临床转化。然而,在实现基于EPCs对缺血性组织损伤进行临床治疗之前,仍需要注意和解决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EPCs潜在的促肿瘤生成效应;严格实施GMP进行EPCs大规模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