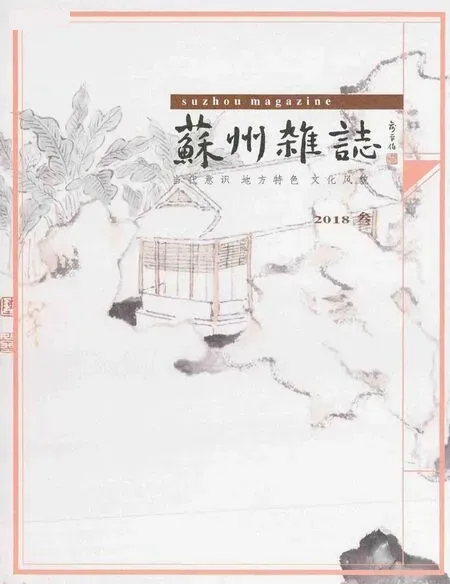怀念我的父亲易枫
易小珠
父亲易枫,曾用艺名易继习,生于1927年,江苏省苏州昆曲院国家二级编导,1988年退休,2006年10月因肺衰竭去世,终年80岁。
父亲出身于旧戏班,受新思潮的影响,不甘囿于传统表演,17岁便考入上海剧专(上海戏剧学院前身)学习西方戏剧。1946年毕业,此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父亲便与同学一起满怀革命热情参加了解放军部队文工团。我小时候曾看到一张一寸的小照片,清秀俊朗的父亲穿着军装神采奕奕地微笑着,当时的我又惊喜又兴奋,高兴地叫起来:“爸爸,你当过解放军?”一手高高扬起父亲的那张小小的一寸照片。哪知父亲脸一沉:“谁让你乱翻大人的东西!”说完便把照片收走了。从此,我再没看到那张让我惊喜让我骄傲的小照片。
著名编剧、省剧目工作室主任李培健老师曾是我在南艺学习时的编剧指导老师,他见到我常说:“小珠,你父亲当年在上海剧专是我的学长,我对他印象很深,他人很幽默风趣,常跟我们讲故事,说笑话,绘声绘色。”我猜想,那时的父亲一定是个充满朝气、开朗、阳光的年青人。
解放后,由于家庭背景和历史问题,父亲受到部队的审查。祖父易方朔,解放前为上海滑稽戏名艺人,作为戏班主,在社会上卖艺,常常会受到地痞流氓的干扰,祖父为了给戏班找个靠山,便给父亲在国民党的组织里挂了个名。这个历史污点让父亲深受打击,不仅离开了他所热爱的部队文艺生活,在以后的工作中,父亲在政治上始终抬不起头来,这种无形的压抑与负罪感,改变了父亲的性格,从此深自敛抑,遇事小心谨慎。
尽管这样,父亲的艺术才华却难以掩盖。父亲从小在小京班受过残酷而严格的戏曲训练,加之当时的上海舞台,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下看得多、听得多、学得多,也懂得多,对传统戏曲的表演有深厚的功底与修养。十七岁便考入上海剧专表演系,授课老师都是当时全国一流的戏剧专家,接受了大量西方舞台艺术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中西结合、融会贯通,艺术才能日趋成熟。当年上海剧专《剧讯业刊》的毕业专栏中,就刊有对父亲的个人介绍:
“易枫,名艺人易方朔先生的公子,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在戏剧上的造就也不同凡响,因为有个时期病倒,丢掉了许多演戏的机会,仅就《表》里的顾大爷,《同病相怜》里孙科员,《结婚进行曲》里的王科长而言,已有惊人的成绩。”
母亲说,父亲年青时曾参演过两部电影,可她只记得一部叫《表》。有次,正好电视里在播放老电影《表》,我满怀兴致地观看。父亲在里面演一个修表的大爷,较瘦。我猜想那时他大概只有二十二三岁吧,可把一个四五十岁风趣可亲的修表师傅演得维妙难肖。
父亲离开部队后,先在地方越剧团担任导演及技导工作,1953年加入苏州民锋苏剧团。当时剧团还没有被政府收编,苏剧老艺人,曾在苏州电视台任吴语主持的丁杰老师在世时曾对我说:“小珠,我和你父亲建团初就在一淘,我是团长,他是导演。那时候真苦啊!有一次连着几天大雪纷飞,路被雪封掉,剧团困在宜兴乡下角落里,要过年了,没钱没粮,饥寒交迫。我一个人顶着大雪出去借钞票,再背仔几十斤米、十几斤肉在雪地里一脚深一脚浅走仔十几里!”言语间充满了对剧团艰苦创业的感慨及与父亲的患难之情。
2006年父亲去世,那时丁杰老师还健在,特制了一盘VCD追忆父亲,在录像中他谈到了父亲的身世、学问、为人和他在剧团的工作,改编导演的《五姑娘》,还谈到了我们子女对父亲的关爱。在录像中他叙述道:
“1953年,易枫同志来民锋苏剧团,排的第一本戏是《秦香莲》。苏剧前身是苏滩,因为是坐唱形式走上舞台的,表演上沿用沪剧加唱的形式,没有用过锣鼓家生进行舞台表演,自从易枫同志来了以后,这一大功劳,功不可没!在苏剧中首次运用锣鼓家生,演员必须踏准锣鼓家生格点子来做戏,使苏剧舞台艺术走向成熟。他不仅在锣鼓家生上对我们有很大帮助,而且帮助我们许多演员从坐唱走上舞台表演,作了很多的指导工作,其中也包括我……
易枫同志很有学问,这个学问不是一般人所懂的。他从小出生于一个很苦的环境,他父亲虽然是名演员易方朔,但不是亲生。易方朔自己有剧团,易枫就在当时上海很有影响的小京班里长大,但他对小京班的表演不满意,于是在很多朋友的启发下,考入上海四川路横滨桥格上海剧专。先生很好,特别是洪深,觉得易枫在表演上很有灵性,很欢喜。但不满意他经常迟到。有一次洪深把他叫到自己房间里,易枫面对老师的责问讲了实话。原来祖父易方朔不同意他上剧专读书:‘你要读书我不负担,生活费自己唱出来!’易枫耿,你不准我读我偏要读!为了读书,易枫日里上课,夜里唱戏,戏班常要演日场,易枫只好上课、唱戏两头赶,分得一点点包银,勉强维持生活。
洪深听了学生的身世及处境,觉得这孩子这么辛苦,仍对戏剧艺术这么执着、这么热爱,两行热泪流了下来……从此,对易枫更加理解与怜惜。”
看了这段录像,我想起母亲曾对我说起,父亲读书,有一次放学晚,为要赶场子演出,急冲冲跑到剧场公司楼下,电梯不开,心一急拼命奔到七楼,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我想父亲的肺病就是那时落下的吧?
丁杰老师在录像中还提到了父亲的为人,他说:
“易枫同志为人有三大优点:不抽烟不吃酒;不弄牌;不搬嘴弄舌,搬弄是非。这些优点在剧团里是非常难得的,特别是最后一点,相当了不起!别人风言风语讲给他听,只当耳边风。这种事,他子女都不一定晓得。我是经过人,我晓得。”
丁杰老师继续说:
“由于历史问题,易枫一生在剧团没有被重用过,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但他仍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工作。他排过许许多多格戏,演过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格角色,剧团在发展过程中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二百多人,凡是演员,没有一个不经过易枫格手,没有一个不得到过他的帮助与指导,尽管他从来不讲……”
说到这里,丁杰老师沉吟片刻,继续说:
“他的伟大是真正的伟大!我对易枫很敬仰,很惋惜,他的过世,是苏州戏剧界的损失。”
丁杰老师的录像言之凿凿、情真意切,老友之情溢于言表,让我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从而对父亲的认识更为全面,更为理性,也更为丰满。
著名昆剧理论家、父亲的老朋友、上海剧专学友丁修询先生在父亲去世后特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欣慰的远行》,其中写道:
“我和枫兄相识于六十年前,俗说一个‘甲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是上海剧专,他是高班学长。我们接触不多,只知道他父亲是文明戏名家易方朔,那时三年解放战争正转入势如破竹的大反攻,旧政权乱象丛生,剧专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很多反对旧政权的宣传活动,主要是到各大学去辅导和演出进步的歌咏和戏剧。其中也常见枫兄的身影在忙碌奔走。那时,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枫兄从戏剧世家走来,从小耳濡目染,见多识广,对传统戏曲的了解非常深厚,加之当年在校又受业于洪深、田汉、曹禺、张骏祥、黄佐临等名师巨匠,因此他的艺术实践能力强。记得有次看他导演的苏剧《红楼梦》,每个人物都经过了一个类似镜框的空间说上几句台词,犹如电影蒙太奇,让人印象深刻。枫兄不仅能编能导,还能粉墨登场,小生、老生、丑行来者不拒,且表演出色。人手不够时还反串老旦,更难得的是像包公这样的黑净角色,他也照演不误,生动传神。但这样的全才,未能发挥所长,他又生性谦让,忠厚待人,遇事和顺,然而我知道,他的内心也是失落无奈的。
他肺疾缠身多年,近年喘息更甚,然而会面时,他娓娓而谈,病态全无,对昆曲命运的忧虑,是我们共同不变的话题。他对戏剧的深刻理解,常给我有益启示,他是我的学长啊!
枫兄的一生,是君子的一生,仁者的一生。这次远行,丝毫没有惊扰家人。因为他的宽厚,总是想着别人;因为他的无愧,他坦然地笑对这个世界。
他远去的背影,是安详的,欣慰的。他也把欣慰留给了别人。”
丁修询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1971年,我插队到盐城龙冈公社,次年冬,随公社宣传队赴射阳黄沙港河工地开展宣传演出,意外遇到做宣传报道工作的丁修询叔叔,他见到我非常高兴。那时我才十七八岁,河工工地,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我们宣传队和民工一样住草棚睡地铺,每天青菜煮芋头,顶风冒雪搞宣传,条件十分艰苦。丁叔叔就像父亲一样照顾我,让我倍感温暖。河工工地离父亲下放的特庸公社较近,工程结束后,丁叔叔得知我要只身走几十里回家探亲,当即决定绕道护送我回家。我们沿着河的堤岸一路走来,荒郊野外,少有人家,碱地枯苇,满目苍黄,唯有陌头树梢,喜鹊喳喳,一路相伴,歌唱甚欢。
天黑时分,我们终于到家,父亲秉烛打开柴门,一看竟是我们,真是喜从天降,笑逐颜开。我和弟弟忙着帮母亲厨房做饭。父亲与老朋友西窗剪烛,谈兴甚浓。屋外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屋内烛光人影,饭菜飘香,其情切切,其乐融融,那种流放中的欢乐至今难忘。
苏州昆剧继字辈命名六十周年之际,钱璎老局长特嘱我写一篇父亲的纪念文章。我知道父亲其实不能算是正宗继字辈,继字辈命名那会都是一群年少的男孩女孩,俊男靓女,朝气蓬勃。父亲年近三十,已是团里的导演兼演员,可他非常乐意与继字辈为伍,改艺名为易继习。上世纪许多演出说明书上都有父亲的这个名字。孔子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说:学过的东西继续不断地去温习、去实践,不是件很愉快的事吗?父亲的艺名取得好!
为了收集父亲的素材,2014年11月4日,我参加了一次纪念继字辈六十周年筹备会议,会议结束后,继字辈老师们提起父亲,一个个异口同声地说:
“你父亲是一位好导演、好老师、好演员!”
“无论演什么角色,演啥像啥。”
“不为名、不为利,演戏认真。”
“作为导演,不仅会排,还会教身段,教表演,分析人物心理,既有戏曲的身段和基本功,又有话剧表演的内心体验。”
其中,章继娟老师对我说:“我演出的第一只戏就是你父亲导的《秋江》,他不仅导,还和我同演剧中的老渔翁,船上的身段都是他教我的,演起来非常美。他的表演轻松、幽默、诙谐,与我演的陈妙常形成鲜明对比,一个逗趣调笑,一个害羞焦急,一老一少,一庄一谐,满台生辉。这个戏我们在台上演出,第一次就赢得观众拍手叫好,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演出成功的喜悦。”
朱继勇老师坐到我身边对我说:“50年代,苏剧团刚成立,到无锡、宜兴乡下演出,为争取观众,你父亲想个办法,每到一个地方,被头铺盖一放就拿仔锣鼓家生,带我们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宣传,招揽观众,这一招还蛮灵格。我上台格第一只戏是《贩马记》,就是你父亲教我格,教我唱,教我怎样上场,教我怎样表演。”
尹继梅老师对我说:“你父亲戏好,什么角色都能演,《十五贯》里的况钟、《金玉奴》里演金阿大、《刘三姐》里的地主,还有《王定宝借当》。《水淹七军》里的周仓,架子?花脸,身段漂亮,唱啥像啥。”
周继康老师讲:“你父亲对于我来讲,一半是导演,一半是老师,一半是阿哥,感情相当好!他的去世我真的很伤心。他做导演,我总能学到东西,从不会唱戏到会唱戏,易老师功不可没!他改编导演的苏剧《打子》,教得仔细,排得精彩。他不仅会排戏,每个行当都拿得起,演得好。他演的海瑞,身上有海派的东西,很亮人。《邬飞霞刺梁》里的万家春,小花脸,演得好!你父亲身体不好,但一直坚持工作,不容易!”
柳继雁老师接着讲:“你父亲演况钟,《见都》一场戏,心理活动表现得真好,这场戏前半场没有几句话,全靠心理活动的细腻表现。时间紧迫,人命关天,可深夜冒昧打扰,又要顾全礼节,虽然耐心等候,实则心急如焚,一有动静连忙起身施礼,结果一看,又失望而坐。将人物那种等人心焦、坐立不安的心理活动表现得非常真实、非常有层次。”
她接着又说:“和你父亲演戏,常常会感动我,把我的戏激发出来。我与你父亲演《金玉奴》,他演父亲我演金玉奴,有一场戏,我从船内出来,看见父亲竟然睡在冰冷的船舱外,又难过又生气,要找丈夫莫稽理论,你父亲一把把我拉住,不让我去。他生怕以此影响女儿的幸福,强忍悲痛,强颜欢笑,劝我不要发怒,只要你们夫妻好,做父亲的受点委屈呒啥关系。我看他眼里流露出那种复杂的父女情感,眼泪马上就夺眶而出……”
其实,平时我也常听团里人夸我父亲,记得南京昆剧院的范继信老师曾对我讲:“小珠,我在苏昆剧团最感激两个人,一个是易枫,一个是丁杰,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大概是梁琴琴老师、张继林老师都曾对我讲起,父亲在《十五贯·见都》中演一个小角色夜巡官,没有一句台词,只是走一个过场,他却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夜深人静,父亲手提灯笼,弓腰曲膝,老眼昏花,不紧不慢一步一步走向舞台,后台不知是谁注意到了父亲的表演,轻声惊呼:“你们看易枫!”候场演员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舞台上,大家屏声静气看着父亲表演……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父亲却把一个饱经风霜、步履蹒跚、兢兢业业、不慌不忙、按部就班的夜巡官形象生动展现在观众面前,更加反衬了况钟焦急难耐的人物心理,产生舞台戏剧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得好:“在戏剧舞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记得小时候我看过父亲演的现代戏《千万不要忘记》,父亲头戴鸭沿呢帽,身穿深色中山装,戴副老花眼镜,时不时生气地从老花镜的镜框上面看人,臂上还戴有一副袖套。给我的印象是表演生活化,一点也看不出戏曲演员端架子的痕迹,很放松很自然。
父亲一生对戏剧孜孜以求,只要是有关戏剧和艺术方面的书他都喜欢买来阅读。他常感叹小时候没条件多读书,因此对子女的读书非常重视。那时家庭困难家底薄,母亲又不善持家,父亲刚领到工资,一半先还借工会的钱。维持了半月,再借,月月如此。尽管这样,我和弟弟的学费从不拖欠,每逢开学第一天,父亲便早早起来,兜里揣着准备好的学费,一手牵着我,一手拉着弟弟去学校报到。学期快结束时,班上一些迟迟拖欠学费的同学,总会被老师叫起来批评亮相。每逢这时,我常暗自庆幸,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记得二三年级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本厚厚的儿童文学,书的第二页写了几句打油诗:“小珠读书成绩好,爸爸知道心欢笑。买本书儿送给你,学习之中好宝宝!”许是受了父母的影响和鼓励,我从小就养成喜爱阅读的好习惯,让我终身受益。
父亲原先住西园新村,由于是一楼,阴暗潮湿,少有阳光,特别是到了夏天,一遇暴雨,家里常常水漫金山。1999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居,我先生体谅我的孝心,主动提出接父母同住。父亲和我们住一起,再也不用为刮风下雨、柴米油盐、看病配药、买菜做饭操心,气色竟一天比一天好。我中午下班回家,厨房里钟点工阿姨正在炒菜做饭,父亲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戴着老花镜安详地看着书报,温暖的阳光沐浴在他的身上……每每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2002年初,我从剧目工作室调任中国昆曲博物馆。研究昆曲对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来说真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父亲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通过探讨与学习,让我从更高层次感悟中国戏曲的独特之美。我慢慢体会到,中国戏曲之所以有别于西方戏剧而独树一帜,是因为她和中国古老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一曲多用,一服多用,一桌两椅多用,每个行当多用(一个行当可用于众多人物),都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同根同源。再如,虚实相生的写意性、虚拟性表现手法,与古老易经所提出的阴阳概念同出一辙,其思维方式就是宇宙万物无不包含在阴阳变化的范围之内,并相互映衬。由此触类旁通,联想到中国的书法、绘画、篆刻乃至中医、建筑、园林等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
我常常会问父亲,比如:“戏曲中的丑行,其程式身段要求微蹲曲膝收肘,既显得灵活、风趣,又有独特的人物美感,可古人怎么会想到设计这样的造型?”父亲说:“因为丑行代表的大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封建社会,上层人物被尊称为‘大人’,普通百姓就贬为‘小人’。小人在舞台上要收、要缩。”父亲的话让我豁然开朗,由此又让我连想到生行、净行那具有独特美感的厚底靴。对呀,那代表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那些做官的、有本事的人,若在舞台上要美化这些“大人”形象,不就需要用厚底靴来增高放大吗?(穷生、书生属未来的发达之人)中国曾经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社会等级非常鲜明,戏曲艺术就是中国的社会等级、社会风俗、社会心理和伦理道德的美学体现。
这又让我想起家里收藏的许多美术作品中的古代人物画,如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的韩熙载、唐代阎立本《步辇图》中的唐太宗、汉墓出土帛画中的老夫人等等,里面的主人公都画得高大丰腴,边上的侍者侍女都画得很小,人物与人物的比例明显不对。但现在想来,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符合当时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视觉和审美理念,其美学思想和中国戏曲如出一辙。父亲的指导,使我对中国戏曲艺术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父亲退休在家,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学习,对热爱的戏曲艺术孜孜以求,有时学到妙处,常会感叹地说:“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他虽然离开了剧院,但对剧院的消息仍十分关心,有一点好成绩都会由衷地替剧院和演员高兴。2004年,剧院排全本昆曲《长生殿》赴台演出,有两只折子《权贿》、《权哄》需要父亲指导,虽然当时他已不方便出门,还是欣然应允,认真做好功课,并在家里尽心为登门学戏的周继康老师和唐荣进行辅导和排练。其实,那时父亲离去世只有一年多了。
让父亲意想不到的是,晚年的他竟然获得了由贝晋眉昆曲传习奖理事会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父亲一生唯一获得的荣誉奖励。高兴之余,他把几百元的奖金捐给了苏剧社,希望苏剧能像昆曲一样繁荣发展。
晚年的父亲随母亲信佛,每天默诵《金刚经》,追求心泰身宁的精神境界。每天还要为早已离世的祖父易方朔默诵心经。我想,岁月的沉淀,让父亲懂得了感恩与宽容。
父亲生病期间,钱璎老局长,姚凯老团长、剧院有关领导,办公室主任徐伯仁老师及继字辈老师们都很关心登门探望。特别是他非常敬重的钱璎老局长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去医院看望,给病重的父亲极大的安慰,更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存感激!因为在父亲的意识里,领导就是党的化身,领导和同事的探望让他倍感温暖。
如今,父亲去世已八年多,每当吃到美味、看到美景或家里有什么高兴事,心里常常会想:若父亲健在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吧!可人生就是这样,时光如流水,逝者如斯夫,往者不可追,存者犹珍惜。
父亲一生从事心爱的戏曲事业,他把舞台当作自己的第二生命。在这个舞台上,他努力创造绚丽多彩的艺术人生,这个人生让他快乐,让他痴迷,让他陶醉,让他感受到生命的绽放和精彩!
爸爸,作为你的女儿,我为你骄傲!爸爸,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