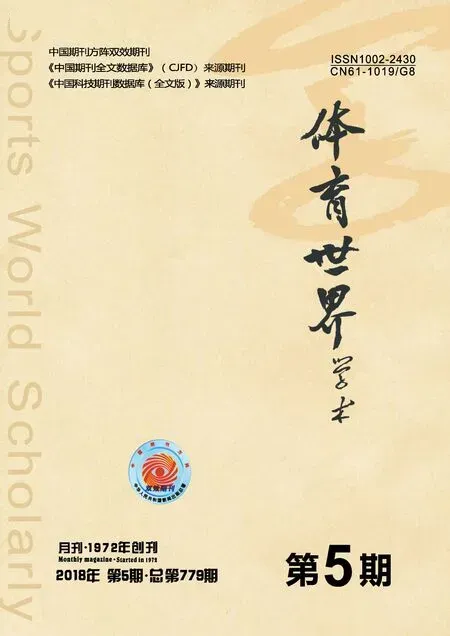阐释人类学: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基础
童国军 候鸿辉
美国科学哲学家(Thomas Kuhn)在自己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范式”这一概念并对其作系统的阐述。“它指的是一个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是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1]。“是对于这个学科的诸如问题意识、学科属性、研究领域以及方法特征等相关知识的共同认知”[2]。“范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认知观,其本身也是在不断被理解和认知过程中构筑成型的。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身体文化,长期以来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同时随着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也成为一个具有学科交集性质的研究领域。“然而,认真审视已有的各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会发现,它们不管是借用什么理论工具、从何角度开展研究,其关注点都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身,”[3]而忽略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需要的理论关怀和自觉的学科边界意识等问题。这也许是因为民族传统体育这一学科本身,还没有形成具有“范式”意义的认知架构,或者它正在形成,但还未能被完全的解读而有所呈现。本研究试图在建构论的意义上,以阐释人类学的核心思想为基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认知逻辑进行深度思考,从而对其可能被认知的研究视域做出尝试性的探索。
1. 阐释人类学的核心思想
阐释人类学是各种民族志实践和文化概念反思的总称。“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受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帕森斯社会理论、经典的韦伯社会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结构和转换语言学、符号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阐释学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4]。
探讨阐释人类学,必须了解阐释学理论产生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追溯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人类学危机”[5]。使得人类学界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关联,结果“文化重心从社会转向个人,从客观转向主观,而这种转变也影响到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方向”[6]。那种在人文学科领域里认为学科的研究目的在于用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并以此来界说学术研究之宗旨的观点正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人文学科的这种表述危机对于人类学理论的影响直接表现在民族志写作上的革新,同时,西方社会又处在一个集经济危机、文化颓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历史时段,这种影响使得人类家敏锐地洞察到了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使人类学学科走出困境,维护民族志地位,西方人类学领域产生了如格尔兹这样的人类学大师及其代表的阐释人类学学派。
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格尔兹,首先在《模糊的文类:社会思潮的再形建》(Blurred Genres:The Re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一文中,对社会文化做了一个“深层描述”性的解读和说明(1983:19-35)。他认为:“人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中,而文化正是这个有系统的意义网络,对一个文化的分析了解是要去解读其隐藏的意义,而不是以科学实验的态度去找寻规律与通则”。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7]。格尔兹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上也异于其它阐释人类学派的代表,如施莱艾尔马赫、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8]。可见,对于格尔兹而言,他对文化意义的分析又是一种“意义的猜测”与对该猜测的评估,然后再从较好的猜测得到结论的解释。那么我们似乎可以领略到,其实格尔兹的核心思想应该是在寻求不同文化彼此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的目的不在于寻找恒古不变、跨越时空的通则,而是在对话中,澄清其中的意义,然后从论述的过程将人的存在与所有推向更深层的自觉,一种自我了解的意识状态。
2. 民族传统体育基于的学科属性及其学理基础
法国学者莫兰认为:“学科是科学知识领域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科学范围内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特长,迎合科学各方面的需要。尽管科学涵盖百科,但每一个学科由于有自己特定的边界,有自建的学术用语、研究方法和理论,因而都是独立的。”[9]“某一学科的形成往往首先是独特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当人们关注于某一个对象并力图深刻地对其进行阐述时,学科就因此开始萌芽。”[10]
民族传统体育学(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从其字面意义上看,其研究对象无疑是“民族传统体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确立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时,我们时常需要做一些适度抽象,以尽可能地明确对象的具体指称。这既是学科自身理论体系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获得自身独特性的内在根据。“民族传统体育学是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通过表层的文化现象去透析其深层的文化内涵的学科。其学科体系包括基础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社会人文科学理论和综合性理论等几个部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来讲,民族传统体育学具有原先的武术学科和专业的一些遗存,也担负着在成为体育学之下二级学科之后重建学科体系的迫切要求,因此,在阐述其学理基础时,既要考虑原有的武术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现状,又要借鉴体育学、民族学和人类学。
3.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所凸显的意义取向
民族传统体育学,从其字面意义上看,其研究对象无疑是“民族传统体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确立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时,我们时常需要做一些适度抽象,以尽可能地明确对象的具体指称。这既是学科自身理论体系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获得自身独特性的内在根据。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具有原先的武术学科和专业的一些遗存,也担负着在成为体育学之下二级学科之后重建学科体系的迫切要求,因此,在阐述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领域时,要考虑原有的武术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现状。在目前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的研究中,当前有学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属性和学理基础,不能从单纯的体育科学视角进行推演,因为这样难以深刻地分析、演绎出各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特征。“应该以多学科角度透视为基础,多方位、多层面地对民族传统体育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科学的理性探索。”[11]因为“学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自觉形态的代表。学术作为自觉的文化反思,对于现代社会具有特殊意义。”[12]同时,“学科体系的价值功能在于其解释功能、指导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功能和预测未来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趋势。”[13]甚至,有学者在费孝通、张之毅、林耀华之后,将人类学的理论模型—说明(Interpertive)模型运用到地域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的研究中,如刘朝晖(2010)、周伟良(2007)、白晋湘(2013)、涂传飞(2010)、杨海晨(2012)等,这也许是诸学者在思量民族传统体育学未来走向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其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4. 阐释人类学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交集
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是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中的两种范式。这两种范式的侧重点不同,分别体现在方法论原创、研究程序、研究步骤、收集资料的方法等多个方面。而当面对某一个民族传统体育个案时,研究者往往会趋向于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例如,有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赣皖交界区域农村妇女参加民俗体育的行为、意识、选择民俗体育活动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14]“虽然量化研究用数据说话,一目了然,但是,量化研究的数据只能反映表面现象,缺乏对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关注,更难以触及到民俗体育文化主体的社会心理、价值观等层面。”[15]“运用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要么停留在简单的数理统计层面,要么模仿西方的研,借用别人的命题设计进行填充,得到的结果脱离中国民俗游戏实际,这使民族体育的研究踯躅不前。问卷调查忽视了被调查者回答问题时,在时间和环境条件上的不一致性,舍去许多细节,放弃了具有个性化特征的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息,尤其对局限于偏远地区的缺少记载的历史文化内容,更是鞭长莫及。”[16]
在目前以阐释人类学的理论探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问题上,学者多采用“认知逻辑的启示”、“深度描写法”以及“重视地方性知识”等研究方法。因为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大多数研究把民俗体育作为体育活动项目来进行研究,剥离其寄予存活的社会生境而孤立地进行解释说明,使其成为“单纯”的体育项目,失去其应有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基调。例如:李志清在对抢花炮活动的研究中,“不仅仅止于抢花炮是怎么个抢法的,怎么定胜负的等技术性的问题,无论做的多么细致,也是远没有把抢花炮这项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价值挖掘出来。”[17]“胡小明等学者在对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具有与现代体育活动类似的竞技形式,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民族体育。然而,它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身体活动、是否具有体育的目的和功效、它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都需要研究。”[18]以上的问题,都是值得当前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值得深思的,因为对于任何人类的同一种行为,在不同文化的脉络中有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人类学者对同一脉络中的同一行为也会有不同的了解,这使得同一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体现了“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7]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文化,它的发展和推衍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和看待,是用科学、理性、标准化、数字化等为表征的现代体育观还是其它标准来评价?阐释人类学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认知逻辑的重申和倡导启示我们,每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都应放在它所属的价值体系中进行评价,应将该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猜测性的论述,我们从不同的文化主体中,了解产生对比、对话、以学习“新”的可能性,从这些可能性中得到新的自由—一种了解的自由、一种人性的自由、一种超越文化的自由。民族传统体育其不可或缺的理论关怀和自觉的学科边界意识“不是为了回答我们自己深层的问题,而是使我们能接近我们接近别人已经有的答案,但仍保有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并将之包括于可参考的人类已经说过的档案中。”[19]
5. 结语
“众所周知,每一种理论流派都有其局限性,阐释人类学流派也不例外,如有研究者认为该流派的学术思想存在着泛符号化和过度阐释的倾向。”[20]但是阐释人类学流派所主张“不可或缺的理论关怀和自觉的学科边界意识等问题”对拓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因此在我国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中,可以尝试阐释人类学流派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