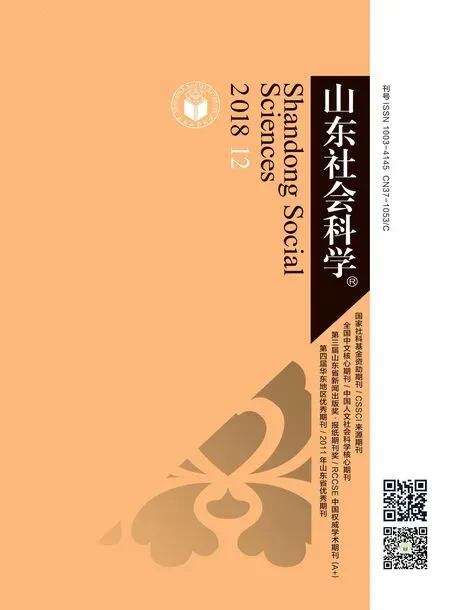乌托邦的二重性:审美乌托邦研究的出发点
周均平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乌托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现象之一,是一个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乌托邦及其精神植根于人的本质,为人所特有,是人类前进的精神原动力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指向完美的乌托邦的追求,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作为一种“元叙事”,它几乎贯穿人类世界的整个历史,构成了人类想象世界与现实生活里的特殊一隅;但乌托邦也是引发激烈社会和学术论争的重大社会和学术问题,对它的基本认识和价值评价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否定和肯定的根本对立。否定派以其理论上的缺陷特别是实践上的屡屡失落和严峻困境,给其加上极权主义等等帽子,推出种种乌托邦衰落、穷竭、告别、终结、死亡论,主张拒乌托邦于千里之外乃至置之死地而后快;肯定派则以其种种积极因素和作用,提出乌托邦复兴、召回、重构、重建论,希冀将其复兴和重构。可谓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为什么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和分歧?这是乌托邦本身的问题,还是乌托邦所依存的人和社会及实践的问题?有人认为,乌托邦本身没有问题,是人对乌托邦的认识和实践或使其历史化和现实化有问题。有人认为乌托邦本身即有二重性,而且正是它本身的二重性导致了人对其认识和实践的二重性。笔者则认为,乌托邦本身和人对其的认识和实践都有二重性,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乌托邦本身的二重性。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未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一情况,对于我们全面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乌托邦性质和规律,扬长避短,以长补短,尽可能跳出恶性循环的宿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即以尽可能全面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乌托邦的二重性为旨归,为探讨审美乌托邦、走出两难困境、实现悖论超越,确定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或出发点。
笔者认为乌托邦是一种悖论性存在,具有二重性甚或多维多层二重性,具体表现在乌托邦本身及与其不可分割的主要因素上。乌托邦悖论或二重性的主要表现可大体归纳为如下五大方面。
一、人学前提的二重性
乌托邦是依存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社会现象。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类社会,乌托邦将不复存在。众所周知,人是我们目前已知的最复杂、最高级的生命存在。当然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最富于矛盾性、悖论性的存在。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此曾做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如:人生而自由,却又是“被抛”进人世来的;人生而自由,却又无时不在枷锁之中;人会思想,却只是一根“芦苇”;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许多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对此也曾做过无比生动形象的表现。如鲁迅塑造的蜚声世界文坛的文学形象阿Q,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但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但又安于现状,其性格就是一个由各种性格因素按一定的结构方式构成的充满矛盾的复杂有机整体系统。“各种性格元素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它们又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人格”。[注]林兴宅:《阿Q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这是阿Q之所以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奥秘所在。
就连审视科技发展,也无法脱离对人的复杂性和二重性的反思。就人与自然、人与科技的关系而言,人性系统自身就表现出极强的矛盾性。人性的矛盾就在于,既要依赖于外界自然而生存,又要谋求自己独立的、愈益否定这种依赖的生活世界。越来越高精尖的科技,便是人性企图否定和超越自身对大自然之全面依赖的产物。在这样的矛盾中,人性有时跟物性难以区别,有时与兽性难分伯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人性有时又颇类神性。当人在改天换地的各种社会实践中展现出无比的智慧和卓绝的能力,当人把自己的道德人格修养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民胞物与”“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时, “神”的形象会浮现在脑海,人俨然上帝。于是,有人把人性看成是物性、兽性和神性的矛盾统一体,有人把人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表现抽象成“人性的优点”和“人性的弱点”等。其实这都是人性现实表现的悖论。甚至科技的矛盾与人的矛盾也不是独立于人性而发生的,它归根到底是人性的矛盾的一种表现。[注]吴文新:《慎重对待人的自然——从人的自然属性看科技》,《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期;《科技与人性的矛盾:人类困境的一种分析》,《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年第 2 期。
显而易见,在人的身上,纠结着兽性与人性、人性与神性、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身体与精神、伟大与渺小、崇高与滑稽、悲剧与喜剧、聪明与愚蠢、谦虚与傲慢、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等多种多样的矛盾对立关系和因素。它们有时严峻对立,有时趋于和谐,有时此消彼长,有时齐头并进,千变万化,不可方物。人性的这些矛盾性和复杂性不能不影响到乌托邦的性质及对其的认识和评价。
二、基本语义和原始文本的二重性
乌托邦基本语义的二重性是指从词源学的角度看,“乌托邦”相关关键词或核心词基本含义的二元性、矛盾性和对立性。
关于乌托邦的语义二重性,西方学者如曼努尔兄弟(Frank E.Manuel & Fritzie P.Manuel)的《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UtopianThoughtintheWesternWorld)、克瑞杉·库玛(Krishan Kumar)的《现代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UtopiaandAnti-UtopiainModernTime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乌托邦的故事》(TheStoryofUtopias)等均有论述。西方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剑桥乌托邦文学指南》(TheCambridgeCompaniontoUtopianLiterature)的论析。该书在探讨乌托邦的语义和乌托邦概念的界定时指出:对乌托邦定义的研究不能简化为与1516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书中给小岛命名的相关历史,尽管如此,仔细梳理词语产生的环境有助于理解莫尔赋予该词的意义以及后来发展出的含义。需要铭记的是:1516年该词是新词,新词用于命名新事物,通过揭示既定团体的共同价值经历的变化,新词研究不仅提供特定社会的动态形象,还有既定时期该社会的代表。新词有三类:命名概念,综合已存在的词(词汇性新词);用于新的文化语境的已有词(语义新词);其他词的变体(衍生性新词)。
乌托邦作为新词,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起初作为词汇性的词,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再创造过程,意义变化为衍生性新词,被作家与研究人员用于不同研究领域,带有不同利益、兴趣及相互冲突的目标,其历史可以被视为明确语义的更好融合。该词被用作形成新词的词根,包括eutopia(优托邦)、dystopia(敌乌托邦)、anti-utopia(反乌托邦)、heterutopia(异托邦)与hyperutopia(超托邦)等等,都是衍生新词,伴随每个新的关联词的创造,乌托邦就具备了更加细致精确的意义,对于区分莫尔赋予的原始意义与不同时期及思潮认定的不同意义起了重要作用。
问题是乌托邦的原初意义并非很明显,莫尔用来命名葡萄牙水手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ed Hythloday)描述的无人知晓的岛屿并作为自己的书名,这就产生了乌托邦的两种含义。事实上,尽管这个词用来暗指想象中的天堂世界,但还指代一种叙述文体,即乌托邦文学。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其创新性证明了新词的必要性。
有趣的是,在新词出现之前,莫尔使用另一个词命名其想象出的岛屿:Nuxguama——在拉丁语中指“乌有之地”。如果莫尔用这个词作为书名,并称呼想象的岛为Nuxguama,就是在拒绝这种地方存在的可能性;但莫尔想传达一种新思想、新感受,来表达欧洲兴起的新思潮。莫尔的乌托邦想法,事实上是文艺复兴的产物,那时古典世界(希腊、罗马)被视为人类智慧的顶峰,成为欧洲人的典范;而它也是人文主义逻辑的结果,基于人类不甘命运的这一发现;用理性构建未来,源于中世纪社会秩序的瓦解,对人类能力的信念出现——不是达到完美境界的能力(在天主教视角看来是不可能的,堕落的思想仍然存在),而是组织不同世界以确保和平的能力,思维境界的扩展受前所未有的地理边界的扩张的影响。地理扩张意味着另一处新大陆的发现。莫尔利用“另一处”的意识为发明新地方正名,那里有别样的人民与不同形式的组织结构,这也是新的,需要一个新词。为了创造新词,莫尔利用了两个希腊词——ouk(意为not,简化为u)和topos(pkoue),他加上后缀ia,意指某地。语源上,乌托邦指“乌有之地”,同时包含了肯定与否定的二元悖论。
莫尔在其开创性著作第一版发表时,发明了另一个新词,在《乌托邦》中乌托邦岛国的桂冠诗人艾那毛留斯(Anemolius)称他的岛国为 “Eutopia”。“eu”意思是美好的、理想的等等,Eutopia即美好或理想的地方。第二个新词在组成上源于第一个。通过创造这两个在组成及意义上相同的词——词汇性新词(utopia)与衍生性新词(eutopia)——构建了一个矛盾、历史悠久、乌托邦意义持续性的基础,一个同时代表乌有之地(utopia)和美好之地(eutopia)的地方。utopia与eutopia发音相同,意思却截然相反,对此的完整准确的词源学解释应是:乌托邦指一个不存在的美好或理想的地方。书中的诗强调了这一矛盾,这一矛盾不会终止。[注]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edited by Gregory Clae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pp.4-6.
近年来这个问题引起更大关注。我国学者牛红英在吸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她认为:“几百年来,很多读者无暇理会上述的两封信和众多双关语的含义。他们更多地关注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对比,即乌托邦国与英国乃至欧洲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读者已经认定莫尔的目的是鞭挞现实社会,歌颂理想社会。然而,如果把上述的两封信、众多的双关语,以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综合来看,所谓鞭挞和歌颂的支配性解读就站不住脚了。在一个所谓理想社会的表面叙述之下,《乌托邦》真正阐释的是一个含义深刻的悖论:人类追求理想境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和模糊性。‘乌托邦’一词则是这个悖论的集中体现。仅从词源学的表面解释判断,‘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已经很明显了:‘不存在的’与‘理想的地方’是一对矛盾。……在‘不存在的’和‘理想的’这两个相抵触的词语之间隐藏着这个概念的悖论本质。这个悖论有着巨大的张力,而这正是它自身的生命力所在。”[注]牛红英:《被忽略的两封信:对〈乌托邦〉的解构主义阐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她还指出,“毫无疑问,在薄薄的《乌托邦》一书中,‘乌托邦’这个关键词可以说是最为基本、核心的概念。这部著作正是以这个概念而构成的文本体系。……除了‘乌托邦’一词外,各种带有双关意义的名称都在巧妙地暗示、加强着‘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了解这些双关语,有助于读者从真正意义上深入地理解《乌托邦》的本质。”[注]牛红英:《被忽略的两封信:对〈乌托邦〉的解构主义阐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牛红英对《乌托邦》关键词等的解构主义解读并非无可商榷,但她的探讨对我们充分认识乌托邦基本语义等的二重性,还是颇有价值的。
《乌托邦》原始文本的二重性,主要是指其最初出版时文本内容的复杂性和悖论性。关于《乌托邦》真正的或原始的文本内容,通常大家都认为是由现今都能看到的书中的两部分内容组成的。然而,和上述两部分同样重要的还有莫尔假托写给他的朋友兼出版商彼特·盖尔斯的两封信。最初,这两封信是全书的《序》和《跋》。了解这两封信对于真正理解莫尔的写作初衷和他对乌托邦的真实态度极为关键。但是,后来经出版商的要求和作者的默许,在1517年以后的许多版本里,第二封信被删除了。牛红英认为:“这些信作为《序》和《跋》,把作为书的主体的两部分夹在其中,和后者共同组成了一部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作品。两封信的内容看似寒暄和闲谈,却透漏出非常关键的信息。在这两封信里,莫尔一再声明自己只是忠实地记录了航海家西斯罗代对乌托邦国的描述,而至于乌托邦国的真实性以及好与不好,他没有、也不打算做出任何明确的评论。莫尔正是以此暗示读者不要把他对乌托邦国的看法和航海家西斯罗代的看法混为一谈。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删除或忽略这些信无疑是对最初的、原始的文本进行了刻意的截肢。而对被截肢后的文本进行的解读必然是有疏漏的、片面的。这样的删除或忽略虽然迎合了读者的阅读乐趣和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却篡改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一部煞费苦心创作出的扑朔迷离的作品就这样被简化了。重读这些信,将其内涵与传统的支配性阐释进行比较,是对《乌托邦》一书进行批评的必要环节。”[注]牛红英:《被忽略的两封信:对〈乌托邦〉的解构主义阐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
对此,库玛也指出:乌托邦是乌有之乡(outopia),也是美好地方(eutopia),是一处不可能存在却令人憧憬神往之地——这是乌托邦的文学精华,从这个角度讲,其具有梦的特质,这是最具魅力之处,但又不限于此。托马斯·莫尔1516年首次命名并描述了乌托邦,它出自想象,界于现实的边缘:莫尔笔下的旅行叙事者拉斐尔·希斯拉德及亚美利哥·韦斯浦契(Amerigo Vespucci)访问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进行探险,希斯拉德独自旅行时发现了乌托邦,每个航海家都曾描述过这块远离美洲大陆的地方,它处于文明之地的边缘——而文明之地在不断扩大。希斯拉德描述的乌托邦习俗——共产主义、废除君主制、视珠宝如粪土——都可见于韦斯浦契关于新世界奇遇的描述。希斯拉德:空谈的见闻家。莫尔这一打趣的寓言保持了乌托邦构想的矛盾性。他著作的第二部分是乌托邦习俗与制度,其戏谑性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品的特征。第一部分控诉都铎王朝,第二部分描绘乌托邦蓝图之后表现当时英国的罪恶,而乌托邦则是一个异教徒的社会,尽管对天主教缺乏好处,但几近完美。
莫尔真的认为英国或其他某一国家会成为乌托邦吗?乌托邦是一种社会改革吗?在莫尔的时代,乌托邦有实际意义吗?“乌托邦人过的才是天主教徒的生活”——乌托邦的实际意义是这样吗?或者乌托邦不是一种规划,而是精神家园,是伊拉斯莫斯(Erasmus)、彼得·贾尔斯(Peter Giles)这样的学术友人的人文主义小册子?这些都不得而知,在《乌托邦》末尾,他写道:“乌托邦的公共福利是现代社会从未企及的。”这使乌托邦成为一种梦想,同时乌托邦的价值和习俗与莫尔本人对律师、人文主义改革者和政治家的成见有关。
所以不论多么综合,乌托邦从一开始就体现了相互对立的两种冲动。它不只是旨在改革的社会政治小册子,它总是超越现实,但它不仅仅是梦,也一只脚踏入了现实。[注]Krishan Kumar,Utopianis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pp.1-3 .
三、性质内容和构成要素的二重性
乌托邦的二重性也表现在其性质内容和构成要素上。这种二重性,应是乌托邦基本语义、原始文本二重性的推而广之。原始文本二重性实质上也是性质内容及构成要素的二重性,只是由于其特别重要的初始基础地位,才单独论列。乌托邦包含的现实与理想(梦想)、实然与应然、总体与个体(社会与个人)、规范与自由、理论与实践、经验与超验、事实与价值等等各个方面几乎都有二重性问题。
库玛在论述乌托邦理想(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乌托邦也有界限,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具有独特的历史及特色,这并不是说乌托邦的形式是非常明确地被界定的,事实正好相反,具有历史意味着成为变化的实体。但这种变化并非随意,它们限定了乌托邦所能做的,乌托邦可能是乌有之地,但历史地看和概念上看,它又不仅是某地。[注]Krishan Kumar,Utopianis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p.72 .在审视规范与自由、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时,库玛仍然看到了乌托邦的二重性:乌托邦表现了复杂的现代社会的核心困境,这同时体现出秩序与自由,集中制的大规模组织与地方自治、个人创造力之间的矛盾。[注]Krishan Kumar,Utopianis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p. 51 .
《剑桥乌托邦文学指南》论乌托邦性质的二重性时也指出:尽管乌托邦的概念起点是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的《乌托邦》,但如今的乌托邦文学领域更宽广,柏拉图主义,古典神话学,东方黄金时代,失落世界的理想,奇幻旅程,人居月球及星球,想象的社会政治实验、国度、帝国及理想共和国,大量涌现的小说及科幻作品,大量跨世界的共产主义社区,以及过去一个世纪因恐惧社会黑暗而引发的悲观绝望趋向而把所有乌托邦主义归结为极权主义所转向的反乌托邦或敌托邦,都属于这个领域。乌托邦源于莫尔的“美好地方”与“乌有之乡”的双关语,矛盾地成为一处美好之地及没有恶魔的只有希望的地方。
无论是作为“理想共和国”的思想史分支、一种文学类型,还是宗教意识史的反映或重要心理愿望的反映——希望更好的生活或作为探索“社区”的形式,乌托邦研究领域反映微观层面上有关历史发展的进步或倒退的讨论,现代生活对进步观念的肯定与基于“发展”及“增长”成果的清醒相平衡,在持续的辩证互动过程中,后期现代性的焦虑,源于面对种族灭绝、核战争及生态失衡。乌托邦主义已不被认为包含救赎、完全性和千禧年,虽然它们与宗教相交织于漫长的集体主义历史,现在遇到了重建愿景的可能解决方式,如这个世界想象的、重新改进的社会、人类关系及对自然态度的更和谐的重建,这主要是托马斯·莫尔及16—20世纪众多革命性运动认同的理想共和国的传统。但正如科学中怀疑的信念产生了科学反乌托邦,政治工程中的极权主义则引起了现代政治反乌托邦,随着最大规模的现代乌托邦政治理想的覆灭,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与乌托邦终结的必胜主义宣言,人类欲望的攀升,解放—民主的资本主义视角的努力与进步,是自我修正的市场机制提供了充分条件。但因全球经济危机的幽灵,这个视角也变得空洞。更糟的是,环境破坏在我们身边隐约出现,新的反乌托邦威胁着我们,幻想给予另一个可能的替换性的未来以新概念,见证了消极与积极形象的并列,再次关注乌托邦与其反面如何穿越几个世纪成为人类渴望的焦点。[注]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 edited by Gregory Clae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pp.1-2.
乌托邦的构成要素也体现出这种二重性。如库玛认为乌托邦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黄金时代、桃花源、天堂(乐园)、安乐乡、千禧年等等。这些要素本身有协调性,但各个要素之间也包含对立矛盾关系。如所谓“安乐乡”与“黄金时代”“天堂乐园”。在库玛看来,“安乐乡”该称之为“穷人的天堂”,相对于严格恪守朴素和精神的诗人和牧师眼中的“黄金时代”和“天堂乐园”,安乐乡是一个奢侈、繁荣和过度的地方,产生了“法尔斯塔蒂安”和“巨大”之类的词。它的主题是富裕和远离工作。在这里,一切都是免费的,可以随心所欲:烹饪过的云雀飞进嘴里;河中流淌的是红酒;睡得越多,挣得就越多,男女性混乱;有一口不老泉,使每个人都保持青春和活力。[注]Krishan Kumar,Utopianis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p.6.甚至同一个要素也可能包含这种矛盾对立的二重关系,如所谓“千禧年”。库玛指出:“千禧年”作为人性的理想化状态,与“曾经和未来的天堂”思想相连,既是黄金时代,也是新纪元、原始天堂和希望之地,与之相关的信仰和运动相互激荡,使“千禧年”呈现出极端保守与极端激进的特点。[注]Krishan Kumar,Utopianis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pp.6-7.
四、功能作用和实践效果或现实化、历史化的二重性
乌托邦功能的二重性是指乌托邦在作用价值上所具有的矛盾性和两面性。关于乌托邦二重性的这一重要表现,许多思想家做过精彩的分析。
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k)就曾提出和论析了乌托邦的三种积极作用和三种消极作用,实际论述的是乌托邦性质功能的二重性。有学者指出:“蒂里希深刻分析了乌托邦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乌托邦的第一个积极特征是它的真实性。乌托邦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和人生存的深层目的。这种对乌托邦的理解既适用于人的个人生存也同样适用于人的社会生存,而且不理解其中的一个就不可能理解另一个。如果社会乌托邦并没有同时实现个人,那它就失去了其真理性。同样,个人的乌托邦如果不能同时为社会带来实现,它也失去了其真实性。蒂里希指出,我们处境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乌托邦被割裂,没有把它们看成是统一体。乌托邦的第二个积极特征是它的有效性,这一点与乌托邦的真实性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蒂里希是从人类可能性的自我实现的角度来看乌托邦的有效性的。每一个乌托邦都是对人类实现的预示,许多在乌托邦中被预示的事均已经被证明是真正的可能性。没有这种预示的创造力,人类历史中无数的可能性也许依然得不到实现。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乌托邦的第三个积极特征是乌托邦的力量,即它能够改造已有的事物。无论何处都找不到的乌托邦已经证明了自身具有高于已有事物的最大力量。”[注]刘新军:《蒂里希乌托邦思想的本体论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蒂里希在肯定了乌托邦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又指出了乌托邦的消极意义。蒂里希的分析是辩证的,相应于乌托邦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力量,他从深度的关联上又强调了乌托邦的不真实性、无效性和软弱性。”[注]刘新军:《蒂里希乌托邦思想的本体论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蒂里希的分析指明了乌托邦的功能具有深刻的二重性。
库玛也明确指出并分析了乌托邦的二重性在其价值功能上的表现。他指出:乌托邦的价值在于与现在及未来的关联,其实际功能是超越现实勾画一种引人入胜的境况,其空想性、不切实际是它的力量所在,如隐蔽的上帝,吸引我们揭秘,去探寻真理与道德,因此,乌托邦的乌有性引人探索,禁锢可以限制人也可以刺激人去超越,可能性的边界常依时空而定。乌托邦打破了这种边界,它试图揭开当时及所有时代的面纱。乌托邦描述了一种不可能的完美,但未超越人性。
乌托邦表现了复杂的现代社会的核心困境,这同时体现出秩序与自由,集中制的大规模组织与地方自治、个人创造力之间的矛盾,乌托邦理所应当要克服这些矛盾,这么做的结果往往是为遵循某个原则达到逻辑上的极致而付出代价。这是乌托邦的部分价值,其启发式的用处之一,实际上是通过试图解决现代社会的困境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将其用生动高效的形式戏剧化,而且它自身的历史是对政治论争的主要贡献。因为乌托邦不仅产生竞争性乌托邦,如贝拉米·莫里斯(Bellamy Morris)的例子;还刺激严肃的反乌托邦的产生,这对乌托邦来说是调和的巨大挑战,是其辩证的对立方。[注]Krishan Kumar,Utopianis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p.51.
乌托邦实践效果或现实化、历史化的二重性,是乌托邦功能二重性的实践体现。回溯乌托邦问题史,可以明晰地看到,近代以来或从古典乌托邦到近代乌托邦的一个极其明显的转变是乌托邦从静态空间转向动态时间。从静态空间到动态时间,意味着乌托邦的历史化,即从抽象走向历史,从静观走向行动。这一直接走向现实的转变,催生和促进了19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在这里,既有革命成功经验,更有惨痛教训,似乎乌托邦不可现实化、历史化,一旦现实化,走向实践,就会走向反面。以致有学者认为乌托邦主义是乌托邦由观念转变为行动的产物,乌托邦主义蕴含着诸多消极因素,并在实践中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提出对乌托邦现实化的质疑,得出所谓乌托邦现实化的悖论的结论,断然作出拒绝乌托邦直接现实化的选择。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对乌托邦的否定,乌托邦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乌托邦的边界,让乌托邦停留在想象和批判的领域,而不是转化为一种激烈的干预现实政治的形式。[注]参见陈周旺:《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还有学者指出,从18世纪到19世纪,乌托邦思想更多地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参与,但到了20 世纪和21 世纪,由于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斯大林式统治和其他形式的集权主义,人们开始憎恨和提防“乌托邦主义”和由此建立的“恶托邦”现象。尤其是那种垄断了未来设想而使用国家权力去强行推动的政治乌托邦设计,被人们深恶痛绝。乌托邦主义虽然产生自对生活现实的不满和改革的愿望,但它也可能带给我们更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也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案例,具体讨论究竟是乌托邦思想本身携带危险品,它必然导致恐怖的政治实践,还是政治实践中的乌托邦主义十分危险;或者说是不是应该让乌托邦的思想更多地保留在文学、哲学研究领域和我们的精神领域,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可供直接应用的制度设想或负责任的政治设计。[注]潘一禾:《经典乌托邦小说的特点与乌托邦思想的流变》,《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笔者认为,因噎废食并非明智之举,更不是最佳选择。关键是如何现实化的问题。应区分乌托邦的多种现实化,比如一蹴而就现实化和循序渐进现实化、整体现实化和局部现实化、强制现实化和自然现实化或合规律现实化等等,酌情对待。
库玛从乌托邦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乌托邦的多种现实化方式做过较细致的分析。库玛指出:我们涉及的思想与实践的关系是字面的、狭义的,我们在寻找社会文学想象的表达与社会实际生活之间直接的关联,大多数具有哲学思维的读者会开始思考作者多久以后指出这个方法的肤浅,当然他们是对的,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在起源和作用上,社会思想或理论有其形式与逻辑。社会实践提升理论,或多或少属于人类思想活动或幻想的自身范围。理论也作用于实践;而实践也有自身的范围,思想的纯粹或“理想”逻辑必须有一种不适的存在,并且必须经常让路于其他更合理的要求。
这些单调的陈述对于他们批评的立场不是一种进步,他们的反对太过简单,所有思想贯穿实践因素,没有无理论的实践,都是被某种理论化的理解支配着,在马克思实践概念上,思想与实践不是对立的,是人类统一活动的抽象化。将人类活动做区分很重要,理论与实践就是如此,需区别对待,它们之间不会有一致性。乌托邦也是如此,要注意乌托邦理论与乌托邦实践的不同性质,还有重合与相互影响的部分,它们目标不同,它们的成功必须以各自的目标来衡量,而不是假定努力的统一。
曼努尔提倡一种学科来区分“理论乌托邦”与“实践乌托邦”。这肯定了乌托邦理论与实践的强烈对比,姚那·费德曼(Yona Friedman)却认为写乌托邦就是用来实现的,并提供了一份实现条件的列表。这些成为判断乌托邦实现可能性的标准。其他人,如古德温(Goodwin)和泰劳(Taylor),采取折中态度,认为乌托邦有部分实现可能性,且乌托邦以“原则或精神”方式存在实现,而不是以细节或全部实现的方式,乌托邦的关键部分会在实践中有所体现。天主教乌托邦以制度方式体现,如教堂、修道院;共产主义乌托邦以大多数当代西方国家规划和福利制度实现(尽管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失败的)。许多欧洲和北美的公社从傅立叶(Fourier)和欧文(Owen)的乌托邦规划中寻找灵感和实践导引,其工作、家庭生活、男女关系、亲子关系、教育与艺术等所有方面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深受乌托邦或乌托邦思想影响。
有一种“实践乌托邦”,即“某一时期的制度或社会秩序的尚未具体化的真实存在的预期形式”。某些实践可以看作未来的极端预测,标志着“之前不存在的社会空间”的新产物,这样的实践乌托邦是理论家的正式文学乌托邦的模型。如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对位于丹麦汶岛奥利堡地区的研究,这是16世纪末的科研焦点,世界首例,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它是物质的、实际的灵感,对于康帕内拉(Campanella)、安德列(Andreae)和培根(Bacon)的科学幻想乌托邦而言。在培根的知识生产的想象化机构之前,第谷·布拉赫就做了这个大胆的乌托邦实验。
首要的是乌托邦实践,然后是乌托邦思想,而后是进步的乌托邦实践。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lic)中的著名实例,以毕达哥拉斯社区的“实践乌托邦”为模型,通过柏拉图学院的学生,影响了古代世界的宪法制定。它还可以运用于莫尔的《乌托邦》,启发了不同时期天主教社区的实践乌托邦,成为现代世界共产主义实验的主要来源之一。
这些例子表明了建立乌托邦思想与乌托邦实践的决定性关联的限制与可能性,这些关联模糊且普遍。很难论证,有时是名义上的,实践经常偏离理论,甚至成为对其的嘲弄,天主教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在西方思想领域引起最激烈的反映。社会主义社会无法匹配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希望,引起了谴责与绝望的文学。
我们又一次不得不承认乌托邦思想与实践或许是不同的,不能用想当然的一致性来判断,它们分享完美的理想;但它们构想理想的方式、完成的方式,遵循人类活动不同方面的不同原则,乌托邦不是写来实现的,不是直接的、字面的意义,它们的完美理想是理论化的;它们的作者对于在实践中实现目标表示漠然(与对乌托邦的实践价值漠不关心不是一回事)。实践乌托邦主义者同样努力实现一些被大多数同行视为不可能、愚蠢的或异想天开的事,他们的成功不在于与理论的理想多么接近,而是在于能呈现多少生活的可能性——即使非常短暂——来拒绝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妥协与堕落。“思维实验”——思想与想象上的乌托邦发明是一回事,“生活实验”——小社区或整个社会的乌托邦实践是另一回事,都有其功用,既实用又有理论性,但它们带给我们的会是各自的不同之处。[注]Krishan Kumar,Utopianis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pp.70-73.
库玛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乌托邦,表现出他的某种偏见,但其对乌托邦与实践关系的论析特别是关于乌托邦现实化的具体方式的概括,对我们认识乌托邦与现实的关系及其可否实现还是有借鉴意义的。这种情况恰恰显示出审美乌托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五、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的二重性
关于乌托邦价值评价及价值取向的二重性已如本文导言所述,此处不赘,这里仅扼要论及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向前看与向后看的二重性。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向前看与向后看的二重性是其价值取向二重性的重要表现之一。纵观乌托邦思想史或文学史,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乌托邦的思想理论形态及其形象表现形态都包含时间维度上向前看和向后看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当然,相对而言,似乎西方更侧重于“前瞻”,中国古代更侧重“回望”。这一问题已在《审美乌托邦的中西比较》中探讨,这里不再展开。
综上表明,乌托邦是个复杂性存在,不可简单化待之。乌托邦的二重性更启示我们,对其既不能绝对否定,也不可一味肯定,而应全面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乌托邦的性质和规律,选择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方面且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弱化乃至消解其消极方面的更好的方式,扬长避短,走出乌托邦二重性的悖论和困境,实现悖论的超越。“条条大路通罗马。”达到这一目标,可能存在多种有效方式,但在笔者看来,审美乌托邦应是最佳选择之一。
德国学者约恩·吕森(Jöm Rüsen)在其主编的乌托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思考乌托邦》的压卷之作《重新思考乌托邦:为灵感文化而辩》一文中,较系统地探讨了乌托邦的前提二重性、性质二重性、功能二重性及实践二重性等等问题,颇富启示意义。在该文的结尾,作者提出了这样的构想:“乌托邦思想是针对文化中的不安分成分而言的,为了给我们基于价值观念的行动提供方向,我们曾总是带着这种乌托邦思想生发出种种观念、祈愿、希望和恐惧,其范畴超越了任何既定事物所限。但是,是何种价值观念引导着我们冲破对现有生活环境的简单再造而打开新的局面?我们怎样才能想象这种价值观念?我们又当怎样任由我们分享这种观念?作为文化中‘不安分的精灵’的乌托邦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不安分引发了骚动、动荡和焦躁;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冲劲、动能和活力。如果我们成功地构想出这样一种作为文化定向途径的乌托邦成分,并避免使其因渗透到权力和暴力机器中而产生危险,那么,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这些乌托邦思想将鼓舞我们的行动,锤炼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之处境与发展前景的批判性看法,并且坚定作为我们生命灵药的种种信念。”[注][德]约恩·吕森主编:《思考乌托邦》,张文涛、甄小东、王邵励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笔者认为,审美乌托邦恰恰具有使我们“成功地构想出这样一种作为文化定向途径的乌托邦成分,并避免使其因渗透到权力和暴力机器中而产生危险”的优越条件。审美乌托邦除审美中心甚或至上以外,它还具有双重的终极关怀、经验的超验品格、在场的永不在场、无用之大用、个体本位的个人与社会统一等重要性质特征,特别是其包括了先验中介、中和中介、形式中介、交往中介的多重多维的审美中介性,“审美中介”等所蕴含的独特内涵及其方法有助于审美乌托邦超越乌托邦的二重性的悖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的二重性就逻辑且历史地成为审美乌托邦研究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