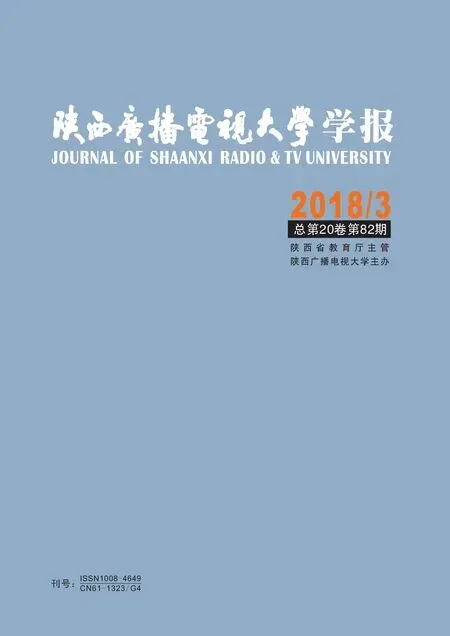《诗品》“兴”观探赜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钟嵘《诗品》的“兴”,历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探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这里把“兴”放在首位,足以见出钟嵘对“兴”的重视。除此之外,钟嵘对“兴”的解释“文已尽而意有余”也和传统儒家诗教观中的“兴”迥然不同。
一、钟嵘与先秦两汉的“兴”比较
“兴”字的本义是“起”,甲骨文中的写法是,繁体字是“興”。《说文解字》释义为“兴,起也,从舁从同。”[2]指的是共同合力完成一件事情,后来特指文学中诗歌的发生产生。“兴”最早作为和《诗经》有关的含义被提出,首次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之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3]这里主要提出关于诗的六种含义,并没有对“兴”进行深入具体的阐述。春秋时期孔子也有关于“兴”的著名论断,《论语》中孔子论及“兴”主要有七处。《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孔子认为《诗经》对于个人的修身养性起着至关重要的启发作用,他从文学作品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解释“兴”的。与之类似的还有《论语·阳货》篇中的“诗可以兴”。除此之外,“兴”在《论语》中还有两种用法,一是起床的意思,如“从者病,莫能兴”(《论语·卫灵公》);另一个即是兴起,如“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毛诗序》提到的“诗有六义,”[5]排列顺序与《周礼》相同,但也仅是提及“兴”,并未作阐释。真正对“兴”进行具体解释的是汉代的郑玄,他在《周礼注》中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淡,取善类以喻劝之”[6],强调的是“兴”具有一种引发的作用,以及“兴”所具有的比喻效果,可以看出,郑玄看到了“兴”的社会影响以及讽喻的效果。另外,郑众在《周礼注疏》中说“兴者,托事于物也。”他窥见了“兴”与“物”之间的关联,注重的是“兴”作为一种表达手法的使用法则,同时也将“兴”与文学创作糅合为一体。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钟嵘《诗品》中的“兴”观,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首先,在排列次序上,钟嵘没有按《周礼》及《毛诗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顺序,而是将“兴”放在首位,改成了“兴比赋”,这一做法史无先例,极大提高了“兴”的理论地位。尤为可贵的是,钟嵘认为,“文已尽而意有余”为“兴”,和以往在创作者的角度进行审视不同,钟嵘是站在文学接受的审美角度来阐释“兴”的含义的,他跳开了以往将“兴”视为一种创作手法的局限,独辟蹊径的从文学接受这个层面对“兴”做出了更为透彻的新颖解释。除此之外,钟嵘在《诗品》中提及“兴”字,共有八处,其中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勃尔复兴”,“亦文章之中兴也”,“故称中兴第一”(郭璞),这一类主要指的是社会政治的再度繁盛;第二类:“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这里“比”、“兴”连用,指一种创作方法;第三类,“嵘谓若人兴多才高”(谢灵运),“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张华),“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陶渊明),“然兴属间长”(谢庄),这一类“兴”均与“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含义相关。钟嵘尤为重视“兴”的第三类含义,并且这种“兴”与他的“滋味说”密切相关。学者袁济喜曾指出:“作为‘兴’的沟通桥梁,一是甲物使乙物起情,二是甲物与乙物有内在拟人化的譬喻。……使二者产生联系的是原先心境的几点。而心境的触发形式却是无功利的自然感兴的过程。”[7]
二、钟嵘与魏晋时期“兴”比较
在文学逐渐走向独立、文艺理论逐渐成熟的魏晋时期,不仅仅钟嵘曾经提及“兴”,同时期的诸多文学理论家,也曾对“兴”进行过探讨。西汉时期,人们对“兴”的解释大多是从“六义”的角度出发,自汉代末年至魏晋时期,人们一方面继承传统的“比兴”观,另一方面也试图将“比”与“兴”进行剥离。晋代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举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8]他将“赋”、“比”和“兴”分别进行阐发。通过分析他对“比”和“兴”的理解,可以发现,他结合了传统的“六义”说,并且捋出了“兴”所具有的情感体验的审美因素。这对魏晋文论家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南朝的文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体会到“兴”所具有的情感兴发特点,“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9]不同于两汉经学对从“美刺”的角度解读“兴”,刘勰对“兴”的认识深入到文学创作层面。“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他特别强调“兴”是无功利的发自内心的生成机制,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因素。刘勰对文学理论非常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兴”与“情景”相联系,突出了“兴”的偶发性和自然性。
与魏晋时期这些文论家的观点相比较,钟嵘的“兴”观尤为大胆创新。首先,和挚虞不同的是,钟嵘一反传统两汉经学“六义”说中对“兴”的解释,独创性地将“兴”放在首位,大大突出了“兴”的地位。钟嵘超越挚虞,不仅看到了“兴”所具有的情感色彩,更深入一层地洞悉到“兴”的“文”与“意”之间的关联,而挚虞只关注到了“情”与“文”的关系。
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可以说是魏晋时期文学理论著作的双璧。对于“兴”,两部论著都有进行论述和阐释。对比二者的不同,更有益于增进对“兴”的理解。首先,刘勰论“兴”,是立足于“主情论”的基础之上进行阐发的,认为自然景物对人有感发作用。同时,他还提到“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可见,刘勰认为“兴”是一种包含讽刺意味的文学创作方法,他也指出“比”同样具有情感因素。钟嵘论“兴”,从他的“滋味说”出发,他不仅看到了自然界的景物对人有兴发感触的作用,还强调社会中的悲剧体验对内心的激荡作用。前者如“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后者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塞客衣单,孀闺泪尽”等。其次,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对文章纲领、文体源流、创作过程、批评鉴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全书论及59种文体,内容庞杂。而钟嵘的《诗品》是一部专门品评诗歌的批评专著,所论及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相对于《文心雕龙》的驳杂,文学和非文学难解难分的状况,《诗品》可以说是一部纯文学理论作品,对“兴”的理解更为纯粹。
三、钟嵘《诗品》“兴”观的影响
(一)对后代的影响。钟嵘对“兴”的阐释,影响了后世的许多文人。初唐陈子昂的“兴寄”说,更侧重个人的情感与寄托,继承了钟嵘《诗品》中“兴”的美学观。唐代殷璠的在《河岳英灵集》中提到“神来、气来、情来”[10],充分体现出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神来”,指的是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矫健昂扬的精神;“气来”,则牵涉到文学作品的遒劲风骨;最后一个“情来”,丰沛的情感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浓墨重彩的为盛唐划上了醒目的标志。殷璠继承了钟嵘关于“兴”的阐释,从崇尚盛唐佳作的角度,提出了“兴象”说。后来的皎然,也偏向于钟嵘论“兴”的旨趣,提出“夫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经……”。他将“兴”与“情”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明显与钟嵘论“兴”重视情感审美体验是一路。随后又有白居易、朱熹等文论家,对“兴”作乐新的发挥,对“风雅”、“美刺”等儒家的政教传统进行了再次复兴。
(二)局限。钟嵘对“兴”的阐释,的确做出了开创新的贡献,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不得不说钟嵘的“兴”观也有其局限之处。与西方文论对某概念精细雕琢,动辄成篇的论述相比,中国的评点类的文学批评著作,显然有些点到为止,并且在逻辑上欠缺了一些,更多的是从个人的体悟出发,用经验去诠释某一概念。钟嵘的“兴”观,也失于篇幅太短,所以导致论者的思想犹如昙花一现,难以捕捉。从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中所论及的文学四要素来看,文学由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四个要素组成,[11]钟嵘的“兴”观仅仅只涉及到作品与读者、作品与作者两个方面,对于其他的环节则没有涉及。毋庸置疑的是,钟嵘为后代的读者解读“兴”,大胆的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并且对后代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