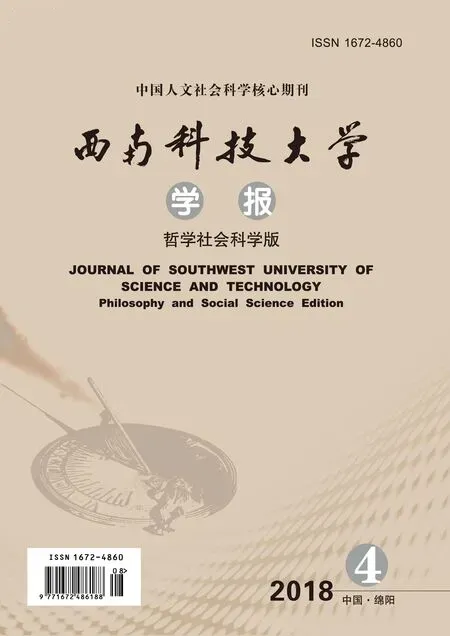新时代生态与伦理的有机融合
王 云
(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4)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21世纪人类面对的严峻课题。在社会发展的频频剧痛中,人类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而在崭新的文明形态之下,人类更需要付之以行动的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有效地缓解这种疼痛。
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
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解决生态危机的迫切需要。
(一)生态危机呼唤生态文明
“当前的生存体系是自我毁灭性的,当前人类文明的进程是自杀性的。”[1]237多年前,利奥波德认为,大地伦理的发展是双面的,即意识化和感情化的进程。因而,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适宜的方法去解答当前存在的生态问题。
当前,全球生态危机具体表现为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超标、酸雨严重、水资源不足、水污染加剧、沙漠化扩展、沙尘暴增多等世界重大环境问题,对我国而言,不但全部涉及且态势非常严峻。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多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切身体会和新闻媒体的诸多报道。到目前为止,“总体来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的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生态环境保护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仍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短板,仍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2]学者们分析了诸多原因,一方面是自然、经济发展等客观原因,一方面是人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生态价值观等主观原因。
然而,生态环境问题自古有之。在生存层面人类和其他动植物一样,本能地依赖大自然所提供的最基本需要。在原始社会,人类需要树叶兽皮为衣,捕猎采集为食,如此简单的获取,便已产生生态破坏,所幸问题并不突出,以至于人类毫无察觉。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态意识受到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统治的影响,对自然的认识仍处于混沌之中。就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生态环境本身与经济利益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但在某个特殊阶段,受到特定时期外在利益的驱使,本就微弱的生态意识便被轻易地抛之脑后。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我们不仅把大量土地变成了良田,而且还建起了城镇,这些行为已经导致了生态的变化:现代文明的物理、化学、生物的伴随物随处可见。除非我们这个时代支配自然的倾向得到控制,否则,我们将会把地球自然环境变成一个巨大的人工产物。事实上,不仅整个大地表面而且辽阔的海洋甚至大气本身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2近现代工业化进程仍然在不断推进,并且在特定政治因素的作用下,技术的进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市场利润倍增等带来的喜悦无一例外地使人类忘乎所以,原本并不强烈的环保意识和微弱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利益的驱使下显得更加岌岌可危。
单纯因为经济效益可观便放松了对生态危机的警惕,人类未免过于心存侥幸了。事实上,“环境的紊乱必然是由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中的某种错误引起的。”[4]99人类也逐渐意识到:当我们在地球上的不恰当活动积累到一定量时,自然界的反馈便会发生质变,最终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到了21世纪,由于我国党、政府的重视以及学者、环保人士等的共同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接受,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民生工程。因此,“人类社会正在跨入崭新的生态文明时代”[5]这一提法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了深刻阐述,明确了我国努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大思路。”[6]这也为全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生态文明践行的新诠释
生态文明是一种理念,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一种实践方式。实践者们首先需要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理解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西方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与生态文明相近的概念和思想却首先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兴起。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尤以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拉开了当代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序幕。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上先后面世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这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正逐渐地成为世界的共识。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各个方面绘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7]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与可持续发展内涵相一致,都是尊重自然为前提,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什么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因为“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观念,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导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8]29对中国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汲取各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走科学发展之路的必然结果。从党的“十七大”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发展循环经济”[9]到“十八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10],再到“十九大”更是明晰了目标:“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11]。中国化的生态文明研究把生态化目标作为人们活动的基本目标之一,从而使人与自然得以和谐共存、协调发展。
为什么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这一危机?因为“自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来,自然界就有了自己的对立面,它不再是一个按照缓慢节奏进行演化的纯自然系统,而是逐步变成了人化的自然系统。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一直存在一个副作用,就是对生态系统的破坏。”[12]1可怕的是,这种破坏并不是某一局部的,我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着这一令人焦虑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不单单是人类应对时代挑战的现实要求,而且是全人类面对这一危机时的积极回应。
毫无疑问,生态文明是一项牵连甚广的系统化社会工程,重点在于建设和完善,可贵在于持之以恒。确实,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集中体现了以科技创新来推动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不竭动力。换言之,人与自然都在发展中成长变化。人类能通过一定的科技使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使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和谐统一,在循序渐进中实现既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又维持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平衡稳定。
那么,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该如何做?众所周知,政府、企业等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承担着双重角色:既是环境危机的缓和者亦是危机的制造者。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或政绩不惜牺牲自然环境,暂时逃过了眼前自然的反击。然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生态危机的发生取决于人类毁坏生态的程度。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频繁发生的生态危机,人类终于逐渐意识到这样的生态规律。
(三)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生态文明建设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党和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学校、新闻媒体及个人的宣传和努力之下,全社会的生态意识确实有所提高。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普通民众的新理念,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存之道得到社会各界的倡导和弘扬。然而生态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因为意识形态上的改变和影响缓慢而深远。如此,更需要将伦理型的文化传承下去,才可能潜移默化、深远持久地熏染并转化为坚定的执行力,从而改变个人、全社会乃至全球。
实际上,现实中实践起来确实任重而道远。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等客观因素导致城乡的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农村更为落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分析:“2016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人口13.84亿,城镇人口7.87亿,城镇化率56.9%,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13]。其中一些极度贫困落后地区的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尚不能满足,更无法奢望其受教育程度和素质良好。就全球而言,“截止2017年,世界上共有230个国家和地区”[14]。显而易见,各国的差异众多,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因此,大多数人所谓的生态意识也多是基于生活经验和朴素的情感,并没有上升到本质的认识,环境保护的实际长期参与力自然较为低下。城市的经济状况略好,受教育程度亦会高一些,但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下,人们的生存压力并不一定比城镇轻松,虽然对生态问题感知强烈但力不从心,这在整体上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中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弱化。
二、生态伦理是新时代文明的内在要求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催生新的伦理观念。伦理诉求的深意可能并非只是想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引导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
(一)生态问题的伦理思考
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产生,就是由于大自然受到了人类的过度干预后所反馈给人类的各种负面连锁效应。当今社会,人类遭遇了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双重打击。
当人类为达到自身欲望,企图利用某种技术以控制自然使之臣服于自己时,正如卡逊(Rachel Carson)所言:“‘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的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15]263。当“人在生态关联网中遇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作为主人面对这一发展,我们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成为进化的帮手,可以影响其方向,但是自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物体,而是我们得适应自然,以便使自然根据其规律按照我们的意愿起作用。”[16]480人类开始觉醒后,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尝试着寻找一种可持续的、和谐的方式维护彼此的共生共荣。“很清楚,如果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文明,要保持在与整个地球系统和谐一致的状态中,那么,生存就必然能适应自然部分——生态圈的要求。环境的紊乱是一个我们还未能,至少至今还未能取得这种适应状态的信号。”[4]97-98康芒纳表示,人类活动导致了环境紊乱。同样卡逊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积极呼吁“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17]22人类对其盲目使用化学物品带来的伤害,及短视利己行为带来的问题,应当有所反思。“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生态上的失败。”[4]120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为经济学家或者环保主义者有必要跨越学科间的蔽障去包容并解决生态危机暴露出来的各种学科之间的断点问题。因为人属自然性,但同时也具有社会性,人类自身并不独立于大自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产物都来源于自然,不管人类是否承认,人类与大自然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影响制约是客观事实。因而人类的科学不仅关乎自然科学更牵连人文社会。
尽管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危机仍在不断加深。主要原因是人类的文化需求很自然地被抛在经济和政治之后。由于经济增长需要而产生的政治主张促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上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崇拜到征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挑战。尤其从工业时代开始,人类除却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外,各式各样的生活需要以及未知的欲望变得沟壑难填,人类的心理也在悄然改变:对生态从小心翼翼地开发和利用到盲目自私地污染和破坏。爆炸性增长的经济规模必然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量。然而,“地球生态系统受掠夺的总速度,是有某种上限的,它反映了生态系统周转所固有的限度。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这个系统将最终趋向崩溃。它已经被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生态系统的每一件事所确信无疑地证实了。”[1]220在当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资源的损耗速度远比索取更快。
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环境受污染严重程度已不容忽视正是生态危机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原因。而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的资源宝库也是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各种生物由于人类的掠夺而失去家园,生态平衡被打破,生态灾难开始频发。自然危机如温室效应、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物种濒临灭绝甚至已经消失。作为始作俑者的人类并未幸免,雾霾、受污染的食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引发的各种疾病正侵蚀人类的身体,疑难杂症、患癌几率剧升且呈年轻化趋势不得不令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所作所为。
更令人堪忧的是,人类对生存环境的不友好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与功利主义唯实唯利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因此,生态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和显现出改善效果的过程,其实异常艰难和缓慢。
“环境问题提出了基本的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它有关我们追求的目的。科学和技术最多是我们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18]7“生态的生存并不意味着抛弃技术。它只是要求技术产自科学的分析之中。这种分析为技术要闯入的自然界是适当的。”[4]150
确实如此,“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或已认清,既然人类自诩科学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工具,那么如今被“工具”所左右的局面,实在有些讽刺。利奥波德看来,人类反思自身的结果表现出生态学理论与各种生态问题产生的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矛盾。对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就是要把理论与现实相联系,它是某种聚合的力量,不但控制着人类的日常生活而且包括历史发展进程。因此,人类需要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
那么,人类在这之间找到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平衡点是什么?
(二)化解生态危机需要伦理考量
要解决生态问题带来的危机,诸多专家学者表示,伦理考量是必要的、普遍的、有效的根本平衡点。
人类正在努力改善,但仅仅依靠党和政府所做的强制措施并不够。既然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生态危机又多由人为因素造成,那么每一个人都参与到维护生态平衡的行动中是理所应当的。除了法律、制度的强制措施,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的就是道德和伦理的软制约。然而,人们的伦理现状正经受着时代的考验。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千百年传承至今的丰富伦理文化,在经过时代的变迁和科技影响的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和伦理意识没有得到普遍的发扬和传承,加之经济基础的不断变革促使形成新的伦理关系后,在中西方、各民族、各宗教文化的激烈碰撞下,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某些消极影响使得人们陷入一系列信仰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等。人生价值的迷惘、道德滑坡使得精神家园残垣不堪,促成了当代一些人精神上的病态。
要逐步化解这些难题,首先便要重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新型伦理来规范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三、新时代伦理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生命力
新时代伦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系,内含着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旨归。
(一)生态伦理走向新时代文明的应然性
学者李建华结合了现代人的生活实践和时代要求,对伦理进行界定:“所谓伦理,是指一定社会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应然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一种应然性的有序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价值指向性,内含着人们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价值取向。因此,伦理关系中内蕴着规范性要求。伦理总是表现为一定时代中一定人的伦理,并且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对道德的认识,在中西方都是从人们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应然性关系即伦理关系的认识、理解和践行角度来理解的。”[19]
对于新时代伦理应然性问题的考察,有学者提出仍然从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关系出发去理解,虽然伦理理论上是应然性的关系,“但是,自由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 ”[20]正如人已经脱离对大自然的被动依赖,能够利用科学技术达到自身所想的各种欲望,但是人类仍然不知足,妄图摆脱道德、伦理、法律、制度等的束缚,以实现绝对的自由。
到那时不只是生态问题,恐怕所有生物的生存危机都会爆发,届时等待人类的灾难,将难以估量。
(二)生态伦理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因此,这就理解了为什么拯救生态的行动迫在眉睫,作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应当做什么?如何做才能避免这可怕的一幕发生?
单从人本身思考,作出某种行为,是需要从思想上改变的。伴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道德和伦理关系的反思也应当与时俱进。生态伦理是伦理体系一个新的分支,是人类基于生态价值观念认同基础上维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要求,把道德和伦理的范围扩大到自然界一切,重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应用性伦理。在当今生态文明的理念下认识到危机的紧迫性,不可逆性等特征,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孕育而生的新伦理,不仅有传统伦理学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审慎思考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似乎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作为能动性主体的人类不仅遵循新伦理规范,而且深知这样做的缘由。成为让人类和自然彼此依存的新力量,相信人类能够借此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实现生态伦理的真正价值。
中国已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并且作为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悠久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其中不乏丰富的伦理思想,但历经世界文化的碰撞后,出现了纷繁复杂的文化局面。一些令人堪忧的文化危机如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状况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因此,在新的生态文明时期,需要批判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扬弃外来文化,以此来开创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并重新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为生态文明理念深入大众内心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如此一来,优良的伦理得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结语
由于生态危机不仅与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背景纠结相连,并且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主义下的技术对自然的控制就是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因此,新时代的伦理诉求不但包括对人本身行为价值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而且包含对全社会的合理新秩序的理性认识。犹如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所言“人应该有一种伟大的情怀:对动物的关心,对生命的爱护,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这种伟大的情感有助于稀释和冲淡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过分关注,有助于把人们从对人际利益永无休止的算计纠纷中解救出来。”[20]
因此,作为拥有高级智慧的生物——人类,在化解危机时的思考“我应当做什么,如何成为更好的人?”这大概是生态伦理的意义。人类应该行动起来了,从提出“生态文明”就表示人类已经在反思自我,进而从“生态文明建设”开始,人类的行动正在对“生态危机”加以弥补。无论以何种方式开始,这个过程定会充满艰辛。只有人类记得为什么开始,如何实践才能让这个美丽而脆弱的生命之网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