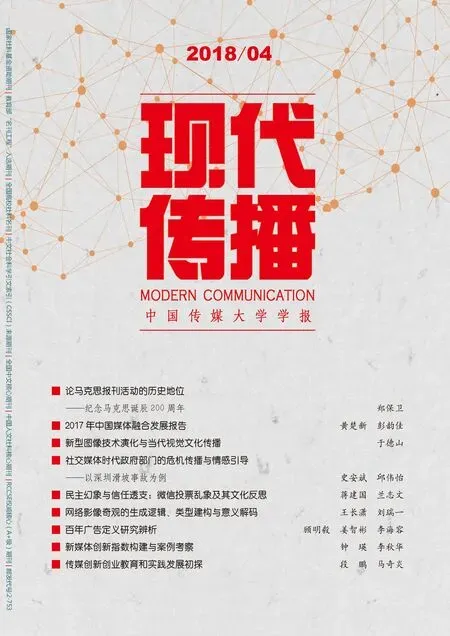传媒公共性: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
■ 黄 艾 张晓星
一、传媒公共性的“前世”与“今生”
当哈贝马斯将现代性指称为一项未竟的事业,传媒公共性的实现无疑是其蓝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也成为了以“现代化”事业为己任或者视“(西方)现代性”为社会进步基准的诸多传媒学者的理论研究原点;而今无论传媒技术如何日新月异,谈及公共性的议题似乎就绕不开“公共领域”的概念。
实际上,探讨传媒公共性的历史源远流长,其研究脉络也更为错综复杂。从埃德蒙·伯克最先提出的“第四权”概念到加布里埃尔·塔德将报刊视为公众的“精神纽带”;从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批判大众传媒炮制刻板印象与“拟态环境(pseudo environment)”,到以杜威、库利与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强调新闻媒体要超越信息传递者的角色、通过促成集体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①,再到由哈钦斯委员会提出、后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盖棺定论的“社会责任理论”以及由其衍生出的“看门狗”理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传媒公共性的探讨发轫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反映了资产阶级传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需要。在工业革命达到高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Gesellschaft)剧烈转变的过程中,关于新兴社会如何凝聚的疑问以及对于高度集中的“乌合之众”的恐慌使得这一议题得以进一步发酵。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面对文化差异、种族冲突等矛盾,芝加哥学派基于勒庞、塔德、西盖勒等欧陆理论家关于“大众”的既有探讨,将跨文化语境下共同体营造的议题引入传媒公共性的框架之内②。最后,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制度危机以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意识形态重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整顿沦为私人生意、反对政府干预、拒绝承担社会责任、日益失去公信力的新闻行业③。由此可见,关于传媒公共性的讨论自始至终都内嵌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脉络之中,不断回应着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之间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与危机。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以“公共领域”理论的广泛传播为标志的传媒公共性讨论的复燃亦不例外。
伴随着西方传播思想的普世性建构、意义输出与话语争夺,以及我国本土的行业转型、理论贫弱与社会诉求,传媒公共性这一舶来的概念如何“落地”便愈发必要而紧迫。
二、“公共性”概念的“西学东渐”
阿伦特和哈贝马斯都在其著作中详尽地回溯了前现代社会中“公共”与“私人”的概念是如何的泾渭分明:经济活动从属于私人领域,而政治行为则定义了公共事务。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确立,经济活动逐步超越其原本所属的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的范畴,成为了“政治经济”。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给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们以灵感,让他们看到了一种公众自发组织、自我管理的可能性;而当时以君主专制形态存在的“国家”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自由市场的对立面并妨害着这种“公共性”的可能。④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理念自其诞生之初就蕴含着内生性的市场逻辑,而国内学界呼应这一“潮流”的声音亦不绝于耳。有学者认为,市场所代表的非官方话语开始进入报刊与电视等媒介,打破了官方声音“一言堂”的局面;⑤而公共话语的日趋多元,促使消费导向的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官方话语和精英话语的主导权则日渐式微。⑥更有学者直言,当代中国传媒公共性的产生正是拜传媒的市场化改革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所赐。⑦
然而以市场化、商业化的形式来实现传媒“公共性”的论调恰恰是哈贝马斯公共理论所批判的核心之一。阿多诺拒绝为其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在1989年被翻译成英文,并随即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学术反响,恰恰是因为其中关于媒介商业化的批判回应了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媒介行业所日益凸显的种种弊病。秉承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态度,哈贝马斯在书中指责晚期资本主义中高度商业化的大众媒介已经从理性沟通的渠道变为传媒企业钳制舆论的工具,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行动政治转向“旁观者政治(spectator politics)”,从而使原本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不断分崩离析,沦为被动接受公关信息与娱乐消费的一潭死水。通过糅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其后更是鲜明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所具有的难以超越的阶级局限性,以及它在特定阶级利益的操控下沦为一套程式化、非现实理念的最终宿命。⑧这样来看,哈贝马斯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分析采用的正是阿多诺“内在批判”的方式,通过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念”与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状”进行对比,来揭示其固有的困境。⑨这样看来,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被其原本旨在批判的对象——新自由主义——所挪用,为所谓的“极权”统治下的媒介商业化进程提供“合法性”与“进步性”就显得格外戏谑。⑩
除了在市场化的问题上曲解或者(选择性地)忽视哈贝马斯的相关批判,学界对于其理论的引鉴还呈现出教条化和片面化倾向。当公共领域的概念被奉为圭臬,甚至“传媒必须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要求而展开其实践”时,机械地套用这一框架来检视中国的传媒历史和传媒实践就变得难以避免。有些学者消极地认为,隶属于国家机关的中国新闻媒体——同西方作为“第四权”的传媒有着本质的区别——很难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其公共性建构是不现实的。例如,许鑫在梳理中共新闻事业史上的三次新闻改革时认为“1942年的新闻改革强调了党性,弱化了公共性,1956年改革试图回归公共性,1978年以后的改革确立了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并在不经意间产生了有限的公共性”。这样一种“有限公共性”的表述,也就暗示着在传媒体制没有根本突破——形成西方定义下的公共领域——的情况下,传媒的公共性就无从谈起。与此一脉相承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兴盛的专业主义视域中的传媒公共性。报刊方面,这一时期的《南方周末》逐渐注重调查和批评报道;《中国青年报》创办《冰点》专栏,其刊登的特稿议题常常触及社会弊端,而《冰点时评》则开启了中国报业公民表达之先河;电视方面,央视自1993年开始先后创办《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等评论类栏目及《实话实说》等谈话节目,掀起电视平民化浪潮和记录浪潮,满足受众对社会现实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需要。在这一系列的媒介实践及其衍生出的话语体系中,传媒的公共性体现为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保持传媒行业的自主性,不屈服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实现报道的客观、中立。这样一种以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的视角来引用哈贝马斯的做法,虽然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实际上却依然是将哈贝马斯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系统(system)”与“生活世界(lifeworld)”的二元对立,强加在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之上。
由此可见,在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作为哈贝马斯批判的大前提与核心对象——无论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还是《交互行动理论》之中——资本主义社会都被忽视了。“哈贝马斯明言的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作为解决新自由主义下种种矛盾的路径,抛开其理想化和去历史化不谈,更是“有意无意把这个公共领域前面的定语资产阶级去掉了”。换言之,这样的一条传媒公共性之路依然未能超越关于资本主义的想象。而其中,深深植根于西方左派理论之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框架在社会主义中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语境下更是难以适从。
三、传媒公共性“落地”中国的实践
汪晖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就是它的公共性。正如前述的理论回顾与反思所揭示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探讨传媒公共性的重构,就“既需要打破单纯建立在对市民社会想象的公共领域的迷思,也需要重新思考和总结阶级、人民和公共性的关系”。以下,本文将以海口电视台的电视问政类节目《亮见》栏目为例,探讨中国本土传媒公共性建设的最新实践。
《亮见》栏目是由海口市纪委监察局主办、海口广播电视台协办的大型党风政风监督电视直播节目。 在节目的主题选取和采访制作过程中,《亮见》秉承“百姓参与、百姓监督”的理念,邀请群众全程参与其中。在选取问政主题时,栏目组提前通过热线、网络等多种途径向群众征求意见,收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发动群众,拓展投诉举报渠道,并集中归纳筛选出百姓利益诉求强烈的突出问题,由百姓点题。比如2016年《亮见》开春第一问“剑指农村微腐败”、第二问“谁在漠视农民群众利益”、第六问“村民自治还是村官自治”等,几乎每期节目都是紧扣农村基层微腐败、农村环境污染、农村土地管理、农村基层民主等人民群体聚焦的热点问题展开,深度曝光剖析了农村“三资”管理、惠农资金领域存在的决策不讲程序、议事不公开等问题,着力破解农村基层组织不敢、不会、不能监督的难题。在问政问题的调查采访上,记者根据市民反映的线索进行暗访,旨在减少干扰,尽最大可能还原事实真相,真实呈现百姓诉求。在节目现场,始终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场内不仅有行评代表、媒体代表,还有市民代表,共同参与发问、表决,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场外则通过现场热线电话和网上微博平台,实时发表意见建议,或者进行投诉。通过群众代表、专家代表与问政对象之间的互动沟通对话,既开启了群众参政议政的良性互动,也使各职能部门切实感受到为民办事的压力和动力。譬如,2016年《亮见》第二问“谁在漠视群众利益”这期节目深度曝光了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王挺村被5家塑料加工厂包围,导致村庄被污染、村民利益和身体健康长期遭受到损害,海口市环保局、龙华区环保局、龙桥镇政府等相关单位在接到村民投诉后存在监管不力、执行力软弱、责任心不强、相互推诿等问题,使村民渴望环境治理的诉求严重被漠视。对此,节目主持人要求问政单位现场做出正面承诺,在多长时限内做出整改、解决问题。被问政的龙华镇书记表示:“立即行动、马上查处,坚决取缔”。对此,现场评论员矢弓先生犀利发问:“我们海南还有多少污染,如果上不了《亮见》节目,能不能等到‘坚决取缔’这一句?我们关心的不只是个案,这样的问题作为环保局应出台怎样的长效和制约机制?”
可以说,从问题的曝光,到问题的整改,《亮见》不仅进行全程追踪,促进所曝光问题的快速落地整改,而且《亮见》所构建的“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纪委督办问责”的大监督平台,让媒体与群众成为纪检监察机关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在《亮见》实践传媒公共性的具体路径中,大众传媒开启了媒体监督、纪委督办的常态,为人民群众打通了合理参政议政的渠道,强调了媒体的人民性,从而真正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式的民主”,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四、国家、传媒与公共性:中国的经验与挑战
作为中国传媒公共性建设现在进行时的一个缩影,《亮见》栏目所彰显的传媒公共性理念,呈现出与前述“西学东渐”的诸多相关阐释之间明显的差别。一方面,《亮见》栏目对资本力量与市场逻辑的警惕,无疑与新自由主义者以消费行为与消费者为核心构想的“公共性”——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中原本备受“压抑”的文化形式与内容得以复兴与繁荣、满足着日益丰富多样的消费需求——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该栏目与纪检监察机关的通力合作、与地方政府的直接对话,也挑战了哈贝马斯理论框架中的在“国家官僚体系”与“公民”的对手关系下传媒公共性的建构模式——传媒代表弱势的公众一方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国家官僚体系对公共领域的渗透和对公共利益的染指。如此一来,西方传媒公共性理念在解释中国当下传媒公共性实践时的“水土不服”,是否意味着——正如一些西方主导的新闻舆论所指出的——后者正面临着由于所谓的“体制”而形成的诸多现实瓶颈与困境?答案正好与之相反:中国实践的“不可解释性”恰恰体现了西方理论的“贫困”。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都深入地批判了资本力量和市场逻辑是如何一步步消解和蚕食传媒的公共性,以致其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媒介景观中彻底地沦为一种公关性质的“表演”。因而,打着繁荣文化市场、服务消费主体、实现舆论自由旗号的传媒公共性建设如何欲盖弥彰,在此不再赘述。而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尽管他将公共领域与国家的关系放置在“封建化(feudalization)”与“反封建化(de-feudalization)”——即“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动态的、辩证的关系中来考量,却依然囿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视角。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任何形式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交融都是消极的,其借用韦伯的概念称其为“官僚化(Bureaucratisation)”,这其中既包括了国家向社会的渗透,也包括了随之而来的社会向国家的渗透;而权力精英所主导的服务于国家官僚体系的现代大众媒介则在这一“官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传媒公共性的重构在于摆脱国家官僚体系的束缚,在于立足市民社会展开行动,在于保障公共领域中意义的生产与交互不会受到国家与资本力量的侵蚀与操控。然而,这样的理论建构无疑一方面以一种韦伯式的国家理论将国家“物化”并化约为一系列国家机器与一群国家干部,而非将国家视为内嵌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多维度、历史性的矛盾实体与纷争场域;而另一方面又将“(市民)社会”理想化为一个“去政治化”的“国家权力与社会统治关系的真空场所”——这也恰恰体现在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lifeworld)”定义为一个单纯的文化与意义生产的场域之中,从而使其成员失去了积极意义上的参与国家事务、争夺文化政治领导权的可能性与主动性。也正是这些受困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语境的概念性“成见”,使得由其生发的传媒公共性理念在“落地”中国的过程中始终举步维艰、蜗步难移。
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在近代中国被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强行“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中,逐渐瓦解却仍树大根深的乡土社会、分崩离析的封建王权、孱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买办附庸之间的斗争,与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与封建王权之间的相互角力有着显著的差异。因而,与西方将“市民社会”作为历史原点所构建的公共性议题不同,中国的传媒公共性则是萌芽于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解放、推翻阶级压迫的历史环境中。那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投身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事业的时代,社会的诉求在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与国家的意志实现了统一,而其中无产阶级更是以其“被压迫的普遍性来伸张它的公共性和正义性,并逐渐赢得全社会的意志”。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传媒的公共性就并非表现为构筑和维持所谓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而是作为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具有明确目的性和指向性的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存亡联系起来,使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与意义生产的一个主旨;同时,传媒的公共性也并非服务于“去阶级化”的市民或公民,而是旗帜鲜明地代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受压迫阶级的共同利益。今天,面对着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仍然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现实,作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上述脱胎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实践、具有着鲜明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印记的工农联盟的主体性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依然是我们探讨传媒公共性议题的基本点与出发点。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传媒公共性的重构一方面要回归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承诺——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在今天的政治经济架构中已经身处底层的工人和农民能够平等、自由地进入公共舆论的视野并自主地表达诉求,维护其主人翁地位、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而另一方面要将国家所身处的国际国内形势、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融入到人们日常的社会文化生活与意义生产当中,形成与国家建设和发展相联系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培养与民族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主人翁精神。无论是列宁的党报思想还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都为这样的传媒公共性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此外,在回溯与重新发掘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厘清发轫于西方的传媒公共性理念如何贯穿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各个阶段并逐步沦为资产阶级维系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反思其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不断扩张的“领土”上所焕发的“又一春”,是如何通过建构似曾相识的关于“公共”的话语景观来掩饰其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性;更要警惕其所传递并意在不断复刻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框架,对于不断受到跨国资本力量侵蚀的第三世界/“边缘”国家又意味着什么。
注释:
①Ciztrom,D.(2010).MediaandtheAmericanMind(pp.91-121).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②Mattelart,A.InventionofCommunication(pp.256-259).Minneapolis,MN: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③易涤非:《通识教育、媒体责任与美国意识形态建设——从两份哈钦斯报告说起》,《红旗文稿》,2014年7月23日。
④Calhoun,C.(1993).CivilSocietyandthePublicSphere,Public Culture,5(2),267-280.
⑤卢迎安:《当代中国电视媒介的公共性研究(1978-2008)》,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⑥Qing,L.(2003).BetweentheStateandtheMarket:MediaReformandtheChangeofPublicDiscourseinContemporaryChina(p.150).Minneapolis,MN: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⑦李昌忠:《传媒公共性的嬗变及其现实困境》,《新闻知识》,2014年第8期。
⑧Fuchs,C.(2014).SocialMediaandthePublicSphere. Triple C,12(1),57-101.详见Habermas,J.(1989).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AnInquiryintoaCategoryofBourgeoisSociety. Cambridge,MA:MIT Press
⑨Fuchs,C.(2014).SocialMediaandthePublicSphere. TripleC,12(1),57-101.
⑩例如 Zhao,Y.(2000).WatchdogsonPartyLeashes?ContextsandImplicationsofInvestigativeJournalisminPost-DengChina. Journalism Studies,1(4),577-597.
(作者黄艾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站博士后;张晓星系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