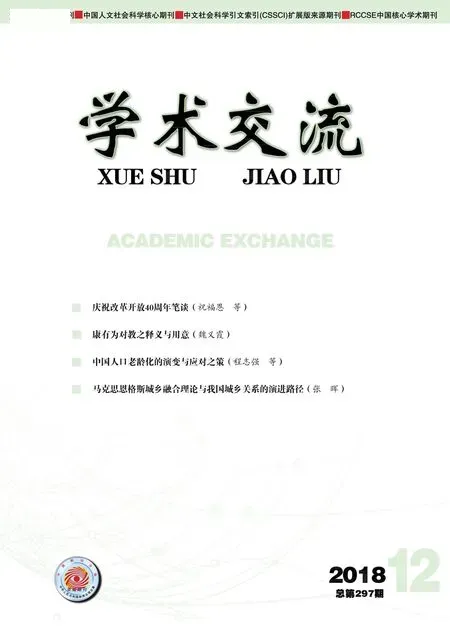文化哲学的俄罗斯思想之维
郑永旺,郑 淇
(黑龙江大学 俄语学部,哈尔滨 150080)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并没有把哲学当成关于文化的知识,这也就是为何早期的(比如20世纪60年代之前)哲学学科分类中找不到当下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在古希腊,柏拉图等人一直致力于让哲学成为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皇后,甚至成为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然而,哲学的面孔总是不断变化,即便今天,人们也不能用科学理性来要求哲学(哪怕是技术哲学),更无法为浪漫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和宗教哲学等哲学流派缝制合适的科学外套,因为哲学知识是思想家对客观世界的阐释,这种阐释也就是对文化的沉思,而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多不确定性。
一、文化学与文化哲学
拉丁语cultura是指农业,具体来说是指“耕地和土地管理”或者“种庄稼”,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和cultura相关的手段,如agricultura(农业技术)。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较早地将农业和今天意义上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他发现,“对身体的训练(耕种)与对精神的培养是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使自己高尚起来的两件必备之物”[1]。时至今日,这种和农业有关的cultura意义渐渐繁杂。研究者都试图依据自己所在的学科对文化进行阐释,英国人类学家B. K.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个方面。这种分类很难让人信服,语言如果离开精神文化如何独立存在?而物质文化没有语言的支撑如何能使人联合起来创造物质财富?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路易·阿尔都塞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在各自著作《狱中札记》与《保卫马克思》中将文化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文化的意识形态论。文化的复杂性给文化研究既带来了困惑,也带来了机遇,文化研究变成了文化学(culturology),但作为研究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等问题的科学,文化学与文化哲学(philosophy of culture)有何区别?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考察了100多种文化定义后发现,“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的各种具体样式……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2],但他们所说的文化依然是文化学研究的范畴,即将文化作为资源的研究,因为哲学或者说文化哲学不会去追问众多的文化现象的成因,它所要做的是论证文化存在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认识文化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茹耶夫断言“哲学也就是文化哲学”[3]11。这是因为,任何哲学家都一定是身处某种文化语境的人,他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站在超民族的立场上,他的研究虽然立足于解决“我是谁”这样对所有人都有效的终极问题,但文化身份和文化语境会使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受本民族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虽然不能否认哲学家有可能有意识地摆脱这些困扰。实践表明,法兰西精神、俄罗斯思想、儒家道德说、德国古典哲学、存在主义哲学都试图解释世界,但结果是,因为文化的支点和人的运思方法不同,哲学家们的理论话语可能只对某一时期某种文化语境中的某种问题有参考价值。
文化哲学一般被认为是哲学的分支,先驱者为18世纪的意大利启蒙思想家维科,他在《新科学》中强调人类社会要经历由生成走向毁灭的过程,人类历史由“野蛮时代”“众神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四部分组成。在“人的时代”,人在创造历史辉煌的同时也会再次回归到“野蛮时代”,维科认为文化是人类主动参与历史活动的产物,而人类文化由盛入衰的过程为后来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文明的解读提供了佐证。至于某些文献中所说的“Kulturphilosophie(德语中的文化学)这个术语产生于19世纪末巴登学派的新康德主义”[4]与今天学科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存在区别,当时的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将文化哲学理解为整个哲学,他们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论证“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在逻辑方法上的区别。
梅茹耶夫更倾向通过对比来厘清文化哲学与文化学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如其所言,“我们应该对比德国文化哲学家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的作品。后者将文化的哲学观点与文化的科学研究对立起来,文化的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对经验材料的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这些经验材料则来自于‘田野调查’以及对原始人生活的观察结果”[3]12,但他对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没有信心,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将文化哲学和文化学严格区分开来”[3]25,美国人类学家怀特在区别两者界限方面更为简单粗暴:“最重要的是,文化学拒绝并禁止哲学,而哲学几千年来始终是人类心灵最珍贵的,它一如既往地激励和滋养着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与爱好者们。这是一种古老而尊贵的人类中心论(антропоцентризм)和自由意志的哲学。”[5]文化学不能在哲学缺席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对文化的阐释。但类似的言说使人们开始关注文化哲学存在的意义,关注哲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可能等问题,思索是不是只有文化哲学才能完成哲学在阐释方面所无法承担的任务。
当然,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将文化哲学理解为古今哲学家们关于文化的论述。不过,这类知识更多地证明了文化哲学的信息来源,却很少能证明文化哲学本身。尽管这类知识对于每一个文化人来说都是必要的,但不能使其成为文化哲学家。文化哲学不仅是一些个别的哲学家对文化所作出论述的总和,而且还是从哲学体系的整体构思中必然分流出来的一部分。然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又是如何与整个体系相联系的呢?
无论哲学家谈论什么——自然、社会、人——他所谈论的都是文化。哲学反思的本质就是反思的任何对象都被揭示为文化现象。按照图罗夫斯基的话说:“文化反思就是哲学。”[6]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哲学都是文化哲学,而文化哲学的历史等同于整个哲学史。哲学家可以不称自己为文化哲学家,但他的哲学就是文化哲学,抑或像卡西尔在论述逻辑分析难以把握宗教和神话时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文化哲学并不询问一种形而上学体系或神学体系所问的那种问题”[7]。作为整个哲学体系中的新兴学科,文化哲学经常因其存在问题而引发质疑。关于文化哲学与文化学概念的困惑在于两者对研究对象的态度,文化哲学中的文化(无论是cultural philosophy还是philosophy of culture)虽然对哲学一词有限定作用,但这种限定反而扩大了哲学这个概念的所指,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流派都是在文化中生存,也依据文化而生存。梅茹耶夫在“哲学也就是文化哲学”的前提之下对文化哲学进一步阐述,指出文化哲学的突出特征在于思索文化中所深藏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而文化之思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以哲学家本人主观价值取向为出发点的诉求,而是一种关于只有文化才具备的对客体有认知能力的哲学知识。
文化哲学的俄罗斯学派强调文化哲学是哲学的子学科,认为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文化现实的完整性和文化存在具体形式的完整性、在文化的构造、功能和发展中”[8]建立文化的理论模式,这和古列维奇对文化哲学所下的定义类似,即“文化哲学是以对包罗万象的文化进行哲学解释为目标的哲学学科”[9]。
然而,这个定义存在同义语反复的逻辑陷阱,文化哲学就是对文化的哲学解释,那么宗教哲学就是对宗教的哲学阐释,语言哲学就是对语言的哲学阐释。但是,如果把语言、宗教、政治等都纳入文化的领地,上述判断就很难成立。所以,梅茹耶夫深知对文化哲学的边界进行划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哲学也就是文化哲学”这种模糊说法不失为对文化哲学定位的有效路径,以表明对文化哲学所思客体的细化和对文化哲学在整个哲学学科中研究对象的确定无助于解决文化哲学与文化学之间分工的问题。很显然,文化学和文化哲学之间的区别不应从文化本身去寻找,而应在哲学与科学对文化认知的特殊性当中去发掘。
如前面所述,哲学家通常处于某种文化语境中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尽管哲学家试图站在超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各种哲学话语依然是某种文化的产物。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可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诗学,但未必适合分析曹雪芹的《红楼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能够用荷尔德林的《面包和葡萄酒》来给出“诗人何为”的答案,但不一定能借助李白的诗歌来消除同样的困惑,因为任何诗人的创作都是文化的映射,而对这种文化映射的阐释是基于诗歌存在的文化土壤,阐释本身就是以文化为依托的阐释。甚至可以说,哲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某种具体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文化哲学中的俄罗斯学派
论述文化哲学中“现代化”概念时,梅茹耶夫指出:“严格地讲,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既和西欧派的现代化理论无关,也与俄罗斯本土的现代化理论无关。科学文献对现代化的阐释看不到对俄罗斯观点的引用。”[3]354但实际上现代化的思想和行动在三百多年前的俄罗斯已经出现,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就透露了俄罗斯和瑞典第二次北方战争的秘密,就是要“凿出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В Европу прорубить окно)。但在追赶欧洲时,俄罗斯的思想家还故作镇定地表示,俄罗斯民族是独特的,这就好像你一边向人家学习,一边告诉对方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19世纪40年代,丘特切夫透露了俄罗斯为什么学习西欧时又为自己的落后辩护:“俄罗斯的真正捍卫者是历史,它在300年间不知疲倦地帮助俄罗斯承受神秘命运带给它的各种考验。”[10]73
这很令人费解,仿佛俄罗斯所经历的一切是世界上其他民族从未经历过的,似乎俄罗斯的独特性并没有被西欧认识,“欧洲的西方轻率地相信,除它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另一个欧洲。诚然,它知道在它的边界以外还存在着自称为基督教徒的人民和君主”[10]74,任何民族都会经历只属于自己的历史,这个自明性的问题在丘特切夫那里反倒成了俄罗斯民族的胎记。和丘特切夫一样,许多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家都在寻找俄罗斯民族独特性的证据,并根据历史上的文化事件来阐释俄罗斯已承受、正承受和将承受的宿命,在此基础上来定型俄罗斯人的文化哲学观。
俄罗斯的文化宿命并不神秘,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兴旺、个人的命运均在时间中展开,展开的时间及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就是历史,也是文化本身,而对文化的理性思考,对民族在时间长河所经历一切事件的研判,对民族所承受的悲壮命运和其所承担使命的追问,无疑是文化哲学所深切关注的。每个民族都会通过透视本民族产生的历史,来探寻自己的起源并追索其中的宏大叙事,而历史的源头往往是无法证明的原始思维。俄罗斯人偏偏就在《圣经》中发现了本民族不同凡响之处,并以此来完成对自己神圣使命的造型过程。
公元1113年前后,涅斯托尔写成了将俄罗斯民族的起源和上帝建立链接的《古史纪年》(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其中一段话令人玩味:
在雅弗的领地内居住着俄罗斯人、楚徳人和其他各种族……雅弗的后裔包括:瓦兰人、瑞典人、诺曼人、罗斯人……[11]
根据《创世记》记载,一次挪亚在葡萄园中酒醉后赤身的情景被含撞见,含将此事告诉了闪和雅弗,两人将衣服给父亲盖上。挪亚醒来后说:
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含的儿子)作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旧约·创世记9:27)
涅斯托尔让神加持了罗斯,他想告诉世界,雅弗的后裔理应比其他民族更幸运。《创世记》中并没有俄罗斯人是雅弗子孙的确凿证据。后来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神圣罗斯”和普京的“新俄罗斯思想”本质上都以神的名义来表达俄罗斯的国家意志。有趣的是,19世纪的俄罗斯许多思想家尽量避免使用文化一词。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例,他在论述“美是生活”这个命题时一次也没有使用“文化”(культура),文中多次出现的是“文明”(цивилизация)[注]俄文原文是:Вс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а не нашей эпохи и не наше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непременно требуют, чтобы мы перенеслись в ту эпоху, в ту цивилизацию, которая создала их。周扬的译文是:“所有不属于我们这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艺术作品,都一定需要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里去。”[12]56将“文明”译成“文化”有待商榷。,文明和文化的指涉不同,цивилизация源自法文civilisation,其拉丁语词根civilis在俄语中具有вежливый和гражданский之意,强调文明是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产物,而культура的拉丁语词根则显示文化是农耕生活的遗存,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喜欢拥抱法语动词civiliser衍生出的просвещать(启蒙)之义项,诚如萨马林所言:“许久以来,我们迫切渴望弄清楚‘文明’一词的真正内涵,该词不久前才在我们这里开始风行,并被广泛使用,几乎完全取代了‘启蒙’的说法。”[13]1880年出生的斯宾格勒对“文明”的理解与俄罗斯思想家的“文明”完全不同,他强调“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衰落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变成文明,文明与工业有关,是没落的标志,“西方工业已经使其他文化的古老传统发生了变异”[14]469,最后,无论文化多么辉煌,传统多么悠久,注定变成受金钱控制的被工业侵蚀的“浮士德文明”[14]469。俄罗斯思想家习惯用丘特切夫著名的诗句“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来稀释问题的难度,强调“俄罗斯不是西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3]325。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代,俄罗斯人对文明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想象,今天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梅茹耶夫在汤因比的论述中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俄罗斯所代表的东正教文明继承了拜占庭最大的遗产,那就是极权主义”[3]328。但极权主义在俄罗斯人的意识里恰好是国家得以维系和发展的保障,“莫斯科第三罗马”幽灵从来没有离开,它潜伏在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之中,每到紧要关头,就会变成强硬的国家意志来主导顶层的决策。
但是,对斯宾格勒而言,俄罗斯的文明不是指向乌托邦,而是反乌托邦,俄罗斯之所以不被西方所理解,是因为在这个民族机体中存在“假晶现象”,具体而言,俄罗斯“被驱使进入了一个虚妄的、人为的历史中,而古老的俄罗斯心灵对于这种历史简直就是无法理解”[14]194,这种无法理解所造成的张力和势能终于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和1991年由布尔什维克自己演唱的天鹅之歌中得到全方位展示。十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验证了《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所预言的“托尔斯泰是先前的俄罗斯”[14]195的假设:
托尔斯泰是彼得大帝的真正继承者,从他这里,也只有从他这里,才会产生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主义不是彼得主义的反面,而是它的终结,是社会的东西对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最后凌辱,因此之故,事实上也是假晶现象的一种新形式。[14]196
只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是不是假晶现象的另一种爆发形式尚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普京执政开始就提出了复兴俄罗斯民族的“新俄罗斯思想”,“新俄罗斯思想”上承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辉煌,下连苏联超级大国的骄傲。俄罗斯人的确信奉威权主义,习惯依靠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也是普京“新俄罗斯思想”有市场的原因。有一点可以确定,俄罗斯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放弃对民族命运的紧张思考,而且,这种思考就深藏在俄罗斯文化哲学学派所说的俄罗斯思想或者新俄罗斯思想之中。
三、文化生成的语言机制
离开语言来谈论文化没有意义,因为语言使文化成为可能。索绪尔的观点是,语言为集体的习俗,反映在语法、语源、语音等方面,尽管世界上的语言千差万别,但从研究的角度看,都是能指和所指相互配合使用的符号系统。文字形成后,人类通过文字来记录文化,文字保存了人类。文化哲学通过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人类原始思维的语言表述、文化和语言关系的内在机制来解析文化的语言之思,“人借助语言表达感觉与思想,为事物命名,并通过语言来巩固自己的发现和所完成的事物。正是语言这个显著的特征使人变成理性的和文化的存在”[3]92,这句话和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栖息于语言之中”及“农夫的鞋保存了世界”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通过“猴王喻”来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呼应。
猴王眺望远方,表情凝重,似有所思,然所思何物,无猴知晓。尔后,猴王仰天长啸,发出一串奇怪的声音。几个目睹了猴王深邃眼神和听见它咆哮的猴下属知道其中的深意,那就是新猴王用声音宣誓主权。[注]该例为笔者自拟。
如此,“同是动物,为什么只有人类能不断的进步,能创造文化?因为人类有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历史,不能把过去的经验传说下去……”[15]这就是说,缺少文字这种能够凝固崇高的系统,猴王的情感永远无法转换成文化。言语作品可以借助自身的形态完成对记忆的塑形。如果猴王能用简单的线条表达自己的所思,那么线条就是文化的存在物,这个猴王就是亚当。文化的发生、发展是人类大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踌躇满志的猴王经过漫长的进化在岩洞石壁上用图画标出自己的心情,于是它就成了他。人变成游戏者,他成了文化的存在,艺术使人能够细腻地感受周围世界。席勒对文化的理解正是建立在对“游戏”的阐释上,“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16]。如此,文化发生的前提是人类有剩余的时间和在这个时间进行游戏。柏拉图“洞穴喻”中被捆住脖子只能看见身后火光映出人影的奴隶们依据所见固然也能去想像世界的样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游戏过,这些“洞穴人”缺少建构文化的自由之身。
语言是文化发生的重要条件,其巨大威力让神都感到震撼:“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12]11;6人是灵长类中的人科,在山顶眺望远方的猴王是人类的近亲,它的后代在很久很久之后从树上爬下来,又经过基因的筛选和物种的进化,成为用言语表达情绪和思想的人。人通过对游戏的感悟发展成巫术等形式,最后在岩壁上留下远古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拉康用“语言世界……诞生了物质世界”[17]151来强调语言对文化生成的重要性,但拉康的观点也经不起推敲,德里达就怀疑语言所生成的图景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世界的真实。德里达提出的“世界是文本”[17]151解构主义命题是评判世界与语言关系的新公式,他用“没有什么在文本之外”[18]来强调世界是语言的编织物,文本回归到了text编织物本质中。因此,文化的世界也是文本。
以上论述是关于语言观照下的对文化的一般性认识,即在不考虑地域、族群和一系列突发审美事件的前提下,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所思的结果。但语言又如何能脱离这些要素而独立存在?语言,一定是某个族群的语言,也一定是不断变化的存在者,因此,而将语言和具体的民族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情况远比人们想象得更加复杂,因为文化的特异性和语言的特异性有关,“文化归属最重要的特征当然是语言”[3]23。生活在异域的中国人,其文化身份有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与中国无关,也就是说,文化认同感与肤色与民族没有必然联系。那些使用相同语言的人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身份。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却通过共同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犹太人通过宗教认同将自己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形成文化共同体(当然也有例外)。人也会逃离自己的文化,二战时期,一些犹太人为了活下去,会设法将自己伪装起来,通过改变宗教信仰等方式来掩护自己的文化身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优势文化(可能和经济有关)很容易入侵相对弱势的文化。日本的动漫、好莱坞的电影和韩流都是文化中的艺术文本,是消费社会对文化操作的成果,也就是斯宾格勒所说的“浮士德文明”。
文字使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印记。通过文字,人们“在大文字传统(相对小文字——口头的)的道路上形成了所谓的民族文化”[3]34,而在小文字传统中,尽管族群文化让族人保留本色,并以其最原始的面貌来保存和再造自己,但族群文化无法让族群的社会进入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因为这种进程需要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和相互理解。民族文化当然不止文字一个维度,每个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特性除了语言的因素外,还受制于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的“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大因素。而语言如何对民族文化进行塑形,还需要从语言内部寻找原因,简言之,持某种语言的人,因该语言内部要素(语音、语法和词汇)的特性导致持有者独特的性格,俄罗斯学者通过对правда、истина、свобода和воля这几个词意义的去蔽来揭示语言对产生的俄罗斯心智的影响,发现“民族性格和民族世界观的一个鲜明反映就是语言,而且尤其是它的词汇”[19],申小龙就通过汉字的象形特质和句式找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原因和动力。当然,这样的观点有待于进一步论证,还需要借助心理语言学找到更为确凿的学理依据。不过,胡塞尔的观点在宏观上给语言与民族心理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供了佐证:“即使欧洲各民族之间所形成的是敌对的关系,但是他们始终具有一种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这种精神上的一致性浸润着他们所有人并模糊了他们之间的民族差异。这种特殊的兄弟般的团结使我们意识到,只要在欧洲民族周围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家’。”[20]302可见,民族语言中能窥见民族性格的一斑,民族心智潜藏于语言之中,而语言建构了民族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影响了语言。没有语言和文字系统维系的文化终究有一天会消亡的。